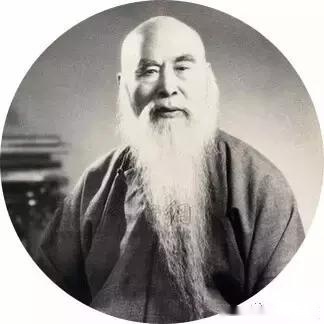《民立报》首先向全国人民报告武昌起义的消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响了!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
当时中国的信息传递,很不发达!再加上清政府的刻意封锁与歪曲,中国人民很难及时获得武昌起义的真实消息!
是设于上海的《民立报》,利用其特殊的条件,首先向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报告武昌起义的真实消息,并加以振奋人心的评论。
《民立报》的前身,是1909年5月15日(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在上海创刊的《民呼日报》,与1909年10月30日(清宣统元年八月二十日)在上海创刊的《民吁日报》。这两家报刊,是革命党人于右任、范鸿仙等人创办,并担任编辑、撰稿等工作,积极宣传反清民主革命思想。社址在上海公共租界山东路望平街160号,这里是上海各报刊集中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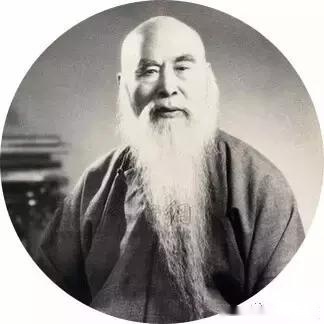
于右任晚年
但这两家革命报纸,先后被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当局查封。但于右任、范鸿仙等人不为气馁。他们一方面投入各种革命实际斗争,一方面到处筹集资金,购买设备,联络同志,聘请有经验、能写作的革命报人,计划办一规模更大的宣传革命的报纸。
在革命党人与上海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下,1910年10月11日(宣统二年九月初九,重阳节),于右任、范鸿仙等人再度合作创办的《民立报》,终于发刊问世了。《民立报》社址设在上海公共租界山东路望平街的三茅阁桥,由于右任任社长,范鸿仙、景耀月、吕志伊、马君武、王无生、徐天复(血儿)、叶楚伧、章士钊、张季鸾、康宝忠等人任主笔或编辑,陈其美任外勤记者,吴忠信、邵力子负责报纸经理方面的工作,都是一时人选;特别是著名的革命党人、卓越的报刊宣传家宋教仁也应邀从日本归国,来到上海,参加报社的编撰工作,并以“渔父”、“桃源渔父”为笔名,发表大量政论文章,更使《民立报》人才济济,可称一时之盛。
《民立报》日出四大张,分为论说、批评、纪事、杂录、图画等五大部分,版面的安排与《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大体相同,只是新闻的比重有所增加。第八版是副刊,上面刊登了南社社员柳亚子、朱少屏、景耀月、宋教仁、叶楚伧、邵力子等人的大量作品,成为南社最重要的公开宣传阵地。
《民立报》的报名仍以“民”字打头,暗示它与《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的血缘关系,被称为“三民报”,在辛亥革命史上赫赫有名。《民立报》继承了《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的宗旨:“与专横政府抗,与强霸列国抗”。这是反帝反封建的声音!但《民立报》吸取《民呼日报》、《民吁日报》仓促被封的经验,在刚创刊的一段时期内,采取了比较稳健的方法。它含蓄地称自己的宗旨只是“唤起国民责任心”和“造成国民正当的言论”,锋芒内敛,给人一种持中平和的印象,因而一直没有被查封,存活到辛亥革命爆发,存在时间较长。当然,《民立报》作为革命党人的喉舌,尽管使用了一些隐晦的宣传手法,可报纸文章的字里行间,仍掩不住革命的火花,并且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言辞越来越激烈,革命的小火花渐成燎原之势。
“三民报”在辛亥革命史上赫赫有名
《民立报》在创刊后正好约一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
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第二天,即1911年10月11日,《民立报》就以头号宋体字,刊出了有关起义的专电,吸引了无数渴求武昌信息的各地、各界、各阶层、各方面的人士。
此后,《民立报》特辟“武昌革命大风暴”等专栏,以整版篇幅,及时介绍有关起义进展情况的消息、通讯、图片。《民立报》还对武汉地区的地理形势、对革命党人酝酿、准备、发动武昌起义的经过,作了详细的报导与追述,为读者提供了十分需要的背景材料。《民立报》成为发布武昌起义消息的权威,望平街的《民立报》馆则成了公开的革命机关,各方人士往来不绝。
在这期间,《民立报》的主要撰稿人宋教仁、范鸿仙等人,共同担负起文字宣传工作的重任。他们以“渔父”、“孤鸿”、“哀鸿”等署名,在《民立报》上连续发表大量极富鼓动性的短评,宣传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热情歌颂革命,号召人民群众迅速奋起支持与参加革命,极大地鼓舞了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的斗志与士气。
1911年10月13日,《民立报》“大陆春秋”栏,以“孤鸿”署名,发表短评《呜呼 大江之上游》,热情歌颂在1911年(辛亥年)革命党人先后发动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四川保路运动和武昌大革命: 川乱方殷,而武昌又失守,今者革命总统已出现,汉阳已被破。危乎殆哉!其大江之上游乎? 始以广州大革命,续以四川谋独立,终以武昌大革命,天运辛亥,其诞生革命之岁乎?诚有史以来所未有也。 此文将辛亥年,热情地称作“有史以来所未有”的“诞生革命之岁”。
《民立报》在歌颂革命的同时,还对曾威风张扬、不可一世的满清专制皇帝讽刺挖苦,施加压力,意味深长地发问,在人民革命风暴面前,昔日“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之君主”将有怎样的下场呢? 四川据天下之上游,武昌为天下之中心。今两处现象已如此,未知我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之君主,又何以善其后也? 1911年10月14日:《民立报》“大陆春秋”栏,以“孤鸿”署名,发表短评《黎元洪》,对武昌起义的领导人黎元洪领导武昌革命军,“干犯王法,目无君主”的革命行动,加以热烈的赞扬: 黎元洪,一协统耳。今一跃而为革命大总统,干犯王法,目无君主,老黎老黎!汝真岂有此理也? 赵伯先,标统也,黎元洪,协统也,二人官运相伯仲。然一则豹死留皮,一则猛虎出柙。呜呼!时运之不齐,洵可叹矣! 10月15日,《民立报》“大陆春秋”栏,以“孤鸿”署名,发表短评《时事观》,以革命党人发动的武昌起义的爆发,撕破了满清贵族政府假改革的画皮,打乱了立宪党人依附清王朝皇帝进行改良的幻想: 贵族的政府,今日要立宪,明日要练兵,彩烈兴高,目空一世。忽然革命一声,打得他魂飞魄散。呜呼!革命党人,你何以不替王爷们留点余地也? 立宪的党人,今日开大会,明日办报馆,不是说明圣天王,就是说内阁总理。今者革命一声,吓得他张口吐舌。呜呼!革命党人,何以不替此等人留点余地也?
范鸿仙
1911年10月14日,清廷重新起用被罢三年的袁世凯,任命他为湖广总督,率北洋军南下武汉,镇压起义军。在10月17日《民立报》“大陆春秋”栏,以“孤鸿”署名,发表短评《袁世凯》,对袁世凯与满清政府的关系及其未来,作了分析与预测: 袁世凯,朝廷疑忌之人也。今一旦授以大权,岂真能捐弃前嫌乎?母亦效祖宗之成法,驱汉人以杀汉人耳! 使袁氏慷慨而出,一战而败,而死。则赐谥建祠,子孙袭爵,均不能得。吾知江忠源、程学启诸人,且当傲公于地下矣。 使袁氏拼死一战而胜,而肃清革党,则始必为中兴曾国藩,终必为国初吴三桂,否亦必为年羹尧,再下之,则与恩铭、孚琦辈相征逐于地下而已。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实了《民立报》政治预见的准确与深刻。当时中外各报的评论,无出其右者。
正由于《民立报》的时事评论的准确、深刻与顺乎民意,由于《民立报》对武昌起义和全国各省消息报导的及时,使得该报成为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最受欢迎的报纸。当时全国人民为了及时了解武昌的真实情况与全国各地的革命形势,均争相阅读《民立报》。《民立报》销路大增,日销数骤增至两万多份。每天,“报纸一出,购者纷至,竟至有出银元一元而不能购得一份者”。
当时在南京江宁布政使(俗称藩台)使署任见习生的南通州国文专修科毕业生吴次藩,在回忆辛亥南京光复前后的见闻时,说:
南京夫子庙等处销售上海报纸的各个处所,每天在上海报纸未到之前,老早就聚集了很多人在那里等候购阅。报纸一到,马上就蜂拥而上,争先抢购,以先睹为快。如果看到武汉打了大胜仗,或某一个地方又光复了的好消息,立刻就欢天喜地的拍起掌来,欢呼起来,不怕受到干涉。当时却也无人干涉。而最受群众欢迎和销行最多的便是《民立报》。
当时在苏州新军——江苏陆军第二十三混成协步兵第四十五、四十六两标任下级军官的孙福基回忆说:
清末,我在江苏陆军第二十三混成协步兵第四十五、六两标任军官。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苏州后,上峰令严加防范。各军官皆喜形于色,湖北籍之军官纷纷请假赴鄂投效,其它军官响应,争阅《民立报》,深佩民军举动文明,赞成湘、陕、赣、晋等省之独立。予将每天《民立报》上所载时局新闻,向所部讲解,劝他们默记而不要妄谈议论,以遭人忌。九月十五日参加苏州光复,以后又参加苏、浙联军光复南京之役。
从这些回忆中,可见《民立报》的时事评论文章,在当时上海、南京、苏州乃至全国各地、各界、各阶层、各方面的人士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