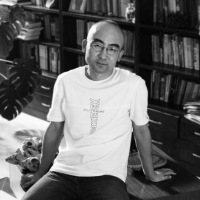清代中国,在外交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中国风格和特色。上篇文章我们看到的好面子轻里子,是一条;第二条,喜欢耍态度,喜欢慷慨激昂地讲大道理,但不善于有一说一地就事说事。
郭嵩焘曾经总结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外交说:“西方人智商不比中国差,而中国外交一味喜欢使诈,习惯勾兑。中国现在内部有很多严重的问题,西方国力强盛,我们应该理性节制,却一味耍野蛮,耍态度。西方本来有也弱点,也有不占理的地方,我们可以有理有利有节地处理,但是我们一味愚蠢到底。在西方的威胁面前,如果以柔克刚,情形还可以缓和。如果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一味使刚强,激怒对方,大祸恐怕很快会来。”(“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夷患至今已成,能揣其情,以柔相制,其祸迟而小。不能知其情,而欲以刚相胜,以急撄其怒,其祸速而大。”)(《郭嵩焘日记》)
因此有人总结当时外交人员的办事风格,就是骗子外交加泼妇外交:
总以洋人为外国,一句话都听不得。明知外国富强,中国不敌,偏要说好看话,不但不怕他,还有胜过他。一味大话,欺哄上司。洋人来商量的事,明知可行,偏要说不行。今朝磨明朝磨,不问自家曲直,也不问外国是非,一味推三阻四。
为什么会这样呢?
晚清以来的中国,有一个规律性现象,那就是在对外交往中,不管国势强弱,凡是主张强硬,甚至主张“蛮不讲理”,敢于在外交场合痛斥洋人的人,通常都会获得民众的热烈欢呼,被称为“民族英雄”,“扬我国威”。而主张和洋人“讲理”、“妥协”的,承认洋人国力比自己强的,几乎都会被骂为卖国,被称为汉奸,声名尽毁。如郭嵩焘所评论:“一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南宋以后,凡主战者在历史上都得美名,主和者都得骂名。所以鸦片战争以来,凡是涉及夷务的人,大多数都落不到好下场好名声。
林则徐其实就是一个代表。

林则徐像
近代以来对林则徐发起最严重指责的史学家之一是蒋廷黻。他在《中国近代史》中认为,林则徐并不是一个诚实的人。通过正面交锋,林则徐其实对中国和英国的军事差距看得非常清楚,他知道以清朝当时的武备是打不过英人的。但他没有像琦善那样公开讲出来,而是仍然坚决主战。这是因为林则徐深知中国朝野的心理,知道中国舆论一贯只推崇强硬派,如果他承认英国人厉害,那必然会挨全国人的骂。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林则徐选择了对全民族说谎。
他的主要证据,是林则徐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谪戍伊犁途中致书友人姚椿、王柏心的信。在信中林则徐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也就是说,英国的大炮射程比中国远,我们打不到他们,他们却打得到我们。而且他们放的是连环炮,一发接一发,我们放了一炮后,得重新操作老半天,才能放第二炮。如果不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即使调来百万精兵也没用。而且更关键的敌人的舰队移动迅速,早上还在南方,晚上已到北方,我们的陆军怎么能防备?我们的军队虽然也不乏能征善战之人,但是以前打仗都是面对面刀对刀,像现在这样隔着十里八里看不到对方的样子就已经被对方大炮轰散了的,前所未闻。
从这封信看,林则徐确实清楚地认识到西方在武器和技术上比中国先进不止一个档次,也明白清朝如果不进行军事改革,百万军队也抵挡不了外敌入侵。按理说,这一结论符合实际,也非常重要,如果能把这个道理对皇帝和同僚们讲清楚,中国也许可以避免很多对外战略上的失误。
然而在这封的结尾,林则徐加了这样一句:“余惟为道自重,不宣。” (《致姚椿王柏心函》,《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卷》,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P3586-3587)请他的朋友不要把这封信给别人看。
蒋廷黻评论说:“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蒋廷黻总结说:“中国士大夫阶级 ( 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 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那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本文最早发表于微信公号“搜历史”,内容有删改。
作者简介:张宏杰,1972年生于辽宁,蒙古族。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现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人的性格历程》《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等。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