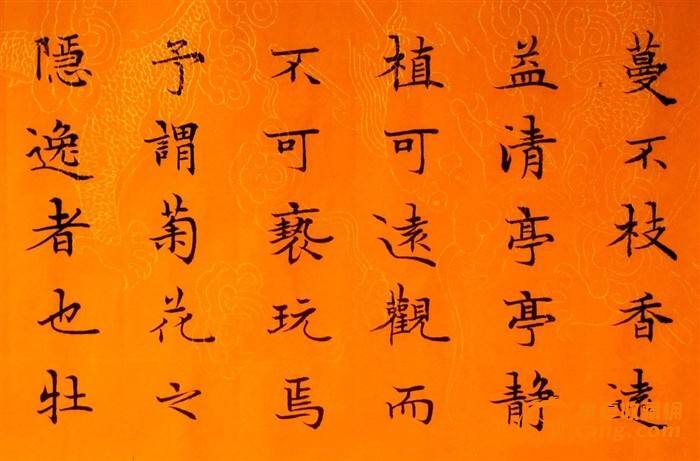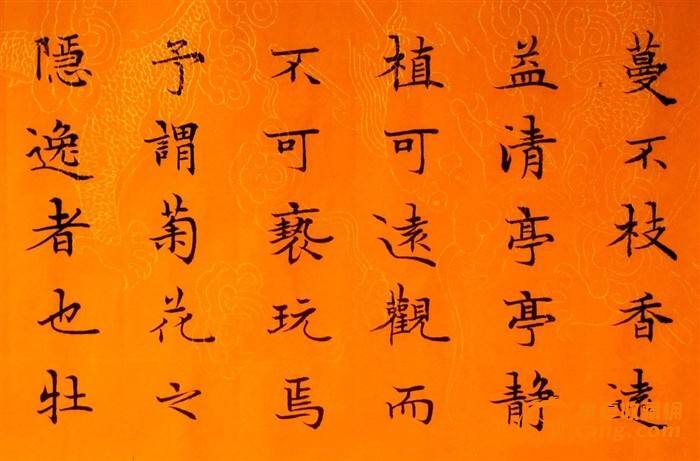
田英章先生对于“扌”偏旁书写经验他是这样描述的:“扌,首短横要略扛肩,不可粗重。竖笔要垂直劲挺,提钩要用‘跪笔弹锋’的方法。穿过横笔时要靠右侧,竖笔与提笔要坚定有力。而且要注意提笔和长度”。
当然提手旁都用在左右结构的合成字之中,从笔画尺度来看,只算是“非主字根”,所以所占面积当然不能大过一半的水平,一般维持在1/3的整字宽度。
笔者非常同意启功先生的一句话:“书法以结字为先”。无论什么书法形式,结构是决定一个人书写技能最重要的因素。
笔法,基本笔画只有那么8种:“点、横、竖、撇、捺、折、提、钩”。
再扩展形成的复杂笔画也就那么几十种,只要勤加练习就可以熟能生巧。而汉字结构可齐腰变化无穷,怎样写才合理漂亮,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行种经验规则。
有人分析说,现代简体楷书规范字就是欧楷的赵楷两大书体相结合的成果。现今书法市场在国家传统文化复兴工程的推动下,又加上“书法进课堂”“教师三字一话”工程不断深入开展,一些书法技术已成为大部分现在的上班族与未来的上班的考核标。
楷书作为法定的公文字体,学习楷书的人越来越多也就不会让奇怪了。
书法创作,首要是临摹。临帖对于创作来说,是最好的基本功的训练。无论是对临、默临、意临等等,其作用都是学习和积累,也可以说是日后进行创作的储备。临帖最忌死临,就是在具备一定临帖基础的时候,不能再刻意去做毫不走样的模仿,一成不变的模仿;在已经掌握一种或几种书家书写风格的条件下,一定要力争多临一些,多储备一些,不能抱一守终。当今的天下,文化的迅猛发展,信息的飞速传播,海内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带给人类的知识积累也更加日新月异,为书法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因此临帖也要有积累和储备的意识,它也是具备多方面修养的基本条件和基础。我在积累一些临帖的基本功以后,临董其昌、王铎时不只是临其本人的作品,而是连董、王二人在学书过程中所涉及的主要书体都临过,从中一并体验其书体积累和演进的过程。当然,无论什么书体,只要有一种书体能够得心应手,与其他书体都有相通之处,笔法基本可以相通,可以临得更顺利一些,掌握得更快一些。能够多临,不光是学帖记忆的积累,而且还有各种帖与帖相互间的比较,更容易了解帖与帖相互间的特点,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同是魏碑,郑道昭与郑长猷,张汝墓志与张猛龙碑都各有哪些特点,只要认真地用心临过才会一目了然。与此同时,储备得越丰富,应变的能力就越强,在日后的创作中就越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才有资格讲创新,否则只是空有其愿望而已。仅仅急于或热衷于创新而缺乏这种积累和储备,顶多成为书坛上一时匆匆的过客,不会成为真正的书家。
书法结构忌讳死板教条,楷书书法更是如此。
书法创作的本意是在表现一种修养,是在写修养,至少在古时候是如此。创作即是写作,意念在前,书写在后,性情亦在其中,通常是先考虑文字的表达,再考虑写得美观,这是由书法以文字为载体所决定的。许多古人的信札手稿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现在的人也承认书法是表现一种修养,但总想把表现性情作为书法的第一要旨,强调创作的主观性、主导性、主动性,主张今天的书法是创作出来的,是为创作才存在的。这种观点我不反对,但我认为这种理由并不完全充分。我现在有时也在裱好的册页上抄自作的旧诗稿、旧文稿,并非在有意创作,但还有不错的感觉。自古以来,至少是到明代以前,书法一直是围绕着书写进行创作的,这种创作技能的训练、创作能力的积累、创作意识的蒙发、创作过程的完成,都是一挥而就,因此那时的随手随机而写的手札、信函、文稿的草稿都成为今天十分难得的艺术珍品。能够随机写得自然、流畅、潇洒、富有神韵,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临写前的所谓安排和创意,而是持之数年的积累与修养。我学书初以颜柳开蒙,后渐临习秦汉碑铭,近十年来潜心于行草法书的临习与创作,曾对王羲之、张旭、怀素、米芾、杨凝式、黄庭坚、董其昌、王铎等名家行草反复品味,精心揣摩,为草书的创作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才会有今天的创作面目。除书法以外,我对美术、摄影、音乐、文字,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都着力培养浓厚的的兴趣。偶尔拈来,也可得其中滋味。如果说他们的作品是在表现一种激情、一种冲动、一种不同凡响的艺术主张,倒不如说是在表现一个书家多年积淀下来的审美意向和基本技巧,从中传达出内心世界的情感。因此我认为书法首先是表现修养的艺术,是对各类艺术的修养的吸取,对各种艺术手段的融会贯通,它不是一种时尚,是一种必需,是对一位成熟书家应具备的基本要求。
田英章先生的工笔楷书,漂亮干净利索,但是初学者难以从中领悟丰富的变化方法,这也成为一些书友诟病的焦点。其实我们总可以从笔画粗细长短,笔画起笔收笔折笔结点、笔画的曲直形态3三大方面进行求变,书法作品也就有了不一样气度。
书法风格落入千字一面或千人一面的状态时,让欣赏者这对于实用书法并无非议,但是要想书法作品有多些欣赏意趣,就得让这样的书法多点不同的东西,这可能是笔法,也可能是结构技巧。
在书法的创作上,我认为对书法的创新要大力提倡,但不能急功近利。书法创作应该具有时代感,提倡对各种艺术风格的探索,创作出既有时代特色又有个人风貌的作品。因此搞书法艺术是既贵在创新,也难在创新。如人所说,创新的基础在于继承,学书要先师承古人,重法度,得传统精髓,学古而不泥古。一个书家的风格应当在继承传统吸取营养的基础上,注重与时代气息的融合,注重民间文化内涵的滋养。随着书法事业的发展,书法作为艺术品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艺术厅。越来越多地注重并发挥展示和欣赏的功能,写作过程被融入了激情而变成为创作过程,这种完全是有意识地进入创作,正在使书法创作从过去的方式转变为新的方式。书法以文字为载体,周密考虑文字内容与书体的关系,书体与书写风格的关系,创作过程中内容书写与情感表现的关系等等。倘若一个技艺精湛的书写者,在一幅作品中不能正确地使用文字,传达不出字里行间的感情,即使是具有再高超的技能也会无人喝彩。创新是一种渐进的过程,一种能够被历史实践不断验证和广泛认知的过程。优秀的书家应该倡导并具备创新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就等于失去前进的动力。但有了创新的能力,并不等于已经达到了创新的水平。如果这些条件都具备,形成一定的量,形成一定的风格,被一个时期所相对稳定和认可,才有创新的可能。在我看来,一种风格的继承与创新,正像一种书体的形成一样,通常并不是由一个或几个人的提倡和创造所能完成的,它是一个时代书家或一批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而那种并无实际意义上的创新的滥觞只能适得其反。
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创新应建立在转益多师,厚积薄发,用宏取精的基础上,力求取诸家之长,不断丰富、滋养自己,在前人浩如烟海的墨迹大观中探幽发微,去寻觅、陶冶、积淀自己的风格。先父生于江宁,曾受过秀润如春的江南文风的滋养,而我则生于东北,经受过粗犷雄浑的北国墨韵的熏陶,既得以感受宽博广大、浑穆浩莽、雄奇壮观、豪爽坦诚的气派,又力求以典雅纯朴、清简婉约、舒朗流畅、俊逸自然的韵致,融进笔墨之中。在气与韵的交织之中,则刻意于风云舒卷,律动于无穷之势;寄情于山海坦荡,旷达于心宁神远之境。我想,无论每一位书家作出何等的努力,历史都会得出最公平、公正的结论。
篇未总结:
想来想去,书法技术,比如书写总是天天与人们打交道,写好字重要。方法也不应该多难,只要应用理性的方法分析,找文字中的层次关系,我们就可以掌握一些结字的美学原则。
再利用这些原则布局书法结构,做到每笔每画都有造型与定位的依据,我们的书法的“法”也就落地了。我们自己的书法也就可上水平了。而作为书法老师,就可以让书法学习者有了“授人以渔”的“捕渔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