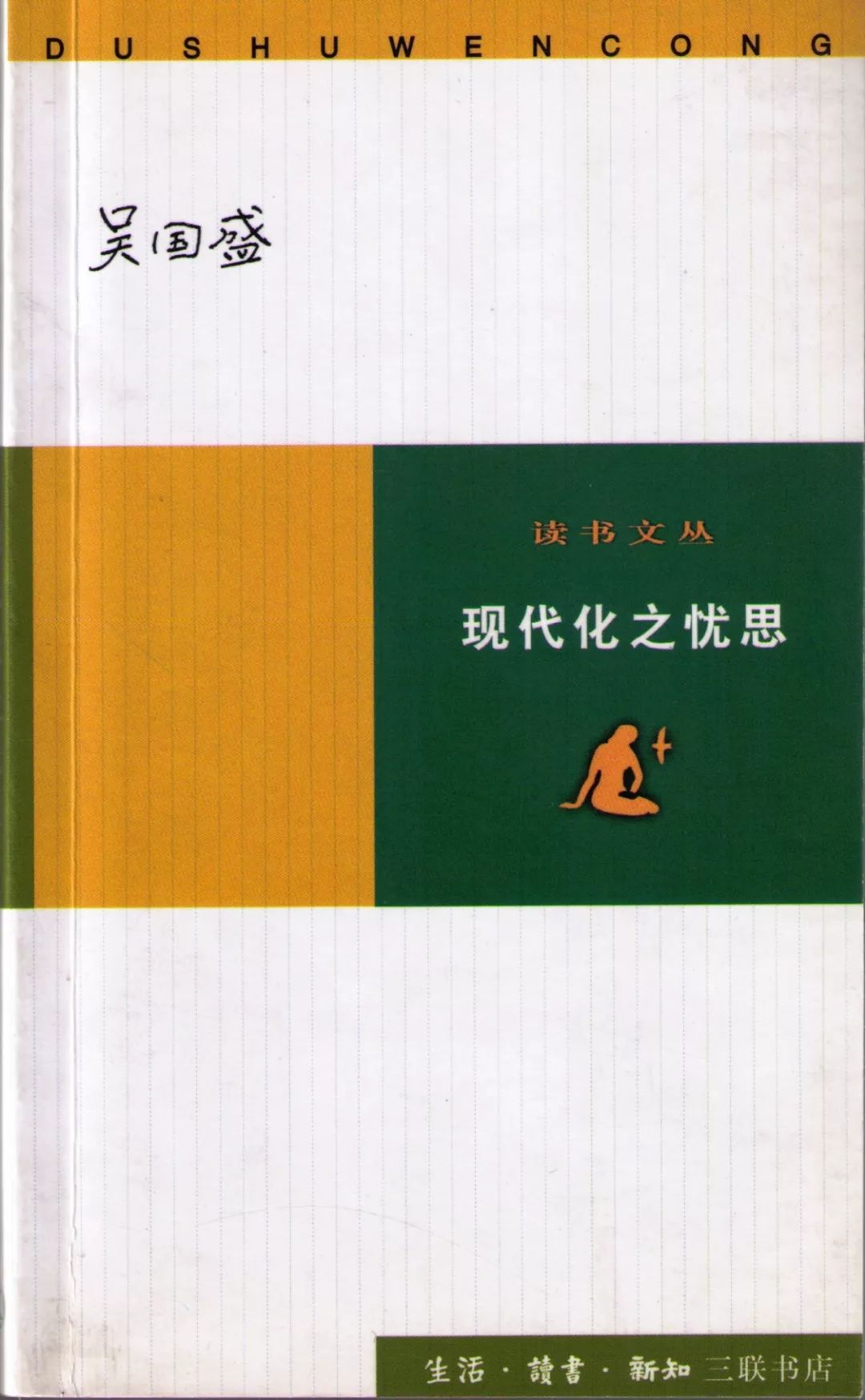原标题:吴国盛 | 在中印乡村建设交流会上的发言

▲吴国盛
作者 吴国盛 (本号主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
责编 许嘉芩 刘愈
◆ ◆ ◆ ◆ ◆
印度的“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KSSP,简称“喀科运”)名闻全球,1996年因“促进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而获得了被称为另类诺贝尔奖的的“优秀民生奖”(Right Livelihood Award)。这个奖项表彰对全球民生最有建设性贡献的实践经验,颁发时间是每年诺贝尔奖颁奖的前夕。2003年10月23、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香港CSD)共同主办了“中国—印度乡村建设交流会”,邀请印度“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四位核心成员与中国的专家、学者及对乡村建设有兴趣的人士一起交流,目的是以印度喀拉拉邦的民众科学运动的经验为基础,交流和探讨中国和印度在乡村建设方面不同的思考和历史,并讨论乡村建设中的重要课题,以及适切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吴国盛:很高兴参加今天这个会议。我本人并不是做社会学的,但是,有些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把我带到这个会场来了。我觉得中国的问题与印度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庞大的人口,但也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个,中国民间力量极为弱势,这是我们与印度一个很大的不同。再一个是,中国农村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所遭遇的极度荒漠化、边缘化,看来跟印度也不大一样。还有,在中国,主流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非常之强烈,可能与印度不同。这样几个特征使我觉得中国与印度的对话和交流是非常有意义的。今天在这里我愿意介绍中国两方面的情况。第一个,中国的科学普及运动与印度的民众科学运动之间巨大的差异。第二个我想讲一讲,在中国目前的科学文化界,正在谈论一种新的观念,就是“科学传播”的观念,并且力图用“科学传播”取代传统的科学普及。我讲这两件事情,跟印度同行做一个交流。
中国的科学普及运动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它是国家行为,不是民间行为。这件事并非一贯如此。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科学普及运动一直是民间的,或者说主要是民间的。但是四九年以后,国家差不多垄断了科学普及活动。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政府包办科普的局面可能会发生改变。
第二个特点:中国的科普有强烈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它所讲的科学,就是现代西方科学,不怎么包含中国的本土知识,有的时候甚至将很多民间科学和本土科学斥之为“伪科学”,是愚昧的,无知的,例如气功、中医等。在正统的科普界,这种声音是很强烈的。所以,中国的科普活动与印度的民众科学运动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
中国现在有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对传统科普进行反省,包括我本人在内,这几年一直在倡导新的观念,即用“科学传播”来替代传统的科学普及。
为什么要用科学传播替代科学普及呢?因为,传播是双向的、交互的,communication这个词译成“传播”实际上有问题,因为中文的“传播”一词字面并没有包含互向交流的意思。但是这个词的翻译已经约定俗成了,没有办法。“传播学”学科和“传播学院”都建立起来,但是,交流和互动的理念要确立起来。传统的科学普及往往是单向的,是科学家们向民众讲解科学知识、通俗化科学知识。但科学传播要强调互动。互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传统的科学普及,由科学家向公众讲述现代科学知识,这方面是主流,我们当然不反对。我们只是强调和提倡另外一个过去不曾有过的维度,那就是:民众对科学的反作用。
这部分我认为有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民众有权力来过问现代科学的发展。过去我们科普的对象普遍被认为是很可怜的人,因为他们是科盲,差不多与贫困、无知、愚昧等等划等号了。但是在现代民主社会,国家出资兴办的科学事业是要向纳税人负责的。所以,民众有权力要求向他们汇报,向他们讲述现代科学的进展。这不是谁的施舍,而是科学家的义务。在传统科普的思路下,科普活动本身总被许多科学家瞧不上,觉得是不务正业,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屈尊降格的事。这是第一方面:民众有权力要求科学家对他们的工作做出解释,而且民众有权力制止某些科研项目。这一点在中国还根本谈不上,还没有这种观念,现在的科学共同体我觉得完全是精英主义的,认为民众懂什么呀,你们还想对我们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科学无禁区嘛,我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要确立这样的观念,那就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民众有权力对他们不懂的现代高精尖技术进行制约。民众有进行质询的权力,要求科学家向他们汇报,要求他们通俗化的向民众讲述他们做的事情。同时民众也有权力制止、选择科研方向。因为现代科学都是大科学,国家花钱。民众有权力问: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造高能粒子加速器?为什么要搞载人航天?中国需要确立这样的观念。这是公众向科学传播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是,我们也要强调民众是可以参与科学知识的建构的。但这种科学知识不是实验室知识,不是现代科学理论知识。在现代科技方面,民众确实是没有发言权的。民众有发言权的不在现代科技。在中国有一些科学主义的误区,以为热爱科学就要从事科学,从事科学就要从事现代数理实验科学。其实你热爱科学也未必要从事科学,从事科学也未必都要去钻研现代数理科学和实验科学。比如有人妄想以初中水平试图解决哥德巴赫猜想问题,或者“发明”永动机。这纯粹是误区。但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完全可以建构另外一类科学知识,即博物学知识,特别是本土的博物学知识、环境知识、生态知识。这方面老百姓是有能力的。而且,我们应该看到,过去的二十年,中国的本土性的博物学知识几乎都被放弃了。我们可以说,近二十年的学生,已经不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耻了。而现在大学中,越来越多的生物系不怎么讲博物学知识,而只讲实验室知识。我很高兴地看到,印度的同行一直在从事适用技术,这个技术是与特定的生活模式、特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文化背景有关的知识,这个知识,民众是可以介入的,而且是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但这一部分本土知识、博物学知识,在过去二十年内被我们中国完全遗弃了。现在这类本土知识、民间知识、原始知识,在我们的主流社会都不怎么被接纳,甚至受到排斥。所以对我们中国来讲,我自己感觉,我们在这方面的问题比印度要多得多。我们的整个观念完全没有转过来。我们多元化的自然生态在破坏,我们多元化的文化生态同时也在破坏。对于我们当代的中国人来讲,恢复这两个生态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想,乡村建设要从这里着手。很遗憾的是,我本人不是一个实践者,与NP教授比起来很惭愧,我只是个理论家而已。我希望将来,我能让我的学生们越来越多的加入实践者的行列。我看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介绍,我想将来是不是可以在这方面做些工作,我很愿意介绍我的学生参加这个行列。我们可以在很多乡村里试验一下,让农民自己来发展本土知识。科学在一般意义上说,就是指导人与事物打交道的理论知识。现在有许多人说,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可是没有科学。我想,说没有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当然是对的,但是说没有科学,那就看你怎么看待科学了。我想应该恢复科学多面的形象,即把博物学同数理实验科学摆在同样的位置。在这方面我们做理论的人可以多做一些工作,要搞观念变革,要引入新的思想,包括向印度的同行学习。当然我们学起来比较困难,我们有我们中国特殊的国情。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大家持续的努力,情况就会慢慢好起来的。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本文选自《现代化之忧思》,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取授权,并注明出处。】
▲《现代化之忧思》是吴国盛科学人文系列丛书之一,1999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