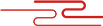北京的大街小巷有许多不同之处,其中的一点就是植物。行车主干道的两旁,多是金黄的银杏和叶子宽大的法桐;比较大的胡同,是国槐和洋白蜡的地盘,有些百年古树足有合抱之粗;而更小的胡同,则是“石榴树,月季花,葫芦蔓子爬满架”。
八大胡同一带,就是这种旧京风貌。几根铁丝和木条,在胡同两侧的墙头之间搭起架子,葫芦和丝瓜在上边肆意蔓延。即使在清冷的暮秋,仍有绿油油的丝瓜和黄色的小花掩映在叶子中间,给青砖灰瓦的胡同增添了不少生趣,很有些写意画的情致。
而今到北京的游客,提及胡同,首必称南锣鼓巷、烟袋斜街,无一日不熙熙攘攘,各色酒吧、纪念品商店、卖网红小吃的摊档密密匝匝。相比之下,八大胡同却还带有淳朴的胡同style,除了服务邻里街坊的小卖部、小吃店之外,仍以居民为主。遥想百多年前灯火辉煌、车水马龙的繁华,着实令人感慨。
论知名度,八大胡同超过八大山人,盖有雅俗之分,不可强求。余秋雨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某次考试出题评析八大山人,有考生回答是八位潜迹山林的隐士。八大山人并非八个人,但其实八大胡同也并非八条胡同,实则泛指前门南大栅栏以西一带。虽然有些词条或文章会列出具体八条胡同名称,但各种版本不一,总数加起来不止八条。不过在大多数版本中,都包括了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胡同、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等。

张二奎、孙菊仙、时小福等京剧名角住过的朱茅胡同。 马浩亮/摄
徽班进京落脚地
二百多年间,八大胡同被打上了浓重的标籖,是纸醉金迷的风月场、夜夜笙歌的销金窟、花街柳巷的代名词。坊间市井最津津乐道的往往是那些风流韵事。而八大胡同在文化史上的那段黄金岁月,却反而被人淡忘。
诚然,这里的确是昔日的“红灯区”,从胡同的名字就可窥一斑。胭脂胡同因售卖胭脂水粉的店铺而得名,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烟花女子。而被胭脂胡同中穿截为两段的东、西壁营胡同,原名皮条营胡同。西壁营胡同是一条死胡同,10号院据说是做臭豆腐闻名的王致和家,尽头墙外就是纪晓岚故居。
纪晓岚故居以东,有一条只有三十多米的小胡同,这就是胭脂胡同。沿着胡同走到头,便与百顺胡同交接,形成了一个丁字路口。路口的东南角墙上,醒目地竖立着三块拼接的红铜浮雕,表现的是京剧《借东风》中领令旗的场面,诸葛亮羽扇纶巾,周瑜两道锦鸡翎子飘逸潇洒。浮雕顶部雕着一句俗语:“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
这句话,最真切地概括了八大胡同的历史地位。其实,八大胡同最应该被纪念和缅怀的地方,绝非那上百家各色妓院,而在于其是京剧发展史上无可超越的丰碑地标。这里不仅是徽班进京的落脚地,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等京剧史上最顶级的“大咖”几乎无一不在此留下足音。不过,精美的浮雕上方,是锈迹斑斑的电箱、成捆成堆的通信电缆,旁边是铁窗护栏和空调外挂机,连一点花花草草的点缀也没有,很有些煞风景,似乎也是反映了京剧的现状。
从乾隆年间陆续开始的四大徽班进京,被认为是拉开了京剧二百多年波澜壮阔发展历程的序幕。当时的四大徽班,都住在八大胡同,三庆班在韩家潭,四喜班在陕西巷,和春班住李铁拐斜街,春台班住进了百顺胡同。于是,这里成了京剧的摇篮和福地。
百顺胡同的“徽班进京”浮雕。 马浩亮/摄
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
八大胡同究竟是哪八条,众说纷纭,但不论哪种版本,都有百顺、韩家潭。百顺胡同在明朝时名柏树胡同,清朝以谐音改为现名,取“百事顺遂”之意。东与陕西巷相接,丁字路口的拐角墙上同样有红铜浮雕,表现的是京剧另一出经典剧目《四郎探母》。浮雕之前立有一位京剧琴师的雕塑。
百顺胡同与陕西巷路口的京剧《四郎探母》浮雕。 马浩亮/摄
短短两百多米长的胡同里,38号是武老生迟月亭故居,40号是武生俞菊笙故居,而36号是就是“伶圣”程长庚故居“四箴堂”,同时也是三庆班旧址。小院是朱漆小门,在近几年的胡同改造中重新粉刷,现为居民区。程长庚是京剧第一代演员中老生“三鼎甲”之首,曾担任三庆、四喜、春台三班总管,彼时的这座小院,堪称是京剧的中心了。
程长庚演戏时常以“四箴堂程”署名。他的戏路极宽,有戴“十头网子”之称,足见其文武全才。因京剧角色分工最早除了生、旦、净、末、丑,还有副、外、杂、武、流,共十行,这十行角色都须头戴网子,故名“十头网子”。那时的四箴堂不仅是京剧的艺术交流中心,也是人才培养中心,热闹非凡,再看今日没为一寂寂无名的大杂院,不禁让人心生“旧时王谢”之感。
四箴堂对面的百顺胡同38号,是青衣泰斗陈德霖故居。如今的小门也只有约一米宽,但两边还留有两方拴马石,雕有莲瓣,如旧时之物。穿过狭窄的过道,小院四四方方,虽破旧,但尚整洁朴素。天井搭着丝瓜架,铁丝上晾晒着被褥,墙根摆着辣椒花,还有冬天生炉子用的木柴和煤球夹子,门窗玻璃上糊满挂历纸,透着浓浓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气息。
陈德霖也曾入四箴堂科班学习刀马旦,后又师从田宝琳学青衣,同时搭三庆班演出。传言他在升平署当差期间,暗中仔细观察揣摩慈禧太后的举止,运用融入《雁门关》萧太后的形象,大得赞赏。
陈德霖有“老夫子”的称号,皆因其广种桃李,提携后学,王瑶卿、梅兰芳、王蕙芳、王琴侬、姚玉芙、姜妙香并称为六大弟子,尚小云、荀慧生也都得其指教。“通天教主”王瑶卿故居在临近的培英胡同(原马神庙街)20号。
百顺胡同墙上的指引牌介绍,梅兰芳曾在百顺胡同读私塾,1900年也曾迁居这条胡同,与杨小楼为邻。在此之前,他住在临近的李铁拐斜街(今铁树斜街)101号院,即其祖父梅巧玲故居,那也是梅兰芳的出生地。而今院落经过整修,青条石的门楼和狮头抱鼓石,黑漆大门上金字隶书“门庭香且宝,家道泰而昌”对联,显得比陈德霖故居要气派得多。
看着地图上密织交错的一条条胡同,宛若一部京剧发展的路线图,千丝万缕的流派渊源、脉络传承、成长轨迹,尽在其中。
位于樱桃斜街的北京梨园公会旧址。 马浩亮/摄
伶人风骨艺海留名
常有人将京剧演员称为“唱戏的”,认为不过是供人消遣娱乐的行当,实则大谬不然。昔日那些住在八大胡同、出入各大戏园乃至深宫大院的名伶,侠肝义胆者层出不穷。
戏曲研究家任中敏《优语集》中曾记载了程长庚的一段轶事,读来痛快淋漓。程长庚某次为都察院演《击鼓骂曹》,彼时内忧外患,国将不国,而达官显宦却尸位素餐,依旧声色犬马。程长庚忧愤之下,在演到祢衡挝鼓怒斥曹操时,指着堂下一众官僚痛骂:“方今外患未平,内忧隐伏,你们一般奸党,你们一般奸党尚在此饮酒作乐,好不愧也!有忠良,你们不能保护;有权奸,你们不能弹劾。你们一班奸党,尚在此饮酒作乐,好不愧也!”慷慨激昂,几至怒发冲冠,目眦尽裂。
在程长庚百顺胡同寓所往西,拐弯分叉出两条胡同,分别是大百顺胡同、小百顺胡同,这居然是三条不同的胡同,如此命名,实属罕见。而更奇特的是,小百顺胡同自然比百顺胡同短小,而大百顺胡同却不比百顺胡同大,十分有趣。这大、小胡同都很短,向北延伸通向韩家胡同,也就是昔日八大胡同中名头最响的韩家潭胡同。
韩家潭胡同的得名来自于康熙年间礼部尚书韩菼居于此。康熙十二年,韩菼参加殿试,在时务策文中直斥三藩拥兵自重,应及早撤藩,正中康熙皇帝下怀,被钦点为状元。然而使韩家潭名声大噪的却是后来的另一位皇帝——同治。韩家胡同遍布“南班”妓院,包括环采阁、金美楼、燕春楼、美仙院、庆元春等20多家。众多清代野史,几乎众口一词指同治皇帝乃是“韩家潭嫖野鸡”得梅毒而病死。
1949年后,北京市政府取缔所有妓院,在韩家潭和百顺胡同设有8个妇女生产教养院。1965年北京整顿地名时,由于韩家潭秽名远播,应群众要求,改名韩家胡同。昔日的脂粉气息,如今早已烟消云散,杳无痕迹。
韩家胡同也是京剧名伶聚集地,刘赶三、王琴侬、白云生都在此居住,尤以刘赶三的“段子”最多。刘赶三在韩家潭寓所自营保身堂,门下弟子众多。
刘赶三原名刘宝山,曾在韩家潭三庆班演毕,由前门进内城,再到隆福寺景泰园、东四泰华园演出,一日连赶三场,同行遂以“赶三”呼之。“同光十三绝”中,他的扮相犹如大观园中的刘姥姥。
《同光十三绝》,左四刘赶三,左六程长庚,右二谭鑫培。
自同治至光绪年间,刘赶三曾与程长庚同任梨园行精忠庙庙首,丑角担此重任,唯其一人。他“击鼓骂曹”式的轶事比程长庚多得多。《栖霞阁野乘》记载,光绪初年某次演戏,刘赶三扮鸨母,高叫:“老五、老六、老七,出来见客呀。”当时京城妓女均以排行相呼。但这场戏台下坐着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欣、醇亲王奕譞,在道光皇帝众皇子中恰排行五、六、七。
刘赶三显然是在借插科打诨揶揄三位王爷。恭王性格洒脱诙谐,听完大笑。醇王(光绪皇帝生父)为人恭谨,虽心中不悦,但隐忍不发。而惇王个性严正,眼里不揉沙子,听到此大怒,叱曰:“何物狂奴,敢无礼如此!”立刻吩咐侍卫将刘赶三拉下台来,重杖四十。
刘赶三对家国之事颇有正义感。甚至对于皇帝,他也敢在嬉笑中嘲讽,颇有黄幡绰、敬新磨遗风。同治皇帝患梅毒而崩,在京城街知巷闻,但慑于皇家威权不敢明言,讳莫如深。而当时刘赶三恰在阜城园演《南庙请医》,饰庸医刘高手,作科白曰:“东华门我是不去的。因为那门儿里头,有家阔哥儿,新近害了病,找我去治;他害的是梅毒,我还当是天花呢,一剂药下去就死啦!”
闻者咋舌,规劝他小心行事,否则“尔死不知其所矣”。但刘赶三正襟曰:“穆宗在位,不因民困而求救拯之方,乃花天酒地,致酿恶疾,祸由自取,可以蒙一隅之听闻,而不可蔽万方之耳目。”戏剧史学者任中敏曾评价:“清优人之大胆,无过赶三。”
但这种口无遮拦,终引来祸水。甲午战败,一时间成为舆论公敌,被指责丧师辱国。时年已78岁高龄的刘赶三,在湖广会馆唱堂会时,“植入”了自编的“拔去三眼花翎”“剥去黄马褂”等唱词。李鸿章子侄辈多人在台下,怒不可遏,吩咐家丁数十人,伺于门口,等刘赶三演完出门时,蜂拥而上,拳足交加。刘赶三回到韩家潭家中已不省人事,未几去世。
京剧圣地历史绝响
与韩家胡同成丁字形相接的是大外廊胡同。胡同最北端的1号,就是谭鑫培故居,距离百顺胡同程长庚故居仅数百米。程长庚唱腔古朴沉雄,人称可“穿云裂石”。晚年,程长庚曾对义子谭鑫培说:“子声太甘,近于柔靡,亡国音也。我死后,子必独步,然吾恐中国从此无雄风也。”果然,在程长庚之后,柔美婉约之风越来越成为京剧的主调,高亢雄浑反而渐渐成为陪衬。
自1863年谭鑫培随父亲谭志道在京城广和成搭班演戏算起,又历经谭小培、谭富英、谭元寿、谭孝曾、谭正岩,谭家七代都从事同一戏种,一脉相承。谭家从清末咸丰年间便在此居住,直到“文革”期间从老宅搬出,前后住了六代人,长达130多年。百年之前的1917年5月15日,谭鑫培就病逝于这处大寓所。
当年的老宅朱漆大门,有6套院子,共有房子46间半。而今这里住着20几户人家,东院正门仅是一米多宽的小门,过道还被肆意攀援的树藤占去一角,成了扇形。最醒目的是老宅西院一幢二层的西式小楼还在,这是当年谭家未出阁的女眷居所。朝北、朝西的窗户,都有拱形上沿,但几经改造,有的是中式窗棂安装铁栅栏,有的是塑钢推拉窗,有的已用水泥砌死抹平,几台空调外挂机安装在墙上,不复昔日典雅。谭元寿第三子谭立曾说过:“父亲因为怕伤感,离开68年从未回来。”如今北京市计划将谭鑫培故居腾退修缮,改建为京剧博物馆。
大外廊营胡同1号谭鑫培故居旧址。 马浩亮/摄
八大胡同之所以成为昔日京剧圣地,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这片区域东邻前门外大栅栏商业区,西邻宣南坊的文人聚居区。文化和商业的相互熏陶浸染,催生了京剧之花繁荣绽放。
但如此一片难得的艺术沃土,终未能抵挡历史大潮的淘漉洗刷。岁月变迁中,旧有的业态消逝,风光不再,历史发展的断层无可弥合。只有胡同墙上橱窗宣传栏里“京剧从娃娃抓起”的标语和照片,让人在无比的惋惜中聊添一丝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