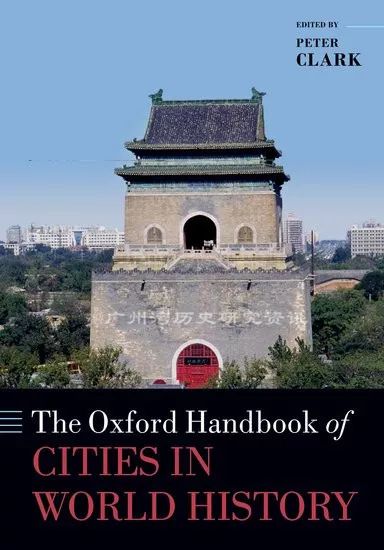一
城市史研究的若干路径
关于城市史的研究,自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得到学界的长期关注和讨论,而长达数世纪之久的西方殖民扩张和殖民管治所引发的城市化进程,亦是城市史学者经常讨论的热门话题。相关讨论可见于由英国历史学家Peter Clark主编的Oxford Handbook of Cities in World History(《牛津世界城市史指南》)。编者在导言中大致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分为早期、前现代、现当代三个时段(即early, pre-moder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依次介绍该本文集44篇文章的内容概要。正如编者所言,该书的主要研究途径包括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两种,各篇文章所涉及的地理分布范围相当宽广,有助读者从总体上和宏观上认识人类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谈及比较研究的路径,Peter Clark回顾三股学术脉络:其一,芝加哥学派(主张以社会学方法考察城市)和法国年鉴学派(主张长时段和广区域的整体历史研究)对于城市发展模式的研究;其二,马克斯·韦伯对于欧洲城市小区认同(communal identity)的研究;其三,社会人类学探讨早期城市化的研究。然而,上述研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遭到许多挑战,因此编者强调该书聚焦“全球范围内城市化的模式”,以及城市发展的多项诱因,如农业分工、商品化、工业增长和权力之间的张力。为使城市网络(urban networks)从古至今的演变得以相连接,编者强调人口流动和国际贸易是两个至关重要的推动媒介。[1]
若我们着眼二十世纪的中国城市,因此不妨跳过前两个时段,转而关注“现代及当代时期”的全球城市历史。编者颇具创见地将经济史领域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的概念引入城市史研究,其认为自十九世纪后欧洲城市急速发展(既有大都会也有专业城镇),大多数亚洲城市只有些微改变。而随着西方殖民扩张等全球化进程,中国亦无可避免被卷入第三波城市化(十九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2]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城市有何变化?下文将以第28和第40章两章为例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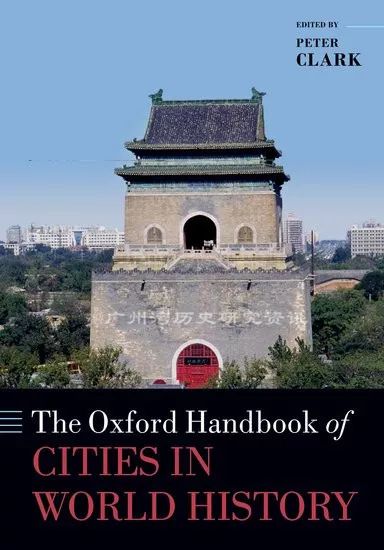
《牛津世界城市史指南》封面
来源:牛津大学出版社网站
二
二十世纪中国城市发展的前后之变
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教授Kristin Stapleton以1949年和1979年为界,在其文《1900年至今的中国》中将二十世纪的中国城市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从该文归纳,1949年前后中国城市处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分别是宽松自发和严格管制。正如罗威廉(William Rowe)等学者指出,近代变迁以前,中国普遍处于“城乡一体化”的状态(亦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一些城市的商业物质文化发达,足以反驳前者观点[3]),而近代城市的发展则促进“城乡分离”之转变。城市发展不仅意味中国官方难以维持帝制时期的社会政治秩序(socio-political),更反映政治领袖与各类民众在中央集权和民间活力之间的长期张力。[4]笔者认为,研究近代城市历史,应着重联系同一时期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nation-building)。例如作者分析,自清末至民国时期,城市管理受到新政改革和新技术的冲击;而1949年之后,苏联制度则深刻影响新中国的城市管理,户籍制度至今仍是一项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重要制度。
随着清末新政等变革的推行,新的社会阶层在城市出现和壮大,他们热衷于商会、社团乃至革命活动,部分精英从海外留学归来,引入有关市政管理和城市规划的新知识,一同促进城市发展。民国建立多年持续政局动荡,中央政府的控制力相对薄弱,亦有利于资产阶级管理市政。(有学者认为,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商人逐渐成为城市的实质管理者。)另一方面,1927年国民党建立国民政府,积极推动一系列城市建设。体现“现代性”的电力、公园、电影、马路和铁路等陆续引入多座城市。随之而来,自上而下的行政和司法制度亦在国民党的“训政”理念下在城市推行。
中央政府与民间社会在城市的张力逐渐浮现,经济增长、工业发展和消费文化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显著改变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抗日战争造成数以百万计难民流离失所,但也带动内陆城市的经济和文化转变。作者指出,这种变化在1949年之后还以不同方式得以延续(如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6]中共建政之初缺乏管理大城市的经验,因此引用强调集中决策和重工业的“苏联模式”。政府将城市居民纳入工作单位和居委会的体制之内,以集体生活作为约束,并通过户口制度控制城市人口。由此,相比于民国时期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驱动新中国城市发展的动力显然已不是来自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而是服务于政治。
建筑师黄玉瑜1929年参与制订的南京《首都计划》
来源:China Comes to Mit网站
三
殖民地城市与中国近代转型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Thomas Metcalf长期研究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历史,《殖民地城市》一文开宗明义地指出现代历史意义上的殖民地城市是欧洲帝国主义与跨国资本主义在海外征服和定居之产物。继而回顾半世纪以来的学术史,作者认为后殖民理论盛行之下,研究者往往将城市史放在有关殖民帝国的语境中解读。许多学者揭示,殖民地城市化(colonial urbanism)不仅受欧洲国家的推动,同时也来自于当地民众的活动。
Metcalf认为,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早期殖民地城市主要是分布在海上航线的港口,当时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等国往往将其视为贸易和军事据点,并不热衷于扩张内陆腹地。[7]而十九世纪英国和法国成为殖民扩张的新兴主力,积极攫取非洲和亚洲的领土,殖民者的野心已不再局限于沿海据点,而是通过铺设铁路深入内陆,进而推动商品贸易和加强政治控制。上述历史进程,同样可见于中国历史。若说澳门可作为“早期殖民地城市”的典型,那么日俄在东北以及英法在华南的殖民扩张则体现十九世纪之后殖民主义的新变化。
对笔者而言,该文关于城市设计和城市管理两部分的讨论颇有启益。区隔(segregation)是殖民当局常在殖民地城市所推行的理念和政策,以种族或血统为由,针对不同的居民群体,殖民当局在卫生、城市规划和房屋设计等方面采用多种手段划分城市空间。如《山顶区保留条例》之于英国殖民地香港,或度假胜地大叻之于法属印度支那,西方殖民者总是试图通过市政建设来保持“种族界限”(racial boundaries)。与之相连,人数处于劣势的西方殖民者面对快速增长的大量本地人口,为了维系殖民管治,他们必须考虑如何有效管理城市。Metcalf指出殖民当局有两种主要手段:其一,推行警政和法律;其二,扶植当地资产阶级。依笔者之见,这是对西方国家管治殖民地城市的精辟总结。警政和法律一方面强迫当地民众遵从秩序,另一方面吸纳掌握社会资源的上层人物进入政制之内,协助殖民当局并共享利益。当少数商人和专业精英接受西方教育或西方文化之后,他们亦充当某种媒介,自觉或不自觉地推广殖民主义的柔性一面。[8]观诸20世纪风靡一时的上海都市文化,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殖民管治对中国社会各阶层造成的深远影响。[9]
Metcalf擅长于英国殖民史,但该文从全球范围讨论殖民地城市,要求全面审视各殖民帝国的殖民管治,难免遭遇若干“心余而力不逮”的困难,值得商榷之处尤其体现在有关法国殖民史的讨论。例如作者认为法当局在印度支那铺设的铁路主要服务于政治联系,并未促进贸易网络的扩张。[10]但其实1910年通车的滇越铁路有力促进法国在中国西南的商业活动,更在抗战早期充当重要的国际交通线。再举一例,作者为了论证殖民当局只愿投放有限资源于关系西方人福祉的事务,指出二十世纪初法国当局对卫生投放可谓微不足道,仅占河内年度预算的百分之二,但并无列出文献来源。[11]可是根据加州州立大学教授Michael G. Vann的研究,这一时期出于对传染疫病的恐慌和筹办国际博览会的需要,河内法当局大力整治城市卫生,在1902至1903年间发起声势浩大的灭鼠运动,不惜花费巨额金钱发布悬赏,诱使越南民众捕鼠,籍以改造城市空间和推行法国殖民主义所提倡的“文明使命”(civilizing mission)。[12]
1920年法国殖民当局在卡萨布兰卡建造的中央邮局
来源:Post Office Postcards网站
四
对广州湾历史研究的启发
阅读上述三篇文章,对于笔者所关注的广州湾历史研究而言,有助于借鉴全球史的视野,从城市史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思考学界集中关注的现代性(modernity)、殖民合作(colonial collaboration)和民众日常生活等议题。在广州湾租借地范围内并无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府城或县城),仅有赤坎是一处较为繁荣的临海商埠,吸引数以千计潮州和广府等地客商聚居。法国人1898年占领当地之后,没有在赤坎设置主要行政机关,而是另觅城址建造新城区,自1910年起以西营为行政中心。赤坎和西营两处城区分别汇聚不同的群体,某程度上类似于堤岸与西贡的关系,法国殖民管治与地方社会的一系列角力由此开展。
有如Metcalf和许多学者所见,中国商人在堤岸主宰商业和贸易,法国当局“因地制宜”地容许他们治理当地事务,甚至以授予专营权的形式驱动他们贩卖鸦片,补贴殖民地财政收入。这种合作模式亦可见于赤坎,各会馆依然保持原有的社会职能,而1917年成立的广州湾商会裁决商事和制定商规的权力被法当局承认,拥有私人武装的实权人物更逐步获得合法地位,成为殖民管治的重要合作者。但在法国人营造的西营,当局则期望通过美观合理的市政建设彰显殖民管治的优越性,乃至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引入电厂、医院、学校和银行等机构实践“文明使命”,争取当地民众的支持。艺术装饰的欧式建筑(Beaux-Arts)如何表达权力,为当地民众带来何种观感,以及法当局在方方面面的市政管理如何改变居民日常生活,均值得进一步探讨。
概而论之,许多学者一直有兴趣于中国肇始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近代转型,城市是广受关注的对象。着眼分布中国沿海沿江多地的条约口岸、租界和租借地,既可见到西方与东方两种文明错综复杂的关系(老生常谈之话题),亦应深入考察西方帝国在这些城市如何实行殖民管治,这些城市的发展兴衰如何联系世界历史,从而启发更多思路,与广泛的研究领域相对话。
广州湾主要商业中心赤坎的街景,约1920年
注释
[1]Clark, Peter. “Introduction.” In Oxford Handbook of Cities in World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2-5.
[2]Ibid, pp. 14.
[3]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4]Kristin Stapleton, “China: 1900 to the Present.” In Oxford Handbook of Cities in World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522.
[5]陈文妍:中国近代史特别专题:城市空间的塑造及内涵,课堂讲座,香港中文大学,2019年1月24日。
[6]Kristin Stapleton, “China: 1900 to the Present.” In Oxford Handbook of Cities in World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527.
[7]Thomas R. Metcalf, “Colonial Cities,” In Oxford Handbook of Cities in World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754-755.
[8]Ibid, pp.763-765.
[9]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23-338頁。
[10]Thomas R. Metcalf, “Colonial Cities,” pp.756.
[11]Ibid, pp. 758.
[12]Michael G. Vann, The Great Hanoi Rat Hunt: Empire, Disease, and Modernity in French Colonial Vietn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通
告
时值岁末,“广州湾历史研究资讯”即将迎来成立以来的第四个新年,感谢各位读者对本号一如既往的支持,祝各位新春快乐,诸事顺遂,平安喜乐!
春节休假,本号将暂停更新两期(2月9日与2月16日),2月23日推送乙亥年首篇文章。如有不便,敬请谅解!
我们始终本着“至新、至全、至诚心”的宗旨,坚持学术性、知识性与原创性,期待新年与您新的相遇。
撰文:吴子祺
编辑:大 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