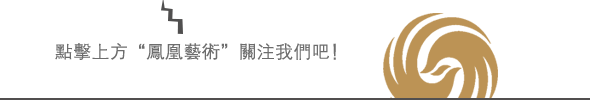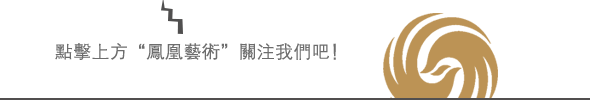
“凌听 | 施慧”
她独喜独忧,一张张薄如蝉翼洁白的宣纸、一根根细细的棉线,一个个小圆点织成了施慧的大宇宙。施慧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第一批从事当代纤维艺术的艺术家,她坚持纤维艺术在当代艺术中的创作方向,作品以棉、麻、宣纸、纸浆等纤维材料为特征,在当代艺术的层面上体现出东方精神的底蕴。作品先后参加国内外许多重要展览及提名展、双年展,引起广泛关注。
施慧持续使用中国宣纸和纸浆为主要媒介,在这种钟爱的后面,显然既是对媒介与自己心灵默契的那种特殊属性的体认,也是对中国传统媒介在当代的价值转换的信念。施慧的作品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图式中,呈现出独特的视觉特征,她将传统意义上的编织拓展为一种视觉空间的建构,编织的过程被作为经验的流程,而成为一种“后现代的万物有灵论”的图像演绎。
▲ 施慧《飘》,2000
艺术史家、策展人、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曾说道:“施慧的作品是游离于宏伟与脆弱之间的对比。”著名艺术史学家范景中教授这样评价施慧:“她虽然是一位现代艺术家,其力量却显然不在于表达现代人的复杂感觉,特别是表达那些焦虑者的现代感觉。她的作品是对健康、朴素、和纯净的感觉的表达。她运用澄明和清澈的艺术语言表达了一种秩序,甚至使那些热烈而华丽的自然也带有一种明朗的色调,它是细腻的、纯真的、丰富的、有序的,它强调了我们天性中的爱好简朴之心,在迷人的纸质和纤弱的绳线中表明了自己是一个现代的朴素诗人。”
▲ 施慧《游影浮墙》,第2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参展作品,2205-2006
今年秋天,第三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即将进入大众视野,期待这位中国纤维艺术的灵魂人物率领着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们呈现更多更具有当代性的思考和全新探索的作品。回顾“凌听”专题,让我们一同走进艺术家施慧的艺术世界……
为什么是凌子的《凌听》?
知微者才能叫“聆”,
感同者才能叫“听”。
听人、听心、听世……
种种艺、文、思想降与人间的妙曼,
唯“知微者”与“感同者”相遇相知。
而这由“知”及“感”的人恰好叫凌子,
“凌听”来得如此自然。
本期《凌听》视频:素心施慧—施慧专访
凌子倾听施慧
以下为节目中的采访片段,施慧简称“施”,凌子简称“凌”。
施:
当我拉起第一根经线时,线已被情所牵,纤维质的材料中,蕴藏着自然植物的生命特点,又蓄满人与自然合用的意愿,我以最单纯的技术为起点,在不断演绎的过程中,创造现代意义上的新构架。
▲ “凌听”施慧
施:
文革开始时我四年级,父亲就受到冲击。在文革的时候我们家抄家四次,每一次来抄家的时候红卫兵就咚咚敲门,听到那个敲门声音就很紧张,那个时候对于一个小孩来说,真的是很大的一种伤害吧。后来到了农村,那时我父亲已经被隔离了,我们见不到他。然后就是我和我母亲两个人下放农村,母女两个很弱的这样一种感觉。当然我觉得人的适应能力也真的是很强,而且那个年龄也比较小13岁,很快也就适应了,跟着农民孩子一起下地干活。
凌:你心里没有落差吗?你从上海一个很讲究的书香门第的家庭来到农村。
施:
好像没有什么怨言。你就是接受,然后去适应它。
▲ 田野中的施慧
凌: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未来?
施:
当时没有什么未来,就是生存下去,不去想很多未来。有一部电影叫《简·爱》,《简·爱》的一句话就是说“人生就是含辛茹苦”。
▲ “凌听”施慧施:
1986年保加利亚的功勋艺术家万曼在我们学校建了一个纤维艺术的研究所,那个时候叫万曼壁挂艺术研究所。在研究所初创时期,其实我们学的就是编织。看到小时候自己喜欢的小手工竟然也可以成为大艺术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这个概念也是万曼带给我们的,壁挂的变革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艺术家自己亲自上机台进行编织。这个机台在他面前就像一幅画布一样,你在上面就可以很自由的绘画了,就是说手与心应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就决定,自己一生可能就是要从事编织艺术,就觉得找到了自己一生要努力的方向。
▲ 80年代,施慧(右)在制作洛桑双年展的作品《寿》
▲ 施慧创作的《寿》1986年入选了瑞士洛桑壁挂双年展,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第一次登上国际大展舞台的里程碑施:
我们系跟国画系在一起,有一天我手一抓宣纸就觉得手感特别软,跟我编织的东西可能可以结合,所以我就抱了一些宣纸回家。还是按照习惯性的编织把它折成纸条,搓成纸条。因为有宣纸有水墨,它出来的东西马上就有一个中国的元素在里面。到了92年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我跟着几个朋友去富阳农村。当时富阳造纸的作坊很多,我们就看看宣纸是怎么做的。看上去还是很清的那种水稍微调一下,就会有一点点浑浊,但是捞上来就是一张纸,我就觉得很神奇。我就买了一个蛇皮袋的纸浆带回家实验,就觉得突然好像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一种艺术语言。
▲ 施慧《扇》,2002
▲ 施慧 《老墙》,2003
施:
纸浆这个材料我一直没有放弃,它背后有一种柔韧性,一种文化的品质。在这个层面上面我会更注重去把握它。
▲ 施慧《飘》,2000
▲ 施慧《凝风》,2004
凌:在创作当中,对您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施: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希望跟中国的文化有一种关联,能够把一些传统的文化和中国人的一种审美的心里能够呈现出来。它不是一种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的那种沉重式的审美,它是一种家园式的回归的感觉。我觉得它是一种非常亲和的、自然的,一种既柔又韧的感觉。
▲ 施慧《本草纲目·1》,2009
▲ 施慧《本草纲目·2》,2012
凌:您使用纸这个媒介,它会不会有局限性?
施:
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别人现在看到白白的纸浆都觉得这个是施慧的作品,要跨出这一步很难,又要有延续性,又要有突破性确实不容易。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遇,不是说就是硬生生地去跨这一步,所以现在一直在寻找,寻找一种方式,寻找一种新的对事物的一个看法理解。
手作的诗
文/冷冰川
▲ 艺术家施慧
施慧像是一直在描写她日常的朴素的心识。一直,就是没有蒙混和逃避。她日常本色视觉的流露也像是源自一种单纯的向往、单纯的触动;这单纯和她少年时代在江西农村田野上的劳作、认识筑起的生命感、世界观相关。从那时起她“就把自己的情感和无声的花草石木融合在一起”(施慧语)。诗人诞生于童年,这童年有多少孤独就有多少真实和真心的表现。这系念自然成了她艺术创作的元气、灵感,也确立了她诗性品、格的表现。仅仅源自一种单纯、沉默地手工显示,不夭不斧不作不害,已有了某种殊心的意味和识别。这本色自然不是寻思来的,是内在感受自然而成;施慧对这真实怀有一种特殊的真恳,并在日常接触的对象、材料、创作上感受到编织生命的种种乐趣。施慧一直弯腰俯拾童年草木果实的滋味,一草一叶一忧一喜种种针脚,像她的出生地语言,她一直幸运地说着自己最初最真的词语(不是太过具体、太过棘手的实体现实),并将记忆里的松、烟、竹丝麻草、田埂、山冈……一个个“中国性”带出来。指尖不停的划过无声无息无尘,未知未解未变之境——她就这样编掇着生机,划过性灵的深美呼吸。我喜欢这样单边主义地沉默有力的进程,一个不断远离的手工进程;手作的沉思跟人最近。
▲ 施慧《结》,1994-1995
▲ 施慧《柱》,1996
▲ 施慧《结》,1998
在施慧天然又虚拟的中国田园式织述中,弥漫着片段化的个人史追溯、原乡,和她在自然材质中发掘构建的新的“微观自然”的娱悦、智识。这是艺术家意志的“天然生长”和体察世界的方法、路径,充满了女性创作人特有的元生本能,自律、沉静品质和思想生命场。施慧始终寻着“元生”自觉的感受,淡淡的悲喜,缓慢的浸润,依照内心的流向编缀发展形、色、临界、结果……那是从一根线中演化出一个世界的冲动,是大千纷繁万象中的一种化约、廓清。她将竹、石、点、线、虚、实、指尖都附上诗词的灵魂、刺痛。一种纯天然的向度才能把“手作”的素境和手工中无意识本真朴拙的绝唱强调出来,这平凡的味道都是出自自然潜藏的能量,大美而无言(她甚至无法超越自己特殊的真诚)。这简单而深刻的快乐,真是最好的诗最好的自然。
▲ 施慧《假的山—— 一个不同的文化情景中的视觉对话》,2001
施慧的日常“真实”——那随手而来的荒野、时光、季节、童年的怅然白描都被转换成自然的不可名状而又能触摸的性灵形状。人的指尖一直地划着身心的界限。这个体的显示品形闲淡直接、气象幽微、又生机勃勃,她擅长将不同的日常自然和天然经验上升到一个迷离的新生空间场,种种天然、含混、单纯、缱绻,清贫地叙述了时、空、线、象、浆色和生机的一丝一缕的寓言;来来回回数以千万计的纤肌碰撞在一起,为人沉浸出万籁俱动、万物花开的和谐情意。从心灵经验到文化经验,从自然环境到文化空间,看得见她一次一次在复杂的形态、临界、构造,在每一个编织环节都循顺着人、物自身的格致态势,暗流潜藏;她一直回到本体汲取再生能量,回到织造的原点(不是简单的绚烂织体、简单的材料叙事,是光、空间和天然见道的畅吸);艺术必须与这样的自然、单纯有密切的联系;也只有这样自然人浸染后的风物,才有足够的滋味、足够丰富的想象。拥有很少东西的人常常生生这么多情地传递、暗示。“多情”告诉了你你想知道的真实,但多情从来不会告诉你最后的真实,因为那是危险、脆弱,我们什么也看不到。
▲ 施慧《融》,威尼斯丽都岛展出现场,2002
施慧的“手造”用了最平常的语言和颜色。创作里“平常”是恰当的词(其它的标准太动荡了),事实上手指自然从心就已经有了足够的情绪、足够重要的东西。我们要用平常的语言,在水银般难以捉摸的流变中寻找石头和石头里的诗,并在石头中说出永恒的事物和回声。施慧说出了她绵长的深意、深呼吸,我们见着了她时间手造的种种,见着了她指尖生发的河流、种子、血脉、戒指,见着了从童年时时趋近的那个自己,我们见着了人一次次用心透过自身年岁的沙、海、燃烧的云石……自然创作的快活就是这样静静地狂欢,静静地收成。这独享,象诗里不可能到达的诗意。
▲ 施慧《悬础》,2008
▲ 施慧《诗意的停留》,2007自然的东西,我总是苛求地读。因为艺术创作中自然的东西不能成为现实,也不反映“现实”。所幸是这种种不能,才可能在布面、纸上,在艺术的千丝万缕中成为一种现实(不是潦草的感官、潦草的现实)。纤维艺术尚未订出学究茧的标准这一事实确是一件幸事——一直不能如期归来,才有指尖编写的意义,一直没有确切的证据才余下未知、空白的最初吸引力;在一种不可知、不能落脚的、直觉地追逐中,让我们尝试用特别的方式阅读这些不分行的诗、阅读“自然人”与自然、自身遇见的弦外之音。施慧单纯靠手指就编出流水自然的温度、编出了复杂幽微的女性力量和滋养;她在千丝万缕里完成了一种自己,在实践中遇见并尽可能完成了不现实,不可知的自己;一种、一千种宁静的骨骼,和她冷淡表情一样,满脸真诚,不带瑕疵。
▲ 施慧旧照
一个人、一生、一条线索一直寻着,完成了独有的思想指尖和它的戒子;一个人做了一件事,做好做透,那是深致。我们要将它辩识出来。
关于 施慧
▲ 艺术家 施慧施慧,艺术家。1955年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工艺系,现为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开始从事当代艺术创作,作品以棉、麻、植物、宣纸、纸浆等纤维材料为特征,同时将这种特征转换到硬质材料的实验中,作品体现出东方精神的文化底蕴。2000年参加第三届上海双年展,2001年参加德国柏林国家美术馆“生活在此时——29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展,2003年参加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间”——中国当代艺术展,2013年在德国科布伦茨路德维希博物馆举办个展。2007年获马爹利非凡艺术人物奖,2014年获 AAC 第八届艺术中国年度雕塑影响力大奖。2002年出版个人作品集《素朴之诗》,2013年出版个人作品集《施慧》。
关于 凌子
▲ “凤凰艺术”主持人凌子
凌子,知名媒体人,旅行家,艺术观察者,策展人。”凤凰艺术“主持人。
(凤凰艺术 独家报道 采访/凌子、视频/刘慧等 责编/Mimi )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凤凰艺术”
凤凰艺术
最具影响力的全球艺术对话平台
艺术|展览||对话
版权声明:凡本网注明“来源:凤凰艺术”的所有作品,均为本网合法拥有版权或有权使用的作品,如需获得合作授权,请联系:xiaog@phoenixtv.com.cn。获得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凤凰艺术”。未经本网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
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查看“凤凰艺术”《凌听》节目全部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