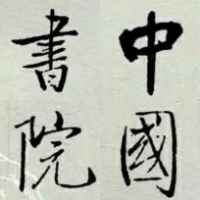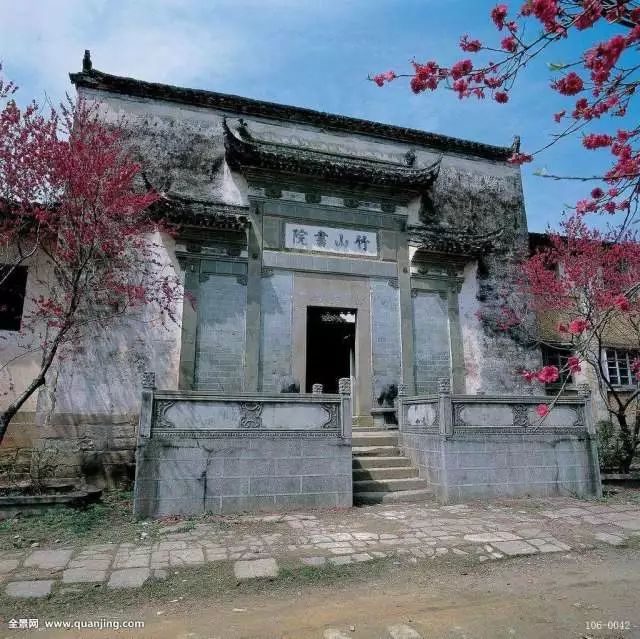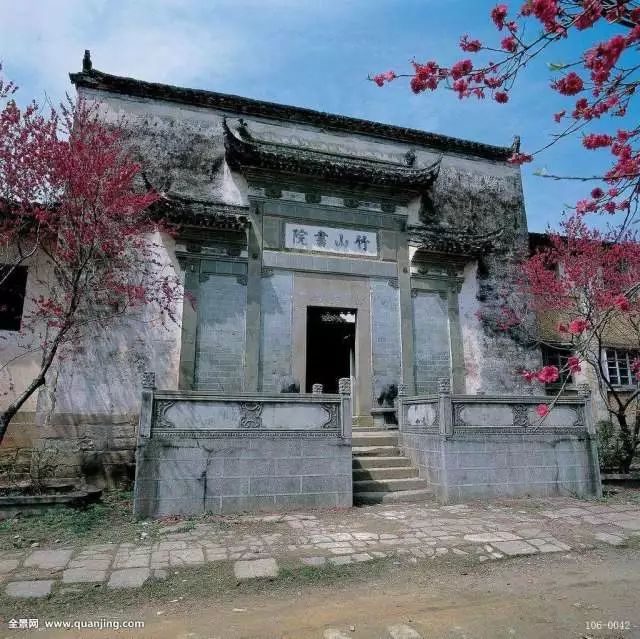
一
明代安徽书院数量考
朱元璋因自濠州(今安徽凤阳)起兵建立了明王朝,故将家乡视为“兴王之地”。安徽在明代并未设省,而是属于南直隶。这使得安徽在明代的行政区划上处于“显赫”的位置,但却为今天学者们研究安徽明代书院的数量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各个学者依据的政区范围、搜索的史料多寡和采取的取舍标准各有不同,统计出的数字互有差异。关于明代安徽书院数量的考证,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有:丁益吾、朱汉民统计为99所,白新良统计为144所,季啸风统计为106所。
本文在考证明代安徽书院数量时遵循两个原则:首先系统搜集原始资料。通过翻阅《大明一统志》、《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乾隆《江南通志》、光绪《重修安徽通志》、民国《安徽通志稿•教育考》和安徽部分府、州县明代方志(主要为天一阁明代方志),以及一些碑刻、笔记等,系统搜集明代安徽书院的资料。其次采用以当时治所在今安徽境内的辖区为准,现划归外省地区的书院一般不再计入的原则,但是对于明代凤阳府和徽州府范围的界定则采取约定俗成的方法,即将现划归江苏省的盱眙归入凤阳府,将现划归江西省的婺源归入徽州府。另外,本文还参考了前辈们的众多统计成果,前已述及。关于明代徽州书院的统计是根据拙著《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的表四“明清徽州所建书院一览表”直接改制而成。统计结果为明代安徽地区共有书院139所。为了方便查核,现将各书院的建置列表如下——
二
明代安徽书院的地域和时间分布特征
(一)地域分布特征 明代安徽地区分属7个府、3个直隶州(以弘治九年即1496年为准),其中有8个府(州)完全在今安徽省境内,分别是庐州府、安庆府、太平府、宁国府、池州府、广德州、和州、滁州;有2个府跨今江苏、江西、河南部分地区,即凤阳府跨今江苏盱眙县、河南省部分地区,徽州府跨今江西上饶婺源县部分地区。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明代安徽书院的地域分布情况,特列表2:
根据表2,我们可以把明代安徽书院的地域分布情况分为三个等级:
一级——20所以上地区,有徽州府(49所);
二级——10~20所的地区,有宁国府(18所)、池州府(17所)、凤阳府(15所)、庐州府(12所)、安庆府(11所);
三级——10所以下地区,有滁州(6所)、太平府(5所)、和州(3所)、广德州(2所)。
通过对表2的仔细分析可见:
1.明代安徽书院的分布已经普及全省的各府(州),由宋元时期的点状分布发展为明代的片状分布;
2.地处皖南的徽、宁、池三府的书院总数为84所,占全省书院总数的60.43%,很明显成为一大分布区;
3.从最后一列“府(州)所属县平均书院数”中,我们可以发现地处皖北的凤阳府显然排在全省的最后,其平均书院数仅为1.2所。笔者在搜集资料时发现,凤阳府下辖的五河县、临淮县、颍上县、太和县、霍丘县、蒙城县这6个县在明代的书院建置数为零。虽然凤阳府的书院总数位居全省第四,共15所,但这些书院几乎全集中于凤阳府治中心及附近,书院的分布极不均衡。
为了印证表2,笔者又根据民国《安徽通志稿•教育考》的记载制成表3:
从表3中可见,虽然《安徽通志稿•教育考》中对明代安徽书院的数量记载与表2的考证有很大的出入,但是表2与表3中所反映的明代安徽书院的总体分布趋势是相当一致的。
(二)时间分布特征
明代安徽书院的建置有时段可考的共115所,分布在明代17朝中的10朝内。其中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共44所,占全省书院总数的31.65%。详见表4:
从表4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明代安徽书院的发展经历了“沉寂——勃兴——禁毁”的历程。从总的时间分布来看,有段可考的书院中,前期137年共设置19所,后期139年共设置68所,分别占21.84%和78.16%。后期明显多于前期,是其三倍有余。在有书院建置的10朝里,嘉靖朝明显最多,有34所;其次是万历朝有24所。其余8朝的建置均在10所以下。嘉靖和万历两朝的书院占十朝书院总数的66.67%。嘉靖、万历两朝长达93年,占10朝年代总数220年的42%,是明代安徽书院发展的两个高峰期。
我们知道,朱明政权建立之初,为了收揽人心,曾下令修复曲阜尼山、洙泗两所书院。受此影响,安徽也重修了个别前代书院,如歙县紫阳书院,并新建了绩溪龙峰书院、歙县枫林书院。但这只是明政府开国时尊崇儒学的一种表示,且尼山、洙泗两所书院只具有祭祀功能,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书院,因此不能代表明政府真正重视书院建设。待政权稍稍稳定之后,明政府大力发展官学教育,禁绝各地书院的建设,下令“改天下山长为训导,弟子员归于了邑学,”使“书院因以不治,而祀亦废”。这样,从洪武至天顺八朝的一个世纪里,和全国一样,安徽书院废而不举,沉寂无闻。明代安徽地区在这八朝里仅新建书院10所左右。与此同时,明朝的官学却得以极大发展,一时形成“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无地而不设之学,……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之盛况。
成化以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官学的规模无法满足广大士子求学的需求,如正德间,祁门县“邑儒学子员凡二百,而学舍仅百之十,无从卒业久矣”。加之官学日渐衰落和科举的日益腐败,书院开始逐渐复兴。据《明史•选举志》载,成化二年(1466年)礼部尚书姚夔说:“太学乃育才之地,近者直省起送四十岁生员,及纳草纳马者动以万计,不胜其滥,且使天下以货为贤,士风日陋”。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详细罗列了自永乐二年(1404年)甲申科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乙丑科之间,通过舞弊实现金榜题名的进士名单。著名的还有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己未科,吏部尚书吴鹏之子登二甲进士,“则倩人入试,途人皆知,而言路无敢言者”。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学生员中普遍存在年老体衰、纳财捐取等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为了补偏救弊,书院重新引起了学者的重视,至正德末,安徽新建书院13所。正如柳诒徵先生所言:“宋元之间,书院最盛,至明而浸衰,盖国学网络人才,士之散处书院者,皆聚之两雍,虽有书院,其风不盛。其后国学之制渐,科举之弊孔炽,士大夫复倡讲学之法,而书院又因之以兴”。
嘉靖、万历年间,安徽省内新建书院数量激增,书院设置达到高潮。嘉靖年间,两位王门泰州学派弟子耿定向、罗汝芳在安徽为官,加上安庆知府胡瓒宗,他们都精深理学,而又当权地方,故倡建书院甚多。此时,另一位学术大师湛若水也先后讲学于徽州各大书院,形成较大影响。一时之间,安徽书院出现了阳明、甘泉、程朱三足鼎立的局面。“心学”和程朱理学在安徽的门户对立不但促进了学术文化繁荣局面的形成,同时对安徽书院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与之相应的却是嘉靖、万历两朝正是明代打击、禁毁书院最厉害的时期。众所周知,嘉靖十六年(1537年)、嘉靖十七年(1538年)和万历七年(1579年)先后禁毁全国的书院。为何安徽书院的发展恰在这两朝出现高峰期?我们仔细考察这三次禁毁书院的背景即知,这三次禁毁不是与政治斗争有关就是与当权者的好恶有关。随着政治斗争的复杂化和当权者的变更,书院又得以恢复。嘉靖十六年和十七年的两次禁毁书院,《明史》为了掩盖未予记载。我们在《续文献通考•学校考》和《皇明大政记》中可似找到有关这两次禁毁书院的记载。当时在朝执政的人,有许多反对王阳明、湛甘泉之学,他们对于王、湛的广建书院,聚徒讲学,妄加罪名,实际上是为了在政治上和学术上进行压制。先是以“倡其邪学,广收无赖”[8]的罪名毁闭王、湛私立的书院,随后又以“废坏不修,别立书院”,“动费万金,供亿科扰”为借口,禁毁所有书院。但是书院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声望甚高,禁是禁不住的。正如《万历野获编》中所说:“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不仅如此,官方越禁,民间越办,所以明代的书院反以嘉靖时期最多。“王学”在安徽又是很有影响,并且王守仁的弟子耿定向和罗汝芳即在安徽为官,他们在两次禁毁书院后都积极创建新书院,如宣城的志学书院就是耿、罗二人在嘉靖三十五年合作创办。明代第三次禁毁书院是万历七年(1579年)张居正执政时,他虽为徐阶的弟子,却最厌恶书院聚徒讲学。《万历野获编》卷八载“张居正最憎讲学,言之切齿。”他的禁毁书院比嘉靖间禁毁的规模更大,措施也更加严厉。然而,当时国学衰微,地方官学名存实亡,但书院讲学制度已深入士人之心,社会影响较大,加之张居正于万历十年(1582年)卒去,其推行的禁毁书院的措施也就烟消云散了。
同时由于嘉靖、万历时期书院的作用已由教育士子、学术传递渗透到政治斗争中,因此书院的兴衰不可避免地受政治斗争的影响,这也为以后书院的悲剧性命运埋下伏笔。天启年间,魏忠贤当道,东林党人大肆对其恶行进行抨击。东林书院是反魏的中心,同时也就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为了排除异己,魏忠贤矫旨禁毁天下书院。天启年间,安徽仅有“龙兴之地”凤阳府建有一所书院,其他地区不仅没有书院地建置,反而大量书院遭到焚毁。
三
明代安徽书院集中于徽州府的原因
前文已述,明代安徽大量的书院集中于“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线,形成了明代安徽书院分布与发展的中心地带,而徽州府的书院数又以绝对优势成为中心地带中的重心所在。从而形成了“新安(即徽州)讲学书院较他郡为多”的局面。为什么徽州府的书院会如此繁盛并独占鳌头呢?这主要是由以下三方面的因素所致:
(一)徽商为徽州书院发展提供了厚实的经济基础。
经济是学校教育,同时也是书院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离开了经济的支持,学校教育和书院教育的发展只能是空中楼阁。明中叶后,徽州以“商贾之乡”而“富甲天下”,经商所积累的巨额财富为该地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酵母”。
徽商在步入商海之前,大都接受过正规的传统文化教育,是一批具有较高儒学素养的商人。他们虽因生存所迫不得不弃儒服贾、经商谋利,但经商谋利并非是徽商的最高价值追求。徽商的重要特色是“贾而好儒”,经商只是解决经济基础的一种手段,用经商所得之厚利让子孙业儒入仕、显亲扬名才是徽商的终极关怀。
正因为徽商的终极关怀是让子孙习儒业、入仕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经商致富后,他们对家乡教育事业的资助可谓竭尽全力、慷慨不吝。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明中期以后,“徽州的书院、馆塾之类的学习场所,大多是由商人或官绅倡修,由商人捐资兴建的。”如明弘治间祁门商人李汛建李源书院,并割田20亩入书院“以助族子弟能读书者”;明万历间休宁商人吴继良“构义屋数百楹,买义田百亩”建明善书院;明后期黟县商人黄志廉率族重建黄村集成书院;等等。可以说,没有徽商便没有发达的徽州书院,更没有那斑斓璀璨的徽州书院文化。
(二)宗族为徽州书院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徽州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这些聚族而居的大姓,皆有千年不紊之谱系,有宏伟壮丽之祠堂,有完备翔实的宗规家法,有严格规定的尊卑秩序,有族田族产作为宗族公共事务和赡贫济穷之资。因此,徽州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宗族制度最为强固的地区之一,并“堪称为正统宗族制度传承的典型”。
徽州宗族大多来源于中原的显宦之第或儒学世家,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他们深知,宗族要发展壮大、强盛不衰,要想在社会上享有威望,光靠经济的力量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确立宗族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地位。所谓“子孙才,族将大”;所谓“族之有仕进,犹人之有衣冠,身之有眉目也”。等等,即是指此。而要确立宗族的政治和学术地位,保持科名不绝,只有通过发展儒学教育才能够实现,正如光绪《绩溪东关冯氏家谱》卷上《冯氏家训十条》中“兴文教”一条所言:“一族之中,文教大兴,便是兴旺气象。古来经济文章无不从读书中出。草野有英才,即以储异日从政服官之选,其足以为前人光、遗后人休者”。
所以,徽州的强宗巨族都有强烈的教育追求,许多宗族都将创设教育机构,“悉力扶植”族内子弟业儒,注意挑选那些所谓“器宇不凡”的族内子弟着力加以培养作为宗族内的重大事务,并将其作为宗族规范书之于族规家训之中,张贴于祠堂祖屋之上,让其子孙时刻谨记、世世遵守。明中叶后,徽州的书院十分兴盛,而这些书院大部分都是由宗族主持创办、由宗族来组织管理的。如:休宁的率溪书院是率溪程氏于明弘治五年创设的;休宁的明善书院是商山吴氏于明万历间兴建的;婺源的桂岩书院是由桂岩戴氏于明成化间重建的;婺源的明经书院是考川胡氏于元初创立的,元末“火于兵”,到明成化和万历间族人分别重建、重修。如此等等。“建立一个向士人社会开放的书院,是一个家庭提高自身声望,表明其对于地方精英身份诉求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文化与社会资本的投资,以财产来交换地位。”美国学者琳达•沃而顿(WaltonLindaA.)在研究南宋书院与社会关系时所作的论述也可视为明清徽州宗族积极创办书院的心理写照。
(三)“心学”的流布为徽州书院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学术资源。
书院自产生之日起,就与学术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明中叶,陈献章远承陆学余绪,提出“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思想,反对朱子的“格物穷理”之学。这标志着明初朱学统一局面的结束,也是明代心学思潮的开始。献章而后,明代心学分“王、湛两家”:王守仁“宗旨致良知”;湛若水“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心学兴起后,特别是王守仁“致良知”学说的出现,迅速传播全国,“学其学者遍天下”,以致“嘉(靖)、隆(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心学遂取代程朱理学而成为明中后期占全国主导地位学术思潮。
心学兴起后,随即影响到徽州地区,明嘉靖以后,徽州这个程朱理学的故乡,也成了心学肆意流布的地域。为了攻破徽州这个固守程朱理学的顽固堡垒,一方面是信奉心学的徽州士子和官绅纷纷在徽州创办书院,如信奉甘泉之学的徽州知府冯世雍于嘉靖间创建歙县斗山书院和祟正书院、信奉阳明之学的休宁县知县祝世禄于万历间倡建休宁县还古书院、信奉阳明之学的徽州知府留志淑与祁门知县洪晰于正德末年创建祁门县东山书院、湛若水门人于嘉靖间兴建婺源县福山书院等等;另一方面则是心学家们鱼贯前往徽州主讲席、兴讲会,扩大心学在徽州的影响,雍正《紫阳书院志》卷十八载:“嘉靖丁酉(十六年,1537年),甘泉湛先生主教于斗山,庚戌(二十九年,1550年)东廓邹先生联会于三院;厥后,心斋王、绪山钱、龙溪王、师泉刘诸先生递主齐盟,或主教于歙(县)斗山,或缔盟于休(宁县)天泉、还古,或振铎婺(源县)福山、虹东,以及祁(门县)东山、黟中天诸书院。”正因为如此,才有天启间阉党张讷的“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之说。所以说,心学的传播是促进明中后期徽州书院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
作者|李琳琦、张晓婧
来源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第04期
“
版权说明:感谢原作者的辛苦创作,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作者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或支付转载费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