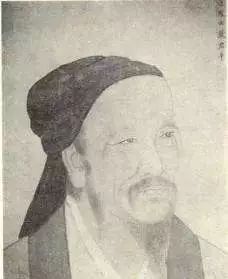自程伊川“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一语传出后,古今学人对巴蜀易学便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或游历巴山蜀水,深入山岩水涘,希望一睹研《易》者之仙风道貌;或征文考献,穷尽金匮石室,力图明白巴蜀学人的易学业绩。由于史缺有间,文献不足,至今还缺乏对巴蜀易学的整体考察,也未出版一部内容全面的《巴蜀易学通史》。对于巴蜀易学的成就及其文献,亦没有全面系统的调查和研究。人们在传述和理解伊川先生当年这一命题时,仍然有若隐若现、若有若无的感觉,甚至对巴蜀易学史语焉不详、欲说还休。本文希望利用近来从事《儒藏》和《巴蜀全书》编纂调查所得资料,讨论一下巴蜀易学的流传及特色问题,以供人们在解读伊川语及讨论易学史时参考。
一、滥觞与集成:汉唐时期的巴蜀易学
自孔子传《易》商瞿,商瞿五传至田何,而遇秦焚儒书,《易》以卜筮之书不焚,故传者不绝。汉初,田何传《易》于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诸人“皆各撰《易传》数篇”(《汉书·儒林传》)。王同传《易》于杨何,杨何于元光元年(前134)征为中大夫,武帝立“五经博士”,易学博士即杨何,史称“《易》杨”,司马迁父亲太史谈曾“问《易》于杨何”(《史记·太史公自叙》),即此人也。丁宽著《易传》三万言,“训诂举大义而已”,又称《小章句》。宽传《易》于施雠、孟喜、梁丘贺,三人之学在宣帝时立为博士,又各撰《章句》2篇。同时又有京氏,自称出于孟氏,亦立为博士,有《孟氏京房》11篇、《灾异孟氏京房》66篇等书。以上皆今文易学。当时民间又有费氏、高氏,未立于学官,独以《十翼》解说上下经,为古文易学(并见《汉志》)。此西汉易学之大略也。
从易学渊源上考察,蜀中易学传授实与中原同步。商瞿是否生于瞿上,为今四川双流人(杨升庵说),乃在疑似之间,姑且无论。仅从两汉时期算起,巴蜀易学已大有传人,并且初有文献。目前有文献可考的巴蜀第一位《易》师,是汉初的胡安。陈寿《益部耆旧传》佚文载:汉初,胡安居临邛白鹤山传《易》,司马相如尝从之问学。据《史记》《汉书》,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在文帝时已经知名,他从胡安受《易》,可能在文帝末年(前157)以前。汉初传《易》的始师田何,至惠帝时尚存,《高士传》谓“惠帝亲幸其庐以受业”,则胡安之在世当与田何同其时。也就是说,田何在中原传《易》时,胡安亦在蜀中传《易》矣,二人时代即或稍有前后,亦相距不远。如此看来,司马相如的时代应与中央第一个易学博士杨何大致相当。相如在他的作品《上林赋》中,有“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云云,说明他是熟读五经,当然也是关注“易道”的。
稍晚的蜀易传人则有赵宾,曾为孟喜师,见于《汉书》。《儒林传》称:“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荄兹也。’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授)孟喜,喜为名(称扬)之。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仞(承认),以此不见信(伸)。……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时人颇有说赵宾从孟喜受《易》者,然视《汉书》所谓“云受孟喜”、“喜为名之”、“喜不肯仞”、“喜改师法”诸语,实为赵宾曾以巴蜀的易学授于孟喜。既然赵宾曾经传术于孟喜,他生活的时代就应当与孟喜的老师丁宽同一时期,在景帝之朝。不过,赵宾除了留下以“荄兹”说《易》“箕子”外,已别无其他《易》说可考了。
宣元时,成都《易》家则有严君平(成都人)。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埶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汉书》卷七二《王贡两龚鲍传》),可见其乃一位隐于卜筮的高人。他“雅性澹泊,学业加妙,专精《大易》,躭于《老》《庄》”(常璩《华阳国志》卷一〇上),又是汉代“三玄”兼治的第一人。郑樵《通志·艺文略》“五行”家之“易占”类著录《周易骨髓诀》1卷,注曰“严遵撰”;《宋史·艺文志》“筮龟类”有《严遵卦法》1卷。兹二书并不见于汉唐之间的文献著录,疑为后世依托,但颇得其易学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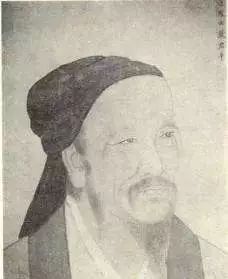
严遵画像
君平的弟子有扬雄,成都郫县人。雄少从君平游学,深得大《易》秘奥,后乃仿《易经》而撰《太玄》,是“太玄学”的开创者。
从治《易》特征来看,西汉博士易学(亦即官方易学)有施、孟、梁丘、京氏,皆今文易学,皆数术之学;民间的费、高二氏古文易学,以《十翼》缘释经文,为义理之学,但亦不废卜筮。反观蜀中易学,诸家《易》都与道家神仙之术有关。先看蜀中第一《易》师胡安:《蜀中广记》卷一三引常璩说:“临邛名山曰四明,亦曰群羊,即今白鹤也。汉胡安尝于山中乘白鹤仙去,弟子即其处建白鹤台。”魏了翁《营造记》说:“临卭虞侯叔平以书抵靖,曰:‘州之西直治城十里所,有山曰白鹤。……远有胡安先生授《易》之洞,近有常公谏议读书之庵。’”胡安居洞授《易》,临台升仙,知其为修道成仙之人,所传易学必为道家仙学易矣。其次看赵宾:宾以术数“饰《易》文”,传孟喜,喜为之改师法,讲阴阳灾变,以传京房,遂有“孟京之学”,赵宾之《易》必为数术易。
严遵专精《大易》,耽于《老》《庄》,而且卖卜成都市,以卜筮劝善,是其易学兼道家易、数术易二术。扬雄从严遵游学,当然是严学传人;而他所撰《太玄》,张行成说他“义取于《连山》”。《连山》为夏易,传为禹所造,汉代兰台有藏,据说今西南少数民族(如羌族、彝族、水族)亦有传之者,是扬雄又传夏易《连山》。《周礼》太卜掌“三易”之法,《连山》在其中,是《连山》亦卜筮书。
清四库馆臣述易学变迁说:“《易》本卜筮之书”,“《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胡安、严遵易学,尚近于《左传》,得《易》之“本义”。赵宾之法,则远启孟、京,为禨祥易学鼻祖。
前人又分汉代易学为四派:“训诂举大义,周、服是也”;“阴阳灾变,孟、京是也”;“章句师法,施、孟、梁丘、京,博士之学是也”;“彖、象释经,费、高是也”。放之蜀中易学,严遵《易》《老》兼治,颇近周、服;扬雄《太玄》仿古,则似费、高;赵宾数术,实启孟、京。
至于讲究“师法”“章句”的博士《易》,本为蜀人所不喜,亦为蜀人所不屑为,如李弘、扬雄皆厌弃“章句”。但是西汉蜀士之学于京师者比比,必有受其传者。如宣帝时郫人何武与成都人杨覆众等偕计前往京师,曾歌王褒《中和颂》于宣室,甚得宣帝嘉奖,“武诣博士受业治《易》,以射策甲科为郎”(《汉书·何武传》)。何武所传者,无疑就是当时的博士易学,亦即“章句”之学,只是不知道当时所传为施氏《易》,抑梁丘《易》也?
东汉太学仍置西京“十四博士”,易学亦守西京施、孟、梁丘、京氏之传,蜀人受学,共从于京师者,自然是“博士今文《易”》;其起于本家或本乡者,则蜀学之特色固在。据《后汉书》载,谯玄、谯瑛世代传《易》,玄始于西汉哀、平之时,瑛为东汉章帝师傅,可见其易学乃其家业;但能为章帝之师,其学必与博士《易》相通,否则必被排摈。又《杨由传》说:“杨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少习《易》,并七政元气、风云占候,为郡文学掾”;《段翳传》说:“段翳,字符章,广汉新都人。习《易经》,明风角,时有就其学者,虽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华阳国志》又载郪(三台)人冯颢,少师成都杨班、张公超及东平人虞叔雅,“作《易章句》及《刺奢说》,修黄老,恬然终日”(常璩《华阳国志》卷一〇中)。杨由、段喜习《易》而尚占,特别是明于风角,是乃赵宾传统;冯颢则通《易》,兼崇黄老,则与严遵道家易为一路,皆为蜀中本有易学之固有特色。
至于《后汉书》之载任安受《孟氏易》,折象通《京氏易》,景鸾治《施氏易》,作《易》说;《华阳国志》又载成都人任熙通《京易》(常璩《华阳国志》卷一一),皆师法家法明晰,又纯然博士《易》矣。说明东汉巴蜀易学传授,仍然是本土传统与中原官学系统,方驾并驰,如日月之同辉。
东汉时,古文经学仍在民间传授,但经郑众、贾逵、马融、许慎等努力,已经取得很多成就,在学术上具有很大势力。郑玄囊括大典,兼治今古,遍注群经,已经开创了经学史上“郑学”时代。这些学术形势,对蜀中似乎没有太大影响,及至三国刘表立荆州学宫,表彰古学,经师司马徽、宋衷,文士王粲、王凯等,皆活跃于其间,颇与“郑学”立异。梓潼人尹默、李仁因“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知其不博”,二人“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名徽)、宋仲子(名衷)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三国志·蜀书》卷一二),古文经学才正式传入蜀中,古文《易》亦然。
李仁有子李譔,也是大学者,《三国志》说他“具传其业,又从(尹)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加博”,后为蜀汉太子师傅。李譔“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是蜀中第一批古文经学著作。史称譔书“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是比较纯粹的古文经学。又说他“与王氏(肃)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三国志·蜀书》卷一二)。因为王肃也师宋衷,他们都是荆州学派的传人,都以贾、马古文学来反对融合今古的“郑学”,自然“意归多同”了。
汉代巴蜀易学家多隐居,盖得“遯世无闷”之旨。他们研究《易经》主于应用、卜筮,不在著述,更不在自炫。宋人青阳梦炎说:“蜀在天一方,士当盛时,安于山林,唯穷经是务,皓首不辍。故其著述往往深得经意,然不轻于自炫,而人莫之知。书之藏于家者,又以国难而毁,良可嘅叹!”所说虽然主要是南宋时的情况,但对于整个巴蜀历史来说也未尝不是如此。东汉时代,蜀《易》传授与博士《易》、古文《易》结合,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易学著作,史书也才有如前述景鸾之《易》说、冯颢之《易章句》、李譔之《古文易指归》等文献的著录。
自是之后,巴蜀易学代有传人,易学文献也时有其书。不过,巴蜀易学的隐者特征和应用目的,却始终传而未改。西晋末年,青城天师道首领范长生撰《周易注》10卷,文句与王弼本颇有不同;其书流行于南朝,由于其著作时不具真名,只署“蜀才”,“江南学士遂不知是何人”,王俭《四部目录》也不言其姓名,只题“王弼后人”。谢炅、夏侯该都号称“读数千卷书”,却怀疑是谯周所作。幸赖颜之推据陈寿《李蜀书》(一名《汉之书》)所载“姓范名长生,自称蜀才”,才将蜀才《周易注》的真实作者考证清楚(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崔鸿《十六国春秋》载:“城以西山,范长生岩居穴处,求遵养之志。(李)雄欲迎立为君而臣之,长生固辞。”李雄称帝,长生乃为其丞相,尊曰“范贤”。史称“长生善天文,有术数,民奉之如神”。其隐者身份和善筮特长,都与西汉严遵相同。
至于三国郪(三台)人王长文、北周蜀郡人卫元嵩,又远袭扬雄故智,依仿圣人以造经典。王长文系蜀汉犍为太守王颙之子,他仿《论语》作《无名子》12篇,又仿《周易》作《通玄经》4篇。其《通玄经》有《文言》、《卦象》,可用以卜筮,时人比之于《太玄》。卫元嵩“好言将来事”,“天和中(566—571),遂著诗预论周、隋废兴及皇家受命,并有征验”(《周书·艺术传》)。元嵩亦仿扬雄《太玄》之为,著《元苞》5卷,颇多奇字奥义,张行成谓其“取义于《归藏》”。蜀人仿经、善筮的特点,在王、卫二人身上仍然得到保留。蜀学的这一传统甚至还影响到外地入蜀的人士,如隋末河汾大儒王通,曾为蜀王侍读、蜀司户参军,后来也曾仿蜀儒故智,遍拟群经及《论语》,作有《续六经》及《中说》。
蜀才《易》今已亡佚,不过其遗说在陆德明《释文》和李鼎祚《周易集解》中多有引录,清人张澍、马国翰、孙堂、张惠言、黄奭并有辑本。王长文书则佚而无存,幸而卫氏书还原书俱在,尚可考见其内容和特点。此外,阮孝绪《七录》著录“齐安参军费元珪著《周易》九卷”,《隋志》有转录;《经义考》引陆德明说是“蜀人”。人亡书佚,不可得而详。
隋唐时期,巴蜀易学著作颇有存者,佚文遗说多有可考。隋何妥(郫县人)通易学,官国子博士、祭酒,撰《周易讲疏》13卷(已佚,马国翰有辑本1卷),借易象以阐易理。袁天罡(成都人)撰《易镜元要》1卷,赵蕤(盐亭人)撰《注关子明易传》1卷,又以数术讲明易道。至于阴颢、阴弘道父子以及李鼎祚诸人,又发凡起例,汇辑汉魏诸家注解以成新著。
阴氏书久佚,据《崇文总目》载:“《周易新论疏》十卷,唐阴弘道撰。弘道仕为临涣令。世其父颢之学,杂采子夏、孟喜等一十八家之说,参订其长,合七十二篇,于《易》家有助云。”其书“《中兴》、井氏皆无之,岂轶于兵间邪”?然而观其“杂采子夏、孟喜等一十八家之说”,则为集解性质的易学著作无疑。
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则是现存最早的集解型《易》书。原书17卷,今存10卷。共录子夏、孟喜以迄何妥、孔颖达35家《易》说,“刊辅嗣之野文,辅康成之逸象”,于王弼玄学《易》外,保存汉《易》资料犹夥。《隋志》共著录汉魏南北朝《易》类文献69部;南北宋之际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这一时期《易》书才有5部而已,其中关朗《易注》不载于《隋志》,《乾凿度》又是纬书,焦赣《易林》也属卜筮,《子夏传》或云“张弧伪人”。这样一来,《隋志》所录诸书,除王弼《注》之外,都已散佚了。所幸他们的遗说,得到李鼎祚《集解》的保存,诸家之学乃可考知一二,其保存文献的功劳是非常巨大的!蜀学的“杂采”与“共录”亦即包容之功,亦由此可见一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