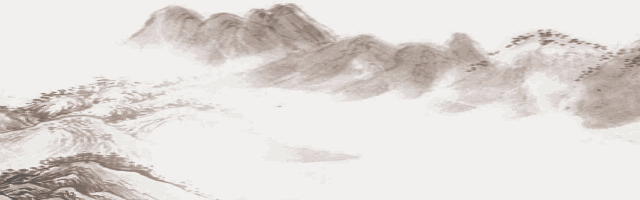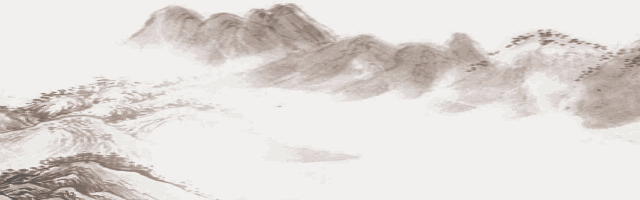
X
刘恒:文学一旦丧失攻击性,也将同时失去诱惑
简介:刘恒,生于1954年,作家、编剧,1986年发表小说《狗日的粮食》开始引人注目,一些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如《菊豆》《本命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编剧作品有《秋菊打官司》《集结号》《金陵十三钗》《窝头会馆》等,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金鹰奖”最佳编剧奖等多项国内外大奖。
他用毛笔写繁体字。这也罢了,还用毛笔写剧本;82场、100页,每次当他停顿,毛笔涮好一搁,欣赏码得整整齐齐的稿纸时,他心里舒服极了。
这就是眼下的刘恒。用毛笔写电影剧本,这在文坛、在电影界都是独一份儿。
他起初临贴,颜真卿、王羲之、苏东坡……不过瘾,索性用毛笔写剧本,鱼和熊掌兼得。写的时候字斟句酌,于内容是一种思考中的沉淀,于书法是一种用笔间的揣摩。做编剧,本来是自己喜欢的事情,用毛笔写,便又增加了新的意义和趣味,他觉得跟文字更亲近了,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被誉为“中国第一编剧”,谁不知道一集剧本的含金量有多少呢?和被粉丝与资金双重驱动下多数网络写手每日海量的灌水不同,刘恒似乎生活在他的“小圈子”里,这“圈子”不受任何利益的干扰和牵制,始终保持自己的节奏和习惯。这大概是他温和敦厚的表象下一种固执的坚持。
从1977年刘恒发表第一篇作品算起,文学之路一晃已过40年。如果说70年代的爱上文学还有炫技的想法,那么现在,他所做的一切,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一种淡定从容向古典的致敬与回归。
1969年,15岁的刘恒穿上了军装。稚气的脸上挂着单纯的笑,军装在他或许也尚显肥大,但他却已是有着7年俄语经验的“老兵”。在做侦听的业余,他狂热地迷上了鲁迅
读书报:您多次说过,自己的小说创作受到鲁迅的影响。喜欢鲁迅的什么?
刘恒:比较吸引我的是鲁迅的锋芒。他作为个体承受的苦难和不如意,向外界表达不满和愤怒的锋芒,符合青年人的状态。行动上不能反抗,至少要有语言上的反抗。
这里也有信息源比较 单一的原因。那时候没有其它的文学书,前苏联的作品也有,鲁迅的著作占有压倒性地位,杂文结集出版了很多单行本,我都买来看了。
读书报:但是今天对鲁迅的评价有所不同。
刘恒:现在从官方到民间对鲁迅的看法都有一些变化。任何轻视他的做法和观点都是目光短浅的。他们可能抓到了某一个鲁迅的弱点,或者他与现实的不和谐,就企图全盘否定,这是错误的。鲁迅的自我反省和对社会的丑陋面的批判,永远是有价值的。
周作人对哥哥有一个很“毒”的评价,他说鲁迅是“富有戏剧性”的。他们兄弟间了解应该很深。褒义地理解,可能是说鲁迅有浪漫主义的一面;贬义地理解,周作人可能扩大了自己的愤怒或者自己的正确。
从某种角度来说,任何文人在以自己的文字表达思想时,都带有戏剧性。严格地说文字是一种表演——所有的文字,包括给人写信时的文字。
读书报:您怎么理解周作人所说的“戏剧性”?
刘恒:不管别人说鲁迅什么,我还是非常崇拜他。鲁迅是伟大的前辈,他最大的价值,是对国民性弱点的痛恨和仇视。国民性的弱点现今仍在膨胀,这种痛恨也依然存在。比如马路上的不守规矩,没有羞耻感,狂妄,狭隘……我们每天都在接触这种国民的弱点——也包括自己。我更感到鲁迅的那种痛恨是一种很无奈的表现。现在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也依然无奈,只是表现的态度不同,有的人可能激烈一些,有的人缓和一些。我今年63岁,没有什么锋芒,一切都可以容忍了。
读书报:曾经有过的锋芒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恒:有一些是政治上的。我是从文革走过来的,回忆起来还是有一些愤怒,虽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对文革中发生的现象还是不能容忍。至于对现实的愤怒,不言自明。久而久之,这种锋芒慢慢淡化了。不知道是更客观了,还是更无奈了。我自己反思,我毕竟是这个社会变迁中的既得利益者——当然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社会发展中,获得了一些利益,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在利益获得一定满足的情况下,斗志有可能被瓦解。这是从贬义的角度说。从另一个角度说,年龄增长后心态自然变化,所谓五十而知天命,对很多事情不较真儿了。
所以我还是觉得,不论是好的作品还是好的思想,恐怕还是适度走极端好一些——不适度也没关系,超常地走极端或接近精神分裂,像卡夫卡、托尔斯泰。当然走极端和疯狂也都可以表演。有人认为托尔斯泰的出走是表演给世界看的,以离家出走的疯狂举动,向世界谢幕。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他只是追随本能罢了。
对电影的爱和梦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或因触动他的某个画面,或因一句记忆深刻的台词,总之,当他潇洒地转身投入编剧,未尝不是一种迟到的回归
读书报:1977年7月,您的短篇小说《小石磨》是发表在哪里?最初走上文学道路时,哪些人对您帮助较多?
刘恒:《小石磨》是纪念长征40周年时写的。写作完全是自我摸索,我把小说寄到《北京文学》杂志,第一次投稿就被采用了,责任编辑是郭德润。后来我被调到《北京文学》做实习编辑,以公代干,一直做下来,1985年上干部专修班,脱产上大学,算有了学历,之前填学历都写初中二年级,连初中都没毕业就当兵去了。
读书报:在《北京文学》时和哪些作家有过交往?
刘恒:那时挂在编辑部的有杨沫、浩然,但是接触不多。八十年代初,我去你的老乡韩石山家里约稿,他当时在汾西的一个公社,正聊着,公社广播让他开会。我去西安郊区找贾平凹约稿,去陈忠实当时所在的文化站组稿,我们一起蹲在马路边上吃过泡馍。那个时候国家刚刚苏醒过来,有着纯朴向上的氛围,大家都很友善,官员都很朴实,老的规矩都在起作用。
读书报:1986年,您的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发表后引起了较大反响。这部作品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出来的?在西学思潮涌入的80年代,您的创作受到影响了吗?
刘恒:读大学后有了完整的时间,《狗日的粮食》就是在那个时候写出来的。80年代改革开放后,很多经典名著翻译进来,都是很好的营养,只是我消化不良。有一段时间迷恋哲学,尼采、叔本华、萨特、克尔凯格尔等都接触过,多少都受了些影响。
人所需要的思想的武器并不多。要掌握很多武器具备强大的思想能力,几乎不可能。每个人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武器。有的时候没有效果,就是选择的武器不正确;有的人用简单的武器取得好的成果,是因为选择了正确的武器。
读书报:您早期的创作,如《心灵》、《小木头房子》、《热夜》、《爱情咏叹调》、《花与草》、《堂堂男子汉》等,多在探寻人生的意义。能谈谈这一时期自己的创作状态吗?
刘恒:早期的作品带有浪漫主义,是没有心机的。我还在生活的表层滑动,好像在湖的表面玩水;到《狗日的粮食》,开始接触到水里的污泥,不再象过去那么风平浪静。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苍河白日梦》。
到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一次转折。我觉得快被污泥浊水窒息了。对抗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参与治理污泥的工程,一是与污泥共存。世界到处都是细菌,有的细菌是致命的,消灭不了,就与之共存。实际上还是承认了心理上的坚持有强大的支撑作用。一个人只要心理强大,污泥不会把他怎么样。
阿Q在心理学上有特别积极的因素,大量心理学都与精神胜利法有关。宗教的信念就是最大的精神胜利法。教徒对世界的看法,尽管表述不一样,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
我看到了自己的软弱、无能和吝啬。不愿意为了某种信念献出既有的东西,不愿意付出,缩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这可能是出于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人最终还是围绕自己个体的生命生存,别人没有保护你的义务,也不可能依赖别人保护你的利益。
读书报:那么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是否找到了一些乐趣?
刘恒:是乏味。我对文学有点丧失信心,觉得没有大的趣味。这是出乎我意料的。也就是说,文学一旦丧失了攻击性,也失去了诱惑力。现在看来,文学对社会或对人类攻击时,应该能刺激起人的激情,为文学做出更大的思想投入和感情投入;而文学一旦成为平衡性的工具,本身的吸引力就丧失了。
读书报:90年代后期的《天知地知》,使您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自十几岁就读鲁迅,又获得这一奖项,是否有格外的感受?
刘恒:这部作品写得比较松弛,和我早期表达愤怒的作品有区别。
在如日中天的小说舞台上退出,是否也算是一种适度的“走极端”?现如今,“电影的生命被抽空”了,刘恒又该如何面对?
读书报:对文学丧失信心的同时,是否也感到一些悲哀?
刘恒:和我对文学最初的设想有很大差距。
读书报:对文学最初的设想是怎样的?
刘恒:有宗教感,有神圣感。从事文学的时候,有一种朝圣的感觉。当朝圣的目的丧失了,动力也弱化了。我那时候开玩笑说,是上帝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安排,让一小部分人继续走极端,继续冲锋陷阵,让另外一些人落伍,被淘汰。
我亲眼目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风云变化,太多的人从文学这趟火车上走下来。这种淘汰可能有肉体上的,也有精神上的。或者是厌倦了,或者丧失了能力。
读书报:走上编剧之路是出于什么机缘?
刘恒:1990年,《黑的雪》被改编成《本命年》,我朦朦胧胧的电影梦实现了,一发而不可收。
读书报:之后就完全脱离了小说创作吗?
刘恒:就是刹不住车了,完全是自然的选择。就像巴甫洛夫心理学,一旦尝到甜头就会继续下去。我在部队的时候,写小说之前就尝试过写小话剧和电影剧本,我对重现某种画面非常向往,看电影的某个镜头时,瞬间被打动。我就想某一天自己的创作也达到这种效果,也能感动别人。这是我最初对电影怀有的期待,可以更直接地和观众交流。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去年,电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读书报:这种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恒:资本介入。影视完全沦为资本的玩偶。电影的生命被抽空了。从精神角度看是不好的;从市场的角度,是顺势而为。现在整个世界被金融操盘手操纵,而且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读书报:您怎么看待这种“电影生命被抽空”的现象?
刘恒:我不确定是一种自然的生态变化,还是真的有某种智慧在操纵。90年代出生的孩子,从小看动画看卡通,他们的思维自然会受到影响。这些电脑游戏、卡通大部分是完全超越现实的。现在电影的题材,表达方式和这些小孩从小习惯的营养有关,直接对他们的胃口:夸张、无厘头,想入非非,充斥荧幕的多是思想含量非常小、但市场回报非常大的电影。这种局面的持续,下一步怎么样很难说。但是传统电影不可能回归了。
电影蓬勃发展,大量资本涌入,无数资本在挤一个梯子。每一个稍好点的项目,都有无数资本在等着,几十个亿的资金盘在找孵化的渠道。这种状况从去年开始,对创作者有极大的冲击,张艺谋他们这一代电影工作者都面临极大的挑战。
读书报:具体到您本人,所受到的冲击是怎样的?
刘恒:主要的“敌人”就是观众。无法找到征服他们的“武器”,真正征服他们的应该是年龄段相似的人,我们这一代人都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和我爱人去看电影,旁边的年轻人笑得喘不过气来,我们琢磨不透有什么可笑的——也许神经类型都不一样了吧。
读书报:您的创作受影响吗?
刘恒:我还是按部就班,尽量在题材里塞入我的私货、我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而且我想趁着体力还没有丧失之前,完全按自己的想法做几个电影。比较可喜的是,也有资本愿意支持。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任何事物都并非铁板一块。
不论“污泥浊水”到什么程度,荷花还是能长出来,并且出污泥而不染。实际上这都是生态的一部分,没有意义的电影就像没有营养的食品,尽管充斥市场,精华的东西也仍然有生存的空间,而且必然是生命力最强的,经典的作品必然会留存久远。精神产品有的时候不在于短时间内覆盖面多大,而在于时间上的延续。
读书报:您打算自己做电影,会在哪方面侧重?
刘恒:还是向传统的经典电影致敬,就是回归。现在的电影视听的效果占的比重太大,电影的技术手段越来越简单,内容反而轻了。我不知道不凭借花里胡哨的技术手段,内容是否还能够强大到对观众有征服的力量。我想试一试,也是对编剧生涯做个总结。
读书报:哪些作品会被纳入您的视野,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刘恒:有对我原来小说的改编,以及文学圈里几个边缘的作品。选择的标准,还是根据自己的好恶,比较能感动我的作品。
现在的项目规划堆积如山,好多事情想做,精力完全被占用了。我努力地把那些杂事推开或扔掉,腾出手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也有紧迫感,有大量的写作计划,但是没有时间完成。做与不做,可能最终也将是上帝之手安排。我最近做了两件事,写了82场的电影梗概,还写了一个项目策划案,专业评价非常高。我觉得能力在衰退,但是凭着经验出手还能放出光来,这让我感到高兴。
张艺谋说,“刘恒是唯一一个只要创作就能成功的编剧”。的确,但凡他出手,几乎无往不胜
读书报:虽然有些人看轻编剧这一行当,但实际上写好剧本很难。圈里好多作家尝试写电影剧本,并没有成功。您被称为“中国第一编剧”,对您来说还存在难度吗?
刘恒:写小说,文字可以控制。你设计了非常独特的惊人的情节,能达到什么效果,一切在小说家掌握之中。编剧中间隔着很多层,导演和演员都有自己的理解,他们的理解有可能和你的表达相差很远。导演如何能最大限度地和你同步,不产生歧义,这个境界很难。双方能达到默契的时候是最令人高兴的。好多时候,碰到思路不一样的导演,也不免失望。
读书报:和张艺谋合作《菊豆》《秋菊打官司》《金陵十三钗》,和冯小刚合作《集结号》。您对这些导演有怎样的印象?或者概括一下中国最优秀的导演有何共同的特质?
刘恒:他们都是业内的精英,都对事业痴迷,比一般同行更能整体控制自己的创作对象。这一行没有任何混水摸鱼的余地,有强大的才华支撑才能走到这一步。天才和能力超常的人确实是少数。
读书报:《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一部笑里带泪的作品。您的作品特别接地气,语言是不着痕迹的炉火纯青。能谈谈您对语言风格的追求吗?
刘恒:我的语言风格受鲁迅影响最大。鲁迅和周作人都爱用相同的文言虚字,我到现在写文章,还喜欢用虚字。这个时候,鲁迅的那个味儿就出来了。
有一段时间的创作,文字是不由自主流出来的。这是写作微妙的地方。老了之后反而搜肠刮肚。像《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逍遥颂》《虚证》,都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写出的。写《虚证》时,我从早八点写到晚八点,像开火车一样能听到文字的声音,词句奔涌而来。那种创作状态不可复制。
有好多作家,曾经非常精彩,一下子大转折,文字突然没有灵气。大概就是所谓江郎才尽。
最典型的是沈从文。他在40岁之前,尤其是写湘西的文字,文笔在民国数一数二。在大学当教授之后,他还在写小说,但是文字没有感觉了。这种状况,在现在很多作家身上存在。这也跟生理上的衰老有关。
读书报:您的小说,特别善于抓住人物的内心世界,善于处理矛盾冲突,总是一波三折,扣人心弦。
刘恒:其实我的情节感较弱,编织复杂的情节能力不强。这和我对情节研究不多有关。无论写小说还是写剧本,我做得比较多的是人物分析,写的时候也是跟着人物走,人物始终处于第一位。这和好莱坞的电影相违背,他们追求人物为情节服务。
读书报:《窝头会馆》是您第一次创作话剧,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您在节目单前面还专门说了一段话,想把观众引到您希望表达的方面,但大量观众并不在意。对于这种误读,您是否也很苦恼?
刘恒:作品呈现的东西和观众的理解有距离。还是得跟观众进行双方“博弈”,也是一种文字上的“诱骗”。不把话说明,观众无法理解潜台词,这就逼着你把潜台词说出来。
读书报: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觉得小说更合自己的心意?
刘恒:写小说,观众的反馈就更少。任何作品,包括小说、电影,所有接受评价的作品,权威的评价非常重要。诺奖评选委员会几个评委的评价,相当于文学皇帝所发出的声音,有强大的影响;亿万读者的评价是分散的。茅盾文学奖的投票,也决定和影响着俗众。
读书报:在您的创作历程中,有没有感受到周围评价对自己的影响?
刘恒:用现代所谓传播学和信息学的理论,我应该主动去影响他们。比如应该有一些策略上的考虑:故意表演给你看,直接把对胃口的东西给你,以此扩大我的声音。但这些在我写作的那个时代几乎是零。现在青年人要想扩大影响力可能有这一层面的考虑。对于洁身自好和孤僻的作家而言,不屑于也无力做这些事情。
读书报:无论像《张思德》这样的“主旋律”或非主流的电影,都是一片叫好。做编剧多年,能谈谈您的创作体会吗?
刘恒:用我生命的一部分做这个事,我特别珍惜。不管别人怎么评价是否值得,是否高贵,是否卑贱,我觉得这件事有意义,去做了,就好好做。最低限度是希望和我合作的人认可,最大的限度还是希望在知音那里获得反响。这就很满足了。再有,我也不是白干。
读书报:您在大家心目中是一位有才华的小说家。当这才华用于编剧放弃小说,很多人会觉得惋惜。
刘恒:坦率地说,你要是可惜自己的人生,是可惜不过来的。有很多生命的轨道和自己设想的有距离。你选择的是你喜欢的事情,你确实取得了巨大的利益,给你带来平静的生活状态,这挺好,是上帝的恩赐。上帝没有恩赐我在小说之路上继续驰骋,也给别人的驰骋让出了道路。
读书报:越来越多的影视剧改编自网络小说。您关注网络小说吗?
刘恒:我不太关注,基本没看过。
读书报:很多网络写手一夜成名,当然也许我们只看到表面的鲜花和掌声。没有一个写作者的成功易如反掌。但是,和您青年时期写作的情况相比,也有很大区别了。
刘恒:时势造英雄。资本膨胀,盯住了网络传播的巨大能量。IP关注的人多,想当然地以为含金量非常高。实际上有的含金量很低,像开采矿石一样,大量的矿石就是石头,如何冶炼成贵金属并制造成工艺品,需要大量的智慧投入,掌握这种智慧的人是有限的,有才华的操作者非常少,所以大量项目死掉,这也是风险投资的风险所在。随着这一过程的延伸,资本也许会慢慢清醒一些。
他也用微信,只是为了便于和家人及朋友联络,在朋友圈也只是潜水。他甚至故意删掉手机里有趣的东西,以防浪费太多时间。即便如此,也不得不承认,被网络耗费的时间算不得少
读书报:一位作家朋友对我说,过去他每天睡觉前是固定的阅读时间,现在改成看微信了。“太可怕了,连写作的人都不看书了,这书指着谁看?”他的这种忧虑,算是杞人忧天吗?
刘恒:这是很实际的感受。网络提供了生动性和不可测性,大量信息的生动性超越人的控制力,很容易让人上瘾。我有时候会故意把手机里有趣的软件删掉。人不需要那么多信息。开发商利用了人的本能——这也是淘汰机制之一。用这种方式,把你的精力吸走。只有不被干扰的人,还继续留在思想的火车上。
有的时候,读书也是一种淘汰机制。有的人成为书籍的容器,可以把知识有条理地分门别类,但是他自己的创作力是停顿的、萎缩的,丧失了行动的能力,这也是巨大的淘汰机制。人很容易落入种种不同的陷阱。
读书报:您怎么看网络时代如此庞杂的信息?
刘恒:网络是双刃剑。利的一面是极大地发挥每个人的潜能和可能性,表达自由度比过去高得多,视野空前开阔,可调配的知识资源空前庞大。如果真有才华,可以不受阻碍地尽情展示;弊的一面是,人也更容易被网络背后的力量操纵——网络上的精英除外。大部分人是网络的炮灰,被廉价的知识层层覆盖,像陷入污泥浊水,最后只有少数精英脱颖而出,利用网络夺取至高地位并获取自己的利益。
绝大多数是芸芸众生,他们的个性在网络中被淹没。比如游戏者就成为电子游戏的零件,自己从网络获取很少,反而将自己掌握的钱财和生命一点点献给别人。这也是重大的淘汰机制。所以说,网络留给精英的余地非常大,聪明的孩子会捷足先登。
原文出处:http://www.chinawriter.com.cn/talk/2016/2016-07-04/2755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