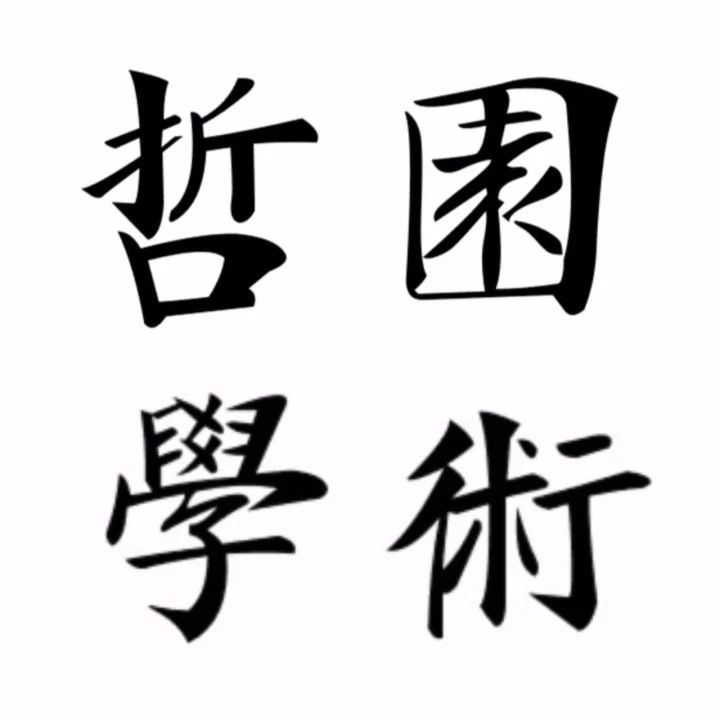克里普克的专名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个体”
钟岩
转自: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如涉版权请加编辑微信iwish89联系
哲学园鸣谢
作者简介:钟岩,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克里普克的专名理论在根本上是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相一致的。通过专名,我们可以直接确认个体实体本身,而摆脱对实体偶性的依赖,由此真正确立本质个体的实体——主体地位。本质个体的实体——主体地位是亚里士多德实体理论的核心思想,本文将通过对克里普克专名理论的阐释来解读亚里士多德的个体实体理论。
关键词:专名;个体;实体;同一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区分了实体和属性,实体是存在的主体,属性依附于主体而不能单独存在。他认为个体实体是第一实体,是终极主词和终极主体(聂敏里 2016)。本文将要探讨的是,我们能否脱离属性来谈论实体?如果可以,那么,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我们将借助克里普克的专名理论来探讨这个问题。
克里普克的专名理论原是为了解决语词的指称问题,针对弗雷格、罗素等人的摹状词理论提出的。对指称的不同理解,会导致我们对实体或存在产生不同的认识。罗素利用摹状词理论解决了“迈农悖论”,即“不存在者存在”的问题,但他在取消“不存在者”实体地位的同时,也取消了作为实体的“存在者”的主体地位,属性成了主体。克里普克则利用专名理论,重新确立起了实体的主体地位,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是相符合的,也为我们理解“实体”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
具体到专名问题,克里普克认为专名与其他词项不同,专名只具有指称作用,而不具有含义,它作为严格指示词,唯一且固定地指称着一个个体。[1]显然,克里普克强调专名的“无含义”,是要排除由于专名作为一个一般词项而可能造成的误解,同时将它与摹状词严格区分开来,从而确立起专名的特殊地位,即只作为主词出现,同时不能被转换成摹状词,从而不同于摹状词的间接指称,而是直接指称着某个对象。
此外,克里普克的专名理论还有更进一步的理论内涵,这就是,专名不仅仅是指称某个个体,它更是在语句中重现了这个个体,而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实体”。专名在语句中与现实存在的个体地位是相同的。因为,在直陈命题中,我们不是将专名作为语词本身来描述,而是在描述专名所指称的对象。而这一点在摹状词理论中是并不清楚的。此外,专名直接等同于个体的说法,也鲜明地表达了专名与摹状词之间的根本不同。摹状词是根据属性从一堆对象中挑选区分出特定的个体,因而,如果从摹状词理论出发,就不可能存在作为主体的个体,相反,属性才是第一性的,个体是依赖属性才被确立出来的。罗素等摹状词理论的支持者就认为专名不是其他,而是伪装的摹状词。
在后文中,我们将讨论到,确立起专名的特殊地位,也就能够确立起专名、个体同主体这三者之间的等价关系。从根本上说,专名指称的是个体的形式。而以专名理论为基础的历史因果命名理论,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克里普克对亚里士多德实体理论的全新阐释。
一 摹状词理论的缺陷
所谓摹状词,其实就是在直陈命题中处在谓词位置上的那些语词,它表达的是实体的属性。就常识而言,属性而非个体是首先被我们所接触和认识的,我们根据属性来认识个体。摹状词理论在这一点上是符合常识的。
摹状词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以一阶逻辑的方式打破了传统命题的主谓结构,从而取消了命题的主词。“迈农悖论”正是依赖主谓结构而造成的。例如,命题“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子”(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 is bald),由于当今法国国王并不存在,但它作为主词为我们所讨论,却又暗示了当今法国国王在某种意义上是存在的,从而这个命题便陷入悖论。罗素将它处理为∃x (Fx ∧ ∀y (Fy → y=x) ∧ Gx),其中Fx表示x是当今法国国王,Gx表示x是秃子,中间的∀y (Fy →y=x)表示“the”这个定冠词,即表达了唯一性。因此,这个命题的含义是:存在某物,它是且仅有它是当今法国国王,并且它是秃子。这样,整个命题就不再是一个悖论。由于不存在某个x是当今法国国王,整个命题为假。就含义来看,罗素的命题与原命题是一致的,但从结构上则可以看出,系词“是”被取消了,传统的主谓结构变成了“”的形式(真值函项),原来的主词被一个具有某属性的、不确定的x取代了。由于x不能起到任何的指称作用,它是一个有待填补的空位,这样,一阶逻辑的命题实际上表达的是具有某属性的那些东西也具有另一些属性,因此主词在这里是空缺的,由主词而得来的实体概念也就不重要了,属性之间的联系才是主要的。所以摹状词理论会认为,属性之外没有实体,一切都是属性。
这就导致两个问题:其一,由于摹状词理论不重视实体范畴,认为一切都可以通过摹状词亦即属性来表达,因此,摹状词理论也就自然地将专名处理为是伪装的摹状词。专名乃至专名所指称的个体在摹状词理论中都被简单化地处理了,使得它们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存在论上的价值都被埋没了;其二,由于摹状词实质上都是对偶性的描述,因而,当专名被作为伪装的摹状词来处理,摹状词理论必然就是反本质主义的,这使得它在描述个体时存在着困难。
摹状词理论通常把例如专名“亚里士多德”,或者处理为“叫亚里士多德的”,或者处理为“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等亚里士多德所含有的那些属性的集合。由于这种处理方式把专名也作为摹状词来处理,不承认专名能够独自地具有指称作用,因此它也就取消了专名在逻辑上的特殊地位。
为什么摹状词理论要拒绝承认专名在逻辑上的特殊地位呢?简单地来说,有两点原因。首先,这是出于理论的简洁性考虑。摹状词理论在一阶逻辑中将所有的语词都处理成真值函项的形式,由于专名所起到的指称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摹状词所取代,所以,这样的转换能够保持前后两个命题的等价,无须为专名单独设立某些特殊的规则。其次,这是由于摹状词理论无法接受语句本身可理解,但语句中的某些语词却可以无含义的情形。摹状词理论的支持者们把摹状词、属性和含义这三者看作是同一个东西的三个方面,摹状词强调的是这个东西作为语言的层面,属性是它在现实中的对应,而含义则是强调它被使用并可以被人所理解的方面。所谓的理解,就是将自然语言中的语词处理成为一阶逻辑中的真值函项,而将整个语句处理成一阶逻辑的命题。在他们看来,所有语词都具有含义,因此,所有语词都可以、也应该按照摹状词的方式来处理。这与专名只有指称而无含义的性质相矛盾,专名能够被理解不是在于它的“含义”,而是在于它能够直接指称某个对象。承认专名的特殊地位,这就会同摹状词理论对语词含义的理解、乃至摹状词理论对语言的理解发生冲突。克里普克则正是因为反对专名具有含义,从而揭示了专名、个体和实体之间的联系,确立起了专名的主体地位。
此外,个体的概念与摹状词理论格格不入。首先,属性总是在流变之中的,婴儿时期的苏格拉底和老年时期的苏格拉底差异巨大,如果运用摹状词,几乎不可能把两者看成是同一的。何况摹状词理论在同一性问题上都遵从莱布尼茨的“等同物的不可分辨性原理”,两个东西只有在所有属性都相同的情况下才能被认作是同一的。流变的、偶然的属性如果指向的是同一个东西,这就意味着属性是可有可无的,不影响实体本身。撇开历时的属性的变化,我们也应该能够想象各种可能的属性的变化,例如,没有收柏拉图为学生的苏格拉底,但是,这并不妨碍苏格拉底是苏格拉底。由于摹状词理论的指称是一种间接指称,是在某一论域中去挑选某个对象(存在某物,它具有A、B、C等属性),因此,如果我们要固定地指称某个对象,我们就必须选择那些不会改变的属性,否则,由于存在者的属性的变化,就会要么不存在某个对象满足原命题,要么有其他的对象符合了原命题的要求而被摹状词理论错误地指称出来。这样,结论很显然,不论是历时的还是可能世界的属性的变化,都会使得摹状词理论失效,我们将由于苏格拉底在某种可能情况下没有收柏拉图为学生而导致“柏拉图的老师”的指称发生变化。
其次,即使不考虑属性的流变,摹状词对个体的指称也存在一定困难。这是由于摹状词对个体的指称是以挑选的方式确立的。我们首先有一个论域,即一些个体的集合,然后我们凭借命题给出的那些属性来对论域中的个体进行检测,含有那些属性的个体就是摹状词所指称的。所以,当论域不同时,摹状词所指称的对象也可能不同,或者数量上有差异。例如,对于“最伟大的哲学家”这一摹状词,如果我们的论域是泰勒斯之前的那些人,那么这个摹状词将不指称任何人,而如果我们的论域是所有人的话,那么我们将指称包含亚里士多德在内的许多哲学家。摹状词的指称数量可以为零,也可以为多。所以,实体“在数目上为一”的这个要求,对于摹状词的指称来说并不是那么特殊,同时也并不容易,这反而是一种巧合,它需要恰当的论域以及足够多的摹状词相互配合才能(而非必然)恰好地只指称一个对象。这个问题在亚里士多德“属加种差”的定义法中也存在,此外“属加种差”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种差”限制在“种”上,种仍然是一个集合,仍然是类上的定义,理论上是不可能指称到“个体”的。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借助个体本质这一概念,而由于摹状词描述的都是偶性,因而摹状词理论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二 专名的主体地位
摹状词理论拒绝承认专名的特殊地位,同时不能处理“个体”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克里普克的专名理论所要解决的。
克里普克反对专名具有含义,从根本上否定了专名是伪装的摹状词这个理论。专名不具有含义,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体不会出现在谓词位置上是同义的。专名不描述任何东西,它只作为个体的指称,在语句中担当同个体一样的功能。
需要注意的是,就专名作为一个词项而言,它可以具有自己的含义。比如“北京”这个专名,我们仅分析其字面含义时,可以得到“北方的首都”这样的意思,然而在我们使用“北京”这个专名时,并没有涉及这个含义,而是在对北京这个个体加以指称。克里普克认为,我们在赋予个体以专名时,会有一个“命名仪式”,在命名过程中完全可以采用某个摹状词作为名称,而一旦它作为专名出现在语句中,我们便不再能够将它作为摹状词来使用。[2]所以在克里普克这里,专名是不同于摹状词亦即属性的。不仅如此,专名也不需要借助任何摹状词就直接指称个体。“中国的首都”作为一个摹状词,它意指我们从中国的城市中挑出是首都的那个,或是从世界的各首都中挑出属于中国的那个,然而“北京”就是北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称摹状词的指称方式是挑选,而专名是直接指称。摹状词理论混淆了这个区别,将专名等同于摹状词,从而错误地取消了专名的特殊性以及个体的主体地位。
否认专名的特殊性会导致误认为专名是有含义的。摹状词理论支持者无法区分“北京是北方的首都”和“北京是中国的首都”这两个命题的差别。前者中“北方的首都”是“北京”作为一个普通词项所含的意思,而后者中“北京”作为一个专名,仅表示北京,中国的首都乃是北京的一个属性,而非“北京”这个词项的内涵。这是十分明白的,但摹状词理论支持者因为看不出两句话中“北京”的区别,所以把“中国的首都”也当作是“北京”的含义。类似地,凡是原本属于北京的属性,在他们看来,都成为了“北京”的含义,所以“北京”这个专名,等同于一簇描述北京的摹状词。这是错误的。假如所有的属性都作为含义已经被包含在专名之中的话,那么所有的命题都是分析命题了。而如果把“北京”这个专名理解为是“叫北京的”,则又会出现循环定义的问题。所以,实际上,这两种处理都是存在问题的。我们不应该把专名处理为具有含义的摹状词。
专名不是普通词项。专名不仅仅标示个体,在语句中的地位也是等同于个体本身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北京是中国的首都”这个命题的意义。它不是在说“北京”具有“中国的首都”这个含义,而是北京具有“中国的首都”这个属性。专名是没有含义的,“北京”这个词项更不可能是中国的首都,唯有将“北京”和北京这个现实的个体等同起来,这个命题才是有意义的。所以,专名和它所指称的个体是直接等同的,不需要借助任何摹状词,是独立自在的。而个体总是作为属性的承载者,本身是绝不与属性等同的,并且能够在脱离属性的情况下被指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必须承认,在属性之外,还存在着实体的范畴,它作为属性的载体,处在主体的地位。如果我们说摹状词和属性是同一的,那么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专名和个体(实体)是同一的。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一实体正是指这些专名。专名不会出现在谓词位置上,是由其主体地位决定的。既然我们已经否定了摹状词理论将实体看作依赖属性而确立的观点,而确立起了实体独立自在的地位,专名就只能是被描述的对象,而不能用于描述他者,而谓词恰是用来描述他者。当然,在一种情况下我们不区分主谓词,这时,专名被允许出现在系词之后,但这是由于此时系词“是”表达的是主谓词之间的一种等同关系,系词两边所指是同一实体,所以没有主次。例如,我们也承认“中国的首都是北京”为合法的命题,因为“是”的两边指的是同一个体。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称“中国的首都”和“北京”等价,是在它们指称了相同个体的意义上来说的,而非就这两个词的地位和性质而言。“中国的首都”作为摹状词,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可以指称南京、西安或是别的一些地方,而“北京”作为专名则总是指称北京。因此,如果我们不加任何限制,说两者完全等价,那么,根据“等同物的不可分辨性原理”,我们就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将“北京”和“中国的首都”相替换,因为它们的一切性质(作为语词,这里的性质则指它们的用法、含义等)都相同,我们会得出“西安是北京”这种错误的命题。所以,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专名同摹状词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它们不能实现完全的等价。同属于摹状词的,比如“红”和“赤”之间,作为含义相等的两个摹状词,可以相互替换;或者同属专名的,比如“启明星”和“长庚星”,它们指称相同的个体,也可以相互替换。因而尽管“中国的首都是北京”与“北京是中国的首都”都是合法的命题,由于它们不是由“北京”和“中国的首都”相替换而得来,所以两者不是等价的(而在摹状词理论下,两者则是完全相同的)。前者强调的是摹状词挑选出来的唯一个体是这一个体,而后者则是一个更为标准的命题,它表达了这一个体是具有某一属性(的唯一个体)。
正是有了专名和摹状词的严格区分,我们才能够在摹状词这种挑选的指称方式之外,构建起一种直接的指称方式。专名在语句中的地位等同于个体,摹状词在语句中描述的是个体而非充当专名的语词。专名不具有含义,是绝对的主词,不出现、也不能出现在谓词位置上描述他者,因而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一实体。因此,专名等同于个体,等同于第一实体,“专名”“个体”与“第一实体”是总被描述的、作为根本的主体的三种不同表述。
既然我们已经通过对专名的分析在逻辑上确立起作为主体的实体,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专名在现实中的对应——实体——是否在现实中也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呢?这个问题同时也是实体范畴之必要性的问题。我们假设实体不是主体,那么,那些实体之外的属性就应该是主体,从而,如摹状词理论所认同的,属性是根本的,实体是诸属性的集合。这样一来,实体就是一个多余的概念,是摹状词的缩写。然而,我们发现,幼年的苏格拉底和老年的苏格拉底绝不是同一个集合,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说两个集合都是苏格拉底这个实体呢?所以,如果实体不是主体,那么,实体范畴由于不能保持其同一性,就一定会作为一个无用的概念而被我们抛弃掉。但是,如果没有实体范畴,不同属性所指的同一性也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没有苏格拉底,我们如何能够知道幼年的苏格拉底和老年的苏格拉底所指的是同一个人呢?所以,只有实体作为主体而存在,而摹状词作为属性是对实体范畴的谓述,摹状词与摹状词之间的同一性才是有根本保障的。
三 专名指称的是个体本质
上文已经说明了,个体作为主体不是属性的集合。因此专名的指称不能落在具体的属性集合物上。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体由形式和质料所组成,质料作为实体的可感部分,是朝着其形式不断演变的潜能,而形式作为实体的目的和现实性,从一开始就是不动者。因此,就实体是一个具体的质形合成物而言,专名的指称就不能落在变动的质料上,只能落在不动的形式上。
亚里士多德认为“本质特性被设定为与其他所有事物相关且又使一事物区别于其他所有事物的东西”(《论题篇》128b33-34)。个体形式与质料共同构成了一个具体的可感实体,两者不能相互分离,但形式不参与到质料本身的变化中去,而是在个体质料的变化过程中始终保持同一,从而能够承担起本质规定性的要求——将这个具体的可感实体同其他事物区别开来。克里普克与亚里士多德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都认同个体形式其实就是个体本质。克里普克的历史因果命名理论可以算得上是对亚里士多德形式-质料说的一种新的阐释。
克里普克认为质料变动演进的过程构成了一个历史因果链条。一个事物在从它产生之初直到它消亡的整个过程中,其属性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现实的历史因果链条就是对这些变化的属性的忠实记录,链条的每一环在逻辑上是一个直陈命题,表达该个体在某时刻具有某属性。不仅如此,历史因果链条也包含该事物可能具有的属性,它由对描述现实的命题的否定所表达。例如,“奥巴马是美国总统”与“奥巴马不是美国总统”,都可以被包含在奥巴马的历史因果链条中,因为两者对他而言都是可能的。历史因果链条会在这样两个命题上分叉,一端继续描述着现实世界,而另一端则展开了一个新的可能世界。依此类推,一个完整的历史因果链条将会是一个庞大的树状结构,它将涉及个体的所有可能性。而这个历史因果链条的起点恰好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作为目的和现实的个体形式[3]。
在这里详细说明一下克里普克的历史因果命名理论是有必要的。克里普克在其中提到的历史因果链条很好地描述和处理了事物随着时间甚至可能世界变化而发生的变化,因而借助历史因果链条,我们将能够对专名的指称,以及在个体变化中始终保持不变的个体本质有更加深入地刻画和理解。
(一)历史因果命名理论
克里普克的历史因果命名理论建立在他对可能世界的理解之上。不同于莱布尼茨和刘易斯认为的可能世界也是实存的,可能世界在克里普克这里只是理论预设,因此他不必去设想一整个可能世界[4],他在《命名与必然性》中说:“我反对对这个概念(可能世界)的误用,即把可能的世界看成遥远的行星,看成另一个空间里存在的、与我们周围的景物相似的东西……我倒愿意推荐他使用‘世界的可能状态(或历史)’,或‘非真实的情况’这类说法。”(克里普克 1988:15)如果说“奥巴马是美国总统”描述了现实世界中的一个事态,那么“奥巴马不是美国总统”可以是一个可能世界中的事态,这个命题就揭示了一个可能世界,尽管只是一部分。因此,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只是一种理论预设,用以说明可能性问题。
历史因果链条的建立有赖于专名理论。专名理论揭示了个体或实体的独立自在,个体不会随属性的变化而改变,因此即使属性改变,我们依旧能够把那些属性归属到同一个体上去,形成相互连结的链式结构。现实中历史演变过程造成的质料变化就是一条历史因果链条。链条上任何一点都可以沿着这个链条回溯直到起点。回溯的过程中的任意一点都是该个体的属性集合,历史因果链条在这个意义上保持其描述对象的同一性。
关于历史因果链条的起点,克里普克主张一个个体的起点就是它产生的那一刻,比如他主张人的起点就是受精卵(他坚持本质应当落实在具体的物质上,将这个受精卵当作这个人的本质)。我认为这个起点只要追溯到命名活动上就足够了,因为命名活动是我们在语言层面上可追溯的最初的起点,命名活动产生专名,从此开始,我们能够在逻辑上、语言上来把握个体的同一,同时,这更符合历史因果链条关于对同一性描述的内涵。
历史因果链条的建立过程是:一个专名起源于一个“命名仪式”,这是最初将某一专名和个体绑定在一起的过程;其后,人们在同等的意义上使用这个专名,将其保持或传播。同等意义指的是,首先,不论个体处在何种状态,专名和它是绑定在一起的;其次,当人们误用了专名,即,没有把专名和它的所指相统一时,我们就不认为他正确地使用了这一专名。这就是说,无论奥巴马是否是美国总统,我们都用“奥巴马”指称他,但如果我把我家的宠物称作“奥巴马”,那么我实际上使用了另一个因果链条,这个同名仅是语词上相同,就其作为专名而言是区别的,因此不会产生混淆。
现实的历史链条的特殊性在于它是被实现了的,众多命题都是对现实世界的描述。在描述现实事态的命题基础上加以变化,我们就能够得到对可能世界一些事态的描述。这里的可能性是指逻辑上的可能。所以,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可能的,而非必然的,上海而非北京可能在某个可能世界中成为中国的首都,但这并不妨碍北京仍然是北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的首都”是北京的偶然属性。没有成为首都的北京和成为了首都的北京分属两个不同的可能世界,但只在这一点上不同,在其历史链条的大部分上还是重合的,能够回溯到同一起点,我们因此可以肯定这两者是同一的。即使更为复杂的情况也能够通过类似的方式进行回溯。所以,同一专名所指称的个体,一定能够通过因果链条回溯到同一起点,这一点是必然的,我们根据这一点确认一个个体。可以说,克里普克的历史因果命名理论做到了刨除质料因素,直接地确立起了个体。同时,在链条的任何一个节点上,个体又紧密地和质料结合在一起,表现出种种具体的属性。
此外,我们还可以想象起点不同的两条因果链条重合的情况,即它们在之后的一切的属性上相同,其实也就是“冒名顶替”。我们可以根据命名理论来区别两者,但这与摹状词理论根据“同一性不可分辨”原则来区分是不同的。在摹状词理论中,“命名仪式”不会同其他属性有任何不同,当没当上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在摹状词理论看来也是非同一的。因此,因果链条的起点在这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相比链条上的其他属性来说是特殊的。
(二)个体本质
克里普克的历史因果命名理论向我们揭示了两点。首先,在仅考虑逻辑规律的前提下,可能世界的数量是无穷的,这意味着任何个体都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以主谓结构命题对个体的描述都是对其偶然属性的表达,所以,我们必须放弃从个体的现实属性中挑选本质属性这条路。其次,我们确实能够在排除众多偶然命题的同时找到一个必然命题,即同一个体必能追溯到同一起点。根据这一必然性,我们能够确认出个体。个体本质的揭示必须走这条路。
根据克里普克的历史因果命名理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历史因果链条的起点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我的理解中,这个起点被称作“命名仪式”更为合适。“本质特性被设定为与其他所有事物相关且又使一事物区别于其他所有事物的东西”(《论题篇》128b30-34),“命名仪式”正好符合这一条件,同一个体的所有因果链条都以“命名仪式”作为共同起点,这同时表明“命名仪式”是一个个体必然具有的条件。此外,起始于不同“命名仪式”的个体,我们也总能够将它们区分开来。所以“命名仪式”符合本质的定义,可以充当个体的本质。
“命名仪式”确立起了专名和个体之间最初的同一关系,这个过程通常是以实指的方式来实现,即实际地指着“这一个”个体,赋予其专名。实指也并不涉及个体属性,它指称的就是个体本身(实体),这与专名的指称是一样的。
以命名仪式为起点(或叫根节点),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树状的因果链条结构。简单起见,我们可以考虑二叉树的结构,每个节点相当于是一个命题,按维特根斯坦的说法,这样的一个命题就是一种事态。由一个节点p出发可以进而分叉达到q和非q两个节点。那么,假如q表示现实发生的一个事态的话,非q则是一种未发生、但可能发生的事态,代表了一种可能性。每个节点都可以按照这样的规律分出两支,从而实现出整个的树状结构。理论上这个树状结构是无穷的,由于每个事态可以反映个体的某些属性,所以这样的树状结构必然穷尽了个体所有可能的属性。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树状结构的根节点,也就是“命名仪式”是特殊的,它拥有命题的形式,即它指定了某个专名是某个个体,但它不是真正的命题,因为它不具备真假,尽管命名仪式作为一个事件而言是真实发生了的,但它本身是正在进行的一个判断,我们尚不能赋予其真值。而在命名仪式之后,所有的节点命题才能够承担起真值。
从根节点出发,沿着分叉经历树状结构,就能够得到一根因果链条,也即该个体一整套可能的演历过程,拥有唯一根节点的树状结构能够帮助我们清晰地把握到,不论因果链条的走向如何,这样一个个体始终还是这个个体,本质上没有发生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根节点的“命名仪式”就是个体的本质。
个体形式实际上就是这个树状结构的根节点。历史因果链条构成的树状结构,穷尽个体所有的可能属性,表明个体不可能超出该结构的限制。因其质料性部分而被我们所认知的个体事物,不过是被现实质料所实现了的、处在现实这个可能世界中的因果链条,它是树状结构的一个分支。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是完全契合的。
个体形式作为本质就是“命名仪式”。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相比于具有必然性的本质,“命名仪式”这个事件本身并不天然地具有必然性,我们在何时命名,采取什么词语作为专名,都是偶然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将“命名仪式”的事件属性和它具备的命题形式区分开来。我们真正要标示的是个体形式,因而个体形式是与这样一个命题的形式等同的。
克里普克其实不是从命名仪式出发的,他采取“受精卵”这样的最原初的物质起点作为本质。但就标示个体形式这一点而言,命名仪式和受精卵的作用是一样的。我认为,“命名仪式”的优点在于它是专名的起点,方便于我们对专名的使用,也方便于我们对必然性的讨论。克里普克关于“启明星必然是长庚星”的命题就是一个典范。如果不把“命名仪式”作为本质,那么“长庚星”可能是对金星以外的行星的命名,从而该命题为假。但是把“命名仪式”作为本质时,那些不把金星命名为“长庚星”的因果链条都会被刨除,因为它要么误用了“长庚星”这个专名,不是在与“命名仪式”时相同的意义上在使用这个专名,要么我们根本没有“长庚星”这个专名,我们也不会有“启明星是长庚星”这个命题。所以“命名仪式”作为本质,是我们因为专名而选定的。
由此,我们可以说,专名指称的是作为个体本质的个体形式,专名唯一标示了这个树状结构所能展现的个体,这一指称的实现正是有赖于作为历史因果链条构成的树状结构的根节点的“命名仪式”。
四 结论
实体作为存在者,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我们探讨实体问题,是借此来探究存在本身。以上三部分共同说明了一个问题——个体(实体)是如何被确立起来的。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克里普克和亚里士多德是一致的,个体是可以脱离属性、独立自在的、最根本的主体。尽管在论证方式上颇有不同,克里普克始终没有偏离亚里士多德实体思想的核心。所以,我们可以说,克里普克的专名理论是对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的一个现代深化。
根据克里普克的理论,我们可以认识到,个体形式是呈树状结构的历史因果链条,它涵盖了个体的完满的可能性,是个体的本质。专名指称的就是个体形式。而专名指称个体形式是通过“命名仪式”实现的。专名与个体的同一关系就是在这种指称中建立起来的。
专名在众可能世界中固定地指称同一个体,真正揭示了个体作为核心存在的本质。个体不是个体事物,而就是个体形式。属性都是作为偶性依附于实体的,它们是实体的各种现实的或可能的属性。第二实体之所以不是最根本的实体,在于我们不是在建立第二实体之后而以偶性去区分个体,而是首先建立起了个体的根本地位,再由个体去组成第二实体。最后,在对个体的确立的同时,我们也揭示了内含于个体之中的必然性,这将是我们通往必然之路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