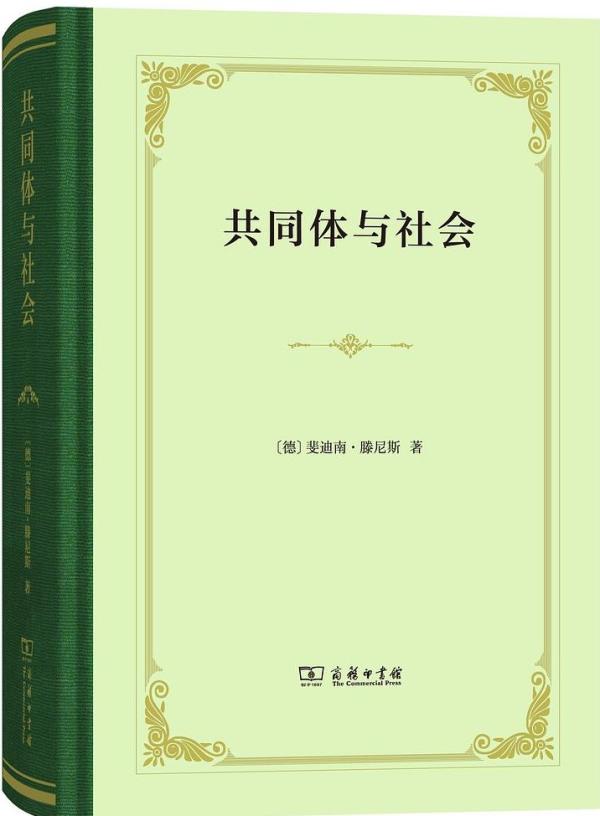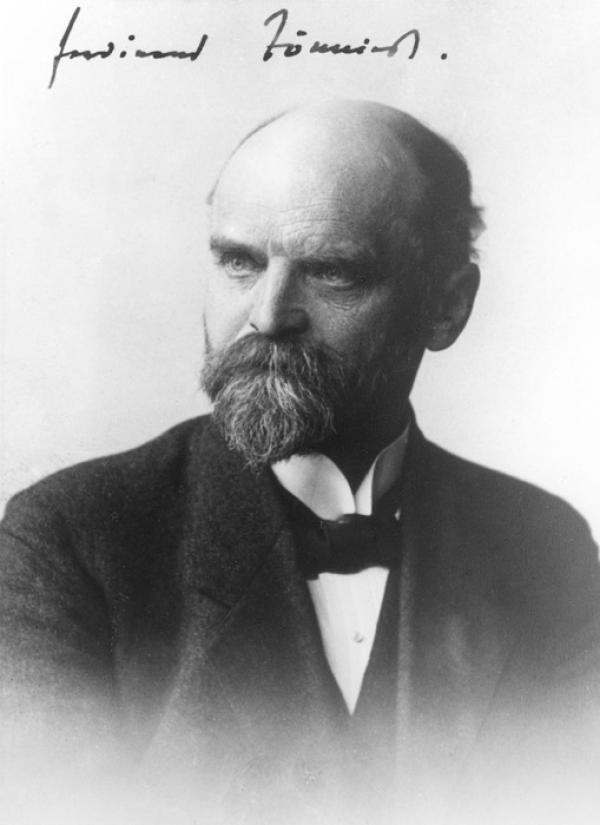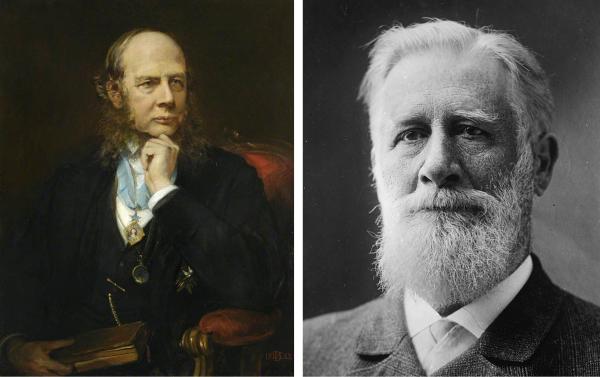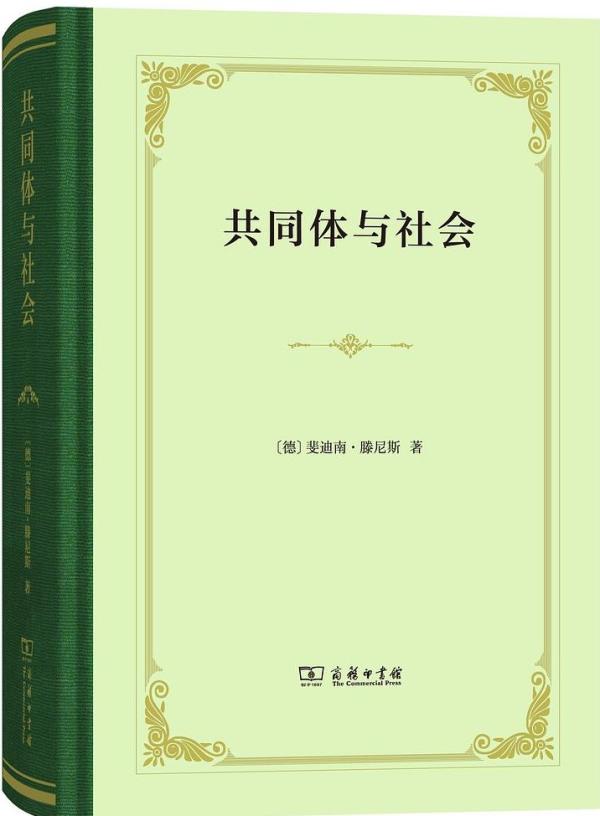 《共同体与社会》,[德]斐迪南·滕尼斯著,张巍卓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出版,616页,89.00元
《共同体与社会》,[德]斐迪南·滕尼斯著,张巍卓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出版,616页,89.00元
一本书的命运——从圣经到故纸
《共同体与社会》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史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 1855-1936)的代表作,滕尼斯亦被后世学者奉为欧洲现代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他的一生著述浩繁,光德国滕尼斯学会计划编订的《滕尼斯全集》就有二十四卷之多,目前收录于德国石荷州图书馆的未发表手稿和信件的数目更是巨大。这些文献涉及思想史与实践领域的诸多方面,交织着现实与历史的多重视野。其中,《共同体与社会》既是他最富盛名的著作,也是最核心的文本,它就像滕尼斯思想遗产的总纲领,集中呈现了他理论的实质问题和伦理关切,并且展现为一套完整的学说体系。
从作者的写作历程来看,《共同体与社会》标志着他思想的成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判断和理论意识:从研究近代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人性论、自然法和政治哲学的作品入手,滕尼斯将它们一步步地向历史的纵深领域推进,通过同欧洲近代以前的“前理性主义”文化传统展开充分比较、对话,奠定了以理解人类共同生活(Zusammenleben)的总体事实、反思其内在规范为要务的社会学。在此后的人生旅途里,滕尼斯见证了从德意志帝国崩溃直到纳粹上台的半个世纪的剧变历史,见证了斯宾格勒所说的“西方的没落”,他为此着力而谨慎思索的关于学术、社会和政治改革的诸议题(包括社会学体系、科学术语、习俗、公共舆论、教育改革、劳资关系、合作社运动、政党与议会、民主制国家的构建等)皆可追溯到《共同体与社会》的天才式的预见以及相应的理论环节。同样,对滕尼斯这位当时的学界领袖和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来说,本书亦是他缔造自由的学者团体、改革社会之弊、捍卫民主政治的实践指南。自从《共同体与社会》第一版问世(1887年)以来,作者终其一生都不断在修订、重版这部年轻时代的作品,根据时代境况的变幻赋予它常新的意义,在作者生前,本书共出了八版,直到去世前一年(1935年),他仍在致力于新版本的修订工作。
《共同体与社会》的初版本
《共同体与社会》不仅是滕尼斯的思想和行动的灵魂,而且深远地影响了同时代以及未来的社会思潮,反过来说,它也在剧烈动荡的时代浪潮下经历着命运浮沉。尽管在第一版面世时,它并有没引起广泛的重视,然而当时几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它,并从各自的角度做了批判性的回应。无论对本书的态度是褒还是贬,他们皆肯定滕尼斯在德国哲学和新生的社会科学之间搭建了一个全新的桥梁,他所呈现的古今世界观的对立意识为反思时局乃至现代性提供了有力武器。长久的沉寂之后,随着俾斯麦集权体制的瓦解,以及工业文明全面危机在世纪末的日益凸显,首谈“共同体”同“社会”对立的《共同体与社会》越来越被大众广泛地接受,甚至说“狂热追捧”都不为过,它成了席卷全德的青年运动的圣经,青年人高喊着回归浪漫的共同体,对抗理性的社会;尤其当1914年德意志帝国投入欧洲战争,同英法诸国展开殊死较量,“日耳曼文化同盎格鲁-撒克逊文明间的斗争”发酵成德国学界最持续、最热烈讨论的议题,《共同体与社会》理所当然被视作发声之源,达到了它声名的顶峰;此后德意志帝国的败落,新生的魏玛共和国经历着持续的政治、社会动荡,纳粹党宣传家利用《共同体与社会》里的“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的口号为其政权的合法性造势;而二战后的局面则迅速彻底颠倒过来,直到今天,政治的自由主义、经济的全球化以及学术和教育的美国化构成了欧洲主流的意识形态,《共同体与社会》不仅被抛入历史的故纸堆,而且多少成为思想的“禁区”。
或许正是因为滕尼斯同他的这部名著(更准确地说是“标题”)太敏锐地触动了时代的神经中枢,故而它们被意识形态的各种潮流裹挟利用,书中丰富而深刻的理论探讨被曲解乃至直接无视。相反,回到历史的语境,追溯本书在同时代的学者共同体那儿产生的真正影响,也许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它对于当今的价值。不可否认,作为一位明确以“社会学”作为自我学术定位的学者,滕尼斯创作《共同体与社会》为欧洲现代社会学奠定了基础(1912年的第二版之后,滕尼斯将本书的副标题改成“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经典的社会学大家也无不从本书获取给养,进而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回应本书的内容:首先,在现代社会科学诞生前夜,本书植根于近代自然法的理论土壤,结合历史法学对于历史事实的要求,将社会置于核心位置,明确提出了社会学的根本关切所在,即“共同生活”或广义的“社会”(das Sozial)的事实及其规范性基础的问题,如早期涂尔干便在此受到滕尼斯启发,他同滕尼斯关于“社会”本性的争论证实了这一点;其次,它将解释的脉络扩展到个体心理、经济生活、政治秩序等诸领域,将“社会”构筑为一个总体的世界图景,如韦伯对个体的社会行动的阐释、桑巴特对传统经济模式与现代资本主义的比较研究都离不开同滕尼斯的对话;最后,它是对现代性与文明格局的价值探索,如特洛尔奇调和信仰与现代性的进路,同滕尼斯寻求克服理性主义与历史主义世界观之对立的努力紧密相关。
《共同体与社会》的第二版
当然,《共同体与社会》的意义也并非局限于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的视域内部,它的内容涵盖了西方思想史的诸多关键论题。作为一位涉猎广博的哲学史家,滕尼斯对古希腊哲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学派)、霍布斯与斯宾诺莎的早期近代形而上学、康德与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思想、歌德与席勒的魏玛古典主义精神、叔本华与尼采的悲观主义的意志学说都曾做过精深的研究,在本书里,他细致地回应了这些思想脉络,形成复杂的从心理到社会行动的理论体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身处近代德语世界思想传统中的知识分子,滕尼斯对贯穿德国十九世纪的唯心主义、浪漫主义、历史主义诸理论思潮及其内含的伦理和法权思想做了全面的反思,重新奠定了一套从个体心灵、社会生活直到政治国家的总体的、带有辩证色彩的伦理秩序。
不仅如此,在本书中,滕尼斯为我们勾勒了理解欧洲普遍历史进程的双重理论谱系:一方面,“共同体”概念囊括了从古希腊城邦、罗马父权制国家直到中世纪日耳曼封建制帝国与自由市镇并轨的历史,而“社会”概念则涵盖了近代市民社会与民主制国家的进程,滕尼斯对“共同体”向“社会”的转变进程的讨论既展现了他同梅因、巴霍芬、库朗热、摩尔根等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关于西方早期文明形态的对话,展现了他如何在洛贝尔图斯、施莫勒、瓦格纳、基尔克等德意志史家的启迪下重构日耳曼祖先的历史,也展现了他同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等政治经济学家关于现代商业社会和国家秩序的论争;另一方面,滕尼斯对“社会”的危机以及“共同体”在欧洲重新繁荣的预见,充分反映了他对世纪末普遍弥漫的悲观主义情调、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及其实践活动的反思,也奏响了二十世纪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和批判理论的先声。
无论从哲学还是史学的角度来看,《共同体与社会》都不啻一部欧洲文化的百科全书。如果说今天的社会科学要突破种种意识形态的幻觉和迷思,培育自身敏锐的感受力、深刻的解释力,打开自己的视野来充分应对现代世界的种种问题,那么回到本书、获取不竭的思想乃至信念的给养仍是必要的。
滕尼斯,1915年。
《共同体与社会》的成书史
(一)1877-1880年:霍布斯研究与怀疑的启蒙
根据滕尼斯本人的报道,《共同体与社会》创作于1880-1887年。在此之前,他已凭借对霍布斯哲学的开创性研究,在学界崭露头角。滕尼斯的学术生命始于霍布斯研究,而《共同体与社会》的创作历程,同样以霍布斯研究为起点。
1877年,滕尼斯获得图宾根大学古典哲学的博士学位。此后,他彻底地投入近代形而上学和国家学的研究工作。在老师兼挚友泡尔生的指引下,他开始系统地梳理前康德时代的哲学思想,尤其以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的生平与学说作为研究的核心。通过全面地考订霍布斯的文献、阐释其哲学体系,滕尼斯彻底扭转了霍布斯在哲学史里的微不足道乃至声名狼藉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的形象。在他的解读里,霍布斯作为十七世纪反叛神学世界观的佼佼者,最完整、最彻底地道出了现代科学世界观与个体主义人性论的原则,也最深刻地奠定了现代自由主义政治的理性基础。在霍布斯之后,他开辟的契约国家观一直延续到了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传统里,以至于在十九世纪边沁和密尔的功利主义学说潮流中,这一观念仍然有所回响。
不过从一开始滕尼斯就认识到:霍布斯的“国家”实际上远比后世自由主义国家观囊括了更复杂的意涵以及更强烈的张力:一方面,霍布斯设想的政治体源于每一个体自身意志的构建,因而相较过去基于传统权威和宗教信仰形成的政治体,它完全是革命性的,这一点直接为自由主义继承;但另一方面,相较于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它确定的主权者的权力也孕育着强大的保守力量。正是通过对此张力的敏锐感知,滕尼斯形成了关于“共同体”与“社会”理论的最初意识。
托马斯·霍布斯
这种意识事实上同滕尼斯所植根的德国法哲学传统密不可分:黑格尔与他的后继者不仅提出判然有别于市民社会的国家,而且认为只有后者能真正地克服前者内在的个体任意性,实现真正的伦理精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德意志帝国这几年间的局势的剧变同样牵引着他沉思的方向。滕尼斯从事霍布斯研究的初衷,很大程度上是要站在启蒙哲学的立场上,克服路德教和封建制度的理论根基,为德国奠定国家理性(Staatsraison),他也确实从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着手一步步地追溯他的形而上学和人性学说,伴随着阅读的深入和对政局的敏锐感知,他更清楚地认识到现实的复杂性:1878-1879两年间俾斯麦政府颁布《反社会党人法》,疯狂地打击自由主义宪政、镇压社会主义运动,国内弥漫着阶级冲突的紧张气氛,令滕尼斯忧虑重重的,既是帝国这一混杂着容克专政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寡头制怪物,更是在它的统治下败坏了的人心:统治者借用传统秩序和道德伦理的名义极力压迫劳动者,他们利用社会舆论,煽动起社会各阶级的抽象的政治想象,让各阶级无不彼此仇恨并力图将对方置之死地,德意志帝国这艘大航船正驶往末日的岛礁。
对此,滕尼斯坦言自己形成了“十足激进的、完全不倾向政府的思想”,然而激进的态度也并没有让他陷入政治斗争和革命的幻觉。相反,他开始彻底地反思近代的理性启蒙:终结封建制和垄断资本主义合谋的寡头政体诚然是德意志未来的政治使命,但是更致命的问题却是早已由它们败坏了的文化和人心,因而仅仅从主权的角度理解政治共同体是有局限的,单纯用“理性”看待“社会”与“国家”也是不够的,如果不超出霍布斯式的理性主义自然法的视域并立足于日耳曼文化的复杂进程,从文化的脉络里考察它们,我们便无法真正认清、解决现实的困境。这个时代需要综合了理性和历史所赋予的信念的更高尚的启蒙,同样,这个时代需要担当这一启蒙责任的强大而冷静的伦理-美学英雄 。
(二)1880-1881年:“共同体与社会”作为文化哲学的概念建构
滕尼斯很快找到了理论突破的方向。1879年夏,他在一封写给泡尔生的信中提出了构建一门所谓“人的共同体生活的哲学”(Philosophie des menschlischen Gemeinschaftslebens)的想法,并且明确地将这门学问称作“社会学”(Soziologie)。在一开始,他是在法学框架内部思考这一问题的。沿着德国法哲学揭示的“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脉络,滕尼斯一方面花了大量精力阅读从萨维尼到基尔克(Otto von Gierke)的德国历史法学派文献;另一方面,他将近代理性主义自然法的精神追溯到了罗马法。在阅读经典文本的同时,他有意识地从当前学术语境出发,把握思想史的实在轨迹,就此而言,耶林(Rudolf von Jhering)和瓦格纳(Adolph Wagner)这两位当代学者对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前者在《法的目的》(1877)中揭示的“目的是法的创造者”的原则构成了理性主义自然法的衍生,而后者在《政治经济学基础》(1879)里提倡的由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思想则是历史主义与有机论自然法的变体,可以说,它们代表了德国学术意识的两种不同实践取向的冲突。1879年,应莱比锡哲学协会的邀请,滕尼斯做了两次题为“自然法的更新”(Die Erneuerung des Naturrechts)的报告,在两种相对立的自然法的意义上重新对“共同体”与“社会”做出规定,他甚至想过写一本题为“作为哲学问题的法”的小册子。进一步地,滕尼斯试图向内探索,为这两种自然法寻求心理学的根基。
耶林和瓦格纳
在1880-1881年间,滕尼斯的理论探索有了初步成果,这便是他为谋求基尔大学哲学系私人讲师职位而撰写的《共同体与社会——文化哲学的原理》一文,在其中,他提出一种基于人们经验的共同情感、以实现伦理生活为旨向的文化哲学。以思想成熟时期的滕尼斯的眼光来看,这篇文献的讨论尚停留在概念构建的层次,还没有将概念同历史有机融合到一起、充分展现出来。澄清心理生成过程的每一环节的伦理意涵并构建它们同民族的实在生活的关系,成了滕尼斯进一步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三)1880-1887年:“共同体与社会”作为经验文化形式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
1881年,滕尼斯成为基尔大学哲学系的“私人讲师”,担当伦理学的教席,此后主要讲授的课程是古希腊伦理学、政治哲学以及近代自然法学说。这段时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对他的“共同体与社会”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关于古今人性论与政治原则的比较研究对他而言极其关键,由此,他从哲学的层面推进了对“共同体”与“社会”之法权基础的阐释;除此之外,在近代自然法脉络的内部,滕尼斯以霍布斯的学说为起点、过渡到对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的研究,这为他提供了理解现代人性与社会的更广阔的视角。
据滕尼斯的学生雅各比的报道,在1882-1883年间,滕尼斯创作“共同体与社会”的重心仍集中于概念体系的建构工作,然而到了1884年,他越发意识到要突破形而上学框架,其方式便是浸淫于大量的比较民族学和政治经济学作品,从心理学过渡到广义的社会哲学,向历史的纵深迈进。1885年初,滕尼斯写信给泡尔生,决定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写作一本小书上来,让他的讲法付诸实现,他把这本书界定为研究人类学和社会现实的作品。6月,他形成了未来理论体系的基本想法以及问题意识。
在滕尼斯看来,历史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两种对立观念所表现出的总体社会哲学的体系,便是在同时代学者们那儿争讼不已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甚嚣尘上的阶级冲突和弥漫着浓烈火药味的政治斗争的年代,它们不仅被混为一谈,而且被当成宣泄愤恨的口号,内容空洞无比,同时牵扯着意识形态上的敏感争执。然而滕尼斯从三位先驱基尔克、梅因和马克思那里辨识到两者在历史上既源于不同的思想传统,也呈现为彼此截然对立的实践生活图景:梅因笔下的早期希腊、罗马乃至印度的法和共同体秩序,基尔克生动而全面刻画的中世纪的日耳曼合作社生活共同构成了“共产主义”的原型;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和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则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方向。面对繁富的历史材料,滕尼斯牢牢抓住“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内在的伦理精神:前者是以家庭生活为原型的一切从属于、亲合于人类自由的共同本质的东西,与此相对,后者则表现为以商业经营为主导的现代生活,其最直接、最简单的形态即经济交往和相应的、以契约为特征的法律事实。由此出发,他既克服了思辨的抽象性、又摆脱了纯粹历史叙事的束缚。
梅因和基尔克
不过,正像滕尼斯指出的那样,单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理论意识,或者说它们背后纯粹的历史主义观或理性主义观都具有片面性,相反,认识它们之间的“转化”(Verkehrtes)极其艰难却又十分必要:一方面,在当今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清醒地认清历史发展的趋势,由此把握现实的社会条件和普遍的人心状况无疑构成了一门有效的经验科学的前提,梅因从法学史角度揭示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规律指引滕尼斯抓住了从“共产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一古今之变的核心线索,继而后者从人心、经济、风俗、政治等诸领域大大地扩展了历史变迁的内容;另一方面,我们的科学视域也不能只局限于当下的情形,伴随着近代商业社会的兴起和民主国家的确立,理性主义哲学所刻画、所期许的“启蒙了的”现代人的形象以及他们的生活图景看似如此牢靠,然而它们仍然是有内在限度的,现代人依靠理性制造出“人格”确保他们获取利益、在世上“过得好”(Wohl),他们却无时无刻不活在分裂的状态里,从个体的角度来说是同本真的自我(Selbst)分离,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则是同具有自然情感的俗众(Vulgäre/Volk)隔绝乃至对抗,社会日益被撕裂,因而滕尼斯认为我们需要在当下“社会主义”的背景里重新反思“共产主义”的意义和价值,“共产主义”不单意味着“前理性主义”(vor-rationalistisch)的生活方式,更是“超理性主义”(über-rationalistisch)的生活方式。
结合上述两个方面来看,滕尼斯因而称他的研究既是经验主义式的,又是辩证主义式的。 在1885-1886年集中写作《共同体与社会》的过程中,他不断在大量历史与人类学材料间往来穿梭,从经济史、政治史、法律史等方面充实“共同体”与“社会”的概念内涵,沉思历史的进程和民族的未来命运,并坚定地将人心的问题或心理学的思考视作理论基础,他致力于从思想史上揭示古代和中世纪的人类共同生活的心理机制,即“本质意志”(Wesenwille),而且试图说明:经过哲学的升华,它能同当下的生活经验结合到一起,成为克服理性主义之片面性的整全的伦理力量。
1886年冬季,应家人的要求,滕尼斯陪同一位生病的妹夫去南方度假旅行,他随身带上了创作中的文稿。旅行的目的地是意大利南蒂罗尔的梅拉诺,滕尼斯同他的妹夫在梅拉诺城的奥博麦斯区住下,在这个风景如画的旅游胜地,他得以心无旁骛地工作。他也时常去奥地利西南部的因斯布鲁克,在因斯布鲁克大学的图书馆里查阅资料,从事写作。1887年的2月,滕尼斯完成《共同体与社会》的创作,为副标题取名为“作为经验的文化形式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他将这本书题献给泡尔生,并将书稿交给了莱比锡的出版商O. R. 赖斯兰,到了这一年的7月,第一版《共同体与社会》正式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