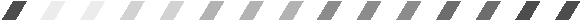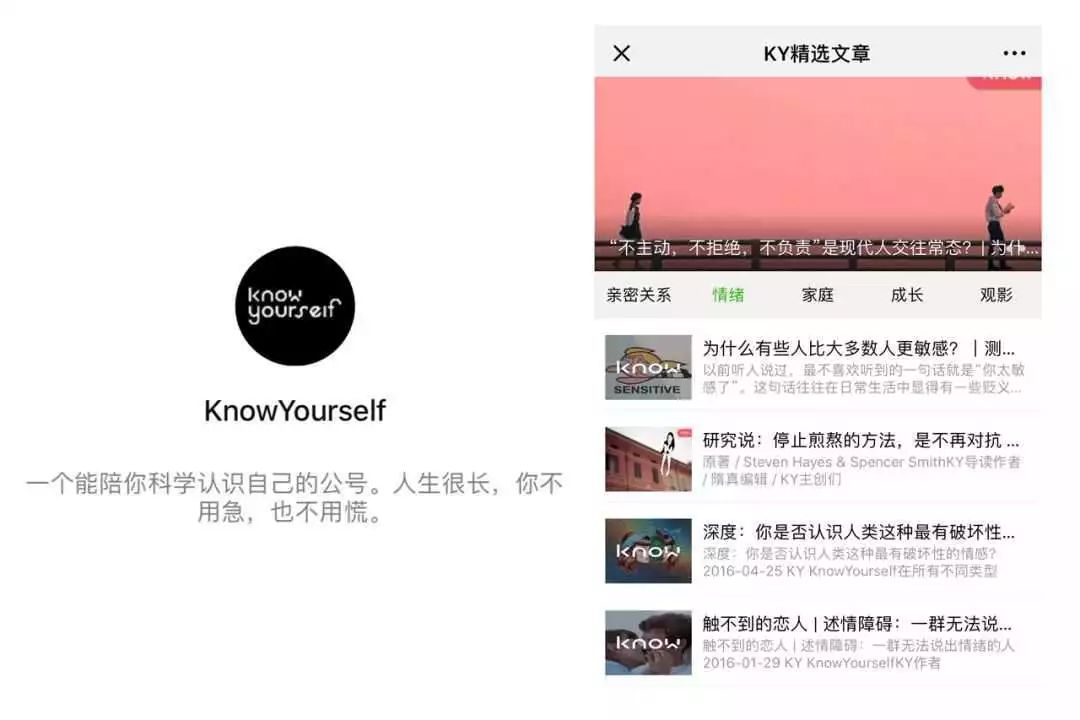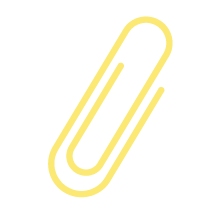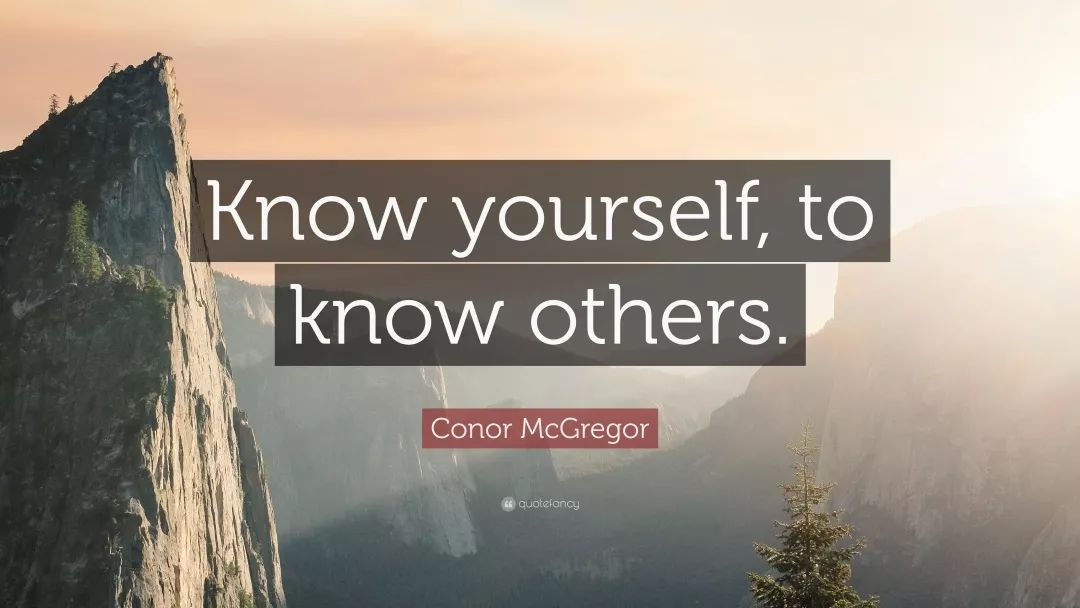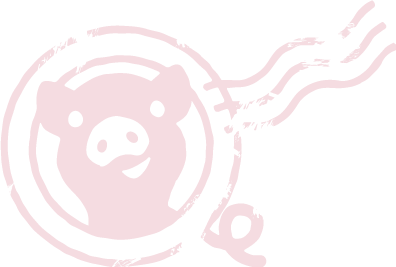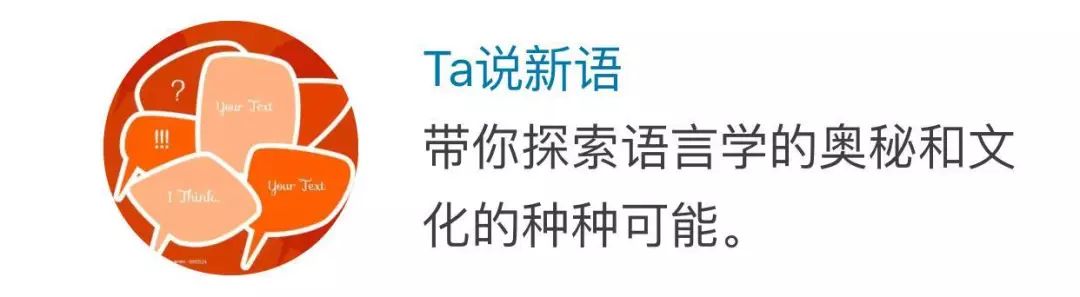编者按:因原文中涉及部分作者与ky之间的内部保密协定,故在作者的希望下撤下;此次重发为作者经过删改以上涉及协定内容的文本。并于文末增加了“作者的话”一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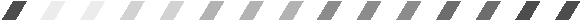
元嘉草草案:
Blue的这篇文章,看似是在质疑KnowYourself公众号的“初心”是否还在,实质是对所有临床心理学工作者的一个沉重拷问。
Ky对于公共性议题有意无意的回避,不仅仅是时代下的缩影(ky从崛起到快速扩张,恰恰是中国互联网言论自由从宽松到收紧的几年),也在某种程度反映了临床心理学对于个体背后更宏观的社会背景以及公共性因素的不重视。广州女权运动者黄叶韵子在一次女权主义沙龙中谈到,当她因为抑郁症寻求心理咨询师帮助的时候,她当时的心理咨询师对于她作为女性遭遇到的歧视归因为个人的原因,并没有看到社会性对于女性的歧视以及她可能遭受的文化性创伤。这一点让她非常失望。
另外一个例子,是近期考研学生焦越在网上质疑清华大学在研究生考试面试时涉嫌性别歧视。一个心理学博主对此事的评价是,大学因为怕学生出事需要负责,会在面试时候淘汰掉那些疑似“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他认为这是很正常的国情,并认为一些人认为自己被歧视了其实是在”外归因“,是”逃避自己的责任“。他的观点被众多心理学博主认可且附和。且不说仅仅依靠面试时候10几分钟的交谈就判定一个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是否科学,这样的操作是否涉嫌对于心理健康歧视也值得深究。
当一些心理咨询师把个体的遭遇仅仅归因于个人,而看不到个体背后社会结构性的影响,这其实是非常片面的。Blue也在文章里质疑,ky创始人钱庄在演讲中对于“虚无”的表述太过于岁月静好(“只要世界上有一个深深懂得你的人,或者是一个帮助你了解你的人存在,和ta在一起是,就真的觉得世界是不重要的。”),而忽视了更宏观的公共性。对此我深以为然。如果说,心理学是帮助人们认识自己,know oneself, 那么思考“我是谁”这样的命题的时候,不应该只局限于个人层面,满足于在自我构建的小圈子里面岁月静好,更应该站到更宏观的角度,从公共性角度、哲学角度思考,我与他人的关系,我与社会的关系,我与人类这个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不得不承认的是,国人也是从近20年开始才逐渐重视的心理健康,即便现在也依然很多人对于心理健康问题讳疾忌医。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连达到个体层面的岁月静好都很难,更不用说从公共性角度思考人生。但这种把“个体心理健康”跟“社会性”割裂的观点,恰恰就是Blue一文所批判的。一些个体层面的创伤很有可能是历史、社会、国家政策、文化等等交互作用下的结果。缺少了宏观角度的know yourself只可能是虚假的、有限的“懂我”。
Blue丨Ky志愿者
亲爱的钱庄小姐您好:
老实说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倍感压力,且心情矛盾。
我问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ky之于我变成了这样一个难以谈论的话题呢?”至少在那段每天期待更新,并且跟身边几乎每一个朋友安利这个公众号的的日子里我是绝对无法想象到她今天的样子的。
我反复的质询自己,今天的ky让我感到疑惑甚至是失望的到底是什么?
要具体罗列的话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一条肯定是“宇宙中最酷的泛心理学社区”现在已经丧失了她的绝大部分“公共性”,以及内在自我价值上的自洽。ky宣布公司化运营之初我就在想,当作为“一个社群”的ky和作为“一家公司”的ky两个身份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主创们要如何取舍呢?现在看来您的方式是抛弃前一个身份。从做“所有人都能看懂,但是只有一部分人喜欢”的内容,转向做“让尽可能多的人都会喜欢”的内容。所以ky变得不再认真的谈论苦难,不再谈论个体有限的悲欢之上那些更宏大但也更难以理解的事物,我看见您从真实人生中令人尴尬的一地鸡毛前转过身去,以另一种妥善管理过的表情去讲述一个更加戏剧化的故事。
而这样的转身,即使在我不算长久的记忆里也已经见过多次。
KnowYourself CEO 钱庄(图源网络)
去年5月去面试社群志愿者的时候,面试官alice问我为什么想做志愿者,我说是因为对于ky怀有期待,而此时此刻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也依旧怀有同样的期待,我依旧愿意相信作为一名ceo的您并未抛弃作为学者和社会工作者的诚实与悲悯。但同时,在一段时间内ky所做的诸多成功的不成功的尝试中,我感受到的是自我重复,以及急速扩张背后的急功近利。
就以粉丝群为例,ky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大量简单以话题类型分类的粉丝群,但是在观察群里话题的过程中我的感受是在这种场域下很难真的深入去交流什么,在虚拟的网络上,人与人要建立起来真实的链接远比想象中更加困难,信任需要时间来累积,情感的通路也无法按照人为的方式任意的铺设,更不要说那个模式是否合理了。
把时间线往前推进一点,那个基于微信的伪bbs也是这样,诚然bbs这种古典互联网时代的平台的确比即时通讯工具要更适合深度交流和沉淀内容,但是那依旧是需要有称职的版主存在为前提的。我想ky如此看重粉丝的社区化运营自然不会轻易放弃,那后续的“产品”(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产品吗?)会以怎么样的逻辑推出呢?
如果把这个问题再往深问一层,ky最终希望与喜欢,信任她的人们建立怎么样的关系呢?ky又打算以怎样的立场把聚集在自己周围的,数量众多的粉丝们联系起来呢?成为粉丝之间相互认识的中介吗?或者一个凝聚共同情感的符号?
know yourself微信公众号截图(图源网络)
Ky最初是一个以普及心理学为主要内容的公众号,现在又成了一家新媒体公司,相比于国内一些类似的机构比如简单心理,我认为ky有两个非常显著的不同,一个是非常注重与自己的粉丝互动。无论是建立粉丝群,还是把收集到的问卷筛选整理成文发布出来都是为了鼓励粉丝的参与并且形成一种基于共同经历带来的归属感,同时ky的内容涵盖了大量的社会热点,远远超过了纯粹的心理学的兴趣范围,而且文章风格充满情绪的感染力。这两点的相互作用使得ky得以在几年的时间内积累了如今数量巨大且高黏着度的粉丝群体。
但是情绪的力量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对于ky这样一个从事心理学知识普及和提供社会服务的机构来说更是如此,在‘煽情’带来的传播力和内容的严肃性、准确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似乎并不那么容易。就比如那个广为流传的概念‘爱无能’,作为一个比喻的确非常好的描述了当下年轻人在亲密关系中的某种状态,但是在“爱”这样一个复杂的高级情感上的表达/感受障碍能简单的等同于情绪无能吗?‘爱无能’这个概念之所以容易被接受是因为它符合我们的直觉与经验,但是这种标签化的判断真的有助于我们去发现每一段具体的关系中那些因为千奇百怪的原因被遮蔽的动机吗?
请原谅我的敏感和多疑,因为ky所谈论的话题无一不关乎我们当下生活中那些最重要问题的答案,而ky选择了一种最有感染力讲述方式以及“心理学”作为当代显学的光环又使得她的听众大概率会对她所说的一切深信不疑。我认为对于她们,ky是多少要负有一点超过“一家公司”边界的责任的。
我想ky的确在做一些这个时代最紧迫的工作,但同时也正是这样一个一切都显得紧迫的时代赋予了ky今天这样巨大的影响力,是今时今日淤积于年轻人们心头的巨大焦虑构成了ky迅速的增长的基础。
正如我看到关于您的一篇访谈的标题所言《“90后”钱庄安抚上百万焦虑的年轻人》,ky的内容的确给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慰藉,“温柔”是大量出现在留言区的高频词,最初关注ky的时候也的确是这种基于独立个体视角的温柔深深的触动了我,可是当这种温柔和对于个体视角的关注变成一种自我重复的时候不由得让人心生警惕。毕竟以您的学识和经历无疑比我更加清楚,当下年轻人们所面对的危机绝不仅仅是“不开心”那么简单,而真正的认识自己更是不可能在脱离社会语境的前提下实现,我们需要通过认识自身与他人,与社会,与历史,乃至与真理的关系(而不仅仅只是借助“科学化”的“干货”试图完善自己私人领域的那一亩三分地),才有可能触及自己内在的真实。
令人失望的是ky早期的内容里以心理学视角切入宏观层面社会问题的勇气与锋芒(比如代际创伤与我们独特历史之间的关系,又比如社交网络对于我们公共人格的影响)都逐渐湮没在那种讨巧的温柔里了,唯一涉及公共性的内容只剩下由您主笔的几篇身份政治色彩极重的女性主义文章,且不论这几篇文章中对于女性身份偏本质主义的解读是否偏颇,单论情感色彩已经是近一年内我在ky上读到的情绪最强烈真挚的文章,但是她们依旧小心谨慎的踩在最安全的线内。
在我的感受里,ky的“语境”已经和最初的时候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说新世相和咪蒙是直接兜售焦虑本身的话,那么在这个人造的寒冬里,提供一套些许斯多葛主义的完全内省式的安慰剂,是否是另一种形式的消费焦虑呢?是否与刺破幻象的主张背道而驰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依旧不得而知。
我最想跟您聊聊我们的是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巨大虚无,以我可以寻找到的最真诚的态度。
当我第一次知道ky的创始人是一个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孩子的时候,内心是无比震惊的。在阅读关于您的访谈和演讲的过程里我被那种自信又充满知性的诉说强烈的吸引,甚至会感到自惭形秽,毕竟您在那时的我看来实在太过耀眼和与众不同了。
您似乎完成了我所有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以一种道德的,自由的,有尊严的方式获得这个社会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认可,并且帮助和影响到其他人,被众人偏爱与崇拜。但是到了去年读到您那篇关于自我察觉和美好生活的演讲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对这样的叙事心存疑惑,当然我得承认那依然是一篇极其优秀的演讲。我当时在那篇推送下面留了很长一段言但是没有入选,所以才有了这封信。
我写的很慢,几度因为自我怀疑想要放弃,我怀疑自己的那些困惑是否是源自偏执和自欺,所以我开始重新阅读ky的早期文章,特别是当初很触动自己,奠定自己对于ky认知的那几篇,还有所有能找到的您的访谈以及演讲,以及公众号上其他具有私人色彩的随笔(虽然没有署名但是您的笔触还是很容易辨认的。)在反复的阅读和思考中,另一个形象逐渐在字里行间浮现,然而我依旧不知道这个形象是否是那俄罗斯套娃一般层层嵌套的灵魂真相里稍微靠内侧的一层。
那篇谢绝一切录像的演讲实录评论区第二行,一位在现场做志愿者的女孩留言道:“小姐姐人美,讲得好,文字更美!还有,演讲的时候自带一种让全场安静聆听的气场。第一次见面虽然觉得小姐姐有一丢丢傲气,但是觉得那只是不熟悉的本能戒备而已,发自肺腑的特别喜欢小姐姐!”
当看到这段留言的时候我脑海中忽然想到剧集《年轻的教宗》里裘德洛饰演的那位矛盾复杂的教皇。在那个故事里,年轻的教皇站在阴影里隐去自己的面容向自己的信众们布道,他的言辞强硬而笃定,有着俘获人心的魔力。可是他对于自己所言,甚至对于上帝都充满了质疑。在旁人眼中,他睿智正直,是当世的圣人,却不知他内心无时无刻不在被巨大的空洞噬咬。他感到无比愤怒,对于他自身以及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
他无法理解,既然上帝是全能而至善,那为何他自己会作为孤儿被遗弃,为何这个世界有如此多荒诞的灾难。聪慧如他,很小便理解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则,遵循这套规则,在教会内部的政治博弈里所向披靡,不断的获得胜利,年纪轻轻就坐上教皇之位,可是这一切依旧无法解答他的疑惑一丝一毫。
您在文章里也反复提到“女性应该有感到愤怒”的权利,那么您会在自己的人生中哪一个时刻感受到愤怒呢?最初的ky在每一篇文章末尾如此写道“人生这场荒诞剧,你应该…..”,应该与荒谬共谋,在这场剧目里保持“优秀”,一直优雅的赢下去吗?对于风险的偏好,对于“自立”优先追求是否都是出于对自己的这种“优秀”的不甘心呢?出于一种强烈的,对于自身的控制欲。
但胜者与英雄的路大抵都是相背的。
而精致的利己者们大抵总是会赢的,因为他们利用一切“善”的原则作为自己功利计算的借口,但是却在内心嘲笑这些原则的价值,所以他们才能显得“超然又合理”,那些真正晦暗尖锐的问题全都被被他们巧妙的抛在脑后了。但我认为这种不诚实的胜利除了导向自身与世界的虚无将一无所得。
《年轻的教宗》截图(图源网络)
您说北方的质朴粗犷,北大的人文精神教会了您责任与担当,让您与自身的精致利己告别,所以我更加好奇站在人文的视角上,您会如何看待我们这个时代里‘人的境况’,以及ky今天身处的这套资本与媒介的游戏规则呢?
您说在后台回复留言的时候会幻想把读者们全部连在一起会不会像一片闪亮的星辰?初次读到这句的时候我被其中浪漫的想象所感动,但以志愿者的身份在粉丝群里同具体的读者交流的过程里我看到另外的风景,我看到个体身上的偏见,自相矛盾,浅薄以及尖锐的攻击性。就像你把视角由远拉近,会发现璀璨的星辰表面崎岖凹凸,寒冷孤寂,彼此无法沟通。
而且随着ky的内容越发局限于情感与私人生活领域的道德叙事,留言区的气氛也逐渐变得充满受害者的戾气。这样纯粹从个体视角出发(与温柔相对的)的怨恨也是您认为的“女性有权力感受到的愤怒”吗?这些复杂的,具体的的粉丝们您打算依靠什么把她们真实的联系起来呢?依靠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现代魔法吗?
您提到ky抢的的是国内“情感咨询”的生意,比起她们ky的优势是使用了科学的方法。Ky使用科学而专业的现代心理学工具为当代年轻人的心灵提供指引与建议。我们知道在1862年威廉冯特博士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之前,“心理学”一直是从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而在那之后测量与实验逐步取代了形而上的思辨,人类的灵魂开始变成一种可以被分析与还原的现象而不再是超验而伟大的奇迹,心理学从哲学衰微的陋室离家出走,迫切的试图把自己打扮成科学的样子。而这一切发生的背景是“理性”对于“经验”和“感性”的节节胜利。
首先是人的“主观”被实验科学从对自然的解释中移除出去,紧接着人本身变成了可以被研究的客体。在行为主义心理学家那里人的内在本质并不重要(巴普洛夫眼中人和狗的反射并没有什么不同),重要的是具体的行为与外界刺激之间的关系,而佛洛依德则冷静而超然的对躺在沙发上的来访者做出诊断“你脑海中的想法并非来自于真实的你,只是潜意识(爱无能,假性亲密,病理性迷恋)在作祟。”而在具体的生活层面,理性的力量塑造出今天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以“效率”和“合理”为根本原则的现代社会,还有包括经济危机和大屠杀在内的一系列献给虚无的供物。
对于这一切尼采说道“上帝死了”然后陷入了疯狂,10年之后《梦的解析》才宣告出版,临床心理学家们永远的错失了诊断尼采的机会。福柯接过尼采的话筒继续说道“人也死了,人将被抹去,就像一张海边沙滩上的脸”正如您在某一篇推文里所引用的那样。我想您一定比我读过更多他的著作,福柯多半是不认为有什么内在的“真实自我”等待我们去发现,在他那里‘人’是一种发明,今后也只能继续在流动性中自我发明下去。而知识即权力,知识通过发明概念的方法规训桀骜不驯的肉体。
如果福柯还活着,他会怎么看待ky的这种叙事呢?他会如何看待每一篇推送末尾一长串的文献引用,以及对于“科学性”的推崇呢?他会对“爱无能”“假性亲密”“病理性迷恋”这样脱离了‘物’的羁绊自由漂浮,并且试图反过来定义‘物’的语词发明作何感想呢?
让我们试着回到原点,回到德尔斐神庙墙壁上那句“know yourself”,回到心理学,哲学与科学最初的起点。在古希腊的语境下“know yourself”的过程即是通达“身体”这座诸神宫殿的过程,在这条路的尽头绝不仅仅只有私人领域的“幸福生活”,而更多的是“城邦”的传统,荣誉与认同,是一种追求卓越的实践。“认识自己”天然的是一种“公共活动”,而不仅仅是沉思与言说。
您在那篇《你可以选择原谅,但前提是“ta”值得》中也写道“personal is political”,您说私人的即是公共的,我对此深表认同,所以我选择尝试以这样的语境写这封信,我认为我有义务去探讨我所见所感所思的这些问题,这对我来说是“matters”。但是关于那篇文章,我难以认同的是您一边在以“公共”为名展开讨论,另一方面又预设了“女性的感受”有一种“不证自明”的正当性。
例如在文章一开始的那个个案里没有任何具体事件的描述,只有作为当事人的“一位女性”的心路历程。最终通过分析这种内心的感受得出她在这段关系里被另一位男性忽视和伤害的结论,进而推理出作为一个整体的“女性”在社会系统里受到的情感上的压抑,最后通过论证这种压抑得出,“女性愤怒”不证自明的正当性,以及“我们女性”应该伸张正义,反抗加诸在女性身上的不公正。
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以父权制为基础的社会当中,性别的结构性不平等总是以明显或隐晦的方式彰显着自己的存在,但我依旧不认为您的这种叙事是一种讨论公共问题的理想方式,它甚至可能都算不上一种探讨。因为关乎正义之事没有什么是“不证自明”的,公共话语并不拒斥私人情感的表达,但是我们终归是要“讲道理”的,而不是毫无节制的利用煽情去传播自己想说的话,没有任何个体和身份可以既是被告又是法官。任何事物之所以有公共性(比如亲密关系中的伦理与道德)恰恰是因为它与所有人相关,同时又没有标准的答案,我们才需要立足在具体的人和事件上去思考,去分辨,去在视角之间跳跃试着找到一个不那么糟糕的选择。而不是一边依照某种直觉式的,神话式的思维得出一个偏见,再通过堆砌文献和偏向性统计以及语词发明,把自己的偏见科学化,客观化,权威化。
您说“如果说每个人的心理问题像一条河一样,他们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那座桥走过去,而心理(学)只是其中的一座桥,它服务于相信心理学的人。”但如果对于您来说心理学是像星座或是锦鲤这样信则灵的理论,那为什么要不断强调ky是科学的呢?如果现代心理学只是对于这个世界多元的解释方式的其中一种,她并不具有回答人性中那些普遍而恒常问题的能力,甚至没有这样的野心的话,那ky在凭什么立场言说“公共”呢?
而我认为怨恨是没有什么公共性可言的。
那么我们应该对于什么感到愤怒呢?答案之于我大概是您所言的“不重要”的,笼罩于我们时代精神之上的虚无。
关于虚无您的表述是这样的“只要世界上有一个深深懂得你的人、或者是一个帮助你了解你的人存在,和Ta一起时,就真的可以觉得世界是不重要的。虚无是不重要的,因为我们是携手面对着虚无。”
听上去依然十分浪漫不是吗?她提供了一种诱人的想象——在这个复杂荒谬不连续的世界上存在那么一条神奇的界限,在这道界限的内侧我们柔软纯真的内在可以被妥善安放不受到一丝伤害,界限之外的人与事在这种对比下显得肮脏丑陋毫不重要,而划分这条界限的标准叫做“懂得”。因为“懂得”所以我们所有的感觉都必然会被充分的照顾,我们自己也可以彻底的“懂得”自己感受背后的全部原因,只要在ky提供的建议与帮助下,您或许会把这称之为“在自我中安居”。
(图源网络)
在这种想象下世界或者我们置换一个词语“公共”才能被认为是“不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成为自我的内在世界的绝对主宰,“懂我”既是是我们为自己内心的自由王国制定唯一的律法,又是王国最可靠的城墙与海关,它把不懂我们的那些人与事物挡在墙外,只放行那唯一值得被信任与爱的人携手笑看心墙之外一切价值崩解之后荒诞的人群。
可是这样的自问自答般的循环论证不是任性又虚伪吗?(甚至与关于“私人即公共”的论述自相矛盾)我们怎么可能仅仅凭借是否“懂我”来草率的把世界划分成重要的与不重要的两部分?而“虚无”之所以是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它消解了一切坚固的和巨大的事物,个体因而失去了任何可以参照的坐标来定位自身。
我们要怎么去无视虚无投下的巨大阴影来想象那条神奇的界限呢?我们凭什么能确定与自己携手的人就是正确的选择呢?我们靠什么相信所谓的“懂得”不是自欺与逃避呢?依靠心理学吗?可是心理学不是“只服务于相信她的人”吗?又或者一种关于情绪与心灵的科学,一种“有用”但是无关乎善恶对错的“技术”?但是这样不是更加彻底的把人排除出人自身之外了吗?
您用作签名的那句《悲惨世界》里的歌词“生命充满谬误,我把它还给虚无”让我想起《十三邀》里许知远采访马东的那一期。马东先生在这期节目里说出了那句广为流传的自我评价“底色悲凉”,同样是在《十三邀》里,许知远采访哲学家陈嘉映那一期,现场的女编导提问道:“与哲学相处了几十年之后您是否依然有困惑,依然时常感到恐惧?” 陈老师的回答大致是这样的,“困惑和恐惧在平常是力量,而更重要的是哲学培养出与不确定性相处的能力”。
这个时代知道马东喜欢《奇葩说》的人必定比了解哲学知道陈嘉映的人多的多,文化商人看上去比严肃的哲学家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最理想的样子,因为前者敢于在时代尺度的问题上下惊堂之论,后者对基本的问题都要斟酌再三才能给出犹豫的回答。可我想一句“底色悲凉”看似决绝其实远比不上“与不确定性共处”来的诚实,来的勇敢。前者是一种“失望”,是通过把自己放在退无可退的位置来换取那最微末但也看似最坚固的确定性,可后者才更接近“刺破幻象”后真正的清醒。
就像您说“人类最难能可贵的品质就是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寻找到出路”,所以ky讲了许多关于个体通过自身努力幸存下来的故事,这些真实的故事都是动人的,可是而幸存者偏差之外有更多的人无声的沉没在世界的阴影之中。事实是世界是充满不确定的,心灵的样貌也晦暗难明,所以正义并非总是战胜邪恶,赤诚之心多半没有回报,绝望后的希望时常会爽约,而此时此刻驻留在我们身上的幸存里总是少不了偶然的参与。我想这种绝对的随机性包含的“无意义”是多少“失望”都没办法托起的,它只能无限的滑入虚无的深渊里。
而我们自身又在多大程度上是这种偶然性的产物呢?容貌,家庭,天赋甚至一些更加具体而微小的事情都在无比深刻的影响和塑造着我们的生活,选择和命运。就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美国读文科博士或者回国通过一条大致铺好的路进入体制内都是难以想象的选项。对于一个工薪阶层的孩子来说,在年轻时就看够这个世界足够多的风景从而得出“高贵的也好,低俗的也好,都是一样化为乌有”这个结论之前,还有更多琐碎而不堪的事情需要烦恼。
当您还在做咨询师的时候会以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推门进来的访客呢?对于那些可以用黑暗来形容的个案与家庭您会感到悲悯吗?
或者说,除了拥抱虚无我们还有可能做出什么真正的“行动”吗?这是我对于know yourself,对于您同时也是对于我自己怀有的最大疑问。
所幸,我们大致还是年轻的,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去通过感受,思考和尝试来理解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我们自身的复杂性,然后做出抉择以期待能改变潮水的方向,而不是成为潮水的一部分。
所幸,我依旧还相信虚无的背后另有真实,可能是愤怒,可能是悲悯,可能是苦痛,也可能是任何微末的个体能对于世界和自身做出的顽强反抗。
杂七杂八想说的大致就这么多,最后感谢ky曾经给与的慰藉,也希望她能越做越好。
作者的话:
出于各种原因稍微删改了一下。
虽然动笔之前就明白这可能是一个难以去在公共语境下谈论的话题,但还是有些情况出乎意料。之前您在访谈里说不排斥商业化,但是我觉得这篇文章所遭遇的阻力本身就证明了ky所处的立场和ky所言说的内容之间存在某种矛盾。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庆幸自己谈论的是ky而不是其他更加无法谈论的话题?又或者我此刻的庆幸也是一种天真?或者我斗胆再问一句,这样一篇文章对于ky来说是有害的吗?
这是一封公开信,所以才特意使用了在社群的id也提到了具体的人名,我觉得这样的立场可以提醒自己用更审慎的态度去对待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另一点就是我的确认为自己没有恶意,我也认为这些疑问对于钱庄小姐您来说是可以讨论的,不把自己藏起来是一种最基本的尊重。
这篇漫长的论述里我几乎没有下什么结论,我只是就自己所见所感提出疑问,因为我认为ky的面相是复杂的,不应该以非此即彼的态度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但是既然您说“personal is political”,那么公开信就是我能想到的最恰当的方式。而且我也希望能基于事实和具体文本做出尽可能严谨系统的表达。
但是我现在想下一个自己的判断了,我认为对于增长的追求最后会反过来绞死ky自身赖以自立的价值。我认为比起拥有更多的粉丝,说正确的话更重要,我认为拥有资源的人在凛冬里装聋作哑本身就是作恶。
我不认为删了这篇文章会“对彼此都比较好”。
以上。
编辑:西西弗斯
微思客重视版权保护,本文首发于微思客,如需转载,请联系微思客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