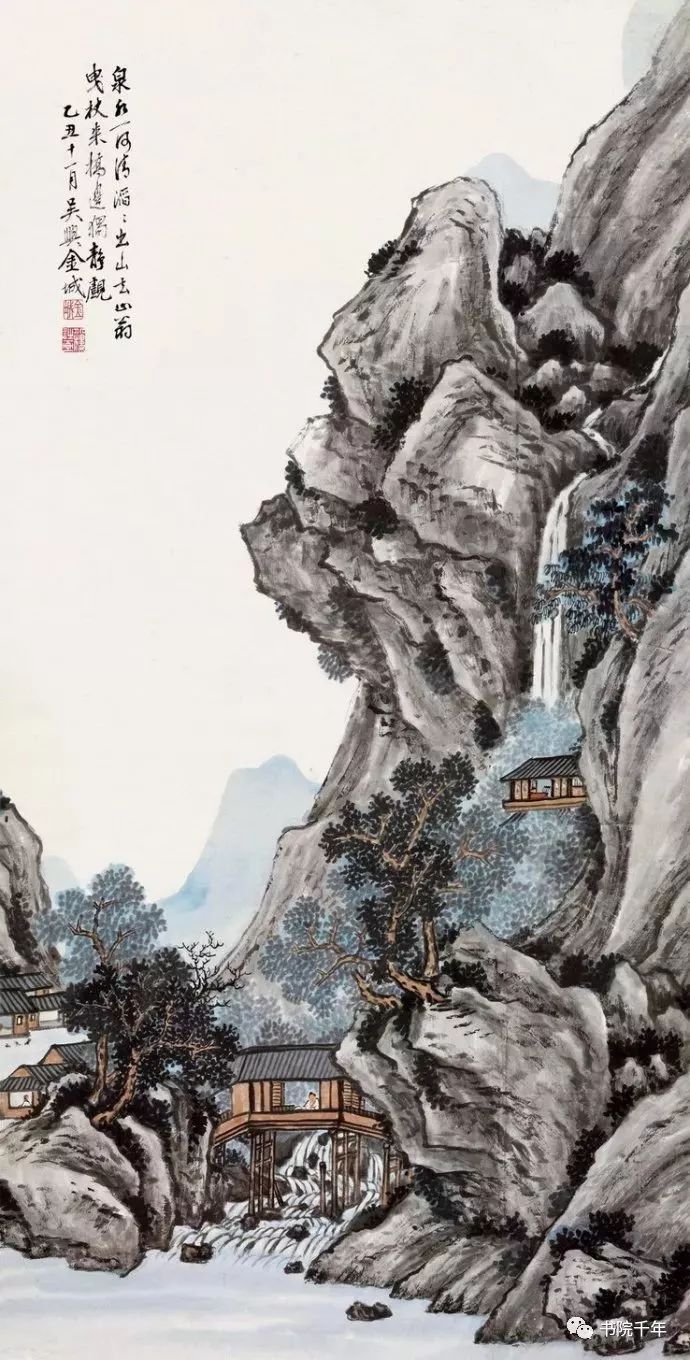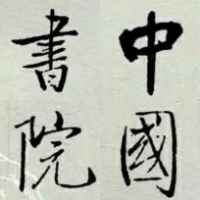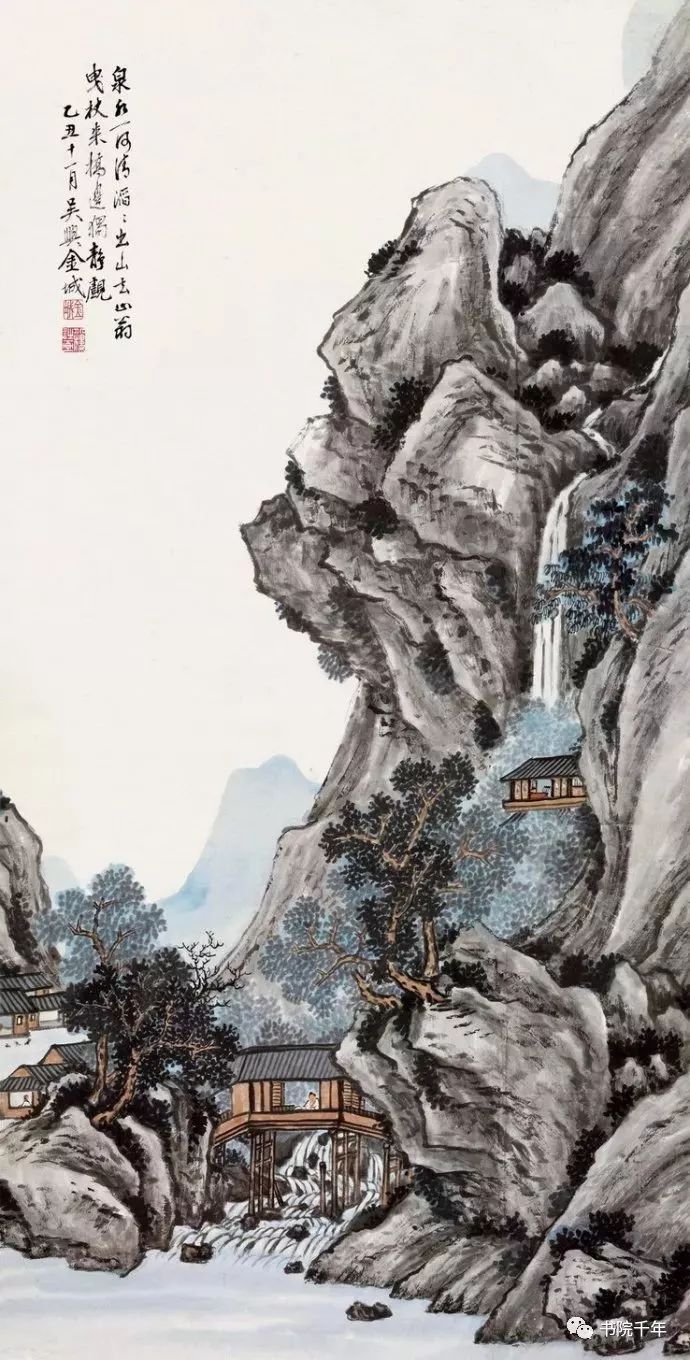李才栋:关于古代书院中实施大学教育的教学组织形式
中国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始于中唐以后,约在贞元、元和间(785—820年),如西川遂州的张九宗书院,江右洪州的桂岩书院,湖湘衡州的石鼓书院等,而江州浔阳陈氏东佳书堂(义门书院)所遗存的唐大顺元年(890年)制定的规章(家法)则可确证唐代民间已有具备教学功能的书院(书堂)[1]。
由唐五代入宋,正如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学,大师多至数十百人。”[2]据此时书院的发展真可称盛。古今学者说到此时的书院有鼎峙江南三书院(杨亿),天下四书院(范成大),海内六书院(盛朗西),八大书院(陈登原)诸说[3]。总而言之,其时著名书院甚众,有十余所之多。
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所以在神州大地涌现,有多种原因,诸如中国早有私家讲学的传统,佛、道两家聚徒山林讲经说法的影响,中唐以后由于宦官乱政、军阀割据,天下大乱,官学废坏,士病无所于学等等。而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书的生产力的提高,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印版本的出现、发展,促使民间书籍的流通量和典藏量的大增,士子求学与师徒传递的教学方式亦逐渐由仅依教师“讲说”,转化为既用“讲说”复有“诵读”的状况,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学校形式:将藏书、教学、习礼相结合的书院。
中国古代的世俗教育,从来有大、小学两个层次(不是大、中、小或高、中、底三个层次)。一般是七岁上小学,十五六岁升大学。故孔子说:“十五而志于学”,“束修以上未尝无悔”。[4]朱熹则明确地规定小学的任务是学其事、学其文,大学的使命才是明其理,讲明小学所学之事、之文的所以然。据朱熹弟子杨骧所记朱熹的话说:“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十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所以为忠信、孝弟者。”[5]江州陈氏东佳书堂在陈氏家法的条规中亦明确规定:陈氏子弟七岁入宅西的书屋肄习,由东佳书堂派学生前来执教。至十五岁选其俊秀者赴离宅二十里的东佳书堂深造。宾客亦延待在彼,一一出东佳庄供应。朱熹曾经非常赞赏其门人程端蒙和董铢所订《学则》,他称其有“古人小学之遗意”。[6]然而朱熹对于他自己创办的书院则主张使学生“苟知其理之当然”,“责其身以必然”。不取仅为“规矩防禁之具”来束缚他们。朱熹“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这大端”揭示之,而鼓励生徒自觉遵守而“责之于身”[7]。由此可见,在朱熹看来他所创立的精舍、书院实与东佳书堂一样是实施大学教育的学校。
一
我国真正独立的、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大学始于春秋战国以孔子为代表的私学,在这以前的所谓“学校”、“庠序”、“辟雍”、“泮宫”,恐怕都是一些官师不分,政教不分的社会上层建筑的综合机构。
在私学刚刚出现的时候,由于书为竹简,甚是难得,故清末著名的经学家皮锡瑞先生在他的名著《经学历史》中说:其时的教学“皆用口授”。即由教师言传身教,传道授业。我们可对这种学校称之为“师授学校”。
正如前面所述直至雕版印刷技术发明以后,才促使学校教学的主要形式,随之而转变为:“视简而诵。”[8]
书院则正是随着这种教学方式的转变而出现的新型的学校、新型的“大学”。
由“皆用口授”向“视简而诵”的转变,这是古代实施大学教育的学校教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飞跃。就教学过程而言是从单纯依靠教师口授向由教师指导下学生自己读书为主的转变。这不仅对学校本身,而且对于中国人民思维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学校教学方式的转变必将影响人们的思想方法的变化。正是指导学生读书,泛观博览为基本特征的书院这类学校教学形式的扩展,促进了唐、五代、宋初疑疏、疑注、疑经思潮的发展。而《七经小传》的作者刘敞,刘攽兄弟恰好正是在临江军刘氏墨庄这所私家讲学、读书的书堂(书院)中成长的学者。
近几年来有一种教学论见解,认定教学是一种“三体现象”。这种见解与过去仅把教学看作是一种教师向学生传递、传输的单向过程大不相同;也与仅把教学看作师生的“双边活动”不太一样。这种见解将教学分解为教师、学生、教学资料三种因素构成的整体。而教学资料则可扩展为学生将要认识的客观世界,或者简化为教材、课本、书等。这种见解认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而学生则是读书,掌握教材、认识客观世界的主体。古代具有教育功能的书院,在其教学活动中强调教师的教导,讲书和学生的读书、理会,正是把教学看作三体现象的典型模式。在书院中,教师说书讲学,学生读书求学,这是书院教学的基本特征,她与先前以“皆用口授”为特征的学校有根本的区别,从而开辟了学校教育发展中“读书学校”这一新的发展阶段。[9]
二
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所建立的书院教学体系,是书院发展过程中又一新阶段。前面说到书院始于唐末,从时间上看,大大早于朱熹,也大大早于理学的产生。有的论者说书院的思想基础是理学,那就不妥当了。然而如果是针对后来的,北宋中叶以后,直至明清的书院而言,那也不算错。因为理学从她一产生就和书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周敦颐、朱熹这些大师既将理学作为兴办书院的指导思想、又通过书院教学传播其理学思想,并使书院的面貌焕然一新,说此时的书院,其思想基础其理学,大概恰如其分。
唐末,具有教育功能的书院产生于兵荒马乱、官学废坏之时,有补于庠序不修之效。宋初赵宋皇期尝未来得及建立州县官学时,书院则已适应赵宋晏武修文的政策需要,适应科举取士,读书做官的时尚而大批涌现在神州大地上了。此时在各地书院中讲学的大师已有数十百人之多,实大有补于官学在数量上不足之效。不仅如此,书院又在教学的方式方法方面有了新的建树,正如前面已经说到的从说书和读书两方面,充分体现了教学中三个要素的作用,在这方面亦有补于原先官学教学“皆用口授”之不足。
正是书院在教学方式上的变化,促进了人们思维发展的新变化,促进了理学的产生。不论是宋初戚同文、胡瑗、孙复、石介,还是周敦颐、朱熹,他们都是在私家讲读的书院一类的学校中成长起来的,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理学孕育于书院之中。
理学从它一产生就与书院建立了不解之缘。从庆历年间周敦颐讲学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和袁州芦溪镇(今江西萍乡芦溪县)建书院始,理学已与书院联系在一起了。理学与书院的结合,当然不是一天完成的。它经过了由周敦颐、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而朱熹几代人的努力,众多学者奋斗的结果。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建立一整套书院办学和教学的模式,特别是他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教条、学规)更是书院这种学校形式成熟的标帜,意味着理学与书院结合的完成。这份揭示经过而后朝廷的支持成为七百年中,书院教学的指导方针。
朱熹所定《白鹿洞书院揭示》包含5个条目和《跋》。这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关于书院教学思想的精髓。
作为理学创始人的周敦颐在创建濂溪书堂时曾对其好友潘兴嗣说:“此濂溪者,异时与子相从于其上歌咏先王之道足矣!”[10]周敦颐在《通书》中又说到:“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士子应“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学圣希贤,歌咏先王之道这是理学家的教育理想。故朱熹在《揭示》中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在这里周、朱二人明确表白了他们所创书院的教育目标。
《揭示》将儒家传统的五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书院教育的基本内容。正如朱熹所说:“学者,学此而已。”
《揭示》又说到“为学之序,亦有五焉”,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其“学、问、思、辩四者”,“所以穷理也”。“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就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总之,穷理的目的是涵养德性,教学的目标是修养身心。
在书院中教学由山长[11]负责。无论是周敦颐还是朱熹,或是吕祖谦、陆九渊,皆自掌院务,亲临讲学、既为经师,又为人师,对学生全面负责。用西方和今日关于教学制度的说法那就是实行了一种教师负责制,或者说“导师制”。当然作为读书学校的书院所实行的教师负责制(导师制)与师授学校有所不同,教师的工作已着重于指导学生读书,履践、修养。当然亦不同于实行班级授课这种教学制度的学校,教师的责任已转由整个学校、各科教师集体承担了。
在实行导师全面负责的教学制度的情况下,书院中采取了多种的教学组织形式。有教师的“升堂讲学”;有生徒个人的“读书”、“作业”、“自修”;有教师与学生的“质疑问难”;有生徒之间的“互相切磋”;有包含祀祭和遵行日常礼仪的习礼;也有优游于山石林泉与考察名山大川的活动;还有组织讲会、诗会、文会,适时展开会讲、会诗、会文活动等等。也还有定期或不定期的考核、课试。
书院的教学中学生以自我进修为主,然而仍是在教师教诲下进行的,故有大师掌院讲学士子不远千里负笈云集的盛况。书院中学生学业进展终与教师的辛勤教导分不开,决不是某权威人士所想像的完全没有教师指导的自学。
三
学生在书院中,在教师的启发诱导下认真读书,自行理会,独立作业,慎独修身。这是书院教学活动中反映书院本身特点的重要教学组织形式。
朱熹的《读书法》是书院中指导学生读书的经典名言。朱熹在精舍、书院中聚徒讲学一贯注重对学生的读书指导。他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门人荟萃教师平时训语,节取其要定为《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咏”、“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此六项据其后学程端礼阐述,就方法而言则以“熟读精思”与“切己体察”尤为重要。前者是“博文”之功,后者乃“约礼”之事。这正是孔子之教和颜子之学的精髓。“用力”要用在“博文”和“约礼”之上;“居敬”也敬在读书和应事之中。这正是孔子之教和颜子之学在书院教学中的承继。在《读书法》的六法中,前二法是就读书本身而言的,而后四者则在学子心理上下功夫,而其展始、致用,恐怕还得要教师的诲教、启发、指导、诱引。
朱熹在白鹿洞时就提到学生作读书笔记的事,以此为“日课”。将精思、涵咏,体察的心得、收获,书写下来,既可由自己玩味,更可呈教师批改指点。关于书院教学中的日记教学法近年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学生在书院中定期作业,或由教师命题,或由学生抽签定题,教师往往作范文以供学生观摩,或推荐学生的作业作为其他同学观摩的范文。作文或要求学生当堂交卷,或按时交卷,教师批改讲评。这里似既有个别教学,也有群体教学的因素。有的教师批改学生作业相当认真,据《碑传集》所载有顾镇其人,“以经师名天下”,先后设教金台、游文、白鹿洞诸书院,终老于钟山书院。袁枚为其撰墓志铭说:“先生淳良介朴,善诲人,每阅文,数百卷旁乙横抹,蒿目龟手,一字不安,必精思而代易之,至烛烬落数升,血喀喀然坌涌,而蚕眠细书,犹握管不止。”
四
书院强调学生视简而诵,熟读精思,同样注意师生之间的质疑问难和生徒之间的互相切磋。
读书有疑难,师生之间相质询,亦大有助于精思、涵咏、体察的展开,如《宋元学案·草庐学案》载:临川熊本闻吴澄教学于崇仁山中,负笈徒步前往书堂,“摘经中所疑七十二条,反复诘难”。吴澄“一一答之,中其肯綮”。熊本竟“为之喜而不寐”。“间论《古文尚书》亹亹数千言,援据精切”。吴澄“器之”。这是学生请教质询教师的例子。亦有先生考问学生的例子,如《宋元学案·双峰学案》载:饶鲁尚赴隆兴府(治今南昌市)豫章、东湖书院,肄业于黄榦门下,黄问其“《论语》首论时习,习是如何用功?”饶鲁回答:“当兼二义,绎之以思虑,熟之以践履。”黄“大器之”。著名的《朱子语类》大都是朱熹与弟子质疑问难的实录。如林用中问:“且涵养去,久之自明?”朱熹答:“亦须穷理。涵养、穷索,二者不可废一,如车两轮,如鸟两翼。”又如朱熹向学生讲解“持守”时说到:“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程端蒙问:“莫是功夫间断,心便外驰否?”朱熹说:“此心才向外,便走了。”再如甘节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朱熹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书院中,似尚有类似后世的“导生”之设,与同学切磋学问,解答疑难。这种学生或称都讲,如杨简讲学慈湖书院以钱时为都讲。有的书院称堂长,还有学长、经长、斋长之设。他们是学生的职事,或负督察之责,或任辅导之务,或者承担勉励学友,互相切磋的使命。白鹿洞书院在康熙间曾明确规定:凡学徒有疑义,先求开示于经长、学长,不能决再叨堂长,再不能决,才请教副讲、主讲。
对于互相切磋的问题,当然不仅存在于“导生”与其他学生之间,在明万历间白鹿洞书院山长章潢所订《为学次第》这分学规中明确要求全体生徒都应“学以会友辅仁为主意”。要求生徒“群居切磋”,“专在辅仁”,“爱众亲仁”,“同归于善”。清代汤来贺主白鹿洞讲席,在学规中亦要求生徒“公心共学”。
五
书院重视生徒自己读书,独立钻研。但决不否定教师的指导、教诲。书院重视教师对个别学生的质疑问难,批改作业……但更为属意于面向学生群体的讲说。正因有大师在书院中讲说教才闻风而集了大批士子,如李觏在盱江书院讲学几十年中东南闻风而来者竟有数千百人。陆九渊升堂讲说于象山精舍,前后五年阅其簿著录者亦有数千人之多。
我们有不少《教育学》的教科书,甚至专著在讲到教学制度和教学组织形式时往往要加上一句,“过去的书院、官学、私塾只有个别教学”的话。往往将教师面向一批的学生,在同一时间,就同一内容,进行教学活动限定为班级授课制度的“专利”。我以为这是一种缺乏中国教育史常识,生搬“洋教条”的现象。其实在中国古代的官学和书院中都不缺乏教师面对一批学生,在同一时间内,就同一命题进行教授活动的记载。
十多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汉代就有大师讲学精舍、精庐,学者数百数千,唐代高僧说法,听者成百上千。这都是同一教者,在同一时间,就同一内容,面向一大批学生,采取讲演、讲授、讲解、讲读以及谈话等方法进行的群体(集体)而不是个别的教学活动。
在五代,史书更有关于南唐庐山国学实行“升堂讲说”,这种教师面对一批学生进行群体(集体)教学的记载。马令《南唐书·朱弼传》称:朱弼知庐山国学,“每升堂讲释,生徒环立,各执疑难,问辩蜂起。弼应声解说,莫不造理。虽题非己出,而事实联缀,宛若宿构。以故诸生诚服,皆循规范”。陆游《南唐书》亦载:朱弼“每升堂讲说”,“座下肃然”。前书所载生徒“各执疑难”,“问辩蜂起”,而朱弼“应声解说”,其所指固然有学徒出题,师生质疑问难的性质,然而朱弼却是在“生徒环立”的情况下面对一批学生,在同一时间,就同一内容进行的答疑和说教,而决非个别教学。后书所载更明白地讲“座下肃然”。
这种升堂讲说的事例曾屡见于史籍。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三月,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初成,白鹿洞释菜开讲,朱熹升堂讲《中庸首章》。次年二月,陆九渊访朱熹于南康军,据《象山年谱》载朱熹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堂讲席”。陆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陆讲得非常生动、感人,有的听讲者流下眼泪,时在春天,天气微冷,而朱熹却“汗出挥扇”。讲毕,朱熹乃离席曰:“‘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再三云:‘熹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朱熹复请陆“书其说”。陆“书讲义”。“寻以讲义刻于石”。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堂讲义》。《象山年谱》还记载了陆九渊在
象山精舍(应天山精舍)升堂讲说的情况。年谱载:“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轿至。会揖,升讲座。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学者又以一小牌书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观此以坐,少亦不下数十百,齐肃无哗。”陆九渊“首诲以收敛精神,涵养德性,虚心听讲”。其讲经“每启发人之本心,间举经语为证,音吐清响,听者无不感动兴趣”。据《宋史·黄榦传》载:黄榦于嘉定间尚与同门友李燔、陈宓等在白鹿洞相会。黄讲《乾坤二卦》其时山北山南士子群集。朱熹另一弟子陈文蔚亦有《白鹿洞讲义》传世。它如朱熹三传弟子程若庸在饶州余干斛峰书院讲学有《斛峰书院讲义》。朱熹四传弟子文天祥在瑞州高安西涧书院有《西涧书院讲义》等。这都是书院中升堂讲说的实录。再如《景定建康志》著录了建康府(今南京市)明道书院师长的十份讲义,他们是江东安抚使兼沿江制置使,行宫留守权兼知建康府马光祖讲《大学》,江东安抚使干办公事兼书院山长吴坚讲《论语》,江东抚干兼山长胡崇讲《大学》,江东抚干兼山长朱貌孙讲《礼记》,建康府节推兼山长赵汝洲讲《大学》,沿江制置司参谋兼山长潘骥讲《太极图并说》,江东抚干兼山长周应合讲《论语》,添差江州教授权充山长张显讲《中庸》,注差山长胡立本讲《大学》,上元县尉暂权充山长翁泳讲《大学》。这每一位师长都在释菜时讲说,既通过讲说开导学生,也是表明自己的学术观点,从而引导学生读书穷理,修身应事。志书还明确记载:“每旬山长入堂会集职事、生员授讲,签讲,复讲如规,三八讲经,一六讲史,并书于讲簿。”
元代仍有许多著名学者升堂讲说的记载。如元贞元年(1295年)吴澄在龙兴路(今南昌市)讲《修己以敬》,路、县学和东湖、宗濂两书院生徒群集听讲。程端礼在集庆路(今南京市)江东书院讲学,有《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传世。明清两代的白鹿洞书院志书中就著录了胡居仁、王梃、蔡宗兖、邹守益、赵参鲁、张治具、朱廷益、葛寅亮、王畿、方大镇等许多人的讲义和讲说提纲。
应该说,升堂讲说是书院中基本教学组织形式之一。
升堂讲说是教师面对一批学生,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内容讲说的教学组织形式,书院中的升堂讲说是实行导师制的读书学校中的一种面对学生群体的教学组织形式。既不同于实行导师制的师授学校和读书学校中的个别教学组织形式,也不同于班级授课制学校的上课这种教学组织形式。这种升堂讲说的教学组织形式可能出现在实行导师制的师授学校中和实行班级课制的学校中,如马融的绎帐设教和现代学校中的大报告。
这里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有的教学论中往往将教学制度与教学组织形式混为一谈。似乎实行导师制的学校只有面向个别人的教学组织形式。而实行班级制的学校才有面向群体的教学组织形式。其实不然,在实行导师制的师授学校和读书学校中既有师生的个别传递、指导、答疑等个别教学组织形式,也有面向群体的教学组织形式。同样在实行班级授课制度的学校也兼有面向群体(集体)和个别两类教学组织形式。我以为在教学论上将教学制度和教学组织形式混淆,认为实行导师制就必定是个别教学,实行班级制度必定是面向群体的集体教学的误区必将突破。
六
书院的教学任务包括穷理与涵养两个方面,而最终目的则在于涵养、笃行。故亦极重视有助于笃行、履践教学组织形式。朱熹等理学家讲敬,不仅敬于学,敬于读书,特别重视敬于习,敬于行、敬于事。而应事、笃行、履践的中心内容,则在于演礼、展礼。
礼,礼的遵行,包含着知识,也包含情感、意志,尤其是包含着行为习惯,而后三者的发展则更离不开履践,实习。习礼成为儒家教育,书院教学的重要组织形式。
习礼包含祀祭和日常生活中礼仪的演习。
祀祭,曾经为诸多学者称之为书院三大使命之一。祀祭什么人物亦被看作为
表示书院学术倾向的标帜。祀祭孔子以及颜回、曾参、子思、孟子,还有一大批哲、贤、儒,这是儒家后学的共同旗帜。而各个学派、各个地区的还有各自特别的祭祀对象。就地区而言,书院多有祀祭本地乡贤、名宦、寓贤的。如欧阳修、周敦颐、朱熹、王守仁等人的出生、游宦、执教之地的书院大都有针对他们的祀祭设施,或称志欧书院或称濂溪书院,紫阳书院,阳明书院,或者就在书院之中设祠祀祭。就学派的书院而言,往往祀祭本学派的大师。如考亭学派祀朱熹及其后学,象山学派祀陆九渊,湛若水办书院祀其师陈献章,汉学家的书院祀许慎、郑玄。鹅湖书院则将参加鹅湖之会的朱熹、吕祖谦、陆九渊、陆九龄同堂而祀。有的家族办的书院则祀本家族的祖先和名人。有的书院还祀祭有功于地方发展,以及书院建设的人士,为他树碑,设主,定时祀祭。
祀祭谁固然是表明书院的宗派旗帜,然而我以为更为重要的是它自身具备的教育价值。祀祭按照朱熹等人的观点这是格物致和的重要途径,它包含着尊师、重道、崇贤、敬学、尚气节、讲风格等诸方面的知识和精神。儒家教育讲究三不朽,崇扬立德、立功、立言。祀祭为国家、民族、地区、百姓、书院、学派作出贡献的人士。这些人是学生的榜样、理想人物。通过对他们的祀祭把教育目标形象化,既敬仰、怀念前贤,又教育和激励后人。其中有丰富的文化传统教育、思想品德教育的内涵,是一种既严肃、又活泼的教学组织形式。据《宋史》记载和吉安地区民间流传故事说,文天祥少年时在学校(一说乡学,一说书院)祭祀时立下了要向欧阳修、杨邦、胡铨等人忠节行为学习的志向,立志将来也要“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在许多书院的志书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很多有关祭祀的记载,在现存的书院遗址中我们亦可以找到祭祀的遗迹。大书院有祀祭的殿堂、专祠,小书院亦有永久性的,或临时性的神主。白鹿洞书院除祀祭圣、哲、贤、儒的礼圣殿(大成殿)及其庑外,先后还有周朱二先生祠,先贤祠,报功祠、宗儒祠、紫阳祠、邵康节祠、忠节祠、启圣祠、三贤祠、崇儒祠、十贤堂、君子堂,以及祀祭有功于书院某某官员的讲堂和专祠(生祠)。岳麓书院除大成殿外亦有诸贤祠、崇道祠、六君子堂、道乡祠、濂溪祠、三闾大夫祠以及祀祭某某长官以及某某山长的专祠。在书院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关于祭祀的仪程、祭辞、祭器、祭物,以及预算开支的记载,几乎应有尽有。书院开学时举行释菜的祀祭活动,春秋有释奠,圣贤生日,忌日往往亦有祀祭。除书院师生外,尚有地方士人、官员、宾客参与。一般皆由书院师长主持,亦有地方官员主持的。
书院的祀祭中有丰富的内容,是重要而生动的教学组织形式,不能因为有所谓“封建糟粕”,“滥竽充数”,“鱼龙混杂”,“刻板烦琐”,而简单否定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书院的有关记载中还有许多日常礼仪的内容。学生对于师长、前辈、朋友、宾客皆有礼仪,上课、休息、告假、饮食亦都有规矩。总之洒扫、应对、进退都是习礼场合。如教师升堂讲说,师生先须共同对孔子神主行三通跪拜之礼,接着学生对教师行一拜,教师还半礼,然后教师开讲。这既是礼仪活动,亦近似现代的组织教学。这是尊师、重道的行为习惯的培养。把教师升堂讲说看作是非常严肃庄重的事情,使师生“且静”,并“专一”于课堂之中。
创办、掌教于书院的学者,固然主张并且身体力行地在课堂中“整齐严肃”,不能“嘻笑”“懒散”,然而也主张藏息相辅。朱熹本人经常带学生游山玩水,寓启示,教诲于山石林泉之中。
考察名山大川,游历城乡,寻古访幽,体察民情,也往往是书院师长培育门徒的重要途径。行万里路是读万卷书的另一方面,也是磨练意志的重要手段。书院生徒由教师带领,或个人或结伴游学是书院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优雅、清静,远离市尘的自然环境,这是书院的设教的首选。既有利于安心读书,亦有助于清心修养,即所谓“绝其尘昏,存其道气”。庆元年间陆九渊门徒彭兴宗访问朱熹,朱还赠诗:“象山闻说是君开,云水参天瀑响雷。好去山头且坚坐,等闲莫要下山来。”
个别书院在履践方面还有自己的特色,如明代著名学者吴与弼在崇仁小坡康斋书院设教。生徒来学均须与其一同参加农业生产的体力劳动,参与从耕耘、栽插、收割、制作的全过程。这是秀才体察民情,磨炼意志手段。在吴与弼看来若不如此,如何到得程颐门下,孟子、孔子门下。《明儒学案·崇仁学案》。
书院中组织生徒参加讲会、诗会、文会,定期、不定期地举行会讲、会诗、会文活动,这也是书院教学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学术界对于讲会这个命题有许多误解。我以为讲会是一种学术团体,学术组织,或称集、或称社、或称会、或称盟。而会讲则是讲会的重要活动方式。
讲会可能是聚徒式书院中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参与者是书院的生徒。也可能大大超出这个范围,成为有广大社会人士参加的社团,而书院则成为这种社会团体的会所。这就是讲会式的书院。鉴于本文所涉及的主要聚徒式书院中的教学组织形式问题,故对于讲会式书院的各种活动就不一一了。然而聚徒式书院中生徒同时参加社会上的讲会活动,这也成为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一种机遇。
作为古代大学的书院,其教学内容、制度和组织形式,以至于采用的教学方法,当然有别于仅仅学其文,学其事的小学。
在书院的历史发展中,也有一些仅具有小学程度的学塾,却滥竽充数地打起书院的旗号,然而我们不能因为有这种的情况出现而否定书院的大学性质。
将德行的修养当作读书的最终目的,甚至近似唯一目标的古代大学教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将学校的一切工作都作为改造思想的手段的时代亦已不再。然而她的教学实践经验和理性思考中的许多问题仍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对教育史和教育原理的研究会有帮助的。
注释:
作者单位:江西教育学院书院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