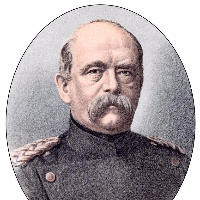罗马征服世界用了三百年,我们征服世界只用了三次战役,而目前的世界比罗马时期扩大了一倍。
——英国政治家霍勒斯·沃波尔
大英帝国作为人类历史上海权帝国的杰出代表,为后世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当我们回顾大英帝国三百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时,可以深刻的体会到:这个帝国就是一个由贸易、战争、信仰和不断进取的精神连接在一起的有机实体;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与之相关的“大陆均势”、“光荣孤立”等早已家喻户晓的政策并非通常认为的是理所当然出现的,而是在英国面临的现实压力下不断探索尝试才形成的。本文即是以此入手,通过回顾大英帝国的构建历程,为读者梳理和分析支撑其海权帝国的基石,从而可以更准确地认识这个“海上的庞然大物”。
对任何一个帝国兴衰沉浮的分析都不能离开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因此,我们在开始论述之前,有必要先搭建好英国崛起的“舞台”。同葡萄牙、西班牙一样,虽然起步稍晚,但英国的海权发展同样根植于那个史诗般的“大航海时代”。1589年理查德·哈克卢伊特的《英国主要航海、航行、交通和地理发现》一书出版,详细介绍了英国早期探索海洋的历史,论证了英国与海洋密不可分的关系。实际上,早在16世纪,英国就已经开始尝试在大洋彼岸的北美洲建立立足点,可惜大多以失败告终。那个时代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的时代,英国则将更多地注意力放在了以近乎海盗的方式与前者的竞争上。
英国在北美洲建立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当属弗吉尼亚殖民地。1607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颁布了殖民许可证,标志着其殖民事业的正式开始。弗吉尼亚殖民地在建立的早期非常艰苦:当时的殖民者没有预想到当地气候条件的恶劣。直到1617年殖民者开始种植从南美洲引进的烟草,才扭转了这一颓势。在当时的欧洲,烟草属于奢侈品,北美洲烟草成功的打开了欧洲市场的大门。在触动了欧洲消费革命按钮的同时也使英国在北美大陆拥有了坚实的立足点。
早期的弗吉尼亚殖民地
与弗吉尼亚的成长史相类似的是英国在加勒比地区的立足点——巴巴多斯。1627年查理一世颁布了巴巴多斯殖民许可。起初殖民者希望将巴巴多斯建设成第二个“弗吉尼亚”,但很快发现这里种植的烟草无法与后者竞争。如同烟草拯救了弗吉尼亚一样,甘蔗种植拯救了巴巴多斯。但是,巴巴多斯的甘蔗种植业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为了补充热带劳动力,黑奴贸易在英属美洲盛行了起来。与此同时,为了拓展贸易市场,十七世纪早期的英国也开始在印度海岸上建设贸易据点。
这就是英国从早期殖民扩张开始一步步发展成海权帝国的起点:英国在北美大陆和加勒比海上的殖民事业,烟草和蔗糖的种植、对欧洲和海外市场的开拓,以及为了补充劳动力而开展的同样利润丰厚的黑奴贸易,这些彼此无法分离的事件将大西洋沿岸的三个大洲连接在了一起,英帝国的雏形由此形成。
行文到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这也是古往今来所有帝国都在思考的问题——如何加强帝国外围领土与帝国中心的联系。克伦威尔统治之下的英国给出的答案是《航海条例》的出台,即禁止英帝国间的海上贸易使用其他国家的船只,也就是说将利润丰厚的贸易垄断权掌握在英国自己的手中。这里就又牵涉到另一个问题——贸易在帝国建设中的作用——与通常的认识不同,国家间贸易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欧洲海权国家是深谙此道的。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西方国家外交普遍遵循的“权力外交理论”,即国家之间的竞争其实就是努力扩大自身的相对权力。贸易直接涉及到一国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对其的把控与调节自然成为扩大相对权力的重要手段。在17世纪那个奉行重商主义的时代更是如此。因此,国家间的权力竞争和贸易竞争从来都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贸易成为大英帝国的第一个基石。
繁荣的海上贸易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理解16至18世纪,英国与西班牙、荷兰和法国之间战争爆发的原因了。让我们离开理论回归史实,来寻找大英帝国的另一块基石。
在先后击败了西班牙和荷兰之后,另一个更加强大的竞争对手出现在了英帝国的成长道路上——法国。英国的贸易扩张不可避免的触及到了法国的利益,正如上文分析到的,贸易竞争很容易就上升为了权力竞争。十七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正值“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的鼎盛时期,其核心目标是称霸欧洲大陆,而此时的英国刚刚完成光荣革命,荷兰执政奥兰治和玛丽登基成为英国国王。因此,法国必须斩断英荷两国之间的纽带。英法之间跨越一个世纪的战争就此拉开序幕,即九年战争(1689-1697)、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4)、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39-1748)、七年战争(1756-1763)以及北美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
老皮特
英帝国的第二块基石正是在这些战争中形成的。英国的国家资源始终弱于法国。1700年法国的人口接近2000万,而英国只有690万。因此,从正面对抗对英国来说显然是行不通的。我们以最具代表性的七年战争为例进行论述。在英国扩张其北美版图的同时,法国人也来到了这一地区并沿着密西西比河北上,希望构建一个连接加勒比海到魁北克的纵贯北美大陆的庞大帝国,这样的版图堵死了英国向西部扩张的通道;另一方面,英王乔治二世同时也是汉诺威选帝侯,也必须保卫其在欧洲大陆上的领土。这就使英国面临着三线作战的困境:保卫本土、保卫美洲殖民地和保卫欧洲大陆上的汉诺威。面对国家的危机,威廉·皮特——获得丘吉尔盛赞的老皮特——登上历史舞台。他力排众议指出,保卫英国在美洲的帝国要优先于在欧洲大陆上的争夺,因此必须将有限的资源更多地集中到这个方向上来。为了配合这一战略,老皮特看似矛盾的给予普鲁士大量援助,“借德意志的刀来置其于死地”。这一战略有效的扭转了英国的颓势,夺回了战争主动权。这里有一点值得说明,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的间歇期,英法争夺北美的战斗始终没有间断,1754年英属殖民地决定联合起来请求英国派兵支援,并得到了英国政府的积极回应。这一事件影响深远,它标志着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重视,同时也用事实说明,殖民地同样有汇报母国的义务。总的来说,正是在七年战争中,英国形成了调控欧陆力量对抗、趁机抢夺海外殖民地的战略,即大陆均势战略的基础。这就构成了大英帝国的第二块基石。
七年战争实际上是一场世界大战
在梳理了史实之后,让我们再次回到理论。英国为何可以战胜国力更加强大的法国,换句话说,大陆均势战略是一个宏观战略层面的指导,我们有必要弄明白其在英法对抗的现实中是得到有力贯彻的基础是什么?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早已众所周知。英国拥有比法国更发达的金融体系,可以在不显著增加赋税的情况下筹集更多的财政资金。第二个原因在于法国的地缘劣势,这是“大陆均势”战略在英法对抗这个事例中得以实现的基础。法国就其本土本土而言面对三个正面:陆地上与尼德兰、普鲁士和奥地利相邻,这是陆地上的正面。由于法国西南边伊比利亚半岛的存在,将法国的海岸分割成了大西洋和地中海两个不相邻的海洋正面,迫使法国无法自由调度其海上力量,因此只能寻求与西班牙的结盟来弥补这一不足。而英国恰恰可以利用这一点,通过支持普鲁士从欧洲大陆方向和自己从海洋方向来夹击法国,夺取主动权。反观英国,作为一个岛国,其所面临的正面全都在海上,通过保卫英吉利海峡来保卫本土、通过切断法国与美洲的海上航线来孤立法属殖民地,即使是在陆地上,也可以通过援助普鲁士来间接地保卫汉诺威。因此,虽然英国的整体资源不如法国充裕,但是其可以更好的将优先的资源调集到发挥最佳作用的位置。这是英国“大陆均势”战略的精髓。
综上所述,大英帝国是一个由本土与殖民地,通过贸易和海军紧密相连的有机统一体。从早期殖民拓荒到贸易兴起再到大国争霸,大英帝国的成长史就是权力政治和地缘政治的现实教科书。贸易与地缘,这就是支撑大英帝国的两大基石。
帝国的根基:贸易和地缘如何成就大英帝国?
罗马征服世界用了三百年,我们征服世界只用了三次战役,而目前的世界比罗马时期扩大了一倍。 ——英国政治
打开APP阅读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