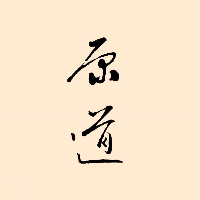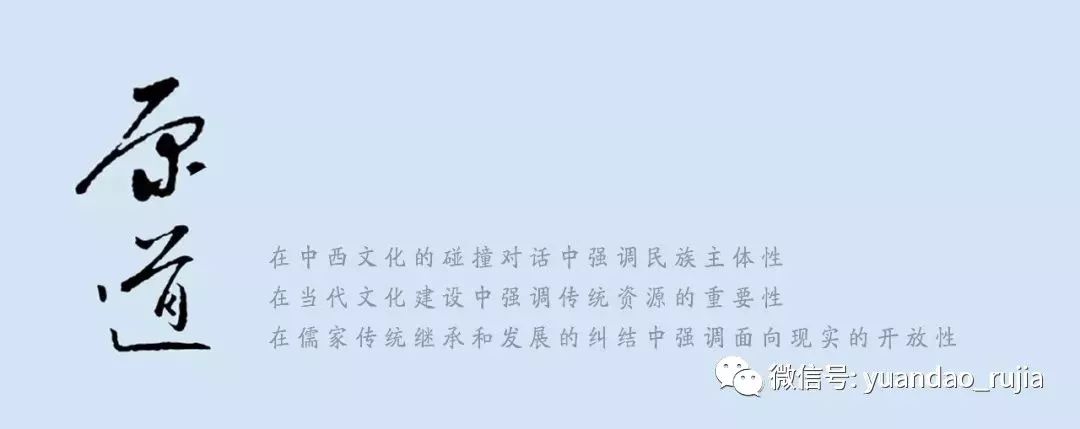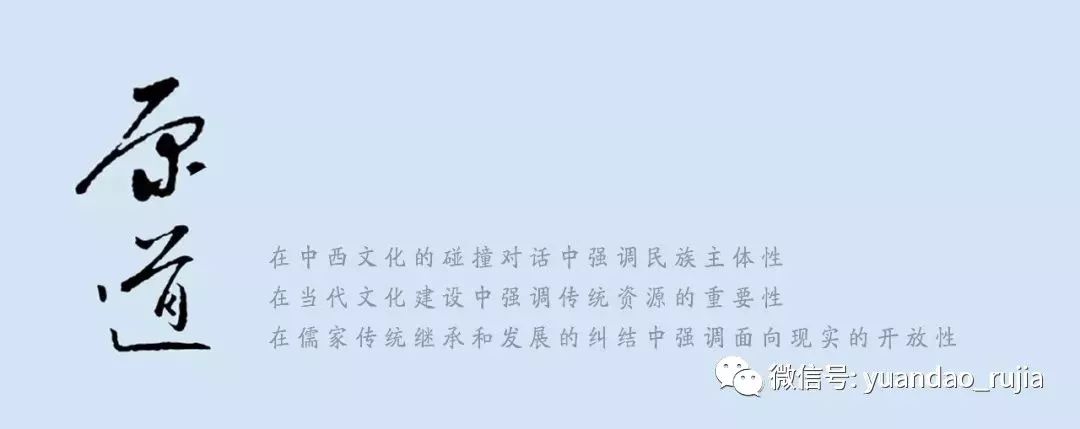
高丽文人诗中的佛教观:以三位诗人作品为例
敖 英
【韩】《韩国文集丛刊》,景仁文化社1990年出版。
内容提要:本文以高丽文人李奎报、李穑和郑道传的诗歌为基础,从对佛教思想、佛教和僧人的看法三个方面考察了三人的佛教观。
佛教在高丽是非常兴盛的,《楞严经》在当时比较流行,尤其受文人的欢迎。因此李奎报、李穑和郑道传了解很多佛教思想,如禅宗思想、法华天台思想、华严思想等等。
但是了解佛教思想不代表他们对佛教思想的理解是正确的,也不能说明他们信仰佛教,是佛教徒。李奎报、李穑和郑道传三人对佛教的许多教义和典故都很熟悉,这是因为佛教在高丽极为盛行。
李奎报与李穑和郑道传对僧人的看法有所不同,因为李穑和郑道传是性理学者,而李奎报则不是。从李奎报、到李穑,再到郑道传,可以看到儒学的影响在逐渐加深,尤其是性理学的影响。
由于本文只是选择了三人的诗歌而不是全部作品,所以可能只反映了他们佛教观的某些侧面而不是全部。
关键词:高丽;文人诗;佛教观;儒学;性理学
高丽时期(918-1392),佛教非常盛行,甚至到了“香灯处处皆祈佛,萧管家家尽祀神”(安珦《晦轩实记》)的程度。佛教在高丽的广泛流行,必然会反映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如汉诗。
本文以三位有代表性的文人:高丽中期亲佛教界的文人李奎报、高丽末期温和排佛论的代表李穑以及彻底排佛论者的郑道传的汉诗为例,尝试通过对他们作品的考察,
分析当时文人的佛教观,即他们对佛教的看法、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和他们眼中的僧人形象,或许由此可以从侧面反映出高丽时期佛教的兴衰及儒佛之间的互动。
- 一、李奎报诗歌中的佛教观
李奎报(1168-1241),字春卿,原名仁氐,父为户部郎中李允绥。李奎报九岁便能做文章,被誉为奇童。稍长后,“经史百家佛老之书,一览辄记”。
(李奎报)
参加入国子监考试前梦见奎星报喜,后果然考取第一,故更名为“奎报”。高丽明宗二十年(1190)登同进士第,惜此后十年间都无升迁。
后经禁中诸儒举荐,补翰林院,后累迁,官至门下侍郎平章事,多年司制诰,“一时高文大册,皆出其手”。李奎报生性旷达,不事生产,自号白云居士,以诗酒自娱,有《东国李相国集》存世。(《高丽史·李奎报传》)
其中《全集》卷一到卷十八是诗歌,《后集》卷一到卷十是诗歌,整个《东国李相国集》大约收录了两千多首诗歌。下面,笔者将考察这些诗歌中与佛教有关的内容,分析其佛教观。
(一)李奎报诗歌中的佛教教义
如《高丽史·李奎报传》中所说,李奎报稍长后“经史百家佛老之书,一览辄记”,且他又多与僧人交游,所以对佛教教义有所了解是很自然的,但他的理解未必是正确的。这一点在他的诗歌中也时不时地反映出来。
1.般若思想。李奎报的诗歌中,出现了佛教的般若思想。其中有的诗歌则直接反映了李奎报对佛教般若性空思想的理解。
如《谦上人观虚轩》一诗:“碍则有所见,虚则复何观。我初观轩铭,于意谓未安。诘师所以名,此名不可删。山河本无形,未识初造端。
苟能循其本,复于空可还。空本合天地,剖判乃为间。还以实相观,天地即一般。心观不以目,何廓亦何关。妙一所独知,凡观安可干。”
李奎报在这首诗开头四句,就对“观虚轩”这个名字提出了质疑。“碍”是有所见,“虚”还用“观”吗?如果我们了解般若学,就知道李奎报的理解是有偏差的,他只知道是要观“有”,不知道还要观“无”(虚)。
不仅要观有,还要观无,才能够既不执于有,也不执于无,不会陷入断灭空。所以诗中从“此名不可删”开始到最后,都是谦上人的解释。
“山河本无形,未识初造端。”,山河本来是无形的,因为不知道(这个)所以出现了以为它们是有形的错觉。“苟能循其本,复于空可还”,如果能寻其本,就可以返回到“空”。
“空本合天地,剖判乃为间”。“空”与“天地”本来是相合的,不过是人为地剖析、间隔开来。“还以实相观,天地即一般”,如果以“实相”观之,天地是一样的。
这才是对于般若思想的正确理解。不过,李奎报把这些写到自己的诗中,也可以认为经过谦上人的解释后他最后理解了“观虚”的含义。
还有一种情况,是李奎报在诗中引用了《般若经》。在《次韵聆首座寄林工部》一诗中,在“吾师释中老,于世真为洲。周回在巨海,高显无狂流。自从得际断,万事徒悠悠”等句子之后,引用了一段《大般若经》的内容,来解释自己为什么称赞“聆首座”于世“真为洲”。
“大般若曰:善现白佛言:何菩萨与世间作洲渚,故发趣无上正等?佛言:比如巨海大小河中高显可居,周回水断,是名洲渚。如是善现色,前后际断,乃至诸佛正等。由此前后际断,一切法断。”这说明李奎报熟悉《大般若经》,随时可以引用。
2.《楞严经》中的思想。李奎报不仅熟读《楞严经》,还在研读过程与其僧统用诗歌的形式探讨教义。
最初李奎报写了《诵楞严经初卷,偶得诗,寄示其僧统》一诗:手披目阅有停时,何似心铭不暂离。诵箒比丘应自愧,伽陀一句善忘遗。
楞严云:周利盘特迦,卽诵箒比丘也。持如来一句伽陀,得前遗后,得后遗前。欲把莲花昼夜观,日沉灯灭见还难。若于三性无昏住,明了心端倍眼看。儒释虽同还小异,时凭法主略咨疑。假饶尽诵藏胸底,那及吾师卷上知。”
前四句说自己读《楞严经》,就像读《心铭》的时候一样,暂不离手。如果此经中的“诵箒比丘”知道的话,会觉得惭愧,因为他连一句偈子都记不住。
第七、八句说想要对于经中的“三性”不迷惑,还得心思清明多看几遍。最后四句,是向僧统请教,因为儒与释还是有点不同,即使自己都记在心里了,也不如僧统从经卷上知道的。
(《楞严经》,中华书局2012年出版)
这是李奎报在读《楞严经》第一卷时作的诗,从诗中可以得知,对于经中的所说的“善恶无记三性”,李奎报可能看了几遍都没理解,所以向僧统请教。
在其僧统回复后,李奎报又写了《次韵其公见和》。这首诗反映了李奎报看到其僧统回复后的思考。
诗云:“忆昔逢公乳臭时,予于外舅家初逢,在一家。一家亲炙未曾离。信然许作阿难比,来诗,以我比阿难。还有亲缘慎莫遗。于予妇为堂弟。我眼先除所观,前尘妄见遣非难。莫论是月还非月,但莫重将第二看。
方识三摩路甚夷,一门超出更何疑。蒙公早指令深挹,免作祈公悔晚知。杜祈公晚见此经,谓张安道曰:知之久矣,何不苦我。安道曰:云云。不可悔,得之早晚也。祈公致仕后见之。予曾为公所引。乃信之。”
这首诗的中间四句是李奎报的思考:“我眼先除所观,前尘妄见遣非难。莫论是月还非月,但莫重将第二看。”意思是说:要先去除看的想法,那么去掉前尘和妄见就不难了。
不管是不是月亮,都不要再将其看作是第二个月亮。僧统回复后,李奎报又写了一首诗:“六用通融互摄时,即于器界傥能离。不然便似凡夫类,性汝真心自失遗。
海眼光中什么观,问师无对问还难。俄然笑指东山语,按上楞严已不看。遣拂心尘尚未夷,刹那分别即成疑。师今纵示无还地,见见元非见所知。”
诗的开头四句是李奎报自己的领悟:只有六用(眼耳鼻舌身意)通融互摄的时候,才能摆脱器世间。否则便和凡夫一样,遗失了自己的真心。
李奎报熟读《楞严经》,结果如何呢?是不是全部理解了呢?答案在他的下首诗《七月初二日,浴家池》中:“我今衰弱怯水寒,六月犹无入池浴。今日炎煎胜夏天,始入池中乱澄绿。
如坐寒冰不奈久,毛发立竖体生粟。一身炎冷自无常,须臾翻覆一何速。洗尘洗体皆幻妄,谁为能触谁所触。见楞严经只应达者知此意,我欲答之道未熟。”
说了“无论是洗尘还是洗体都是幻妄,谁是触摸者谁又是被触摸的呢”这两句后,作者又说,只有理解《楞严经》的人才会知道,我想回答但是我的道还没有成熟。
可见,李奎报自认为自己对于《楞严经》的理解还不够。李奎报与《楞严经》有关的诗歌还有几篇,限于篇幅,不再讨论。
3.禅宗思想和典故。在李奎报的诗歌中,禅宗典故和思想比较常见,这与禅宗在高丽时期的繁盛有关。
如《又和》这首诗,李奎报就用了“丹霞烧木佛”的典故:“万事都空一笑端,尚欺螯叟漫为官。岩连井榻云长湿,地近茶窗雪易残。闲挂铁君经夏结,狂烧木佛御天寒。青山他日应为旧,不惮幽蹊子细看。”
此外还有《复和 二首》:“剩遣谈雷吼舌端,坐敎凿齿作衙官。……相逢得意真些子,莫是他年作梦看。散浪何曾钉一端,只缘上界足仙官。……无心那有安心处,慎勿将心特地看。”
最后一句,是禅宗中土初祖达磨与二祖慧可的一段公案。体现的是禅宗的思想:本来没有心,哪有安心处?如果强调要“安心”的话,那就是执着于有一个“心”的存在。
(二)李奎报对高丽僧人的看法
李奎报对僧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抱有一个平常心的。或者说,李奎报把僧人当作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来看待。
他的诗歌中常有僧人犯酒戒,甚至醉卧路上或寺院中,《戏路上醉卧僧》诗云:“莫笑上人中圣人,醍醐与酒味同醇。始知糟曲神粗猛,解倒金刚三昧身。”
《春日访山寺》诗云:“风和日暖鸟声喧,垂柳阴中半掩门。满地落花僧醉卧,山家犹带太平痕。”这两首诗中,丝毫未见作者李奎报对僧人破戒饮酒的行为有任何负面看法。
《戏路上醉卧僧》这首诗,虽然题目中有“戏”字,但嘲弄的语气并不十分明显。只是感慨酒力之威猛。
而后一首《春日访山寺》,整首诗的意境显得很美。在和风中、暖日下、鸟鸣中、柳荫下醉卧,还有满地落花相伴,像李奎报这样生性旷达的人应是十分向往的。
至于醉卧的是出家的僧人,李奎报也没觉得有任何不妥之处。也就是说,李奎报并没有将僧人看作是天然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他对僧人没有这样的要求,所以他对于僧人犯酒戒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
不仅是酒戒,有僧人犯了色戒,李奎报也给予了理解。《闻批职僧》诗云:“勿论发在与头,好色人心总一般。不有如来神咒力,摩登几已误阿难。此髠谋拙被人擒,国令何曾一一寻。任遣生雏皆壮大,尽驱南亩力耕深。”
这首诗开头两句就是“勿论发在与头,好色人心总一般。”不管头上有没有头发,人心好色都是一样的,所以僧人犯了色戒也是可以理解的。(言外之意,僧人和自己只是有没有头发的分别)如果没有如来的帮助,阿难也可能会被摩登女所误。
在李奎报眼中,僧人没有神圣性。他称他们为“老髡”、取笑他们的光头。如,下面这两首诗。《嘲醉僧夜起嚼冰》诗云:“酒醒中夜嚼寒冰。百品珍羞敌未能。此味平生疑独享。老髠先我饱尝曾。”
《冬日,与僧饮戏赠》诗云:“酒能防凛冽,俗谚号冬冠。秃首如吾子,能无备御寒。”
(三)李奎报不是纯粹佛教徒
李奎报虽然号白云居士,但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佛教徒。虽然他曾经写过的《大藏经道场音赞诗》和《消灾道场同前诗》等诗,也有一些与佛教有关的文章,其中也有“法筵未罢狼烟散,万户安眠亦佛恩”和“天心似水虽难测,佛力如山信可凭”等句子。
但相当部分的作品是高丽国王下令写的,是命题作文,不全是出于李奎报自己的意愿。此外,李奎报也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儒者,他是以“十韵诗”考中的科举,而不是明经科。
正因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儒者,所以他没有从儒佛之辨的立场上排斥佛教。再有,李奎报自己在诗歌中多次表示,自己是道家(道教)这一派的,继承的是李白。
《明日,朴还古有诗,走笔和之》诗云:“乾坤一个身,出岫无心云。师传甘蔗氏,我继仙李君。释老本一鸿,凫乙何须分。何况结莲社,惠远遗风存。(下略)”
《是日宿普光寺,用故王书记仪留题诗韵,赠堂头》诗云:“梦断山窗落月光。耸肩吟到日苍凉。…… ……若将释老融凫乙,莫斥吾家祖伯阳。”
此诗中的“伯阳”应指的是魏伯阳,李奎报将其看作是自己的祖先。说明他还是偏向于把自己看作是道家道教这一系的,而不是佛教徒或者儒者。他研读佛教经典、与僧人交流是出于兴趣而不是信仰。
- 二、李穑诗歌中的佛教观
李穑又与李奎报有所不同。李穑(1328-1396),字颖叔,号牧隐,是赞成事李穀之子。李穑天资聪颖,博览群书,善诗文,以弘扬儒学为己任。先后在高丽和元登第,两次在元做官。
后因母老弃官返回高丽,历任高丽右谏议大夫、成均大司成、大司宪等,元征东行中书省儒学提举、征东行中书省左右司郞中等,为一代儒宗。因立王一事,与李成桂、郑道传等人对立,又几次被贬、流放。
(李穑)
李穑一生从无疾言厉色,不露锋芒。他和李奎报一样不治生产,虽屡陷窘境,亦不以为意。有《牧隐集》行于世。(《高丽史·李穑传》)
《牧隐集》有五十五卷,其中诗稿三十五卷,文稿二十卷,诗稿中有八千余首诗歌。笔者将考察这些诗歌中的佛教思想、李穑对佛教的看法以及对僧人的态度等。
(一)李穑诗歌中的佛教思想
李穑的诗歌中有不少佛教思想,包括般若思想、华严思想、法华思想、禅宗思想等等,也引用过《圆觉经》和《楞严经》等。
1.般若思想。般若思想在李穑的诗歌中较常见。如下面这两首诗中所出现的“人法二空”、和“昔物不至今,今亦不至昔”等。
《自戏》诗云:“褴褛山僧踏软红,自知人法本皆空。笔端赖有真三昧,缕析疑团一牧翁。”
《送定慧瑚大禅师。得庵字》诗云:“机锋不借中人上,道韵难磨北斗南。欲识吾师真活计,江风松月一茅庵。屐留夏雪长吹北,锡卓秋鸿不到南。何用更过葱岭去,算来天下小于庵。昔也非来今岂去,偶然从北却还南。诸公不用勤相送,且举吾言问拙庵。”
本首诗中的“昔也非来今岂去”,源自僧肇《物不迁论》中的“昔物不至今,今亦不至昔”的思想,学界对这句话指的是物质的运动与静止还是反对法身“三世实有”说有不同意见,李穑在这里显然谈论的是运动与静止的问题。
2.华严思想。下面两首诗都提到了重重珠网、重重帝网,也就是因陀罗网。因陀罗网出自《华严经》,譬喩诸法之一与多的相即相入、重重无尽。
《与廉政堂、韩签书约,同诣光岩陵行礼。夜坐。既明有作》诗云:“三人相次拜承宣,蹇步如今尚在前。少壮自甘曾去位,老衰胡不便归田。重重珠网含三界,寂寂山陵闭九泉。碑上数行犹未刻,流传石本定何年。”
《有怀幻庵》诗云:“如来藏号大光明,因地由来有法行。智慧空华知上发,根尘世界觉中生。重重帝纲真同体,的的禅宗可杭衡。欲听幻翁重说偈,光岩钟磬杂松声。”
3.法华思想。李穑的诗歌中还有法华思想。《奉贺懒残子新封福利君》最后两句“况是一云能普雨,时看药草偏丘原”,出自《法华经·药草喻品》中“其云所出,一味之水,草木丛林,随分受润。
一切诸树,上中下等,称其大小,各得生长,根茎枝叶,华菓光色,一雨所及,皆得鲜泽。”
就像这一大片云彩雨润一切草木一样,佛之出现于世,为众生开、示、悟、入诸法实相,众生也随类各得其解。李穑在这首诗中用来赞扬懒残子。
《奉贺懒残子新封福利君》诗云:“龙山一朵碧当门,净对莲经道自尊。奋号懒残忘世事,新封福利荷天恩。神清只有诗魔扰,业白宁容物累昏。况是一云能普雨,时看药草偏丘原。”
4.禅宗思想。禅宗在高丽时期是影响力最大的佛教宗派之一,禅宗的思想和公案也为人们所熟悉。这在李穑的诗歌中也有所体现。
(慧能)
《寄莲花禅师夫牧》这首诗在开头就说出“直指人心不用文”。这是禅宗的著名宣言“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一部分。诗云:“直指人心不用文,藏经题目尽纷纷。小窗出定无余事,坐对长空万里云。”
而下面这首《有怀幻庵》诗中,“指或执为月”说的是,有人会将指月之手指误认为是月亮,但实际上它不过是一种善巧方便,佛教经文也是如此,所以禅讲究“不立文字”。
“矿非烧有金”,说的是矿石不是经过冶炼之后才有金子,而是它本身就有。佛性也是如此,人人都有,不用向外求。诗云:“寂灭元无隐,宣扬却甚深。真机真兔角,似量似猿心。指或执为月,矿非烧有金。两忘情境处,更向幻庵寻。”
此外,李穑《访僧不遇》诗还引用过《楞严经》中阿难与摩登伽女的故事。诗云:“市利朝名共一途,独骑羸马访浮屠。纸窗肯借终年坐,蒲荐犹难尽日趺。乞饭行时随柳岸,戴经归处傍莲湖。知师本自心清净,虽遇登伽不足虞。”
(二)李穑对佛教的看法
李穑是一位性理学者,也以弘扬儒学为己任,但却被人讥讽“佞佛”。我想,这与他性格有关(一生都无疾言厉色),也与他对佛教、对僧人复杂的、暧昧的、摇摆不定的态度有关。
1.李穑认为“佛教是异端”。《指空弟子见访》诗云:“异端超世敎,盛馔慰寒生。野果谈余嚼,宫壶拜后倾。拙辞包不尽,妙道固难名。逸事谁能传,须凭牧隐铭。”
诗的第一句,李穑就点题了,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佛教是异端”,而这个异端已经超过了世俗的教化。
2.李穑不相信有佛慈悲济物。《消灾法席辍讲》诗云:“遇灾深惧似冰渊,数日君王辍讲筵。自是五行频失序,须知一念旋通天。慈悲济物终难验,恻隐存心要在坚。头白老臣无所祷,只忧人欲苦相煎。”
3.李穑不相信无我说和轮回说。下面这首《遣兴》诗,开头两句是李穑对事物的看法,天地间的事物运动变化是由于“气”的运化。
第三、四句则是怀疑佛教的“无我”说,如果由地水火风这四大都不是我的话,那承担过去、现在和未来果报的是谁呢?即轮回的主体是谁呢?这确实是佛教“无我”说面临的最大质疑。
最后两句,既然万物最后都会消失,那还需要百世师(佛)么?诗云:“悠悠天地阔,气化自推移。四大皆非我,三生果是谁。日斜诗满纸,雪落酒盈巵。乘化聊归尽,何须百世师。”
4.李穑一些行动会给人以错觉。有人认为他是佞佛的。如,李穑去佛殿上香,写下《龙头敦公临行,过门告别》诗云:“残暑犹侵我,新凉乍可人。心应在山水,身已离风尘。云散明江练,天高耿月轮。泊舟登佛殿,祝上奉千春。”
但李穑也曾有过与此完全相悖的举动。据《高丽史·李仁复传》记载:“王大设文殊会, 率两府礼佛,唯仁复与李穑至拜时,辄出不拜。”当时李穑四十岁左右,而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已经是晚年屡遭变故之后了。
另外,他还曾礼拜过观音,不过也是晚年的时候,此诗作于骊兴,是李穑晚年被贬后所生活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李穑去礼拜观音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孟秋望日,记事有感》诗云:“盂兰盆法出西天,震旦翻为解倒悬。举国奔驰唯恐后,愧吾流落尚如前。两瓶花蕊真无几,一穟香烟遍大千。幸得祖堂新粳米,日中拜献白衣仙。”
(三)李穑对僧人的看法
李穑与僧人交往很多,但是他处于性理学者的立场,始终对僧人有不满,觉得他们像老鼠和鸟雀一样,不劳而获,靠游食为生。
见下面这首《监郡公送麦二石、脂麻五斗》诗:“老牧今游食,真如雀鼠僧。遨头作檀越,经卷可长蒸。”这首诗写于建郡公送给他小麦和芝麻之后。李穑接受了这些后,是有些羞愧的,觉得自己是不劳而获的,就那些僧人一样。
在李穑众多的诗歌中,笔者觉得下面这首《寄汉阳尹》最能代表李穑对僧人看法,也非常符合他儒宗的身份。
诗云:“三角山中青壑寺,觚棱掩映烟霞里。居僧朝夕眠食耳,斤斧岂嫌劳不已。但患支离四体倦,或者疾生医未易。其人既曰去人伦,上报重恩虚语尔。不如且放山中去,猿鸟鹿麋而已矣。秋风满天野青黄,乞食过冬是其志。九牛一毛岂足惜,老牧斯言亦人事。”
诗中第三句“居僧朝夕眠食耳”,意思是僧人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吃饭和睡觉,清闲得很。“其人既曰去人伦,上报重恩虚语尔”两句,说的是僧人已经抛弃人伦,宣称要上报重恩不过是空话罢了。
“不如且放山中去,猿鸟鹿麋而已矣”,不如把僧人放回山里,因为他们和猿、鸟、鹿、麋等禽兽一样,“乞食过冬”才是他们的志向。
如上所考,李穑了解佛教思想,也与很多僧人交游,但是他并不相信佛教,不相信佛教的教义,不相信佛能够慈悲济物,把佛教视为异端。他对僧人的看法也是比较负面的,把他们看作是与老鼠、鸟雀、猿猴、麋鹿一样的禽兽。
- 三、郑道传诗歌中的佛教观
郑道传(?-1398),字宗之,号三峰,父亲是检校密直提学郑云敬。高丽恭愍王时(公元1362年)进士及第,次年任忠州司录,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1366年父母连丧,郑道传“克终圣制”,庐墓三年。恭愍王十二年朝廷重营成均馆,郑道传被诸贤推荐为成均馆博士,“每日坐明伦堂,分经授业”。1371年获授太常博士。
后历任礼仪正郞、艺文应敎、成均司艺等,以文学见称。在之后的政治生活中,郑道传几起几落,曾被流放数次。
(李成桂)
在郑道传的辅佐下,李成桂建立了朝鲜王朝,并用性理学的理念,建立了朝鲜王朝的文物制度。可惜最后死于宫廷的权利斗争中。
与李穑不同,郑道传对佛教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态度,在他的努力下,性理学超越了佛教,成为朝鲜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
郑道传有《三峰集》传世。《三峰集》14卷,卷1、卷2收录诗歌共228篇。笔者将考察这些诗歌中承载的佛教思想,分析郑道传诗歌中的高丽僧人形象。
郑道传的诗作现存不多,是李奎报诗歌数的十分之一左右,与李穑相比就更是小巫见大巫。而在这二百多首诗歌中,与佛教有关的也不多,所以笔者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讨论。
(一)郑道传诗歌中佛教思想
郑道传是比较了解佛教思想的,这在他的著作《佛氏杂辨》中得以充分反映。他的诗歌中,也有所涉及。
如下面这首诗:“贞白子问于玉洁先生曰:诗可学乎?曰:不可。学诗如学禅,自有古人公案。先生因甚道诗不可学?曰:待汝学禅了,方向与汝道。曰:学则不问。请问不可。曰:言之则触,不言则背。
触也落这边,背也落那边。不触不背,中中而入。方许你觑得本分风光。曰:弟子根机下劣,时缘未到。今闻先生之言,与蚊虻咬铁牛相似。请先生不惜方便,下一转语。以终惠焉。先生默然良久,微吟上八絶。
贞白子听之,竦然有个省会处。即呈偈曰:缕玉制衣裳,啜冰养性灵。年年带霜雪,不识韶光荣。又:夜静雪初霁,淡月横半天。肠断江南客,哦诗独不眠。先生曰:汝得吾皮肉。婆娑广寒夜,冷淡楚泽秋。一般清气味,独自占风流。
又:明牕横棐几,不许素尘侵。燕坐读周易,端的见天心。先生曰:汝得吾骨髓。贞白子欣然而乐曰:不亦善乎?问一得三,闻诗闻禅。又闻君子之心切于老婆也。西湖人不见,天地徒为春。
旷然千载下,冥会精与神。先生曰:白也,可与言诗矣。其告也,往也。其知也,来也。先生自是不复言诗。如有请者曰:贞白子在。”
这首诗较长,作者用对话把五首短诗串起来。本诗中的佛教思想主要在序文中,有两处:一是“言之则触,不言则背。触也落这边,背也落那边。不触不背,中中而入”这段话,在这段话里,郑道传运用了佛教的“不落两边,也不落中间”的中道方法。
另外一处是“弟子根机下劣,时缘未到”一句,涉及到了佛教的“根机”“时”和“缘”这三种教义。“根机”是接受佛法的能力。
佛教认为佛是针对众生的根机来说法的,先说浅显易懂的法门。待根机逐渐成熟后,接受佛法的时间恰当,因缘具备,再授以更高深的教义。
下面这首诗,也有两处与禅宗的思想有关。序云:“次韵题日本茂上人诗卷 庚午,公使还居开京时。按:时日本僧永茂来住石房寺。”
诗云:“一叶扁舟万里行,石房二载住开城。人来问法扬眉见,客至敲门合掌迎。念起心源还自寂,道高骨格不胜清。五台何处寻师去,认听钟声半夜鸣。按:永茂欲游五台山。”
一是“人来问法扬眉见”一句,说的是禅宗说法的方式,语出《楞伽经》,唐译本即《大乘入楞伽经》说的更清楚:“佛言:大慧!虽无诸法亦有言说,……大慧!或有佛土瞪视显法,或现异相,或复扬眉,或动目睛,或示微笑嚬呻謦欬忆念动摇,以如是等而显于法。
大慧!如不瞬世界、妙香世界及普贤如来佛土之中,但瞪视不瞬,令诸菩萨获无生法忍及诸胜三昧。大慧!非由言说而有诸法,此世界中蝇蚁等虫,虽无言说成自事故。”
另外一个是“念起心源还自寂”,说的是虽然意念源于心,但心本身是寂灭。不过,也可以解释为,意念起于心源,但本身是寂灭的。这两种说法,在永明延寿的《宗镜录》中都可以找到依据。
(二)郑道传诗歌中的僧人形象
《寄瑞峰宽上人》云:“桑门有上首,余事能文章。谁谓道里远,跂予可相望。夫何在网罗,未得翔其傍。题诗代良觌,仿佛接清光。”
诗中除称赞宽上人“能文章”以外,还表达了自己困在尘世的罗网中,不能在其身旁的遗憾之情,似乎郑道传非常羡慕僧人的出世。不过,在下面的这首诗中,郑道传又有所不同。
序云:“古岩道人,故先生崔兵部之弟也。予游先生门受业时,岩尚读书。先生卒,与岩别二十余年。见于陶隐斋,乃祝发为浮屠也。感叹久之,因书其诗卷焉。”
诗云:“伯氏斯文秀,微言共尔闻。别来经岁纪,那料入空门。慕古岩为号,居今世不群。此行何日返,有便问温存。”郑道传在这首诗的序言里,讲述了写这首诗的缘起。
他与授业恩师的弟弟二十年未见,再见时,已经“祝发为浮屠”,成了“古岩道人”。所以郑道传“感叹久之”。
为什么感叹久之呢?因为在郑道传看来,“浮屠人,出家与世,弃亲如遗。其他宜若无以为意也”。可见,郑道传对僧人的看法是符合他儒家的身份的。
- 四、结 论
通过对李奎报、李穑和郑道传这三位高丽文人诗歌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
首先,佛教在高丽是非常兴盛的,因此李奎报、李穑和郑道传了解很多佛教思想,如禅宗思想、法华天台思想、华严思想等等。但是了解佛教思想不代表他们对佛教思想的理解是正确的,也不能说明他们信仰佛教,是佛教徒。
其次,李奎报与李穑、郑道传对僧人的看法有所不同。他并未将僧人看做是有别于自己的出家人,而是把他们当作是普通人来看待,所以他看到醉卧路上的僧人、听说僧人犯色戒被抓,都没有表现出负面的情绪,反而给予理解。
这既与他生性旷达有关,另外,也与他不是一个儒者有关。但李穑和郑道传都是性理学者,性理学本就是对佛教的反动,因此他们都认为出家是抛弃人伦的事情。虽然他们有时也会羡慕僧人的出世生活。
第三,从李奎报、到李穑,再到郑道传,可以看到儒学的影响在逐渐加深,尤其是性理学的影响。李奎报以道家(道教徒)自居,没有门户之见。一再强调“释老本一鸿”,不分彼此。
而李穑则认为佛教是异端,他希望儒学可以逐渐兴盛起来。而到了郑道传这里,则是以“辟异端”为己任了。
第四,《楞严经》在高丽时期比较流行,受文人的欢迎。李奎报、李穑都在诗歌中引用过。李奎报有好几首诗都是读《楞严经》的时候写的。郑道传在《佛氏杂辨》中也有引用。
当然,本文只是反映了李奎报、李穑和郑道传三人诗歌中的佛教观,难免有偏颇之处,日后将继续研究三人其它文学体裁作品中的佛教观。
敖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