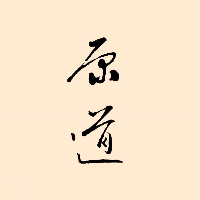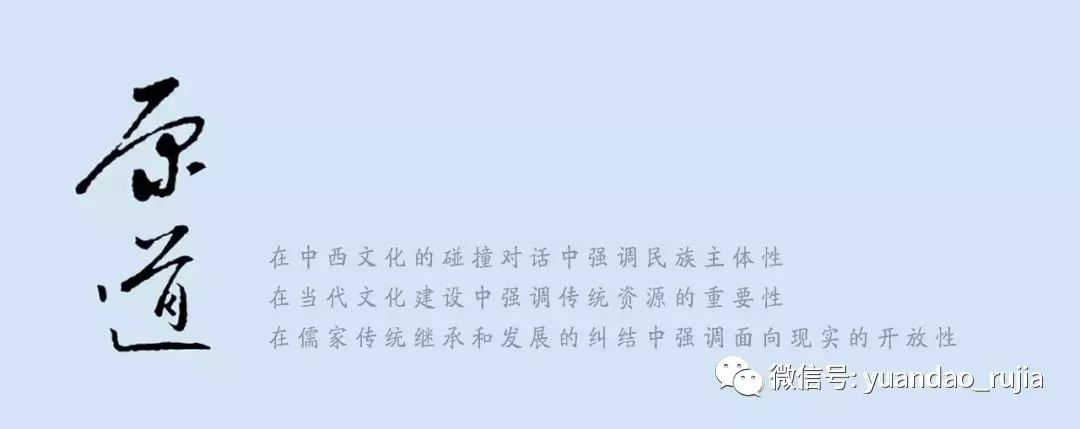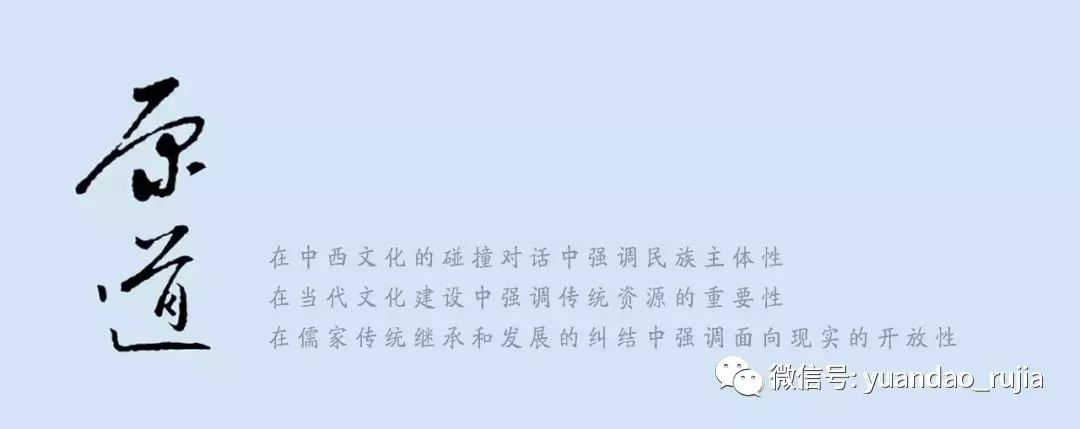
吉尔赞喀勒墓群遗存的文化意涵 巫新华
(【伊朗】贾利尔·杜斯特哈赫选编:《阿维斯塔》,
201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内容提要:2013-2014年,新疆塔什库尔干县帕米尔高原吉尔赞喀勒墓群考古发掘出土了七颗国内迄今年代最早的天珠和其他一些较为特殊的文化遗存。
本文依据琐罗亚斯德教圣书《阿维斯塔》记述的内容,对本次出土天珠和相关遗存的文化意涵进行分析发现:一方面,天珠的珠体上蕴含着琐罗亚斯德教倡导的善恶“二元对立斗争”的宇宙观以及“抑恶扬善、善必胜恶”的宗教核心思想。
联系“最早的天空是石头”的文化观念来看,琐罗亚斯德教徒认为天珠是灵石和上天的神圣组合,具有神格化的意涵。天珠作为琐罗亚斯德教信徒随身佩戴的信物,为我们揭示了他们的精神信仰和宗教崇拜等精神世界的文化内涵。
另一方面,这批国内发现最早的天珠与地表黑白石条遗迹以及装盛在火坛中的黑白卵石遗存相互呼应,彼此关联地向我们表明它们是早期琐罗亚斯德教文化的直接表达。
关键词:天珠;火坛;琐罗亚斯德教;吉尔赞喀勒墓群;特殊数字崇拜
- 一、吉尔赞喀勒墓群遗址基本文化特点
吉尔赞喀勒墓群遗址所在的帕米尔高原,是亚欧大陆两条最大山带(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山带和帕米尔——楚科奇山带)的山结,也是亚洲喜马拉雅山、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等主要山脉的汇集地,素有“万山之祖,万水之源”之称。
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库尔干河谷区域的西、南部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接壤,这里不仅是帕米尔高原八帕中最著名的塔格敦巴什帕米尔腹地,也是亚欧大陆巨大地理区域接界处,而且还是亚欧大陆几大语族、各大文明区域的交汇点,也是人类古代文化在中亚地区最重要的高原通道之一。
吉尔赞喀勒是塔吉克语“Jerzankol”,意思是“鹰站立在岩石上的地方”。吉尔赞喀勒墓群所处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孜那甫乡曲曼村东北塔什库尔干河西岸的吉尔赞喀勒台地,海拔约3050米左右,墓群地表保留有墓葬的圆形石圈和大面积错落有致的黑白石条遗迹。
我们于2013-2014年对吉尔赞喀勒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根据已发掘墓葬中提取的15块人骨、木材、炭屑和织物标本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的数据资料,以及出土文物的类型学推论证据来看,古墓群遗址年代距今2400-2600年。
墓群文化内涵为广义的塞人文化,但是墓群的地表遗迹和诸多出土文物使墓群呈现出业已成熟的早期琐罗亚斯德教文化内涵。
同样类型的古墓葬遗址,经调查在塔格敦巴什帕米尔地区发现还有八处,分别位于帕米尔高原提孜那甫乡北部河谷台地、班迪尔乡塔什库尔干河谷台地、科克亚乡河谷台地、热斯卡木乡河谷台地等地。
另外,境外塔吉克斯坦大帕米尔卡拉库里湖地区也分布有Karaart,Shurali,Jarty Gumbez和Ak-Beit等用黑白石条铺设的三十多处所谓“地画遗址”。
在如此广阔的帕米尔高原地域,多地分别发现铺设黑白石条古墓群遗址,表明这种铺设黑白石条的文化遗迹应该是墓群遗址所在时期曾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
(大流士一世)
古波斯《贝希斯敦碑铭》用古波斯语、埃兰语和阿卡德语配以浮雕的形式向我们讲述了大流士一世及其继任者薛西斯已经信奉了琐罗亚斯德教。公元前550年,居鲁士二世建立了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前522-前486年)将版图扩展为世界上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庞大帝国。
那时琐罗亚斯德教的传教区域主要在讲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朗语诸部族聚居的古波斯帝国东北地区,相当于今阿富汗、呼罗珊及其他中亚地区,包括帕米尔高原。
吉尔赞喀勒墓群遗址不但在年代时间节点上与上述事件相吻合,而且遗址所在地理位置也处于上述事件发生的地理范围之内。除此之外,遗址所蕴涵的文化内容也与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所接受的早期琐罗亚斯德教文化信息相一致。
- 二、墓群出土的天珠及其他遗存情况介绍
“天珠”是指古人用来自大自然的蚀花原材料对半透明的白玛瑙珠的表层分别进行黑、白两色化学蚀染,从而获得表面具有特殊文化意涵纹饰的古代工艺品,古人视之为具有护身符功能的珠宝。
天珠是古代蚀花玉髓(玛瑙)珠的一个种类,关于古代蚀花玉髓珠的研究,夏鼐先生根据其制作材质的不同将这类遗存分为蚀花肉红石髓(红玉髓)珠和蚀花玛瑙珠,此类遗存在我国藏族地区也有发现。
汤惠生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在西藏居民的认知观念中,这种经过黑白两色蚀花得到的古代艺术品并非来自人间,而是一种来自阿修罗世界或谓来自天上的珍贵珠宝,故有“天珠”之称。
(一)吉尔赞喀勒墓群出土天珠情况介绍
2013-2014年,吉尔赞喀勒墓群经考古发掘出土了51颗蚀花玉髓珠,其中7颗天珠集中出土于M11和M32中,为国内迄今发现年代最早、数量最多、且成组出现的考古发现。这些珠子的珠体呈现出繁杂多样的受沁现象,其受沁机理已有讨论。下面,我们介绍M11和M32中出土天珠的情况。
(吉尔赞喀勒墓群)
M11位于B区黑白石条带东侧台地边缘,墓葬表面无明显的封土堆,中间略塌陷。地表散落较多小卵石。墓口石围在表土层下约15-20cm,平面大致呈不规则圆形。堆砌石围的石块风化严重,表面呈颗粒状。
竖穴墓室平面呈椭圆形,深度为130-160cm。墓室内自东北向西南平行排放三个女性个体人骨,尸骨下有尸床,为一次葬。1颗圆柱状天珠出土时位于其中一位女性尸骨的颈部位置。
这颗天珠呈圆柱状,黑底白纹,中间略粗逐渐向两端收细,端部平齐,中间蚀绘一条较宽的白色圆圈纹环绕着珠体。珠体长度为2.04cm,最粗部位直径为0.82cm,一头钻孔的孔径为0.14cm,另一头钻孔孔径为0.16cm。
M32墓葬位于B区台地墓葬区西端,地表有较明显的封土堆,封土堆下有一重墓口石围。地表散布许多细小砾石。竖穴墓室,墓道口铺有草席,其中葬有两具尸骨。
6颗天珠出土时位于其中一位墓主人的颈部,显然作为项饰佩戴。其中出土的5颗天珠为圆柱状,珠体中间直径较大,逐渐向两头收细,两头端部平齐,中间有贯穿钻孔。
每一颗珠子都蚀绘有五条宽窄不一的白色圆圈纹环绕着珠体,中间的圆圈纹相对较宽,被这条较宽的圆圈纹均分的黑色珠体部分又分别被两条相对较窄的白色圆圈纹均分,从而形成了中间为较宽的白色圆圈纹,其两边分布两条较窄的白色圆圈纹的对称形态。
这五颗圆柱状天珠的尺寸分别为:第一颗天珠的珠体长3.53cm,珠体直径最大处为0.96cm。两头钻孔的孔径,一边为0.16cm,另一边为0.17cm;第二颗天珠的长度为3.04cm,珠体直径最大处为0.93cm,一头钻孔的孔径0.13cm,另一头孔径为0.14cm;
第三颗天珠的长度为2.59cm,珠体直径最大处为0.9cm,一头钻孔的孔径为0.15cm,另一头孔径为0.17cm;第四颗天珠的长度为3.03cm,珠体直径最大处为0.85cm,两头钻孔的孔径分别为0.13cm;第五颗天珠的长度为2.29cm,珠体直径最大处为1.04cm,两头钻孔的孔径分别为0.14cm。
M32还出土了一颗圆板状天珠,黑底白纹,背面较为平直光滑,蚀绘有图案的另一面的珠体稍稍凸起,沿圆板状的外沿用双线的形式蚀绘出一个“U形”圣火坛的象形图案。
天珠两孔之间的距离为2.81cm,厚度为1.02cm,一头钻孔的孔径为0.16cm,另一头的孔径为0.12cm。
目前国内其他考古出土和馆藏的天珠资料,计有:1979年在塔什库尔干县香宝宝墓群中发掘出土的1颗天珠,年代和这7颗帕米尔高原出土天珠年代大致相当;
国博的常展柜里也陈展了1颗战国时期的天珠,展示牌标注为“蚀花髓管饰”;2014年在西藏阿里地区曲踏墓群也发掘出土了2颗天珠,其年代距今1800年左右;
1975年在陕西咸阳市西郊的马泉西汉晚期墓中出土了1颗天珠;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晚期的楚国墓出土2颗天珠,一颗藏于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另一颗藏于淅川县博物馆;
云南省博物馆馆藏的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的1颗天珠,年代在前221年-前207年,其形状和蚀绘纹饰的分布都比较特别;长沙市博物馆藏有1颗天珠,出土于长沙咸家湖西汉墓;
大英博物馆也藏有天珠,其中1颗在棕黑色的底色上蚀绘有一个白色圆圈纹,出土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王墓,年代在前2200年-前2000年。
而另1颗天珠出土于公元前十九世纪古巴比伦,它除了在微凸面的边缘蚀绘有白色圆圈纹,还在另一面用楔形文字刻有“国王献给太阳神”的字样;
中亚锡尔河流域的维加罗克斯基泰古墓也出土了2颗圆柱状天珠,它们是在白玛瑙珠体上分别蚀染棕黑色的底色和白色花纹制作而成,白色纹饰由圆圈纹及其他纹饰组合而成,年代为前7-前6世纪。
(二)地表黑白石条遗迹和出土火坛情况介绍
除了上文介绍到的天珠,我们认为还有地表黑白石条遗迹和墓葬中装盛在火坛中的黑白卵石也有可能蕴含着琐罗亚斯德教文化元素。以下我们先简要介绍这些地表遗迹和相关出土文物的基本情况:
1.墓群地表保留有墓葬地表的圆形封土堆和封土堆下一圈或两圈墓口圆形石围,以及大面积错落有致的黑白石条遗迹。黑、白石条由直径5-8cm的卵石有规律地平铺地表而成,呈不规则的长方形。
石条长500-2300cm、宽80-200cm不等,分布排列黑白相间、错落有致,向东北方向呈放射状延伸,给人以强烈的明暗光线视觉感受。石条只铺设于墓葬地表的东部一端,部分石条直接叠压在墓口,成为墓葬地表的组成部分。
2.墓葬中出土的火坛以及装盛在其中的黑、白色卵石。在2013-2014年的发掘工作中,分别于M11、M12、M15、M14、M9、M23、M25、M31、M35中出土了12件木质火坛(其中3件腐朽严重)和1件陶制火坛,具体情况如下:
(木火坛)
第一个木火坛出土于M11,其中1件出土时已残损,剩余约三分之一,一端带柄。残长20.4cm、残宽16.8cm,残高约9cm,柄残长2.5cm。火坛中部有内膛,因烧灼严重被毁坏大半,其中装有卵石14枚,卵石有烧过的痕迹,内膛留有灼烧而成的碳层。
第二个木火坛出土于M12,此木质火坛呈船状,两端各有一突出的椭圆形手柄,火坛长26.8cm,宽13.6cm。内膛为圆形,口径为9.3cm,深8.2cm,内膛壁留有灼烧而成的碳层,里面装有15枚卵石,卵石直径2-4cm不等。
第三个木火坛出土于M15,其外形呈椭圆形鸟巢状,内膛为挖凿而成的圆形,弧厚唇,口径18cm,深9cm。膛壁留有被火灼烧的碳层,里面装有8枚卵石,卵石直径2-4cm不等。
第四个木火坛出土于M14,其外形呈近椭圆形,两端各有一突出的椭圆形手柄,长25cm,宽22cm。内膛为下挖而成的圆形,坛口圆形直径5cm,深8cm。其中装有10枚有烧灼痕迹的卵石,卵石直径2-4cm不等,膛壁留有灼烧而成的碳层。
第五个木火坛出土于M9,此墓葬中出土木质火坛2件。火坛外形呈圆柱形,长约20cm,直径13.5cm。内膛为挖凿而成的深圆形,直径6.5cm,深8cm,里面装有8枚燃烧过的卵石,卵石直径2-4cm不等,木火坛内膛壁有烧灼后形成的炭层。
第六个木制火坛的外形也呈圆柱形,长35cm,高20cm,顶面微平。火坛两侧有鋬耳,耳长2.5cm。中部挖凿而成椭圆形袋状内膛,坛口直径为22×12cm,膛深9cm,内膛壁有烧灼而成的炭层。
膛内装有黑白卵石46枚,其中黑、白卵石各23枚,卵石直径2-4cm不等,卵石表面也有烧灼的痕迹。
第七个木火坛出土于M23,破损严重。木火坛大致呈长方形,长17.5cm,宽15cm,高9.5cm。中部挖凿椭圆形袋状内膛,膛口直径11×9cm,深5.5cm,内膛壁有烧灼而成的炭层,内装有直径2-4cm的卵石14枚,卵石表面也有烧灼痕迹。
第八个和第九个木火坛出土于M25,其中一件已腐朽破损,无法提取。另1件火坛整体呈水瓢状,一边带有圆柱形短手柄,圆底,弧腹。内膛为下挖而成的椭圆形,坛口直径8.3×7cm,深12cm,内膛腹径最大处为8.5cm,膛壁有烧灼的痕迹,内盛有烧过的卵石1枚,卵石直径2-4cm不等。
手柄长5.4cm,横截面直径约3cm。另外,在M25中还出土了陶质火坛1件,为夹砂红陶,素面,弧腹,圆底,底部及周围有烟炱的痕迹。火坛口为圆形,口部为圆唇。
颈腹处有两个2cm长半圆形鋬耳,一个已残。火坛口部外沿直径10cm,内沿直径6.3cm,高8.4cm。火坛口处壁厚0.4-0.5cm,火坛内装有用火烧过小卵石10枚,卵石直径2-3cm不等。
第十个木火坛出土于M31,此件木质火坛以原木截断后加工而成,腐朽程度较大。木火坛顶面修整成平面,长约25cm,宽18cm(高不详),中部掏挖直径约14cm的圆形袋状内膛,内盛有直径2.5-5cm不等的卵石数枚(因木火坛朽碎,无法得出准确数字)。
内膛壁有灼烧而成的炭层,卵石上残留着被火烧灼后留下的烟炱痕迹。第十一和十二个木火坛出土于M35,这两个木质火坛中一件已腐朽成粉末状,无法提取。
另一件发掘出土时已朽裂破损,根据残损状态推测木火炭整体为圆形,圆底。火坛内膛为下挖而成的圆袋状,膛口直径为17cm、深12cm,膛壁有灼烧后留下的碳层,内盛有烧过的卵石27枚,卵石直径2-4cm不等。
木火坛两侧各有一个手柄(一侧残缺),保留的手柄长3cm、横截面直径为3cm。
出土火坛外观多样,不过装盛卵石的内膛都呈圆(袋)状。所有木质火坛的内膛都被火强烈灼烧,内膛的燃火在放入墓穴后被填土压覆熄灭,从而在内膛木壁上留下一厘米左右厚度的碳层,这种现象是由烧红后放入的卵石所致。
更为有趣的是,我们在多个木火坛内部的碳层中检测到了大麻酚,其来自液体的灼烧,这种液体是从胡摩(也译作“豪麻”)中榨取的汁液。
《阿维斯塔》记载胡摩为新生不死的力量与象征符号,是琐罗亚斯德教宗教礼仪中饮用的一种圣液,被教徒奉若神明。先知琐罗亚斯德在世时贬责这种饮料,但《亚斯纳》中却有专门的篇章礼赞胡摩。
这种变化无疑是雅利安人传统习俗影响所致,在教主琐罗亚斯德死后,逐渐渗透到琐罗亚斯德教义理之中。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朝石堂的线刻画面中就有对献祭仪式Yasna的描绘:早期的琐罗亚斯德教不修建神殿、不设立崇拜圣火的固定祭坛,也不崇拜神像。
祭司们托举着可移动的祭祀火坛举行祭祀仪式,一人一边敬献火坛一边在圣火前咏颂大段《阿维斯塔》经文,另一人向诸神奉献圣水——胡摩汁,他将胡摩汁淋洒在圣火上,作为净化纯洁之用,现场参与献祭的信徒也依次饮用胡摩汁。
毫无疑问,北朝石堂线刻画面表现的Yasna献祭仪式承袭自中亚地区,而吉尔赞喀勒墓群呈现的文化现象正好与早期琐罗亚斯德教Yasna祭祀仪式相吻合。因而我们推断,墓群中出土木火坛内壁上的大麻酚可能是该仪式中胡摩汁的残留物。
- 三、对上述考古遗存蕴含文化信息的解析
吉尔赞喀勒墓群考古学文化呈现出一种业已成熟的琐罗亚斯德教早期文化背景,这与琐罗亚斯德本人撰写的《伽萨》《亚斯纳》《维斯帕拉德》等较早时期颂诗内容相一致。
本次出土的七颗天珠所蕴含的光明与火、灵石、“圆(圆圈或圆形)”“火坛”“特殊数字”崇拜以及黑、白对比等文化现象都恰好暗合了琐罗亚斯德在创教之初就倡导的宇宙观和宗教核心思想。
以下我们进行分析和讨论。不过,在尝试解读吉尔赞喀勒墓群蕴涵的琐罗亚斯德教文化意涵之前,有必要先简单介绍琐罗亚斯德教的文化背景。
(一)琐罗亚斯德教文化背景简述
琐罗亚斯德教创立于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于公元前7~6世纪被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奉为国教并广泛流传于古代波斯、南亚、中亚等地,影响遍及亚欧大陆。
琐罗亚斯德教作为最早形成理论体系的宗教,是历史上第一个被认可的世界性宗教,影响深远。琐罗亚斯德教的末世学说、救世主降临、死者复活和末日审判等观念对佛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对古希腊哲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萨满教仪式)
甚至对苯教和萨满教也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它们也都是在各自原始信仰基础上融合、改造、吸收了琐罗亚斯德教文化元素后分别创立了各自的宗教理论体系,三者都存在着“二元论”“三界观”和“多层宇宙观”等相似的宗教文化观念。
琐罗亚斯德教视崇祀“火”和“光明”为最神圣的职责,要求教徒通过专门的仪式礼拜“圣火”,因此在西方也被称为“拜火教”,该教传入中国后被称为“祆教”“火祆教”“拜火教”等。
琐罗亚斯德教形成过程是伴随着印欧(语系)人的迁徙浪潮逐渐完成的。从世界史观角度并借助历史语言学研究成果,学者们认为公元前三千纪以前,原始印欧人居住在俄罗斯西伯利亚以南的广大草原地带,自称“雅利安人”。
雅利安人是一些松散部族联盟,他们操着非常接近的语言,拥有大致相同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由于多种原因(目前尚无定论)而不断地向外迁徙。
其中,向西向北的几支形成后来说斯拉夫语的部族,其中包括凯尔特人、希腊人、意大利人、日耳曼人、波罗的人。在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到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的迁徙活动中,一支南下的雅利安人从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向中亚南部迁徙并进入伊朗高原,史称“伊朗雅利安人”。
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前后,先前来到伊朗的雅利安人中的一个分支进入印度河流域旁遮普地区,史称“印度雅利安人”。
印度雅利安人把旁遮普这片位于印度河上游被各支流环绕的肥沃土地称作萨普塔天竺,意为“七河之地”,以此来感念祖先曾生活过的故乡“中亚七河地区”。
在亚欧雅利安人迁徙浪潮中,新疆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河谷地带是他们通过帕米尔高原前往目的地的重要路径。历史地理文献记载和考古学资料告诉我们,该地区至少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就已经是波斯、亚欧游牧地区、印度、中国文化交错传播的关键通道区域。
正是这些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碰撞和交融孕育了琐罗亚斯德教。在伊朗雅利安人和印度雅利安人各自经历的长达七八百年发展历程中,始终伴随着雅利安人对当地土著居民的征服和雅利安人部落之间的相互兼并,
最终分别孕育出印度雅利安人的四部吠陀本集和伊朗雅利安人的《阿维斯塔》,曾经共同的历史文化本源致使它们的内容有很多相近之处,也隐含着印度人和伊朗人在宗教文化信仰上深层的内在联系。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琐罗亚斯德教创立后在中亚、西亚得以广泛传布和对后出宗教产生深远影响的内在客观因素。
虽然学界对琐罗亚斯德教发轫于亚欧游牧部族原始宗教信仰(亚欧草原青铜时代斯基泰文化恰好在历史阶段上与其重合)这一观点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对先知琐罗亚斯德的生活年代却颇有争议。
W .B.亨宁认为是在公元前六世纪,而其学生玛丽·博伊斯却认为应该是在前1400-前1200年间。
关于《伽萨》的诞生之地,一些学者根据《伽萨》所记述的情况推测,先知琐罗亚斯德最早在一个叫做airyānəm υaējō的地方传布教义,这里位于花剌子模,但贾可诺夫和格诺利却认为airyānəm υaējō位于锡斯坦及其周边地区,这里位于古代伊朗东部的中亚地区,当时尚未被波斯人所征服。
《伽萨》颂诗作为《阿维斯塔》最早创作部分,其思想内容将吉尔赞喀勒墓群呈现的文化信息与琐罗亚斯德教的早期教义关联起来,成为本文讨论内容的基本指向。
(二)相关遗存蕴涵的文化信息
1.黑白两色对立的文化寓意与光崇拜
黑、白两色在上述遗迹和文物中的反复出现,提示我们黑白两种颜色在吉尔赞喀勒墓群遗迹中应有特殊文化含义。
琐罗亚斯德教徒认为,在宇宙之初就存在善(光明)、恶(黑暗)两大各自独立的本源。其中“善”本源是智慧、善良、真诚、纯洁、仁慈、创造的体现,是光明和生命的源泉;“恶”本原则是愚昧、邪恶、虚伪、污秽、暴虐和破坏的代表,是黑暗和死亡的渊蔽。
善与恶在经过长期斗争后,善界虽然取得了最终胜利,但这只是善界的纯化而非消灭了恶界,善界和恶界都是永恒的存在,它们的斗争起于“二”又复归于“二”,这一过程此消彼长,周而复始。
在琐罗亚斯德教信徒的观念中,阿胡拉·马兹达(意为“智慧之主”)是善界的主宰和全知全能的宇宙创造者,它具有光明、生命、创造等德行,也是天则、秩序、真理的化身;而阿赫里曼则是黑暗世界的魔王。
该教信徒认为每一个人在善恶两端之争中,都可以凭借自由意志的选择来决定自已的命运,而宇宙在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不懈斗争之后必将阳光普照,充满光明和幸福。
这一观念正是琐罗亚斯德教所倡导的“善、恶二元对立斗争”的宇宙观以及“抑恶扬善、善必胜恶”的核心教义思想。
白、黑两色的相互映衬和对比且以白色为主的关系确凿清晰地呈现在吉尔赞喀勒墓群遗迹和文物中,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正是琐罗亚斯德教倡导的宇宙观和核心教义思想的具象表达。
墓群地表遗迹中代表明暗光线的大面积黑白石条表现了“漫无边际的光芒”,是“光”崇拜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
在《阿维斯塔》的《伽萨》中“光”是正义的象征,是火的升华,其精神属性优于火,也是诸善神的原始意象,是知识、智慧、悟性和辨识力的隐喻表达,而拜光和拜火侧重面的不同恰好反应了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亚欧游牧部族和印度雅利安人在宗教观念上的差异。
在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亚欧游牧部族眼中“光”被视为“凌驾于一切被造物之上的神明,它源于光本源阿胡拉·马兹达,实为善界神主的象征和化身,代表着阿胡拉·马兹达的神力和福佑,同时“漫无边际的光源”也是神主阿胡拉·马兹达创造万物的始基。
不仅如此,伊朗雅利安人的氏族神梅赫尔还含有“光芒”“太阳”“誓约”等意。在根据《丁·卡尔特》编写而成的古波斯神话中,也把阿胡拉·马兹达的出世描写成是灵光(祭火)、灵魂(豪麻草)、和躯体(青草和牛乳)相结合的产物。
在《胡尔达·阿维斯塔》(小阿维斯塔)的《西鲁泽》篇中,有专门赞美阿尼朗的诗句,其词义就为“漫无边际的光源”,即光明天国,是阿胡拉·马兹达永恒无限光芒的庇护神,也是每月第三十日的庇护神。
这些铺设于墓群地表表现“明暗光线”的大面积黑白石条显然有着鲜明的琐罗亚斯德教文化印记,突出了2500年前居住在帕米尔高原的亚欧游牧部族的“拜光”意识。
墓群地表铺设表达明暗光线的黑白石条方向基本都指向“夏至”日日光最长的方向,而墓葬所在方位与黑白石条遗迹相对应一概位于“冬至”日全年日光最短的方位,这一现象暗合了琐罗亚斯德教历法内容和宗教习俗。
(阿契美尼德王朝地图)
琐罗亚斯德教宗教历法最早出现在伊朗东部的中亚地区,从阿契美尼德王朝晚期开始便在伊朗地区广泛使用,到萨珊王朝时期完全取代了巴比伦历法而成为伊朗的官方历法。
从吉尔赞喀勒墓群地表遗迹的陈布特征来看,本地游牧部族早在2500年前已经熟知琐罗亚斯德教的宗教历法内容并在重要的祭祀仪式中加以遵循。
人们在大自然的季节变化中发现“冬至日”是一年中太阳光照射时间最短的一天,“夏至日”则是一年中太阳光照射时间最长的一天。
遗址地表遗迹中,每一组黑白石条和与其相对应的墓葬共同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其中墓葬正好位于“冬至日”方位,黑白石条所指方向则是“夏至日”方位。
地表遗迹中黑白石条和与其相对应的墓葬的陈布关系表明,这一现象也是早期光明与黑暗对立教义理念在关于大夏季(白昼最长)和大冬季(暗夜最长)季节崇拜习俗中的直观表达。
由此可见,在琐罗亚斯德教徒的观念中,“夏至日”是光明与黑暗斗争的转折点,也是生(光明、阳)和死(黑暗、阴)的分界线,万物的生命力自此将由旺盛的极致而渐趋衰竭;“冬至日”则相反,虽然阳光照射的时间最短,但却是世界万物生命孕化的肇始。
这一理念隐含着先知早在《伽萨》中就已提出的“善恶二元对立斗争”的宇宙观和“抑恶扬善、善必胜恶”的宗教核心思想。
在琐罗亚斯德教习俗中,冬至日(12月25日)还是“不可征服”的太阳神密斯拉(Mithra,即梅赫尔)的生日,后来西方把这一天定为基督的生日。
墓群地表遗迹中的黑白石条和圆形石圈不仅表达了当地游牧居民为逝去亲人布设另外一个光明世界的美好愿望,更是他们对琐罗亚斯德教大夏季(光明)和大冬季(黑暗)自然消长思想的直观表达。
大面积铺设于地表的黑白石条在历经2500年的风雨后,仍然给予我们强烈的黑白光线视觉冲击。我们根据地表遗迹现存状态,对其形成的过程进行推测,认为黑白石条遗迹并非在下葬之前或下葬时一次性铺设完成,而是在初次铺设的基础上,又经过长年累月的不断加强和维护才得以呈现出我们看到的规模和状态。
作为最早形成理论体系的宗教,神话与之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在专为琐罗亚斯德教服务的历法——“阿维斯塔”历中一年有十二个月,每个月有三十天,不论是月或日都有相应的庇护神,
“日”和“月”都由与之相对应的保护神的名字命名,其中一些保护神既是月的庇护神又充任日的庇护神,当每月中的月神和日神重叠为同一位神祇时就要过节庆祝,这样每年共有十五个节日,除此之外每年年末的最后五天也是重要的“伽萨日”。
根据《胡尔达·阿维斯塔》记载,这五天“伽萨日”是庆祝阿胡拉·马兹达创造人类的节日,是“灵体”节的组成部分,也是最后一个“伽罕巴尔”节,这五天分别被冠以《伽萨》五篇的篇名。
而在每年的重要节日里,人们都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早期琐罗亚斯德教信徒们在墓地祭祀以阿胡拉·马兹达为首的诸善神和祖先神,他们通过祭祀活动表达对逝去亲人的思念和祝福,同时也向诸神祈求恩惠与福佑。
由此看来,墓群地表黑白石条和相对应的墓葬应该是2500年前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在宗教活动中遵循宗教历法指导从而规范丧葬和祭祀行为的重要佐证之一。
我们推测:在每一年的重要节日里,琐罗亚斯德教的信徒们从其他地方捡来黑、白两色的卵石分别堆砌在之前铺就的黑白石条上,对其进行加固和延展,从而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壮观黑白石条遗迹。
这种行为是每个节日中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周而复始,直到琐罗亚斯德教在本地区退出历史舞台才宣告结束。
2.灵石崇拜
已有的相关学术研究表明,灵石崇拜历来已久。早在原始宗教时期,人们因为一般石头具有重量和坚硬等共性而通常被认为具有一般的福佑效力,而那些具有特殊形状或颜色的石头则被认为具有特殊的福佑效力。
在《阿维斯塔》记述中,认为世界第一个创造物是“天空”,写作asman,现代波斯语意为“天空”,但在《亚什特》中,asman的意思却被译作“石头”,
由此可见在琐罗亚斯德教徒观念中,不论“天空”还是“石头”都是世界第一个创造圣物,这一传说背后注入了灵石崇拜文化观念,也寓意着通过灵石向以神主阿胡拉·马兹达为首的诸善神祈愿福佑等寓意。
在吉尔赞喀勒墓群发现的考古资料中,我们看到了关于与“石头”有关的诸多文化元素:这里的先民怀着敬畏之情用“具有灵性的石头”堆垒营造了圆形石圈和大面积的黑白石条遗迹;
他们还在亲人的葬礼仪式上将数量不等的白色和黑色卵石燃烧后放入木或陶火坛一起入葬,以求得神主阿胡拉·马兹达对逝去亲人的福佑;
他们中的位高权重者佩戴着从远方贸易而来的天珠,将其视为神圣护身符和珍贵珠宝终身相伴,死后还将天珠作为护佑主人灵魂的圣物陪葬,用以保护和福佑主人的灵魂升入无限光明的天国。
在人类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原始宗教是后出宗教的先导,琐罗亚斯德教正是对原始宗教进行总结凝练和提高创新的结果。
宗教作为具有统治世界的力量已经是有意识和具有人格的,这里天珠作为人工在白玛瑙珠上进行黑白两次蚀花制作而成的神圣“灵石”,更因珠体上蚀绘着经久不褪象征着“以阿胡拉·马兹达为首的诸善神”的图案而成为琐罗亚斯德教义的具象载体。
故此,我们认为吉尔赞喀勒墓群出土的天珠应归属于琐罗亚斯德教宗教圣物范畴。
3.神圣的“数字”
在琐罗亚斯德教圣书《阿维斯塔》中包含着明显的数字文化内容,一些数字往往具有神圣的宗教含义。
在本次考古发掘中,墓葬的石圈有的为“1”圈,有的为“2”圈;天珠上的颜色有“2”种;木质火坛中的卵石也有黑、白“2”种颜色;M11出土的天珠上有“1”条较宽的白色圆圈纹外;
另外,木质火坛中分别装盛着“14”枚、“15”枚、“8”枚、“10”枚、“8”枚和“46”枚、“14”枚、“1”枚、“27”枚卵石,一只陶火坛中也装盛了“10”枚卵石。显然,这些数字应该含有特定文化寓意。
(1)关于数字“1”和“2”。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认为:“对这个或那个社会集体来说,在头十个数中没有一个数不具有特别的神秘的意义。
数字‘1’在一神教和一元论哲学体系中保持着自己的威信;数字‘2’常以自己对称的对立属性与‘1’对立着,因为‘2’所表示的、包含的、产生的东西是与‘1’所表示的、包含的、产生的东西严格对立的。”
在明显蕴含着二元神论宗教理念的吉尔赞喀勒墓群中,数字“1”意蕴了以神主阿胡拉·马兹达为代表的诸善神,是善、完美、幸福、秩序的本原。
数字“2”在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中则是个永恒的圣数,具有宇宙观的象征意义,它从世界观的高度相对集中地体现了琐罗亚斯德教“善恶二元论”的本质特征,
在二元神教(琐罗亚斯德教和摩尼教)及其哲学体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2”也是琐罗亚斯德教神话的基本原型数字,每月第“2”日的庇护神是“巴赫曼”,祂兼任每年“11”月的庇护神。
“巴赫曼”不仅是第一位大天神,还是动物神,代表神主的智慧和善良,被视为神主与人类灵魂交往的中介。
(2)火坛中卵石数目的文化寓意。前文已述,本次考古发掘中分别提取出9件保存较好的木质火坛和1件陶制火坛,每一个火坛的圆袋状内膛中都分别装盛着数目不等的卵石。
下面我们依据《胡尔达·阿维斯塔》相关内容尝试分析这些卵石数目所蕴含的文化寓意。
【数字“1”“8”“15”“23”】出土木质和陶质火坛中都装盛着数目不等的卵石。依据《胡尔达·阿维斯塔》与数字有关教义内容,我们推断每一个火坛中卵石数目具有特定琐罗亚斯德教文化信息。
这里之所以将“1”“8”“15”“23”放在同一组共同解析,是因为与其有关的内容在《胡尔达·阿维斯塔》中有直接表述。
《胡尔达·阿维斯塔》作为《阿维斯塔》的精简本,主要用以指导和规范教徒日常的祈祷、每月的祭礼、每年的宗教节日、婚丧嫁娶等行为,其内容主要引自《亚斯纳》《维斯帕拉德》和《亚什特》。
在琐罗亚斯德教的宗教历法中,月和日都有相对应的庇护神,其中阿胡拉·马兹达以“霍尔莫兹德”之称作为每月第“1”日的庇护神;祂还以“戴·巴·阿扎尔”“戴·巴·梅赫尔”和“戴·巴·丁”之称作为每月的第“8”日、第“15”日和第“23”日的庇护神。
由此可见,木质火坛中分别装盛的“1”“8”、“15”和“46”(由白黑卵石各“23”枚组成)枚卵石分别代表了每个月中的第“1”日、第“8”日、第“15”日和第“23”日,也代表了人们对这几日的保护神“霍尔莫兹德”“戴·巴·阿扎尔”“戴·巴·梅赫尔”和“戴·巴·丁”的颂扬和祈福。
细究之下,不论是“霍尔莫兹德”“戴·巴·阿扎尔”“戴·巴·梅赫尔”还是“戴·巴·丁”,祂们都是神主阿胡拉·马兹达的别称。
当时人们在火坛中放入炽热的不同数目卵石,这种行为归根结底还是他们对神主阿胡拉·马兹达的颂扬和祈福。再者,根据琐罗亚斯德教创世神话,阿胡拉·马兹达还是人类保护神。
因此,人们在亲人葬礼上通过这种颂扬阿胡拉·马兹达的特殊仪式向祂祈愿:祈求神主护佑亲人的灵魂升入光明祥和的天堂并得以早日重生。
当然,人们也有可能选择在这几个被神主阿胡拉·马兹达特别庇佑的日子里为亲人们下葬,以求得亲人的灵魂获得阿胡拉·马兹达的福佑。
很明显,M9出土这一木火坛中装盛着黑白两色各“23”枚卵石,应该是利用石子颜色和数目表达该教“善恶二元对立斗争”的宇宙观。
【数字“14”】M11和M23出土两个木火坛中分别装盛着“14”枚卵石。根据《胡尔达·阿维斯塔》中专门歌颂每月三十天庇护神的篇章《西鲁泽》记述,阳历每月第“14”日的庇护神为“古什”(Gūsh),祂还是牲畜的庇护神。
显而易见,“14”枚卵石应该代表每月第“14”日,也寓含着人们向这一日的庇护神及牲畜的庇护神——“古什”祈求恩惠与福佑。
【数字“10”】M14出土木火坛中有“10”枚卵石。同理,《阿维斯塔》中数字“10”代表了每月第十日的庇护神阿娜希塔(Anāhīta,又名阿邦等)。
根据《西鲁泽》的记述,祂还兼作阳历每年八月的庇护神,《亚什特》中还将“阿邦”尊奉为“江河女神”,其中的第五篇《阿邦·亚什特》(水神颂)即为专门赞颂祂的篇章。
阿娜希塔的固定修饰语为“纯洁而强大的”(Aredvī-Sūra),前琐罗亚斯德时期就被雅利安人奉为崇祀的重要神明,主司生育、丰产等。
根据传统习俗,每月“10”日(阿邦日)和水神节(八月十日),人们在江河岸边向阿雷德维·苏拉·阿娜希塔女神致祭祀礼时专门吟诵《阿雷德维·苏拉·内亚耶什》(水神颂),夜间绝对禁止吟咏。
由此可见,装盛在火坛中的“10”枚卵石象征了阿娜希塔女神,寓意着人们向祂祈求恩惠与福佑的美好心愿。
【数字“27”】M35出土木火坛中有“27”枚卵石。根据《阿维斯塔》之《西鲁泽》记述,阳历每月第“27”日的庇护神是“阿斯曼”(苍穹之神)。
而在琐罗亚斯德教的创世神话中,霍尔莫兹德(即阿胡拉·马兹达)为了对抗以阿赫里曼为元凶的黑暗世界,用“火、气、水、土”四大元素创造出天穹、江河、大地、植物、动物、人类等世间万物,并设计创造了七层天空上的众星体。
这一创世神话告知我们,苍穹之神“阿斯曼”在早期琐罗亚斯德教神话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木火坛中的“27”枚卵石,寓含着人们向每月第“27”日的庇护神“阿斯曼”即苍穹之神祈求恩惠与福佑。
《阿维斯塔》记述的各种神话内容反映的正是琐罗亚斯德教基本宗教思想和教义。
通过对照梳理《西鲁泽》和《亚什特》篇章中的神话体系,我们发现在吉尔赞喀勒墓葬出土的火坛中以卵石数目方式呈现的“古什”“阿邦”“阿斯曼”都是《阿维斯塔》中的早期神祇,祂们承袭自十分古老的自然神祇。
而“霍尔莫兹德”“戴·巴·阿扎尔”“戴·巴·梅赫尔”和“戴·巴·丁”以及“戴”都是神主阿胡拉·马兹达的别称,均出现在经典的早期内容当中。
毋庸置疑,上述出土火坛中石子数目资料不仅表明其确实与琐罗亚斯德教教义关联,而且客观有力地证明了出现在吉尔赞喀勒墓群火坛中的众神祇均为琐罗亚斯德教早期神祇。
4.“圆形”和“火坛”的文化寓意
(1)“圆形”的文化寓意。历史长河中,被人类想象过和尝试画过的图形(二维的或三维的)就像意识一样古老,这些“抽象的图形”符号正是因为相互的组合才使图案具有了意义。
圆形作为平面图形中最完美的几何图案,因其开头和结尾在同一个点而具有简单的形式完整性,所以早在石器时期就被人类认为是最完美的图形,常被用来指代神祇,从而屡屡出现在古代人类的艺术创作中。
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上的巨幅浮雕描绘了公元前520年左右大流士一世战胜叛乱首领的胜利场面,其中“波斯人的至上神阿胡拉·马兹达伸出左手递给大流士一世一个环,象征着王权的授予,同时举起右手表示祝福。”显而易见,圆环在此象征着君权神授的寓意。
2500年前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人们将赋有灵性的石头铺设成“圆形”和代表光线的“长条形”,大面积铺设于墓群地表,这一地表遗迹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思想文化。
吉尔赞喀勒墓群考古资料中所呈现的圆形石圈、木质或陶质火坛的圆形內膛、圣火坛中的圆形卵石、环绕天珠黑色珠体有序分布的白色圆圈纹,它们都是“圆形”或“圆环形”。
此时,这一几何图案已经被用来代表2500年前生活在帕米尔高原游牧部族所信奉的琐罗亚斯德教中以阿胡拉·马兹达为主神的诸善神。
(2)“火坛”的文化象征。圆板状天珠上蚀绘有“火坛”象形图案,墓群中还出土了多个木质和陶质的“火坛”。
“火坛”在本次发掘中的屡屡出土,而且是主要随葬物,直观表明“火坛”在该墓群遗址中举足轻重的文化地位。
在琐罗亚斯德教徒观念中,“火”是地上的太阳,太阳是天上的“火”,而最高主神阿胡拉·马兹达就是火和太阳的化身,是神之造物最强大和有力的物事。
琐罗亚斯德教最重要的习俗就是崇拜“火”和“光明”,祭祀活动中人们“向火坛礼拜,火坛上的火作为最高主神的象征而燃烧着”,人们通过祭火达到与神主接近或沟通的目的。
作为装盛火的神圣器物,“火坛”自然而然成为人们祭祀礼拜的中心目标和主要法器,后来更进一步演化为琐罗亚斯德教标志,备受教徒尊崇和礼拜。
(三)本次出土天珠及相关遗存文化寓意的综述
上述遗存首次集中出现在吉尔赞喀勒墓群的遗址中,这些相互呼应的特殊现象不仅蕴涵着早期琐罗亚斯德教的宇宙观及核心教义思想,也为我们分析讨论本次出土天珠的文化意涵奠定了基础。
通过上文对圆圈纹的阐释,我们得知“圆圈纹”在琐罗亚斯德教徒的观念中代表了以神主阿胡拉·马兹达为主的诸善神。
(阿胡拉·马兹达)
具体来说,天珠珠体中间蚀绘一条较宽的白色圆圈纹环绕着珠体,白色圆圈纹是天珠的表意主体,象征着以神主阿胡拉·马兹达为首的诸善神。
较宽的白色圆圈纹使整颗天珠呈现出宽白色圆圈纹居于珠体中间,而黑色为底、为辅对称分布的艺术表达形式,正是琐罗亚斯德教“善必胜恶”核心教义的艺术呈现。
如此说来,这颗天珠应该寓意着人们向以神主阿胡拉·马兹达为主的诸善神祈求福佑的质朴心愿。
天珠的黑色珠体上蚀绘有五条宽窄不一的白色圆圈纹,中间的圆圈纹相对较宽,两组较窄的白色圆圈纹分列两边,形成了中间为宽白色圆圈纹,两边为窄圆圈纹的对称形态。
在此类天珠图案中,作为表意主体的宽圆圈纹和对称分布的窄圈纹共同构成了画面上的统一和秩序,使天珠获得了琐罗亚斯德教神秘的宗教意涵。
中间相对较宽的白色圆圈纹代表了表意主体——以神主阿胡拉·马兹达为首的诸善神,而其两边对称出现的较窄的白色圆圈纹则象征了祂们的“神圣的灵光”。
我们据此推测,此类圆柱状天珠上代表神祇的几何图案的两边对称出现的细圈纹越多,表明珠子所承载的神主阿胡拉·马兹达的福佑灵力越多。
还有出土于M32的一颗蚀绘有象形“火坛”图案的圆板状天珠。结合本次发掘出土的多个实物“火坛”观察发现,这些实物“火坛”的外观虽然多种多样,但它们的内膛却被人为挖凿成圆(袋)状,与圆板状天珠上蚀绘的“火坛”形状一样。
它们都具有圆(袋)状的内膛,从而得以在膛内装盛燃烧着的卵石,继而完成神圣的祭祀仪式。
天珠上蚀绘的“火坛”图案直接反应了人们对“火坛”的崇拜,结合琐罗亚斯德教信徒观念中“火是地上的太阳,太阳是天上的火”以及阿胡拉·马兹达代表了太阳、火、光明、智慧”等观念,这颗圆板状的天珠直接表达了人们对圣火坛、神圣之火、太阳的崇拜以及对神主阿胡拉·马兹达的无上尊崇。
而白色的“火坛”图案居于黑色珠体的主要位置,这种艺术表达形式显然是该教“善恶二元对立斗争”的宇宙观和“抑恶扬善、善必胜恶”宗教核心思想的客观体现。
墓群地表大面积的黑白石条和装盛在火坛中的卵石彼此呼应、内外关联地将早期琐罗亚斯德教信徒在丧葬、祭祀等活动中所遵循的琐罗亚斯德教宗教历法和习俗以具象形式呈现在我们眼前。
不仅如此,黑白石条遗迹还将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拜光”意识和“善恶二元对立斗争”的宇宙观表达得十分形象。
概括而言,上述所论及遗存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琐罗亚斯德教早期教义思想和其宗教理论体系开启了新的视野。
- 四、结 语
天珠的珠体上蕴含着琐罗亚斯德教倡导的善恶“二元对立斗争”的宇宙观以及“抑恶扬善、善必胜恶”的宗教核心思想。
联系“最早的天空是石头”的文化观念来看,琐罗亚斯德教徒认为天珠是灵石和上天的神圣组合,具有神格化的意涵,
是代表“上天”福佑的神圣灵石,在琐罗亚斯德教徒的观念中天珠赋有以阿胡拉·马兹达为主的诸天神的福佑圣力,是上天恩赐的护佑神物,故对其冠以“天珠”之称,的确是名如其实。
人们创造并佩带具有护身符功能的天珠是源于对神祇的礼赞和祈福,这种具有久远历史的工艺品在琐罗亚斯德教创立之始就可能已经直接发展成为琐罗亚斯德教徒重要的随身宗教文化信物。
天珠作为琐罗亚斯德教信徒随身佩戴的信物,为我们揭示了他们的精神信仰和宗教崇拜等精神世界的文化内涵。
这批国内发现最早的天珠与地表黑白石条遗迹以及装盛在火坛中的黑白卵石遗存相互呼应,彼此关联地向我们表明它们是早期琐罗亚斯德教文化的直接表达。
巫新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