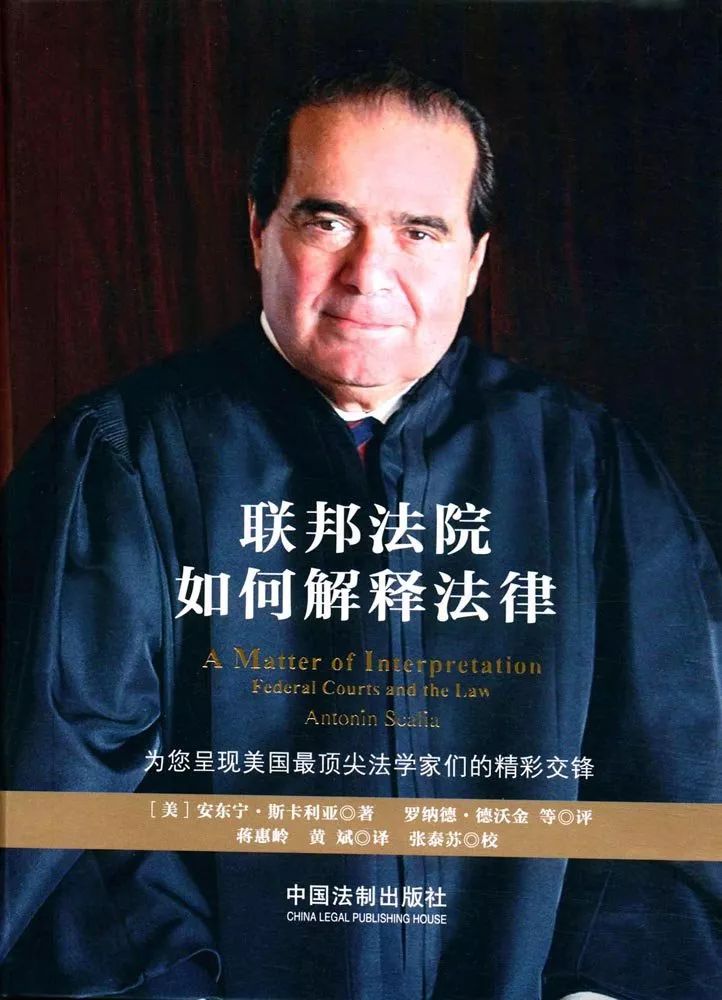授权转自:保守主义评论
作者:斯卡利亚 蒋惠岭 等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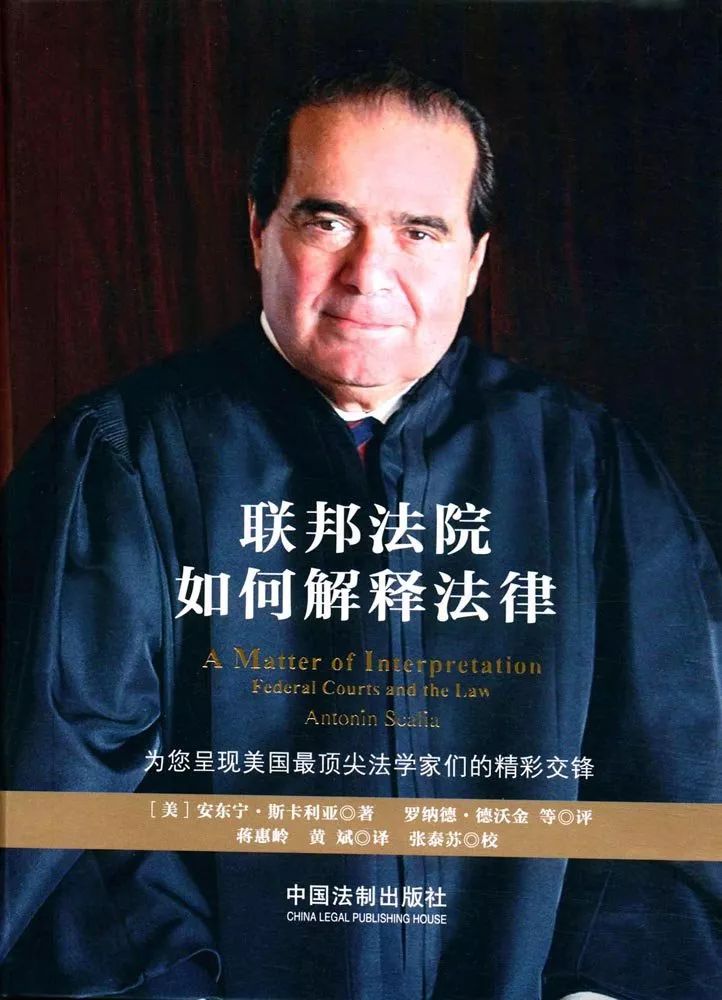
按: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 1936-2016),美国法学家,曾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1986年由里根总统任命,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保守主义阵营中的中坚人物,也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服务时间最长和最资深的大法官。之前曾任职于哥伦比亚特区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并执教于弗吉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毕业于乔治城大学,获哈佛大学法学硕士学位。2016年2月13日去世。本文摘自安东宁·斯卡利亚《联邦法院如何解释法律》(蒋惠岭、黄斌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51-65页。
……………………
解释宪法
我不敢说自己对文义解释中的所有问题都有研究。在此我只希望专门讨论一下宪法解释这个独特问题。这个问题颇为独特,不是因为运用了专门的解释方法,而是因为将解释方法运用到不寻常的法律文本之中。马歇尔大法官将这种观点完美地表述在“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McCulloch v. Maryland)中:
假如一部宪法试图详细地列举其所覆盖的所有内容,以及实现所有这些内容的措施,那么它就会如同一部法典一样琐碎,或许就无法被公众所理解。因此,其性质决定了只需规定重大原则,设计重要的目标,而组成那些目标的不重要的成分则可以从目标本身的性质中推断出来。
在文义解释中,上下文就是解释的全部。宪法的上下文告诉我们不要去咬文嚼字,而是要对用语进行广义而非狭义的解释。当然,并不包含那些用语所不能承载的解释
例如,第一修正案禁止限制“言论或出版自由”。该表述并未列举所有的言论自由。例如,书信既不是言论也不是出版物。然而它们毫无疑问不能受到审查。在这种宪法文本中,言论和出版这两种最普遍的言论自由表达方式代表了言论自由。这不是严格解释,但这是合理的解释。
奇怪的是,大多数坚持认为立法者的本意决定法律含义的人拒绝将制宪者的本意作为宪法解释的标准。我对二者均予以拒绝。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我会考虑一些出席过制宪会议的人的论述(例如,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论述)。不过,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制宪者,因而他们的意图具有权威性必须成为法律,而是因为他们的论述和当时其他学识渊博的人的论述一样,展示了宪法的文本最初是如何被理解的。因而我同样重视杰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论述和杰斐逊的论述,尽管他们俩都不是制宪者。我在宪法中寻找的正是我在法律中寻找的,即文本的原始含义,而非起草者最初的意图。
不过,宪法解释的分界点不是制宪者的意图和客观性含义,而是原始含义(无论是否衍生于制宪者的意图)和当下的含义。主流宪法解释学派断言,存在一种活的宪法(living constitution)以适应变迁社会的需要。而且,正是由法官来决定适应社会需要的具体内容,并“发现”已改变的法律。这听起来很熟悉,不是吗?是的,这确实是普通法的回归,它甚至具有比旧普通法大无穷倍的威力,因为现在它甚至胜过民主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回顾一下我在前面引述的充满激情的立法者兰道尔在国庆日发表的演讲:“通过从先例中抽取原本不存在的内容,法官进行造法。他扩展了先例,而这些先例本来也是其他先例的扩展。通过这种包容性原则,最后在没有权威或立法者干预的情况下,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确立起来。”在这句话中用“人民”取代“立法者”,就是对现代美国法院对宪法的所作所为的完美描述。
如果你走进宪法课堂,或者学习一本宪法案例书,或者阅读一个宪法案例卷宗的摘要,你会发现它们极少讨论宪法条款的具体文字,也不问该条款最初是如何被理解的,甚至不问制宪者的本意。首先分析的反而是最高法院的案例,新的问题将按照那些案例中表达的逻辑进行分析,而不考虑那种逻辑经扩展之后在多大程度上让我们远离了原始的文本和观点。不过,更糟的是,如果那种逻辑未能形成目前联邦最高法院对于手头案件所期望的结果,那么,像普通法的好法官一样,联邦最高法院将识别它的先例,或者加以限定,或者必要时推翻先例,其目的是让宪法具有它应该具有的含义。
举一个不太具有争议的例子:人们应当具有死亡的宪法权利吗?如果应当,那实际上就会有。亲生父母有权向养父母要回自己的孩子吗?同样,应当有就会有。如果这样做有好处,就是应当的。不必去管我们要阐释的文本。假如别的途径行不通,我们也可以通过对正当程序条款进行解释的方式偷偷放入这些新权利,而正如我已经表述的,这个条款本身是不可能包含这些新权利的。此外,昨天的宪法含义并不必然就是今天的含义。正如我们围绕第八修正案(残忍和不正常的刑罚条款)的法律理论给出的司法意见所说的那样,宪法含义的变化反映了“尊严的标准在不断变化,这标志着社会走向成熟进步”。
这明显是一种普通法的造法方式,而非解释以民主方式通过的法律文本的方式。我在前面提到一篇关于法律解释的名为《德沃里斯论制定法》(Dwarris on Statutes)的英国名作。德沃里斯法律格言第4条如下:“议会制定的法令不能由于时间的原因而被改变。但是普通法可以,因为它的原则是,法律的理由一旦消失,法律本身也就不存在了。”这仍然是法律解释中正式阐明的规则(虽然它有时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回避):制定法不能改变。卡拉布雷西法官和埃斯克里奇教授提出的“动态法律解释”主张因此被认为是先锋性的主张。不过,尽管宪法是民主的产物,我们却在形式上像普通法一样对待。那么,这样做的正当理由是什么呢?
比较自然的假设是,文本不会改变这一规则可以牢固地运用于宪法。如果法院因民主式程序的约束而无法修改制定法,因为这种修改是由立法机构进行的,那么,法院就更不应该去修正一部宪法,尤其当他们的修改很难被弥补的时候。当然,更不能说宪法本身自然地隐含着变化。相反,它的全部存在目的就在于防止变化,以这种方式植入某种权利以便未来世代无法将此权利剥夺。一个通过了《权利法案》的社会应该会怀疑“体面的标准在不断变化”是否总是“标志着进步”,也怀疑社会是否总是变得更加成熟”,而不是更加腐朽。无论是宪法的文本还是制宪者的意图(无论你选择哪个)都不可能得出结论说,宪法存在的唯一作用就是将改变权利的权力从立法机构转交给法院。
“活的宪法”的灵活性和任意性
宪法发展理论的基础是实用主义。该理论主张宪法必须具备“灵活性”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宪法不能适时修改变化,那它可能会遭到破坏。如果该理论的倡导者一直以来为我们带来的大部分“发展”是消除对民主政府的限制,还算有些说服力。但事实恰恰相反。特别是在过去的35年中,“发展”的宪法对行政、司法和立法活动施加了诸多新的限制。此处我仅提及一些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在过去可以实现,现在却难以实现的改革:
在州刑事审判中使用通过非法搜查获取的有罪证据;
允许在公立学校毕业典礼上向上帝祈祷;
按照美国参议院的方式选举州立法机构中的两院之一,即以不给所有的投票人数量上平等的代表权为依据;
一旦收到欺诈证据就终止发放福利金,如果经听证证据被合理地驳回则恢复发放;
对投票施加财产限制条件;
禁止匿名的竞选刊物;
禁止色情文学;
宪法发展论者的未来计划也基本上一以贯之,即对民主政府创设新的限制,而非消除旧的限制。政府行为具有更少的灵活性而非更多。正如现在的情况,州和联邦政府可以适用或废止死刑,允许或禁止自杀,这些全都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不过,如果死刑被判定违背了宪法第八修正案,自杀被判定受到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保护,宪法的灵活性就会消失。不,问题的实质是,一般来说,宪法发展论者并非寻求推动社会发展,而是阻碍社会发展。
我必须承认,仍然存在一些宪法推动社会发展的例外情况。不过这些例外情况并没有像宪法发展论者认为的那样带来了更大的个人自由。(宪法发展论者认为那是一种更大的利益,理由我不能完全理解。所有政府都代表着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的平衡,真实的情况是,并非每一种倾向于更多个人自由的主张都必然是好的。)但是不管怎样,历史记录反驳了发展宪法总是带来个人权利这种主张。最明显的反驳是现代联邦最高法院限制对财产进行宪法保护。例如,禁止政府限制合同中的义务这一规则已被破坏。我确信“我们人民”会认同这种发展,因为我们不如制宪者那么重视财产权。因此,我们也不如制宪者(他们认为自卫权具有绝对的根本性)那么重视拥有武器的权利。如果宪法第二修正案被判定仅仅保证了州的国民警卫队,很少有人会失望。不过这只是表明,当(制宪者)担心(在他们看来是受误导的)下一代可能会取消他们认为必不可少的自由,并且希望保护权利法案中的那些自由时,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们可能确实想要限制财产权并且撤销拥有武器的权利,但是我们不要假装这并未限制权利。
或许财产权已经太受冷落以至不能引起热情,而拥有武器的权利又太过危险,让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几年前,联邦最高法院受理了一个对儿童实施性虐待的案件。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发现,在(有嫌疑的)施虐者在场的情况下,该儿童易受惊吓以致不能作证。因此依照相关的州法律,允许她在仅有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证,而被告、法官和陪审团则通过闭路电视的形式听审。这是一项足够合理的程序,联邦最高法院也判定其合乎宪法。我撰写了反对意见,因为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在所有的刑事指控中,被告人有权……与反对他的证人对质。”对质的含义甚至在今天都是确定无疑的。它意味着面对面,而非在不同的房间里。该条款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确定无疑的:就是恰恰将那种让那个小女孩难以承受的压力施加到证人身上。当面控告任何人都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说谎的情况下。自1791年那项条款被采纳以来,外部环境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那时存在性虐待,现在依然如此;那时的孩子比大人更容易受惊吓,现在依然如此;那时的法院有办法将被告置于证人视线之外,现在依然如此(可以很容易地设置个屏幕,使得被告能够看见证人,而证人却看不见被告)。不过宪法第六修正案却赋予所有的刑事被告与反对他们的证人进行对质的权利,因为那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保护措施。我认为,唯一改变的重要事项是社会对所谓的精神伤害(这正是我们被告知儿童证人在此种情形下所遭受的伤害)的看法以及社会在两种极端程序之间的利害权衡(一种程序确保百分之百地将所有虐待儿童的人入罪,而另一种程序则确保百分之百地为那些被错误指控为虐待儿童的人脱罪)。我毫无疑问地认为,从整体上说,社会对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满意的。但是我们不应就此假定判决没有消除此前存在的自由。
宪法发展缺乏指导性原则
我曾提出观点认为,美国人民可能会接受宪法限制公民自由的规定,但这并不表明宪法发展论者在决定宪法如何发展方面遵循了美国人民的意愿。他们并没有那么严格地遵循。甚至,作为一个团体他们根本就没有遵循。或许,宪法发展理论最突出的缺陷,除了它违背了宪法发展的本质外,是在指导原则方面无法达成一致并且根本没有机会达成一致。万物皆流变(Panta rei)并不是一个十分有效的宪法解释原则。法官必须思考的是,发展何时发生以及会朝什么方向进行?大多数人的意志是否区别于报纸、广播节目、民意测验以及民间团体的聊天?这是休谟、约翰·罗尔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只要讨论的问题超出了宪法是否静止不变的范畴,发展论者就可以分裂成不同的阵营,像各种对真、善、美的不同理解那样。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意味着发展论完全是个不切实际的宪法理论。
需要提醒的是,我并不就此认为原旨主义者总能达成一致观点。关于原始含义甚至原始含义如何应用总是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但是原旨主义者至少知道他在寻找什么:文本的原始含义。通常(甚至,我敢说是经常)那很容易识别并可予以简单应用。有时(虽然不是通常)在考虑原始含义方面会存在不一致;有时在原始含义如何运用于新的和不可预见的现象方面会存在不一致。例如,宪法第一修正案如何保证“言论自由”运用于新的技术领域,而这些领域在修正案产生之时并不存在。比如广播车或者政府许可的无线电视。在此类新领域中,联邦最高法院必须遵循宪法第一修正案投射的轨迹,也就是说,决定修正案到底要规定什么。毫无疑问,这项工作没有固定程式,需要进行主观判断。
但是,与宪法发展理论的不确定性相比,在决定原始含义并将其运用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不确定性则显得微不足道。曾经被禁止的法律现在被解禁,曾经允许的法律现在又禁止了。而这些变化的奥秘则不为人知且无从知晓。原旨主义者(即使他不知道所有的答案)至少知道其中的许多答案。例如,对质条款要求面对面。在发展论者看来,每个问题都是有待讨论的,每天都是全新的。最高法院至少有三位大法官坚持认为死刑违宪,尽管死刑的适用问题在宪法中有明确表述。宪法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大陪审团条款规定,未经大陪审团控诉,任何人不得被判处死刑。不过这些都没有用。依照宪法发展理论,死刑可能变得违宪,而且是由每位大法官自己来决定(虽然没有任何我能看得到的标准)这个问题(死刑是否违宪)。
作为最后的分析结论,在无数的可能性中,发展论者在决定宪法发展问题上将遵循何种原则也许并不重要。不管他提出何种主张,最终一部发展的宪法将按照大多数人的意愿发展。人们乐于让九位大法官来解释宪法,只要人们相信这(像解释制定法一样)基本上是大法官的工作,细致考察文本、文本的历史、对文本的传统理解、司法先例等。但是,如果人们逐渐相信宪法与其他的法律文本不一样,这将意味着,(宪法)不再具有它所表达的或者在常规理解之下的含义,而是根据“演进中的合理得体的标准”所应该具有的含义。那么,人们对宪法解释者的要求将不再是公平、合理以及拥有专业的法律人素养。更具体说来,他们将寻找在演进标准方面与他们保持一致的法官,以及在宪法应该怎样方面与他们保持一致的法官。
在我看来,这正是我们现在的发展方向,甚至是我们已经到达的地方。75年前,我们坚定地相信一部根基牢固不变的宪法,因此我们用宪法第十九修正案赋予妇女投票权。斗争并未发生于法院,也很少有人认为它可能会成为斗争之地,尽管宪法保障法律上的平等保护。该条款自其于1920年通过之日起就并未保证平等的投票权,而是允许不止在年龄,还有在财产和性别基础上的区别对待。有谁会怀疑,如果问题拖延到今天,可能出现不以修正案的形式修正《宪法》,而法院却会成为被选定的改革实施者?美国人民转而相信发展的宪法,一个含义视其时代之应有含义而定的“变动的”文本。与这种转变相关的是,在遴选联邦法官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新情况,即根据法官们关于一系列宪法发展方面的观点进行遴选与任命。如果法院可以再次自由地改写宪法,他们一定会将宪法改写成大多数人所期望的样子,法官遴选和任命程序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当然,这将是权利法案的末日,因为其含义将恰恰取决于它原本预期用来对抗的主体:多数人。我们试图使宪法在任何时代都无所不能的企图会导致宪法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