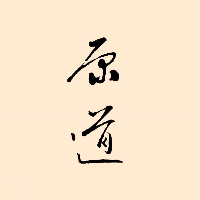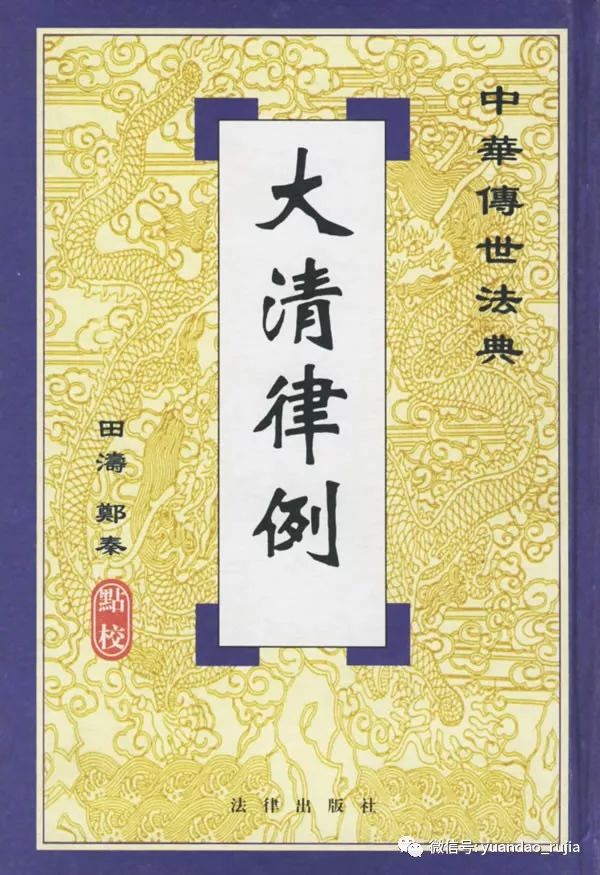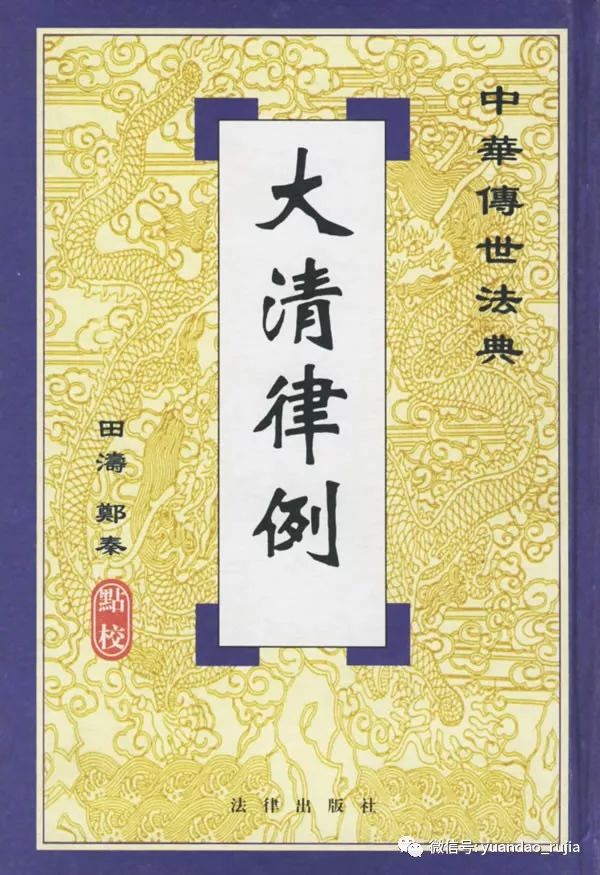清代新疆一体多元法律格局之成因分析
白京兰
(《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1999年出版)
内容提要:清代承袭并发展了汉唐以来的经验,对新疆地区的治理更为深入与广泛,民族立法与法律治理方面尤其突出,其得失足资后世之治。
由于复杂的地理与人文等因素,清代统一新疆后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新疆地区国家制定法、宗教法以及习惯法等同时并存,形成法律体系及司法实践的一体多元格局。
一体之下多元并存,多元法律寓于一体,成为清代新疆法律发展的基本脉络和突出特点。这种法律的一体多元发展趋势构成了传统中国法律文化发展至清代表现于新疆地域的一种独特性,亦是中华法文化一体多元历史发展态势的突出表现。
鉴于清代新疆法律的多元对于彼时现实政治及其后诸时期中国边疆政治所产生的深远复杂影响,清代新疆的法律在凸显中华法文化一体多元特性的同时,也构成当代中国边疆治理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的足资汲取与借鉴的宝贵的资源。
关键词:清代;新疆;一体多元;法律格局
学界有论“直到清代之前,边疆问题并不是决定整个大一统王朝命运的关键所在”。
细绎此说,其中深意有二:其一,清代实现了历史以来中央政权对边疆地域最为广泛与深入的管辖,“拓疆万里”与“规制赅备”绝非妄语。广袤边疆已隶中华王朝所属,边疆治理由此构成王朝政治的重要内容并深刻影响大一统王朝的发展及其演变;
其二,近代以来,清王朝已渐被纳入世界体系并置身国际政治格局之下,在此进程中边疆与内地已成共进退之紧密一体。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形势之下,边疆问题至清代已愈益成为王朝国家核心而非边缘的重要问题。
其中,“东扞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倚葱岭”同时外有俄英之耽耽虎视内有多元复杂之人文环境的新疆,成为有清一代最具特殊性也最具复杂性与重要性的边疆区域。
基于这样一个宏阔而深刻的背景以及诸多与边疆相关的历史问题并未因王朝时代的结束而不复存在甚至愈益突出,边疆问题的深入考察无疑具有超越地域与时代的重大意义。
王朝政治之下法律及其运行既是施政之要端同时亦是决定政治成败之要因,尤当关注。纵观历史,清代的边疆民族法制建设“达到了中国历代民族立法的最高峰”,其法律治理的深度与广度远轶汉唐与元明。
就清代在新疆的法律实践而言,虽不乏成效亦足多发人深省处。其一体与多元的法律格局及发展演变不论是在治边历史经验的汲取还是其所提供的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理论反思都极富价值与启发。
清代新疆的法律治理实践中,以《大清律例》为核心的国家制定法、回疆主体民族维吾尔遵行的伊斯兰教法以及蒙古、哈萨克等民族习惯法多元共存,
他们在施政实践中各有相对稳定的作用领域,以国家制定法为主导的多元法律共同维护新疆地区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形成清代新疆地区独特的一体与多元的法律格局。
清代新疆法律一体与多元格局的形成既有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因素与人文历史渊源,也有多民族格局之下具有深厚底蕴的多种宗教与文化的深刻影响,而现实政治中清王朝复杂多元的帝国构造,更是直接影响了清代对新疆的政治管理模式以及法律发展与演变的格局与方向。
凡此种种,它们共同构成了以一体与多元为基本特征的清代新疆法律得以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背景与生成基础。
- 一、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环境
新疆的历史发展中一直存在着法的多元,同时也一直存在以向心的整合的因素为基础的、以中华文化为核心为依归的多元法律的一体化。
(一)独特的地理环境
新疆地处亚洲大陆中心,长期以来一直是各游牧民族活动的场所和频繁迁徙的交通孔道,俄国学者鲍戈亚夫连斯基曾以略带诗意的语言描述迁徙流动于此地域的诸民族:“他们来到此地,到处游牧,以后或者西向转移,或者黯然从历史地平线上消失,不知去向”。
迁徙流动之中的民族文化同时亦具有突出之特点:“中国西部地区既然地处亚洲大陆中心,自古以来也就自然成为民族大迁徙的必经之路。
同时,作为一个通道,它不过是这个民族大迁徙路程中的一段,不可能成为某种业已定型的文化中心。
它从来就只不过是演出若干历史插曲的地点,这些插曲的幕间休息和前后间隔或长或短,又是相互联系,有时又毫不相干。不可能成为上演一出前后连贯、有一定长度的史诗的舞台”。
鲍戈雅夫连斯基过于强调与关注新疆地区民族与文化的变动不居而并未把握汉以来新疆与中国内地一直存在着的密切的内在联系,然而他对新疆地区民族流动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的多元所作出的洞察和描述却不可不谓深刻。
地处欧亚大陆的结合部、多民族共存与地理环境的南北差异等因素决定了新疆文化的多元特点,同时也决定了多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补成为新疆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
在世界文化中,新疆文化亦因其多元内涵而独树一帜。季羡林先生曾多次强调其重要性并明确指出:“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世界各民族共同创造了许多文化体系。
依我的看法,共有四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穆斯林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体系。
四者又可合为两个更大的文化体系:前三者合称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可称西方文化体系。而这些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世界上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新疆”。
在地处中西枢纽之地理位置而汇聚中西文化的同时,新疆同时具有一种自然地理因素而致的对中原地区的文化内属性质。
新疆基本地貌可概括为“三山夹两盆”,自北及南为东西走向的阿尔泰山、天山和昆仑山,以天山居中将新疆分为北疆与南疆。
(新疆略图)
天山由东向西南倾斜,昆仑山则由东向西北延伸,两山交汇于帕米尔高原,此种地理结构就“好比一个巨型口袋,袋底在帕米尔高原,开口则朝东,通过河西走廊与中原地区相接,交通相对方便”。
这构成了新疆自汉唐以来始终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中原地区保持密切联系并成为一体的重要地理因素。
中亚史学家加文·汉布里也曾指出:“我们可以说,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山链,将中亚地区分成了两半,这条山链起于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附近,终止于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地区附近。
除了新疆的维吾尔人和中国东干人外,伊斯兰教的影响被限制在山链以西。而在山链以东,则强烈地受到西藏佛教和汉族文明的影响。”
鲍戈亚夫连斯基也指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以其地形而言,是世界上最大山脉与戈壁的结合体……这些崇山峻岭,主要集中于该地区西部,成为自然屏障,将它与其他国家隔开。
而戈壁位于东部,一直伸延到长城脚下。由于戈壁是完全可以逾越的,它很自然地将长城外西部中国与中国内地连成一片”。
(二)历史上西域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
因西域地区各民族始终保持着与中原地区展开的密切而广泛的文化交流,新疆文化在具有鲜明的外来文明特质的同时,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之特色。汉唐以来,中原地区与西域文化就始终处于相互交融之中。
出土汉简与绢帛表明,汉代如“历法、占卜、药方、兵学、算学、小学等”都已传入新疆境内。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诸如经史、诗文与佛、道典籍等各类纸质书籍的种类和数量都大大增加。
位于新疆东部的高昌(即今吐鲁番)更是中原文化传播的重地。《魏书·高昌传》载“国有八城,皆有华人”,《梁书·诸夷传》载:“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
《北周书·异域传》载:“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孝经,置学官子弟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胡语”,又载“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
唐代中原与西域的往来更加密切,这突出表现在天山以南回鹘文化与汉文化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汇。
“在此以前的时代,西域人和汉人各保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从而未能表现出明显的融合。现回鹘人则不问文化的系统种类,广泛予以摄取。这些东西在其社会中渐次融合,于是形成了浑然一体的合成文化”。
唐朝都城长安甚至兴起“胡化”之风。宋朝时期的地方割据政权喀喇汗王朝虽然奉伊斯兰教为国教,对外仍宣称自己为“桃花石汗”,即“中国之王”。
同一时期的于阗尉迟氏地方政权仰慕华夏文化,行政建置模仿唐朝并改尉迟氏为李氏,号“李圣天”,后世称“于阗李氏王朝”。
凡此种种都表明汉唐以来中原与西域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著有《西域文化史》的日本学者羽田亨称:“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能否认汉文化从古以来就已及于此地的事实。”
另一位日本学者橘瑞超也在著述中指出:“大体上看,中国多次并很长时间统一着中亚地区,绝不能说印度统一过这里,因为发掘出来的文物表明,印度文明即佛教文化曾盛行于这一地区,但有关政治的东西是属于中国系统的”。
客观地说,汉唐尤其是唐朝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文化对西域地区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时期。
及至清代,新疆的人文环境发生了较为重大的变化。其间伊斯兰教成为回疆地区维吾尔人的全民信仰的宗教,一方面回疆地区因与周边诸中亚政权共同信仰伊斯兰教而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另一方面,以满族权贵为主的清代政权在统一新疆后的施政实践中因多种因素而仅强调军事,消极对待伦理教化及文教事业于回疆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域之推进,因此,清代新疆尤其是回疆与中原地区文化之间渐形隔阂,人文环境愈加复杂。
并不夸张地说,这种变化对清代乃至其后的民国甚至当今新疆的政治发展与法律格局均产生深远与深刻的影响。
(三)清代新疆的民族、宗教与文化
自古以来新疆便是多民族生息繁衍之地。清代是“新疆民族的定型时期,并最终形成了以维吾尔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分布的格局”。
清代新疆的世居民族主要有回(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布鲁特(柯尔克孜族)、色勒库尔人(塔吉克族)、以及汉族等;
从国内其他地区迁入的主要有满(族)、达斡尔(族)、锡伯(族)、汉回(回族)等,其中察哈尔、达斡尔和锡伯主要是由于清朝政府推行军府制以及屯田制而从东北等地迁移而来;
从国外迁入的主要有安集延人(乌孜别克族)、俄罗斯人(族)以及史称鞑靼的塔塔尔(族)。可见,清代是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在历史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定型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些民族共同创造了清代新疆色彩斑斓的多元文化与社会生活。
历史上的新疆一直存在多种宗教的演变与发展。从初民社会的以自然崇拜为主要内容的原始宗教和萨满教,到公元前4世纪迄公元前1世纪祆教、佛教等相继传入后逐步形成以佛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再到10世纪前后伊斯兰教传入后以佛教和伊斯兰教同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
14世纪中叶迄16世纪初,在东察合台汗国的强力推进下,西域宗教文化格局转而演变为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多宗教并存局面。
至清代建立政权前后,随着新疆民族分布格局衍变为“南回北准”,宗教文化也相应形成“南伊北佛”的新格局,新疆进入到以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时期。
有清一代在新疆地区与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并存的还有汉传佛教、道教以及新传入的基督教、天主教与东正教等。
藏传佛教是佛教的一个重要分支,因其自西藏地区传播开来,故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元代随蒙古族传入西域,数百年来一直在蒙古族中流行。
16世纪末17世纪初藏传佛教在北疆地区逐渐兴盛,迨至清代,察哈尔蒙古、满、达斡尔、锡伯等迁入新疆,成为藏传佛教的信奉者,藏传佛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藏传佛教庙宇)
清代藏传佛教的传播范围主要是天山以北及南部蒙古各部聚居的地区。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约公元5世纪前后传入新疆后,主要流行于吐鲁番、哈密等汉族聚居的区域,多为汉族所信仰。基督教、天主教未能在清代新疆有广泛的传播。
对新疆社会政治生活影响较大的是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创立于公元7世纪,公元10世纪左右传入新疆,历经喀喇汗王朝(10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西辽及蒙元政权(12世纪初至14世纪中叶)以及东察合台汗国(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初)大致三个阶段近500余年的曲折发展,伊斯兰教在新疆尤其是回疆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取得较大进展。
伊斯兰教逐渐成为维吾尔族以及其他一些民族主要信仰的宗教之一。17世纪末,准噶尔蒙古归并叶尔羌汗国统治回疆地区时,以和卓教派为代表的伊斯兰宗教势力已全面影响天山南路社会政治生活。
清代统一新疆之后,采取因俗施治的方策,维吾尔族信仰的伊斯兰教与蒙古族信仰的藏传佛教作为新疆主要的两大宗教,深刻影响着清代新疆的政治与社会生活。
与佛教、道教虽同为宗教,伊斯兰教却两世兼重且尤重现实积极入世,以教义为基础而形成的宗教、道德与法律为一体的伊斯兰教法,更是自成体系,特色鲜明。
多种宗教中,伊斯兰教对清代新疆社会始终发挥着不容忽视的持久、深刻的影响。伊斯兰教法更是构成了清代新疆多元法律体系当中重要的一元,深刻地影响着回疆基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及清代新疆政治法律格局的发展演变。
- 二、一体多元法律格局的政治基础
清代新疆法律的多元共存与一体化发展,有其深厚的人文历史渊源,亦有现实政治的深刻影响。
18世纪中叶清朝统一新疆并确立了对天山南北各路的主权管辖,由此结束了元末以来新疆数百年的战乱与割据,新疆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统一王朝的清政权而言,其施政诸端基本沿袭明代,所谓“清承明制”,尤其是法制的承袭,以至于有学者称清代法律“承袭的比创作的多”。
但就统治新疆而言,明代确无任何经验可资借鉴。新疆在蒙元之后便基本未与中央政权有政治上的密切联系,明代无心远域,弃地闭关,基本丧失了对新疆的管辖,势力范围仅及哈密,新疆一直处于地方割据政权统治之下。
与西南地区自元以来中央政权持续不断的经营及改土归流与中华教化的推行相比,统一新疆后清政府面对的是一个长期与中原王朝相暌隔声教不及的陌生的统治环境,
迥异于内地的各种社会组织与经济形式也使州县制的行政管理体制难以普遍推行,尤其是已经形成相对成熟与稳定的伊斯兰文化体系的回疆地区,直接治理难度之大可以想象。
就当时情势而言,新疆无疑是清代边疆治理所面对的一个新环境、新问题与新挑战,绝非简单蹈袭汉唐旧制即能应对。
面对这样一个复杂、陌生与遥远的极边地域,由民族首领各司其民实施因俗而治同时以完善的军政建置为保障成为清廷审慎考虑之后的首选,其可取者有三:(1)弥补军府体制民政职能不足的弊端,节约边疆治理的行政成本进而消弭朝臣“事西耗中”之非议;
(2)规避直接治理下各有其特殊体制、风格和价值观念的文化相接触时必然会发生的各种冲突和矛盾;
(3)笼络边疆各民族上层,形成满洲与西北各民族的坚固的政治联盟以此削减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原对清政权的统治压力,此点突出体现了清王朝满洲统治的民族性。
“因俗施治”体现了清朝对如何实现新疆治理的多种因素的审慎考量,虽仍未脱传统治边之思维,但就其制度设计之严整而言迥非汉唐可比,不失为统治者审时度势的明智之举。
就其实践而言,“因俗施治”是以分权为手段而达致集权的目的,而分权的客观后果之一是权力格局的多元及各民族习惯法与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得以保留,“因俗施治”由此成为清代新疆法律多元并存状态的原因之一。
鉴于因分权而可能引起的地方权力集团的坐大及背离中央政权的隐患,清廷采取了诸多措施进行权力的统合,其要端有三:(1)在赋予各民族首领程度不一的自治权力的同时,确立“众建以分其势”的原则,对其权力进行限制。
具体而言,回疆各城均设阿奇木伯克但相互之间并无统属关系;东归土尔扈特各部被异地安置并分设盟旗以打破渥巴锡总领该部之局面;哈萨克、布鲁特等边地游牧民族亦分设头领而不置总管之人亦是在对少数民族的管理中通过分权以达分化控制之功。
观其要旨即为以民族与民族之间甚至民族内部的分化与牵制限制其自治权力的行使;
(2)以军府官员实施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以此达到权力的有分有统并最终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政治目的。
各民族首领所享有自治权力有大有小,以札萨克王公所享权力较大,即便如此,其施政也处于驻扎大臣之监督之下,其所辖地域也明确为中华王朝主权所辖的一部分;
(3)就法律治理而言,立法权由清代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执掌;重要刑民案件审断依照以大清律例为核心的国家制定法拟断,少数民族习惯法及伊斯兰教法只能在有限的基层民事领域当中发挥效用。
以上诸点体现了清王朝作为中华王朝的政权性质及其在边疆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决定了王朝政治运行及法律一体化的方向。
从政权性质的角度进一步分析,清朝是一个以满洲为统治主体的封建王朝,其统治结构同时具有中华王朝的国家性质与满洲统治的民族性质。这种政权结构的特殊性造成清廷在施政实践中的两面性,即对应于多元与一体的分权与控制。
作为满洲统治者,面对人口占绝大多数文化占绝对优势的中原汉人,他感受到的是巨大的统治压力以至于“各种政策均带有精神紧张性”(尤以民族隔离为甚),出于对汉人的戒备他通过给予边疆各少数民族上层诸多自治权力和种种优遇使其成为牵制汉人的同盟军。
与此同时,作为大一统的正统中华王朝形象的树立与维护,他又必须限制自治权力的行使避免地方权力游离于中央政府控制之外,以此实现帝国政治运行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
这种政权结构的“双重政治构造”在事实上构成了清代新疆法律一体与多元发展的超越清廷行政能力不及与“因俗施治”等表象分析的深层次的原因。
(左宗堂收复新疆)
道咸以来,形势大变,外患的空前严峻迫使清廷放弃王朝内部民族之间的畛域之分转而强化内部力量的整合以应对真正的共同的敌人。
国内政治格局尤其是满汉权力对比随之发生变化,清王朝“满洲”族性不断削弱,边疆政治体现出越来越多的与内地的趋同性,新疆终于打破了长期以来的特殊政权建置成为行省之一,“因俗而治”为划一治理替代,新疆多元法律的一体化也因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由于法制本身与社会的密切关联,影响清代新疆法律格局变化与发展的因素非常多,从某种程度而言,清王朝作为大一统中华王朝的国家性质与作为民族政权的满洲族性这种双重政治结构的现实作用事实上发挥了较大的影响,
新疆政治格局与权力结构由此所形成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深刻影响了清代新疆法律的独特发展路径,其迥别于内地直省及其他民族地区的司法体系与法律运作尽显清代法制之“创作”的同时,其对新疆政治格局的影响是非常复杂深刻的。
- 三、一体多元法律格局的法理依据
法律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除去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清代新疆法律之“一体与多元”的发展亦有其内在的法理依据。
(一)情理法混一的法观念
无论是在语义学角度详加考证“法”字的深邃内涵,还是在绵延相传的法典文本以及正史“刑法志”的字里行间体悟,抑或是透过大量的司法裁决文本展开的对法的实践的历史考量,我们都不能不说传统中国的法是一个天理、国法、人情的混合体。
《汉书·刑法志》有谓:“圣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
清代乾隆皇帝为重修之《大清律例》作序,序文曰:“简命大臣取律文及递年奏定成例,详悉参定,重加编辑。揆诸天理,准诸人情,一本于至公而归于至当”。
(乾隆皇帝)
此又为基于最高统治者的立场对天理、国法、人情共为一体的认识。而司法实践中存留至今的大量判牍文集及司法文书类的资料都充分表明对法的这种宽泛的认识与理解并不仅仅是官方的,亦不仅仅是文本的,更是普通民众的法意识。
概括地说,传统中国的法观念就是一个以“宽泛性、结构性和混合性”为特点的大法观念,在这个大法观念之下的法是“合乎情理亦即具有正当性的秩序体系,包括意识、规则和习惯”,
它涵盖了实证主义法律观所界定的法之外的多样性的规则与秩序体系的存在,同时亦揭示法是一种总体上由国家法与民间法共同构成的多样性甚至是多元性的统一。
同时,法的统一性并不排斥法的多样(元)性,相反,统一性的广大正是建立在多样(元)性的基础之上。
而这正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相通。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首先承认差别,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孟子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
《易》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以上种种均为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主张兼收并蓄的表达。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情、理、法”混一的“大”法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包容性的生动反映,亦为对清代新疆法律多元并一体发展之客观现实的内在原因的解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关于“法”观念的认识亦由此构成清代新疆法律一体与多元发展的文化基础与法理依据。
(二)基于差异的法的互补性
清代新疆国家法、伊斯兰教法、蒙古法、哈萨克习惯法等多元法律共存并以国家法为主导的一体与多元格局是建立在法的互补性基础之上的。基于差异的法的互补性亦构成清代新疆法律多元并一体发展的法理依据。
清代新疆的多元法律之间具有性质上的差异性,以伊斯兰教法与国家制定法为例。
历史上的伊斯兰教法包含教义、刑事法律规范以及相对成熟并发达的民事法律规范等并融道德与法律为一体,是一种宗教性质的法律文化。
清代统一新疆之后,推行政教分离政策并严格限制伊斯兰教法在刑事司法领域内的适用,清代新疆的伊斯兰教法因而更突出地表现出对基层社会民众婚姻、家庭、继承以及民事关系调整的私法性。
相较而言,清代新疆的国家法则是以儒家宗法礼教为内核的伦理性的法律文化,它注重以行政管理与刑事制裁为主要内容的公法领域的调整与规范,具有突出的公法性。
二者之间虽然存在差异,但伊斯兰教法中“亦多可与中律相辅而行者”,而且它们并不存在于同一领域与同一层次,各有其适用范围与领域,因而这差异恰恰构成了清代新疆法律治理方面的互补。
基于差异的法的互补性亦因而构成清代新疆法律一体之下多元发展的法理解释。
(三)行使法的主体的正当性
清代统一新疆之后因民族而异推行因俗之治。回疆地区的伯克、蒙古各部的首领以及部分哈萨克游牧民族的头人等都被纳入国家官制序列,由清廷任命或册封并颁发印记等。
其中对回疆伯克的管理尤为详尽周密,包括伯克的编制、职掌、任免、回避、养廉、朝觐、休致以及违法行为的惩处等等。
根据《回疆则例》,具有司法职能的伯克为“总理刑民”之哈孜伯克、“分理回子头目词讼”之斯帕哈孜伯克、“分理小回子词讼”之拉雅哈孜伯克以及“缉奸捕盗,兼管狱务”之帕提沙布伯克等。
通过吸收了各民族上层的国家官僚体系的建立以及行政权力的授予,回疆地区的伯克、哈密与吐鲁番以及蒙古各部的札萨克王公等成为清代新疆法律治理中拥有行政管理权的国家法律意义上的行政主体,其权力来源于以皇帝为代表的王朝国家。
(艾提尕尔大清真寺)
这样,伯克与札萨克王公等以伊斯兰教法、蒙古法以及习惯法等为主要内容的对属众的司法权的行使便具有了权力渊源的正当性,这同时亦构成了清代新疆法律一体与多元发展的正当性与内在法理依据。
综上所述,清代新疆的法律格局长期呈现国家制定法、宗教法、习惯法等多元法律并存的样态,军府制时期尤为突出。
1884年建省后,虽然法律的多元现象依旧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毕竟新疆行政建制基本实现了与内地的统一,新疆多元法律的整合亦随之进入一个新阶段。
这种基于地理、人文等多重因素而致的法律的多元及一体发展趋势构成了传统中国法律文化发展至清代表现于新疆地域的一种独特性,亦是中华法文化一体与多元历史发展态势的突出表现。
鉴于清代新疆法律的多元对于彼时现实政治及其后诸时期中国边疆政治所产生的深远复杂影响,清代新疆的法律在凸显中华法文化一体与多元特性的同时,也构成当代中国边疆治理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的足资汲取与借鉴的宝贵的资源。
白京兰,新疆大学法学院教授、新疆稳定与地区经济发展法制保障研究基地研究人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代新疆国家法律建设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研究”(15BFX022)和新疆教育厅重点项目“新疆地区法制的历史发展与演变”(Xjedu010915b02)的阶段性成果。
【白京兰】清代新疆一体多元法律格局之成因分析|原道辑刊
清代新疆一体多元法律格局之成因分析 白京兰
打开APP阅读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