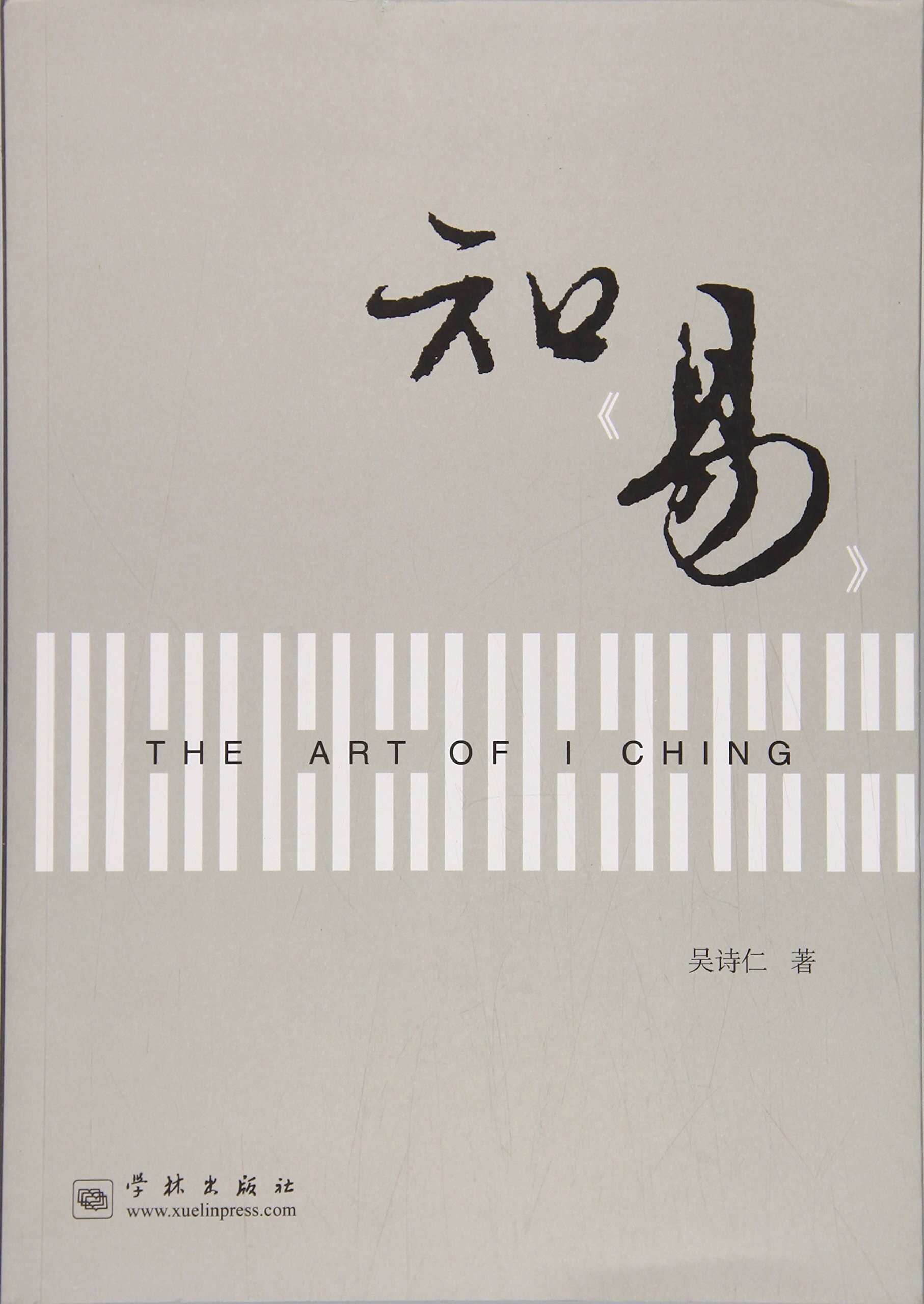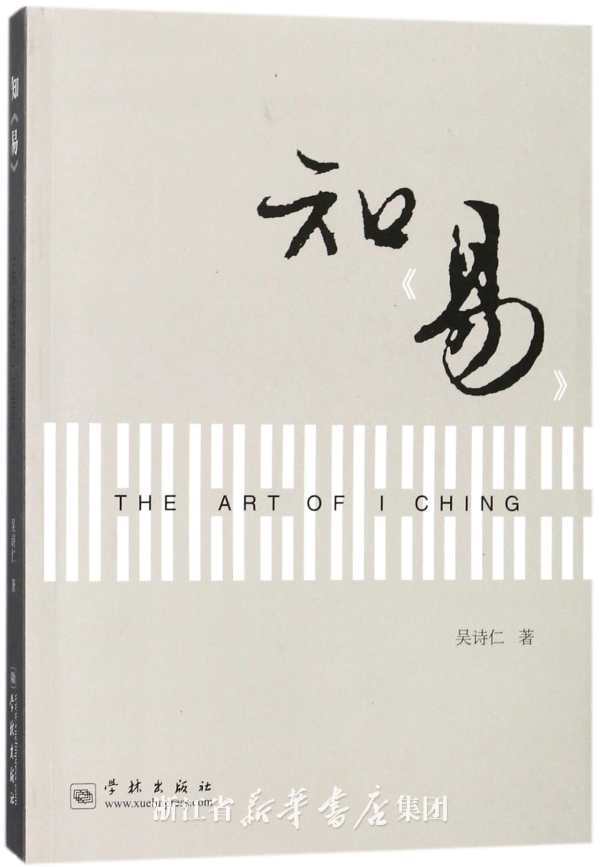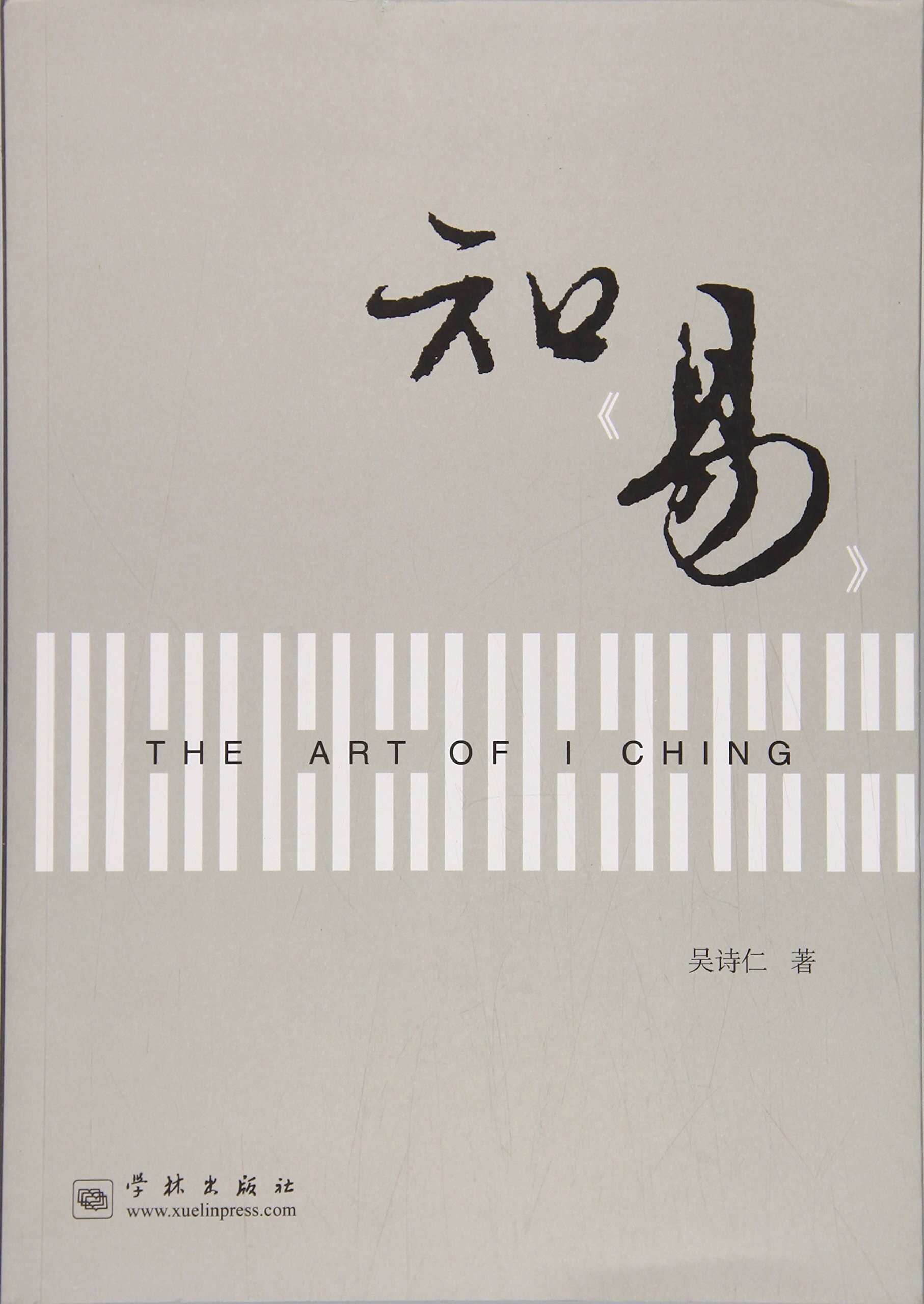汉武帝好《易》尚贤,好伏羲以来圣贤书,慧悟洞彻,尤敬神明。作为史官,司马迁在《史记》中推崇易经的卜筮功能是神奇而灵验的。
并且,《史记》记载了周易一书的成书过程,《史记·太史公自序》“伏羲至纯厚,做《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史记·周本纪》“西伯盖继位五十年,因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汉武帝为啥酷爱易经呢?
刘彘幼时便熟读易经,在景帝前,恭敬应对,有若成人。
有继子杀母,依律,大逆论。景帝疑之,诏问太子,对曰:“夫继母如母,缘父之爱,故谓之母尔。今继母杀其父,则下手之日,母恩绝矣。宜与杀人者同,不宜大逆论。”帝从之,曰:“彘者圣彻过人也。”因改名彻。刘彻就是后来的汉武帝。
孔子解释“咸卦九四☱☶曈: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爻辞时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此处司马迁有误),故长于变;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易经爻辞没有论及五行。但并没有掩盖司马迁对易经的推崇: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太史公曰: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熟能注意焉”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
《史记·日者列传》“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见,代王之人,任于卜者。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 司马季主者,楚人也,卜于长安东市。宋忠为中大夫,贾谊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从论议,诵《易》先王圣人之道术,究遍人情,相视而叹。贾谊曰:“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今吾已见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试之卜数中以观采。”二人俱同舆而之市,游于卜筮中。
天新雨,道少人,司马季主闲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谒,司马季主观其状貌,如类有知者,即礼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马季主复理前语,分别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差次仁义之际,列吉凶之符,语数千言,莫不顺理。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载者,多不见于篇。及至司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为郎时,游观于长安中,见卜筮之贤大夫,观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动,誓正其衣冠当乡人也,有君子之风。夫司马季主者,楚贤大夫,游学长安,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博闻远见。观其对二大夫贵人之谈言,称引古,明王圣人道,固非浅闻小术之能。及卜筮立名声千里者,各往往而在。传曰:“富为上,贵次之;既贵各学一伎能立其身。”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绝人之风,何可胜言。故曰:“非其地,树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者,当视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观士;子有处所,可谓贤人。”
由上可见,司马迁也是深懂易经的真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