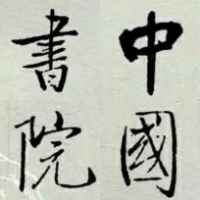邓洪波:唐代官府书院研究
一.丽正、集贤书院的设置
唐代中期,当民间循着“聚书——读书——聚众读书”的路径,衍生出“书院”这一前所未有的士人组织时,官府也依汉魏以来故事,因袭“聚藏群书”,“校理经籍”的秘书省之责,推出了丽正书院、集贤书院这一全新的作为官府的学术性机构。
汉魏以来,国家对图书典籍都极为重视。西汉的兰台、东汉的东观皆为宫中藏书之所,设有秘书郎、校书郎等职,掌管校刊图书,订正讹误。至桓帝延熹二年(59),台始正式设在秘书省,掌典图书,考核古今文字的异同。秘书省隶于九卿之一的太常卿,因其执掌禁中图书秘记,故名。魏文帝时改称秘书监,掌艺文图书之事。晋代曾一度并入中书省,但惠帝永平元年(29)即复置秘书监,不久又改称秘书寺、秘书省,并将原属于中书省和秘书著作改隶于秘书省。按著作之名取于东汉,其职责是修撰国史,即编写当代史,但当时还没有专职专员,都由他官兼领。魏明帝始置著作郎,隶中书省专掌其事。晋因魏制,但以中书省职典中枢机要,兼职史领,事权不专,到元康二年(292)即划归秘书省管理。至此,秘书省除了掌理国家典籍之外,又多了一项编修国史的任务。虽然不久另行成立了著作省,但它仍然隶属秘书省。南北朝时,各政权基本沿习此制,以秘书省领著作省,管理国家图书典籍和编修国史。隋代虽改秘书省为秘书监,改著作省为著作曹,但其职责和隶属关系仍然没有变。
秘书省的工作,不论是校勘典籍,编制目录,还是撰写国史,都离不开图书,因为这些书的聚积,就自然形成了一些有名的藏书机构,除了上述的兰台、东观之外,还有梁武帝时的文德殿、北齐的文林馆,后周的麟趾殿,隋炀帝的秘书外阁、观文殿等,都是“列藏众书”。秘书省围绕这些藏书而开展的修书、校书、刊书等工作,往往很容易就演化出一些学术基地,如北周的麟趾殿就是如此。史载明帝宇文毓(557-560在位)好学,博览群书,集公卿以正月文学修养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掌刊校经史,时号“麟趾学”,参予其事者皆授“麟趾殿学士”之职。《通典·职官三》说:“后周有麟趾殿学士,皆掌著述”,可见作为藏书之所的麟趾殿,已经变成了一个肩负研究使命的学术机构。
到唐代,中国社会进入一个空前繁荣强大的时期,文化发达,书籍增多,国家仍设秘书省主图书、著作二事,这一点在专记唐代官制的《唐六典》中有明确的交待,其称:“自汉延熹至今,皆秘书省掌图籍”。虽然主管大唐“书籍在秘书令”,但“禁中之书,时或有之”,除秘书省之外,门下省的弘文馆、中书省的史官、东宫的司经局和崇文馆等都有丰富的藏书。[1]这些机构都从事与秘书省相类似的整理、校刊图书的工作,如弘文馆,太宗即位时,馆中藏书达到二十余万卷,设学士,“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参议“朝廷制度沿革,礼仪轻重”,设校书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崇文馆设学士“掌经籍图书,教授生徒”,设校书郎“掌校理书籍”;司经局设洗马“掌经籍”,凡“图书上东宫者,皆受而藏之”,设文学“分知经籍,侍奉文章”,设校书、正字等“掌校刊经史”。[2]凡此种种都说明,为了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官府加大了对图书收藏、整理、校刊的工作。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中书省在开元年间又创集贤殿书院,加入到了“刊缉古今经籍”的事业中。
集贤殿书院又称集贤院、集贤书院,它的前身是丽正书院又称丽正殿修书院、丽正修书院。有关集贤书院历史沿革最权威和全面的资料,是集贤院学士韦述所撰的《集贤注记》。韦述从开元五年(717)冬“敕就”秘书省撰续王俭的目录学著作《七志》并刊校四库书籍开始,到八年入丽正、集贤书院的创置与演变历程。至天宝十五年(756)二月,他以院中元老身份,感怀同时之人“凋亡以尽”,而“后来贤彦多不委书院本末”,因作此书,记置院经始、院中故事、修撰史书之次及前后学士姓名事迹。[3]此书今已散亡,惟宋人王应麟《玉海》以类书而保有其部分内容,兹据此并参考其他文献,将丽正、集贤书院的创建情况叙述如下。
丽正书院之设缘起于朝廷的一次大规模的修书行动。开元五年(717),唐玄宗采纳大臣们整理内府藏书,续修王俭《七志》及《隋书经籍志》等目录著作的建议,命昭文学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崇文馆学士褚无量一起“整比”四部之书。据《旧唐书·褚无量传》记载,书时“于东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写”,并“广采天下异本”传录,工作进展顺利。《新唐书·百官志》则称,乾元殿写四部书时,置乾元院使,下设刊正官、押院中使、知书官等职。六年(718)冬,西还京师长安,迁书东宫丽正殿,置修书院于著作院,于是乾元院更名丽正修书院,设置院使及检校官,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至此,丽正书院宣告正式成立。[4]
开元六年(718)设置的丽正书院在丽正殿,位于东宫正殿崇教殿之北,光天殿之南。除了太子东宫的这所丽正书院之外,不久又在京师长安与东都洛阳分置了两所丽正书院。京师丽正书院在大明宫光顺门外,本为命妇院之地,开元十一年分置,北院全取命妇院旧屋,院内东西长五十八步,南北长六十九步,规模较大,院中还设有仰观台,是一行大师为编制《大衍历》而测量天体星辰的地方。东都丽正书院在明福门外大街之西,而对武成宫,原本是太平公主的宅院,东西长四十一步,南北长五十八步,西向开门,开元十年三月始移书院于此。[5]由此可知,当前有三所同名异址的丽正书院在进行着同样的工作。至于其工作情形,我们从院中于开元八年增设文学直、修撰官、校理官、刊正官、校勘官信十一年又置修书学士中得知其概略。
开元十三年四月五日(725.5.21),唐玄宗召集“都知丽正殿修书事”张说等大臣商讨封禅之事,赐宴于集仙殿,谈得高兴,称“与卿等贤才同宴于此,宜改集仙殿曰集贤殿,改丽正书院为集贤院”,并下诏书,称“仙者捕影之流,朕所不取者;贤者济治之具,当务其实”。[6]于是,丽正书院遂改名集贤书院。集天下贤才,以济治于当世,这是唐玄宗为书院改名的本意所在。皇帝既有改名之诏,上述东宫、京师、东都三所丽也就随之改称集贤书院了。从此,“丽正”之声不闻,“集贤”之名大倡,文献记载往往以集贤标著,甚而有“集贤”而忘“丽正”之势。因此,这里要特别费些笔墨,叙述从丽正书院到集贤书院这段缘由。
开元之世,君圣臣贤,对文化事业都很重视,三所官府书院大概满足不了需要,于是又有第四、第五所集贤书院的创设。第四所集贤书院在兴庆宫,又叫兴庆宫集贤院,开元二十四年(736),皇帝御驾东都,西返之前,集贤院学士张九龄派遣直官魏光禄先入京师建造,它在和丰(一儿和风)门横街之南,与中书省相邻,院落不大,东西长只二十三步,南北长三十步。第五所集贤书院在华清宫北横街之西羽林仗院,又叫华清宫集贤院,开元二十八年建造,院内东西长四十八步,南北长五十步。[7]华清宫、兴庆宫两所集贤书院的情况,以往的论者从未涉及,这里有必要提请读者给予特别注意。
上述情况表明,从开元六年到二十八年间,唐代中央政权用22年的时间,由丽正而集贤,从京师到东都,完成了创置“书院”这一全新机构的工作。
诚然,如同所有新事物一样,设置书院作为政府机构,也遇到过阻力。史载:开元年间初创书院,作为学士之一的中书舍人陆坚,就“以学士或非其人,而供拟太厚,无益国家者,议白罢之”。知院士张说则不以为然,驳称:“古帝王功成则有奢满之失,或兴池观,或尚声色,今陛下崇儒向道,躬自讲论,详延豪俊,则丽正乃天子礼乐之司,所费细而年益者大。陆生之言,盖其达耶!帝知,遂薄坚”。[8]可见,在唐玄宗、张说这一代君臣提倡崇儒向道,延俊讲论,蒙古营造“广学开书院”的大趋势下,陆坚的意见很快被否决了,东西二都先后建有五处集贤书院,展开了盛极一时的文化学术工作。而且,后此五百年的唐文宗大和、开成年间,唐宣宗大中年间,集贤书院仍在开展活动,[9]此则又昭示出作为官府的书院已然定制而化入大唐帝国的政体之中。其后,五代各政权及宋、金、元三代都在中枢机构中设有集贤殿书院、虽然或隶中书省,或属秘书省,或与诸院并列,其地位高下有别,职责也有变化,但其因沿唐制而是明显的,可见其影响之长远。
二.集贤书院的职事设置与组织分工
作为官府的丽正、集贤书院,其组织比较严密。据文献记载,院中先后至少设有院使、检校官、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大学士、文学直、修撰官、校理官、刊正官、校勘官、修书学士、知院事、副知院事、判院事、押院中使、待制官、留院官、知检讨官、书直、写御书手、画直、拓书手、装书直、造笔直、直院、校书、正字、孔目官、专知御书检讨、专职御书典、知书官、编录官、典、入院、修书、修书使、刊校、校书郎等三十九种职事,[10]名目可谓繁多。每种职事既责任分明,各司其事,又相互配合,共同协作,维持书院的正常运作。
学士是集贤书院的核心。依官阶的高低,它有学士、直学士之分,按职讲的不同,它又有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修书学士之别。其设无常额,凡五品以上官为学士,六品以下官为直学士。学士中先宰相、常侍各一人分任知院事、副知院事,以为院中正副长官,又设判院事一人,协助正副长官管理院务。留院官、待制官、知检官等要职都由学士充任。唐玄宗拟设大学士居学士之上,以张说坚请而作罢。至德二年(757)曾设大学士,地位在学士之上,但两年后即罢。不为常例。学士的职责,《唐六典》有明确的记载,其称:
集贤院学士掌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申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如外。[11]
以上刊缉经籍、搜求遗书、申表学术是秘书省故有职能的承续,而辨明大典、征求贤才、顾问应对则是集贤书院的新创。可见政府这一新设机构的职能既有发扬传统的一面,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从中我们可以体裁味到大唐文化继承与开创的风采。
集贤书院学士皆一时豪俊伟杰之士,名重当时。开元年间,书院初设,学士有中书令(宰相)张说,散骑常侍徐坚,礼部侍郎贺知章,中书舍人陆坚等四人,其中张说知院事、徐坚为副知院事;侍讲学士有国子监博士康子元,太学博士侯行果,四门学博士敬会真,中书省的右补阙冯陟(冯朝隐)等四人;直学士有考功员外郎赵冬(一作东)曦,监察御史咸业,门下省的左补阙韦述、李剑(亦作李子剑)、陆去素、吕向,拾遗母煚,太学助教余钦,四门学博士赵元默,校书郎孙秀良等十人,合计十八人,世号“开元十八学士”。唐明皇曾命画师为他们画像,刻于东都洛阳上阳宫的像亭,并分列提写御之语,其称张说“德重和鼎,功逾济川。词林秀色,翰苑光鲜”;称康子元“才识清远,言谈幽秘。四科文学,六书文艺”;称赵元默“才比秋明,学兼儒墨。叙述微婉,讲论道德”;称孙秀良为“蓬山之秀,芸阁之英。雄词卓杰,雅思纵横”。凡此种种,虽为褒奖之词,但若非德才兼美之士,料也难得玄宗如此之高的评价。于是可知,芸香四溢的集贤书院确乎群英荟萃,诚为“郁郁文章之苑”,堂堂“礼乐之司”。学士之下,有两个分工比较明显的系统,一个负责“修撰文章”,以修撰官为首,一个主持“校理经籍”,由校理官掌管。修撰官、校理官之设无常员,从各衙门选人兼任,品秩与直学士相同,在六品以下。“皆以学术别敕留之”,即皇帝以学术标准决定其任免升降,若“校理精勤,纰缪多正”,可以褒奖,若“不能详核,无所发明”,则予贬斥。[12]校理一职,曾于贞元八年(792)罢置,改设校书四人、正字二人,至元和二年(807),又罢校书、正字而恢复校理。修撰官知名者有王仲丘、施敬本、赵冬曦、贺知章、孙秀良、咸业,校理官有归崇敬、郑钦说、吕向、工艺东方颢、萧颖士、卢迈、徐浩、冯定、石洪、张仲方、郑涵,校书则有范传正、丁公著、韦处厚,正字有柳宗元,皆为文学贤能之士,其中一些人后来还升入学士之列。
“校理经籍”一系,又可细分为校正制作图书、收藏保管图书,即图书生产与图书保管两条线。生产图书的职事,主要有“书直”、“写御书手”,共设一百或九十人不等,缮写经籍及御书,招擅长书法者充任,“皆亲经御简”,要求较严,后来又规定要散官五品以上者子弟方可“依资甄叙”;“画直”,员额八人,掌绘画插图之事,募擅长绘画者率任;“拓书手”,设六人,掌拓印碑文石经;“装书直”,掌装订图书之事,员额十四人;“造笔直”,制造毛笔,以供院中书写绘画之用,共设四人。图书的质量,则由校书、校理、刊正、检讨、正字诸职检验把关。
保管图书的职事,主要有“知书官”,设八人,分掌经、史、子、集四库之书,“每库二人,知写书、出纳、名目、次序,以备检讨”;“编录官”,管院中经籍的编录,涉及目录之事;“孔目官”,设一人,主管院中文书档案,收贮图书;“专知御书典”,典本是掌管各种事务的杂任职,此则为官司院中御书者。
如果说,以上学士、修撰、校理各职及其主持下的图书生产、图书保管工作颇多文化学术之色而少衙门之气的话,那么押院中使一职的设置,则颇能反映集贤书院作为官府的特色。此职始设于开元年间乾元殿写书之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沿置,由宦官充任,责在“掌出入,宣进奏,兼领中官,监守院门,掌同宫禁”。[13]于此可知,集贤书院平日“宫禁”森严,皇帝御驾,宦官守院,高官出入,一般人难得近前,此乃十足的天子“礼乐之司”,地道的官衙威严之气。
三.丽正、集贤书院的文化学术活动
丽正、集贤书院虽为官府,但它毕竟不同于治世牧民的衙门,刊缉古今经籍的任务,顾问应对的性质,都使它远离赋税兵农的实际政务,而致国于文化学术事业的追求。综约而论,其活动大致可以概括为出书、藏书、讲学、赋诗、顾问五个方面,兹分述如下。
第一.征求天下图书之遗逸,刊缉古今之经籍,是书院的首要任务。丽正书院的成立即缘于广“借民间异本传录”的一次征集图书活动。其后,搜访天下遗书,并将其校正刊缉,就成了院中最主要的日常工作,这从职事所设以书直、写御书人、拓书手、画直、装书直、造笔直等员额百数十人,占院中人员的绝大多数中可以得到反映。而老臣褚无量七十五岁逝世,“临终遗言,以丽正写书未毕为恨,上为举误哀废朝二日”,[14]这一充满感情色彩的记录,更昭示出刊缉经籍在君臣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书院出书数量,史有明文记载者凡二见。一是《唐六典》,称“集贤所写皆御本也。书有四部,一曰甲为经,二曰乙为史,三曰丙为子,四曰丁为集,故分为四库”,“四库之书,两京各二本,共二万五千九百六十一卷,皆以益州麻纸写”。[15]二是《唐会要》,称“天宝三载六月,四库更造,见在库书籍,经库七千七百六卷,史库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九卷,子库一万六千二百八十七卷,集库一万五千七百二十二卷。从天宝三载至十四载,四库续写书又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二卷。”[16]由此可以计算出,到天宝十四年(755),书院创设38年以来,出书累计已达71405卷。原材料的消耗,也可反映当年出书的情况。据《新唐书》记载,集贤书院所用纸、笔、墨等,都由太府供应,“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免五千百皮为笔材”。[17]《唐会要》卷三十五记有历年蜀纸消耗情况,其中大和四年(850)二月一条称:“集贤院奏,大中三年正月一日以后至年终,写完贮库及填缺书籍三百六十五卷,计用小麻纸一万一千七百七张”。由此可知,集贤书院每年出书用纸为11000余张或60000番不等。
由上引材料,我们还可以算出丽正、集贤书院每年成书卷数的一组数据。处开元六年建院士对天宝三年(718-744)更造四库时统计,27年间共成书54573卷,年平均约2021卷。天宝三至十四年(744-755),12年间写书16832卷,年平均给1403卷。开元六年至天宝十四年(718-755),38年时间,累计出书71404卷,年平均约1879卷。从这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集贤书院每年出书的数量呈下降趋势,越来越少。至大和天年(849)跌到365卷,已不及建院初期的1/5。这里,除了天下遗逸之书随着刊缉工作的深入持久越来越少的合理因素,即可以将此下降视作书院的工作成绩之外,我们也不能排除因仍成弊,久而散漫的成份,尤其是大和年间的每天只能成书一卷。这中间还有一种不能忽视的因素,那就是天宝十四年开始的“安史之乱”所带来的政治动荡和经济损失对文化学术事业形成的冲击,它虽不致致命,但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然而,无论怎样式微,都掩盖不了开宝末年累计71405卷图书所创造的辉煌。这是一个不容小视的数字,因为,此前开元九年(721)完成的国家总书目《群书四部录》,集中官府所有藏书,只著录图书2655部,48169卷,比它少23236卷;而此后宋人欧阳修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唐一代之书,计为52094卷,比它少19311卷,如果加上其知而未录之书27127卷,合为79211卷,[18]也只比它多7816卷。此其一,这一多一少的差额,正可标表在以书为主要载体的年代,集贤书院在唐代文化学术事业中所处的崇隆的不可替代的地位,更可反映书院对于文化传播和文化积累所作的巨大贡献。其二,在雕版印刷技术还没有普及推广的唐代,集贤书院手写纸书达到71405卷,所耗材料,以《新唐书》所记折算,自建院到天宝十四年这38年时间,累计用纸2280000番,墨51072丸,兔皮57000张;若以大中三年之数折算,用纸量则为2290242张。这组数据所反映的生产规模,在当年来讲也是巨大的,它远远超乎同期仍在出书的秘书省、门下省的弘文馆,以及同属中书省的史馆这三家之上,成为官府最主要的图书生产的部门。此所谓后来居上,集贤书院确乎可称唐代中期以降国家图书经籍生产的主流,奠定了其作为国家“出版”中心的地位。
第二.收藏典籍,类分甲乙,对所藏图书进行整理编录,是集贤书院中与出书同等重要的事业。院中图书包括旧底本和新写本两部分,总约在数万卷以上,必须使其处于有序状态,才能有效地展开工作。因此,院中平时设有知书官等职,按甲乙丙丁区别经史子集四库之书。各库之书,“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以便于检讨查取。具体做法是,“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钿表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这种“异色经别”四库之书的方法,千余年后的清代乾隆年间仍运用于纂修《四库全书》这种巨大的文化工程,可见其影响之久远。
使众多图书处于一种有序状态的工作,是在类分经史子集四库的原则指导下完成的,其结果是按照名目、次序对所有图书进行登载而形成的大量记录,此即所谓院藏图书目录。当年的院藏书目虽不留传于世,但院中所开展的这项工作及院目本身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新旧《唐书》都记有建中年间集贤院学士蒋将明以安史之乱以后,院中图籍溷杂,请求携其子蒋ㄨ入院编次整理,宰相张镒署为集贤院编录一职,用一年时间,“各以部分,得善书二万卷”的事迹。[19]前述院中出书数量,之所以可以言之凿凿,亦得视作缘于完备的记录。凡此可以说明,集贤书院的藏书工作已超越为藏而藏的低落级阶段,而进至一个分类编目的高级阶段。
书院的藏书数量,丽正书院时期的开元九年(721)冬统计为81990卷,其中经库13753卷,子库21548卷,集库19869卷,若加前述集贤书院时期天宝三年(744)六月四库更造时“见在库书籍”54574卷,及天宝在至十四年“续写本”16832卷,计有163396卷。这15万余卷之数,比之隋代嘉则殿的万37卷,虽不得称多,但比之唐初武德年间府库所藏总为八万卷之数,又可谓不少。至于它在当年国家所有藏书中所占的份额,我们可录《玉海》摘引《韩文》的记述来作说明,其称:“秘书,御府也。天子犹以为外且远,不得朝夕视,始更聚书集贤殿。……集贤之书盛积,尽秘书所有不能处其半”。[20]秘书省在集贤书院创设之前本是典掌国家图书的官衙,即称尽其所有而不能处其半,则集贤书院作为国家藏书中心的地位此时得以确立也就成了不争的事实。
第三.讲论儒道,申表学术。丽正、集贤书院的讲学活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皇帝的“躬自讲论”。前引张说反驳陆坚罢废丽正书院之事,《旧唐书》所记甚详,其称:“时中书舍人陆坚,自负文学,常以集贤院学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尝谓朝列曰:‘此辈于国家何益?如此虚费,将建议罢之’。说曰:‘自古帝王功成则有奢纵之失,或兴池台,或玩声色,今上崇儒重道,亲自讲论,刊正图书,详延学者。今丽正书院天子礼乐之司,永代规模不易之道也。所费者细,所益者大,陆子之言,何其隘哉”。[21]可知唐玄宗曾在书院与学士们讲论儒道。此正唐明皇所谓“广学开书院,崇儒引席珍”[22]的讲学活动。第二层是学士为皇帝讲论文史而备顾问,并因此在历史上第一次设置了专为皇帝讲学的侍读侍讲之职。如开元十一年(723)夏天,“诏学士侯行果等侍讲《周易》、《老庄》,频赐酒馔”,[23]它是史书上最明显的讲学记录。此类依托收藏丰富藏书,延引院中饱学之士为皇帝讲学,而皇帝礼待学士的场景,张说曾有过生动的描述,其称:
东壁图书府,西园(垣)翰墨林。
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
位窃和羹重,恩叨醉酒深。
缓歌春兴曲,情竭为知音。[24]
这种君臣间的学问探讨,飘溢书香,引人入胜没,以致千余年以后的晚清名臣张之洞创建广州广雅书院时,还要用前两句来为其东西斋二十间号房命名。第三层次的讲学是学士对写御书手、书直等人进行的教学活动。书直等百余人“皆亲经御简”始可入院写书,他们是三卫五品散官以上的子孙,入院之后月课岁考,“各有年限,依资甄叙”。[25]我们认为这种简选、课考、甄叙即是集贤书院围绕着日常整理校刊图书工作以及学士们的研究著述而进行的一种辅助性质的教学活动。[26]张说“位将贤士设,书共学徒归”的诗句,其所描写的就是这种以书联系贤士、学徒的教学活动。
以上三个层次的讲学活动中,前两者具有较浓的学术色彩,无论是皇帝的“亲自讲论”,还是学士们的诵诗讲易,其申表学术的目的甚明,意在提倡“崇儒向道”的社会风尚。至于第三个层次中显示的教学授受的倾向,则反映出即使作为官府的书院,也掩盖不了它所拥有的适应并满足较低层次的士人追求文化知识的教育功能。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这些讲学、教学活动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人们习惯于引用清代诗人袁枚(1716-1797)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27]这样一句“随笔”而来的话,否定其业已存在的教育功能,并进而将丽正、集贤列为另类,抛置一边,甚至极言此书院非彼书院,可以忽略不论,此则实违历史事实。而以是否有士子肄业作为定论书院的唯一标准,更有称霸于先人之嫌,诚不可取。
第四.燕饮诗酒,撰集文章。燕饮诗酒是一种盛唐的文人风雅,撰集文章则是学士们应尽的份内之责。集贤书院既集天下贤能文学之士,其把酒载歌,燕饮诗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常事。如开元十一年新建大明宫光顺门外的丽正书院落成,学士“燕饮为乐,前后赋诗奏上百首,上每嘉赏”。十三年改丽正书院为集贤书院,“群臣赋诗,上制诗序”,其时“樱花新熟,遍赐坐上,饮以酴醿清酤之酒,帘内出彩笺,令群臣赋诗焉”。[28]这是一幅极好的君臣诗酒融乐画卷。这种载酒载歌的场景屡见于诗赋,并且出有《集贤院壁记诗》二卷这样的诗集。唐玄宗的《春晚宴两相及礼官丽正殿学士探得风字》、《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珍字》,张说的《恩制赐食于丽正书院宴赋得林字》、《赴集贤院学士上赐宴应制得辉字》等都流传至今,兹引张说第二首诗如下,以见当年概况:
侍帝金华讲,千龄道固稀。
位(一作任)将贤士设,书共学徒归。
首命深燕隗,通经浅汉韦。
列筵荣赐食,送客愧儒衣。
贺燕窥檐下,迁莺入殿飞。
欲知朝野庆,文教日光辉。
集贤书院奉旨撰集文章,史有明确记载者可举二例。一见于《新唐书》卷一三二《吴兢传》,其称:兢不得志,私撰《唐书》、《唐春秋》未成,乃上书“丐官笔札,冀得成书。诏兢就集贤院论次”。查《艺文志二》有吴氏《唐春秋》三十卷,《唐书》一百三十卷则与韦述、柳芳、令孤峘、于休烈同署名,可见其书终成于书院。吴兢(670-749)是唐代有名的史学家,家富藏书,自撰《吴氏西斋书目》一卷,著录图书13468卷,一生撰有《高宗实录》、《武后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太宗勋史》、《齐史》等书,著作甚丰,尤以《贞观政要》著称后世,其史才史识史德更有名于当时。但即便于此,他的《唐书》、《唐春秋》仍得承旨就于集贤书院并和院中同人合作而后始成,则集贤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不言自明了。
另一个例证就是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三》的《开元十八学士图》,也是奉敕而成。开元中,唐玄宗为张说等集贤书院十八学士写真含像亭,并为之出书。该书图文并茂,十八学士之画像先令韦无忝、殷季友等人绘制,以不精奏进而未用,后改由画僧法明一个人完成,明皇称善,并亲题画赞,对学生各加褒美。书成,“令藏其本于书院”。据《集贤注记》说,这些赞语是“并据才能,略为赞述”的,其称张说,赵元默已见前引,赞徐坚之词为:“校书天禄,论经上庠。英词婉丽,雄辩抑扬”。赞贺之章为“礼乐之司,文章之苑。学艺优博,才高思远”。凡此不再赘引。赞语风雅,不仅可以让人体裁味学士神韵,更能遥示书院论经、校书、赋诗、作文等各种文化功能于千有二百余年以后的今天。
第五.招贤论典,顾问应对。集贤书院招揽隐滞贤才的事迹,可考证于《新唐书》卷二О四张果、姜抚两人的传记。张果是著名方士、武则天时,隐居中条山,往来于山西汾阳、临汾之间。自称已数百岁,著有《阴符经玄解》一书,时人盛传其有长生不老之术,武则天遣使征召,以其居住院中,封银青光禄大夫,号通玄先生,并下诏为其画像存真。后坚请回归北岳恒山,不知所终。张果的仙逸贤能,宋元之世终于演绎成神,列为“八仙”之首,流传至今而不衰。姜抚也是以方技异能而于开元末年召至集贤书院的,兹不赘述。
至于辨明邦国大典,而备皇帝顾问应对,前述集贤书院编录蒋ㄨ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贞元十八年(802),唐德宗问及禁卫部队神策军设置之由,“相府讨求,不知所出”,乃召已升为集贤学士的蒋ㄨ应对。ㄨ称玄宗天宝十三年(745)始设神策军,次年安史之乱爆发,神策军镇守陕西。广德元年(763)代宗避难入陕,宦臣鱼朝恩率在陕之兵马与神策军一同护驾,由此神策军入屯禁中。代宗永泰元年(765),其势力坐大,分左右厢,成为天子禁军。大历年间,又领京兆、风翔两府诸军,势力扩张,到德宗贞元初年终于形成宦官执掌之制,其权临驾于诸禁军之上。其介绍情况,“征引根源,事皆详悉”,宰相郑珣瑜极称“集贤有人矣”,翌日即升蒋ㄨ为判集贤院事。[29]此即书院辨明国家军政大典而备皇帝顾问的明证。其应对天子而中作决策,正可显示它作为学术机关而有别于行政部门的独特之处。
注释:
[1]唐·张九龄等《唐六典》卷九,引见笔者与陈谷嘉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以下简称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31-32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2]《新唐书》卷四十七、四十九上(《百官志》),第1209、1294页。中华书局。
[3]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七,《集贤记注》二卷,第317-3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4]丽正书院的创立时间,《唐会要》作开元五年十一月,《唐六典》作七年,兹并存焉。
[5]东都丽正书院的设置,《唐六典》作开元十二年于命妇院安置,《新唐书》作十二年置,兹并存焉。
[6]宋·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37页。
[7]以上丽正、集贤书院的创设情况,见宋玉麟《玉海》卷一六七,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12页。
[8]《新唐书》卷一二五,《张说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9] 宋·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36-38页。
[10]《唐六典》卷九、《旧唐书》卷四十三、《新唐书》卷四十七、《唐会要》卷六十四,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31-38页,
[11]《唐六典》卷九,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33页。
[12]《唐六典》卷九,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33页。
[13]《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一》。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34页。
[14]《旧唐书》卷一0二,《褚无量传》。
[15]《唐六典》卷九,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32页。
[16] 宋·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36-37页。
[17]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
[18]此数乃笔者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四部小序统计所得,它与《艺文志序》所称“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之记有别,少3163卷。
[19]《旧唐书》卷一四九,《新唐书》卷一三二之《蒋ㄨ传》。
[20]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六七,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18页。
[21]《旧唐书》卷九十七,《张说传》。
[22]唐玄宗《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珍字》载《全唐诗·明皇帝》。
[23]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六七,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16页。
[24]张说:《恩制赐食于丽正殿书院宴,赋得林字》,载《全唐诗·张说三》。
[25]《唐六典》卷九,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32-33页。
[26]刘海峰先生更认为集贤书院有以学士为教师、御书手为学生的教学活动,详见其《唐代集贤书院有教学活动》,载《上海高教研究》1991年第2期。
[27]袁枚《随园随笔》卷十四。
[28]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六七,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15页。
[29]《旧唐书》卷一四九,《新唐书》卷一三二之《蒋ㄨ传》。
原载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第四辑,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