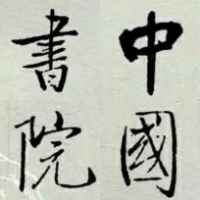李劲松:五代时期的江西书院考述
我国古代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始于唐代,在今江西省所辖地区有近十所之多。进入五代,始建于唐代的那些书院不仅大多继续维持,而且还有新的发展势头。
五代,在今江西省所辖地区来说,始于李唐天祐四年(907)朱温灭唐,至赵宋开宝八年(975)灭江南国(南唐)其间总70年。在这70年中,江西新建书院(书堂),据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书院名录所载有六所。它们是留张书院、匡山书院、华林书院、梧桐书院、云阳书院、光禄书院。
留张书院在洪州高安县境内(南唐时改隶新设的筠州,今属江西宜丰县)西北云峰坛之麓。该书院创办人为张玉。张于唐末由新吴徙居高安,钟传卒,唐亡,张挂冠归隐,键户不出,建书院,讲学其间。其建书院时间应在杨吴政权占领江西之后。
匡山书院,在吉州太知县(今江西泰和县)东匡山下。创办人罗韬,。字洞晦,清修苦学,淡于名利,曾被后唐明宗征授学士。不久引疾而归,建书院教学授徒其间。
华林书院,在洪州新吴县(南唐新吴县改奉新县)西南五十里之华林山。创办人胡珰,胡珰生辰不详,葬于南唐保大四年(949),其书院起始时间应早于此时,为南唐初,或为杨吴间。该书院在南唐、赵宋时都曾得到朝廷表彰
梧桐书院,亦在洪州奉新县境内,罗坊镇梧桐山。为罗靖罗简兄弟所建。罗靖字仁节,人称中庸先生,罗简字仁俭,人称诚明先生。梧桐书院为罗氏兄弟聚徒讲学之所,因山多梧桐故名。有的学者以为该书院建于唐。根据是因《光绪江西通志》有一段记载,“梧桐书院在奉新县罗坊镇南唐罗靖罗简讲学之所”。故有该书院建于唐之说。其实考察实地可见梧桐山在罗坊镇之北。又据宋人徐应云所作《梧桐书院记》称:罗氏兄弟教学乡里,“李氏有江南,国相、郡守知其名,辟召莫能致,独以徐铉为知己”。有的资料甚至讲“从徐铉游”。,由此可知《光绪江西通志》上的记载应断句为“梧桐书院在奉新县罗坊镇,南唐罗靖、罗简讲学之所”。该书院亦为创于五代的书院。
云阳书院在洪州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县)。南唐时吴白举进士,后谪归,建书院聚徒讲学其中
光禄书院在吉州庐陵县(今江西吉安县)。之富田,为邑人刘玉所建,时在开宝二年(969),其时中原已为赵宋王朝,南唐自贬为江南国、奉宋“正朔”,然而实际上该地区仍在南唐李煜控制之下。
有的学者曾将庐山国学称之为建于五代的书院,并称其为书院的四个老祖宗之一,此说当然不妥。因庐山国学是与建在金陵秦淮河畔国子监相同性质的学校,是朝廷之学,帝王之学。它与民间讲学书院是完全不同的,至于入宋以后庐山国学改为白鹿洞书院,或者准确地讲是在庐山中学的旧基上江州士民建立民间的书院,那以不在五代了。故笔者不将其列于江西五代的书院之中。
除以上六所书院外,最近查阅有关史料又有新的发现,补充于后。
据明万历间南昌知府范涞主持,著名学者章潢总撰的《万历南昌府志》所载,新建县之西山有欧阳拾遗书堂和陈陶书堂。
欧阳拾遗书堂创办人为欧阳持,字化基,洪州高安县人(南唐改隶筠州)。唐光化四年(90)进士。为太学博士。天复四年(904)权臣朱温迫唐昭宗李晔迁都洛阳。欧阳持看到朱温有异志,遁归乡里,隐居于洪州之西山。当时杨氏占据江淮、奏除欧阳持为左拾遗、团练判官。持又见杨氏之心思不在匡复唐朝,故又辞官归西山。欧阳持在西山建书堂读书讲学其中,其书堂在江西凤翔洞侧。据《同治新建县志》载,其门人扁曰:“拾遗书院”。
陈陶书堂乃陈陶读书受徒之处。陈陶本人是福建剑浦人,世以儒业名家。据《江南野史》、《南唐书》、《十国春秋》等史书记载,其少学于长安,常以国器自负,以世乱不得逞。南唐升元南奔,居洪州,将诣金陵见南唐烈祖李弁。但“自度于宋齐丘不合”,遂隐居于洪州之西山,建书院自处。陈陶常说:“世岂无麟凤,国家自遗之耳”。陈陶博学,历象声韵无不精究,以诗名,兼通释,老之学,自号为:“三教布衣”。元宗李景迁都南昌,曾欲召见之。后李景晏驾,陈亦绝意仕进,以修炼为事,久之复变姓名徙去,不知所终。其书堂原在西山香城寺左。
洪州新建县尚有一所得名于太平兴国四年(979)的书院——秀溪书院。其创办人邓晏,本为南昌县人,太平兴国二年(977)江西安抚使兼知洪州王明请其典教州学。二年后归里,其时朝廷割南昌西北部置新建县,邓晏故里在新建县。众多生徒侍从习学,其原先讲学之所易南精舍容纳不下,因此扩而大之,改名秀溪书院。邓晏在应聘讲学州学之前已因讲学易南精舍而盛名,故易南精舍之建成应在开宝九年(976)即太平兴国元年之前,时在南唐(江南国)。
再一所为“墨庄”。为庐山国学生徒、南唐状元、清江(今樟树市)人,刘式所建。刘式字叔度,他精于《春秋》公、谷之学,南唐时由张洎知贡举,试《三传》,独放其一人状元及第。后归里建墨庄,教训宗族子弟。入宋,太宗赵光义重其名望,授鸿胪、大理丞、太常博士最终官至刑部郎中而卒。刘式有五子,立本(咸平三年进士)、立言(大中祥符八年进士)、立之(大中祥符元年进士)、立德(天禧三年进士)、立礼(天圣二年进士)。终宋代刘氏子弟中进士者有十七人之多。《道光清江县志·列女传》有一段关于刘式夫人陈氏的记载:“陈氏,新淦人,幼贤慧,为父鄯钟爱,清江刘式游学新淦,鄯见妻之。式为郎中卒,或劝陈多置产为长久计。陈叹曰:丈夫官贫,藏书数千卷墨庄也,安事陇亩。诸子习学有怠则为不食。由是诸子能植立”。胡安定、朱晦庵曾叙记刘氏墨庄故事。朱熹《刘氏墨庄记》赞刘氏说:“非祖考之贤孰能以诗书礼乐之积,厚其子孙,非子孙之贤孰能以仁义道德之贤,光其祖考。自今以来有过刘氏门而问墨庄之所以名者。于此乎考之则知其土之所出,庐之所入者,在此而不在彼矣”!墨庄应该是建于南唐朝末年的刘氏家族的书院。
除上述四所书院外,还有两所值得进一步探究的书院,一是毛炳讲学南台山,一是沈彬进士书院。
关于毛炳,不少有关五代庐山国学的文献都将其称为庐山国学教师之一。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毛炳,洪州丰城人,好学,不能自给,因随里人入庐山,每为诸生曲讲,得钱即沽酒尽醉。时彭会好茶,而炳好洒,或嘲之曰‘彭生说赋茶三斤,毛氏传经酒半斤’。炳闻之微晒而已”。后徙南台山。据《万历南昌府志》称:毛在南台山曾聚生徒数十人,“讲诵迨数年”。然而终酒醉如旧。一次卧道旁。据马令《南唐书》载:里首张谷掖炳而起,炳曰:“毛炳不干于张谷,张谷不学于毛炳,醉者自醉,醒者自醒”。毛炳讲学说经,从其学者多为成人,他从事的是较高层次的私人讲学活动,而且是索起报酬——酒的教学活动。其南台山学舍,实乃一所佚名的书堂或书院。
关于沈彬进士书院,引起人们注意是因为一首诗。
《全唐诗》卷八四四记录了僧齐已的《沈彬进士书院》一诗。
相期只为话篇章,踏雪曾来宿此房。
喧滑尽消城漏滴,窗菲初掩岳茶香。
旧山春暖生薇蕨,大国尘昏惧杀伤。
应有太平时节在,寒肖未卧共思量。
对于沈彬,有关他的记载不少。郑文宝《南唐近事》载:“沈彬长者,有诗名,保大中以尚书郎致仕,闲居江西之高安。三吴候伯多尚以粟帛……”。龙衮《江南野史》则载:“沈彬者,筠阳高安人,少好学,读书有能诗之誉。唐末离乱随计不捷,南游湖湘隐居云阳山十年许,与浮屠辈虚中、齐已以诗名互相吹嘘,为流辈所慕。寻归里访名山洞府与学神仙,慕乔松虚无之道,往来多之玉笥,閤皂二山人游息焉。先主移镇金陵。旁罗隐逸名儒老宿,命郡县起之……授秘书郎,入赞世子,未几以老乞归,乃授曹郎致仕。年将八十修齐不怠,嗣主至南昌乃撑舟往见……厚赐粟帛盐贷放还,寻卒。”马令《南唐书》则载“元宗南迁,彬年逾八十求见”。昊仕臣《十国春秋》则载,其“唐末应进士不第,遂浪迹衡、湘”,“隐云阳山,好神仙,善赋诗,句法精美。寻归乡里”。“烈祖辅吴表授秘书郎”,“以吏部郎中致仕”。“元宗南迁彬年八十余”,来见。
邓洪波先生在《唐代民间书院研究》一文中认为沈彬所建书院应建于唐末、理由是沈于唐末进士举不第已入中年。其实光化四年(901)沈彬第三举纳省诗《赠刘象》,主司杜德祥贝而放刘象及第,沈彬落第归。如果说建隆二年(961)李景南迁时沈彬年八十余的话,光化四年只有二十余岁,尚未入中年。而后南游湖湘十年才归故里,此时朱温已灭唐建梁朝多年。如果沈彬确有书院的话应为始建于五代的书院。
另外,沈彬进士书院究竟是聚徒讲学之处呢?还是诗人会诗之处呢?或如邓先生所以为是讲会之处?或者仅为沈彬读书晏客之所?尚需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五代,在江西始建书院(书堂)有十余所之多。
五代时,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中原板荡,而江南却比较安定。中原士人,以至世家大族纷纷南迁,而割据江南的杨吴、南唐的执政者,则比较注意发展其经济和文教事业。尤其是南唐三代君主李弁、李景、李煜都比较重视文化教育。故马令《南唐书》记载说:“呜呼!西晋之亡也,左衽比肩,雕题接武,而衣冠典礼会于《南史》。五代之乱也。礼乐萌坏,文献俱亡,而儒衣书服盛于南唐。岂斯人之未丧,而天将有所寓欤?不然,则圣王之大典扫地尽矣!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见于载籍,灿然可见。如韩熙载之不羁,江文蔚之高才,徐锴之典瞻,高越之华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价于一时。而徐铉、汤悦、张洎之徒,又足以争天下。其余落落不可胜数。故曰:江左三十年间,文物有元和之风,岂虚言乎!”又说:“学校者国家之矩范,人伦之大本也。唐大乱,干戈相寻,而桥门壁水鞠为茂草。驯至五代,儒风不竟其来久矣!南唐跨有江淮,鸠集典坟,物置学宫,滨秦淮开国子监,复有庐山国学,其徒各不下数百,所统州县往往有学。方是时,废君如吴越,弑主如南汉,叛亲如闽楚,乱臣贼子,无国无之。唯南唐,兄弟辑睦,君臣奠位,监于他国,最为无事。此好儒之效也。皇朝初,离五代之后,诏学官训校《六经》,而祭酒孔维,检讨杜镐苦于讹舛。及得金陵藏书十余万卷,分布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都雠校精审,编秩完具,与诸国本不类。昔韩宣子适鲁,而知周礼之所在。且周之典礼,故非鲁可存,而鲁果能存其礼,亦为近于道矣!南唐之藏书,何以异此。”
我国历史上自东晋开始,有一个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过程。自五代以来,南方在经济、文化发展上超过了北方。这是不以某些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事实。五代,对于江西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就教育而言,有庐山国学,有一批书院,造就一大批人才,在科举考试方面成就亦颇为辉煌。这都为在而后江西数百年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
原载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第四辑,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