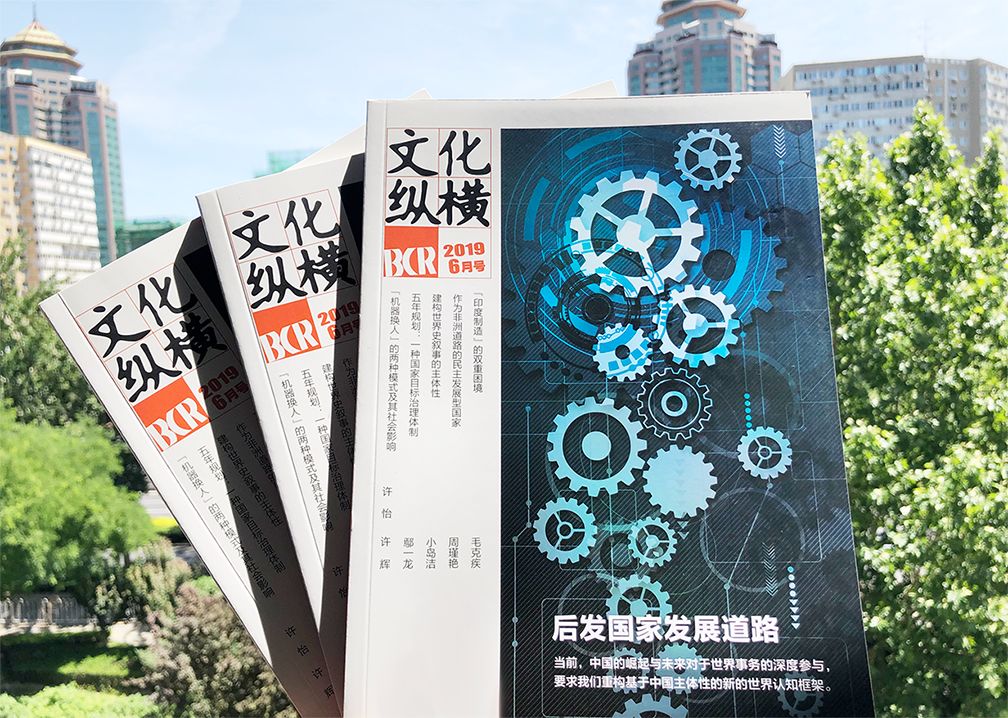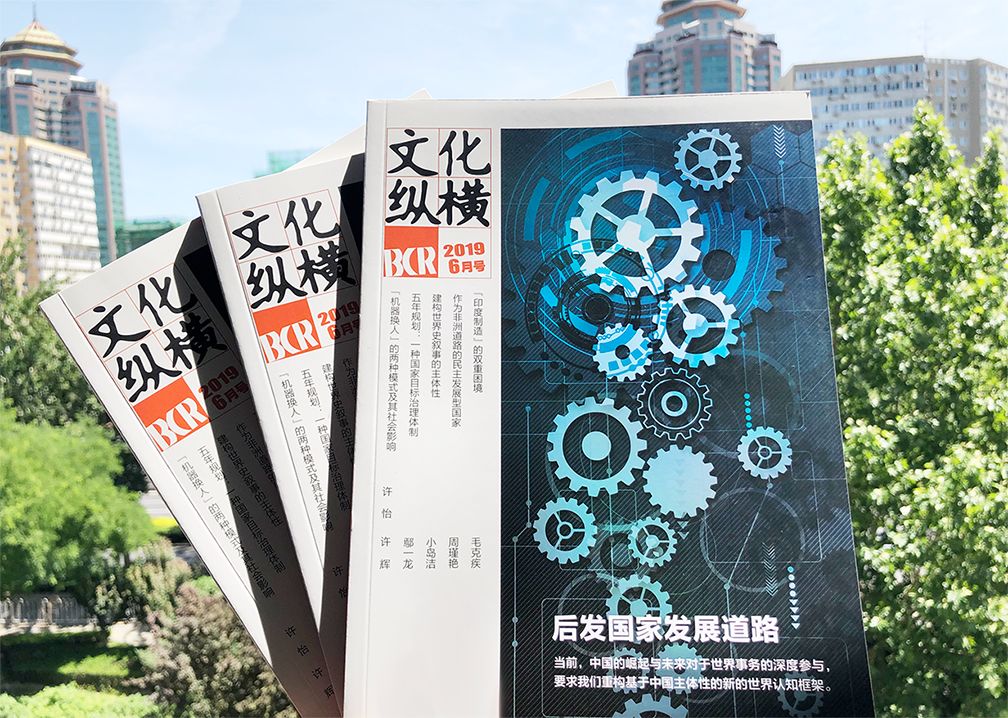
✪ 潘易植、余一文
【导读】上个月,随着豆瓣评分高达9.6的HBO新剧《切尔诺贝利》上映,这一场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在切尔诺贝利的背后,不仅是不计其数罹难者的逝去与创伤,也是对西方社会乐观主义神义论的摧毁,以及对政府管理与科技进步的彻底怀疑。无论是核技术所带来的挥之不去的潜在风险,还是权力对公共话语的操纵,切尔诺贝利都可谓人类现代命运的一个缩影。在人类文明与大自然抗争了几千年后,切尔诺贝利使人们醒悟,真正危及人类生存的已经不是自然,而是人类自己。文章原载“澎湃思想市场”,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切尔诺贝利:“灾难”的现代形象
1986年,位于苏联乌克兰共和国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严重爆炸事故,大量辐射物质泄露,这些物质所造成的辐射剂量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400倍以上。据苏联官方统计,在此过程中,苏联政府动用了共计60多万人参与事故处理,爆炸发生后3个月内造成了31名工作人员死亡,此后15年内可以明确由核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约为60—80人,134人罹患各种严重的辐射疾病。然而这些数据依旧是处于争议之中,在绿色和平组织看来,因这场事故而死的人数至少有9万多人,而不是苏联官方声称的4000多人。事故发生之后,全欧洲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辐射影响;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部分地区的土地依旧存在相当剂量的辐射。
与地震或是洪水不同,核物质泄漏这种灾难类型是现代独有的人为灾难。一方面,切尔诺贝利事故所泄露的核辐射是出自人类的创造,然而它比许多自然事物都更为持久——甚至比人类自身都要持久;在后者的意义上,它成为了人类无法控制之物,成为这个世界自身的偶然性。在切尔诺贝利,近代政治哲学关于灾难的观念失效了。以前我们曾相信,通过合理的组织形式,人类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在由自然的各种暴虐力量支配的世界中建造宜居的稳定空间。长久以来,这构成了近代政治哲学的伟大使命。而在切尔诺贝利之后,观念从根源上发生了颠覆:我们所建立的世界,或许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
辐射摄影下的切尔诺贝利居民区,植被因遭受严重辐射而呈现白色
▍里斯本大地震及其争论
在欧洲启蒙时代,曾发生过一起与切尔诺贝利十分类似的自然灾害。1755年11月1日,里斯本附近海域发生大地震,地震掀起的巨浪对非洲西北部和伊比利亚半岛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里斯本受灾尤为严重。大地震同时引发了火灾,多种灾害的侵袭在里斯本至少造成了十万人的死亡,同时摧毁了大部分的建筑。得益于印刷媒体,欧洲舆论界得以同步关注里斯本地震的信息。但是,里斯本大地震并不只是流传于民间的消遣新闻,它也在欧洲知识界引起了一场争论。
当时主要流行的是神学家的观点,即这场地震必须被看做末日来临的前兆。这一解释背后是乐观主义的神义论:这个世界存在着不幸与罪恶,但这一切都将导向更高的善,而眼前这个世界已经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那一个。因此,需要用更高的理性来看待里斯本大地震,不能将它看做纯粹的灾难,而是这个最好世界中为最终的善服务的必要缺陷。蒲柏作诗云:“凡存在的都合理”。不久,伏尔泰写下《里斯本的灾难》以反驳当时这种乐观主义的神义论论调。在伏尔泰看来,这个世界充满着人类所不能回答的问题,充满了人类对之无能为力的偶然性(吴飞:《伏尔泰与里斯本地震》)。这一观点招致了卢梭的反对。卢梭认为对于里斯本大地震主要原因在于人祸而不是天灾:地震诚然是自然运作所致,然而是人类自己将房屋造的如此紧凑。他同时指出,正是因为地震影响的是城市,人们才会予以关注;地震时时刻刻在发生,只是当它碰巧发生在人类城市的时候才被叫做灾难。实际上,自然界中的地震也是自然和谐运转的一种体现,正如死于自然同样符合着自然的和谐(罗秉祥:《伏尔泰、卢梭对 1755 里斯本大地震的思考》)。
然而无论是伏尔泰还是卢梭,他们都共享着一个相同的前提,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秩序的分离。伏尔泰所设想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离散世界,其中到处都是毫无意义的灾难。对于伏尔泰来说,真正重大的打击不在于这些灾难本身,而在于其无意义性:属于自然的事物再也无法为人类社会提供任何启示。这种自然与社会的断裂构成了近代政治哲学不得不为之的自我折磨,人类必须自谋出路,不再希冀从自然中获得某种保障。卢梭同样意识到了这种断裂。而在卢梭看来,自然灾难之所以不会影响那种预定的和谐,是因为在最原始的和谐中,原本就没有“灾难”一说,只因有了文明社会才有灾难。在理想的场景中,地震发生,原始人死去,这一切依旧是和谐的。两人都将自然秩序排除出人类社会,区别在于伏尔泰哀婉于人类文明的脆弱与不确定,而卢梭则批判人类文明自身的腐朽。
▍切尔诺贝利的记忆
随着HBO新剧《切尔诺贝利》的热播,这一场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的核事故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这部剧带给人们的惊讶不只在于核辐射的危害之大,同时也有苏联政府在应对灾难时所扮演的丑陋角色。4月26日凌晨1点,切尔诺贝利四号核反应堆发生事故,第一时间核电站的主管人员选择瞒报,坚称并未发生泄漏。在随后的逐级上报中,官员始终称事故已经在掌控之内。苏联官方对此事的第一条消息发布在4月28日晚上,没有提及事故的时间和具体伤亡以及正在扩散的核辐射。直到位于瑞典的一家核研究机构检测到切尔诺贝利的泄露,世界才得知这一消息。事情并不像戈尔巴乔夫所说的那样,“当时我们和其他人一样还不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为了在西方世界和本国人民面前维护自身形象,苏联政府隐瞒了信息,直到5月14日戈尔巴乔夫才在电视讲话中向民众告知这一事件。在官方未承认泄漏之前,那些身处切尔诺贝利附近的普利亚特镇的居民,对自己身处的情境一无所知。
正如电视剧中所表现的那样,在一开始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它与普通的爆炸没有区别。在那个晚上,人们被爆炸声惊醒,看着核电站上空的光,还在称赞它的美丽。这种灾难从一开始显得精致文雅,“直到天空中下起黄色的雨”。剧中,在政府下达移民命令并出动军警强制执行的过程中,一位老妇拒绝撤离,她称自己经历过白军、红军以及德军的驱逐,但他们都失败了,现在她拒绝因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而搬走。这种灾难发生在沉寂之中,并且带有透明的特质,如同遥远古代的巫术。然而正是由于这种透明的特质,这一灾难变得难以辨认,以至于必须依靠权威的解释力量。灾难的范围、程度、应对方式,乃至最首要的,是否发生灾难,这些不再是依靠感官直觉就能不言自明的事实,直到它真实地对身体造成伤害。
▍科技、权力与风险:人类的现代命运
与自然灾害和原子弹爆炸的可见性不一样,核泄漏的危险是用肉眼所看不到的。这种灾难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取消了“空无”本身,空不再是中立的什么都没有,而是可能是“恶毒的”。在经典的弗洛伊德的理论里,焦虑是没有客体的,而恐惧是有客体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现代科技取消了虚空,在感知的虚空里发现了可以计量的物质,从而产生的焦虑感改头换面成了对具体物质的恐惧。这涉及的当然不只是核泄漏的问题了,对空气质量、水质量、食品安全等问题或许都可以和辐射一样被看作是现代性的症状。
不幸的是,测核辐射的仪器也不再能保证我们能认识到真相,因为对科学的解释权从来不是属于大众的,权力甚至可以假借科学操纵真相,选择性地引用科学数据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用事实说谎。因此,在灾难的发生和灾难的解释之间,存在着一段暧昧的间距。只有从一种事后的回溯性视角,我们才能将其看做一个事故,而对于身处间距之中的人们而言,正常的生活崩解,而这背后除了政治权力的运作之外看不到任何东西。事实上,哪怕在事故公开于世之后,一切依旧处于不透明之中。据统计,关于事故起因的解释有一百多种;而对于事故所带来的死亡人数,苏联官方、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绿色和平组织各有不同的数据(梁强:《切尔诺贝利的政治意义》)。
这或许是在转基因食品等问题上公众对“科学”那么不信任的原因,科学总是被言说出来的,即使在众多的证据面前,依然感知到某种要欺骗的意志。即使是“正常”的人,都难以完全相信那些话语是不欺骗的,他们也会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妄想狂只是在程度上取到了一个极端,从怀疑中纵身一跃到了确定性,他们确定了灾难、迫害、战争的都会发生,陷入了极大的焦虑当中。但是,他们疯狂的信念未必没有道理,在逻辑上,科技的发展确实会造成巨大灾难的可能性。现代科技仿佛是一位危险的“鳄鱼妈妈”,她仿佛是全能的,既能保护孩子,又能将孩子毁于一旦。当代人经常以一种“我知道危险存在,但轮不到我”的倒错来获得心灵的平静,但这只是进入了不同于恐核症的另一种疯狂。
与核辐射的穿透力形成对比的,是苏联政府对消息的层层锁闭,以及在久远年代里不断累积的谜。或许,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维柯命题的倒转:只有人为的事物才是不可认识的。这是近代政治哲学观念的反面,也是其极端:曾经人类社会与自然相对抗,如今前者已再无敌人,连自己都不是自己的对手。人为的偶然性取代了自然的偶然性,成为了当今真正的议题。因此,我们不再能够谈论对偶然性的克服,因为人类的作为本身就成了最不确定的事件。我们无法再隔绝危险,因为这已然构成现代人的本质之一。要接受这一点,需要莫大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