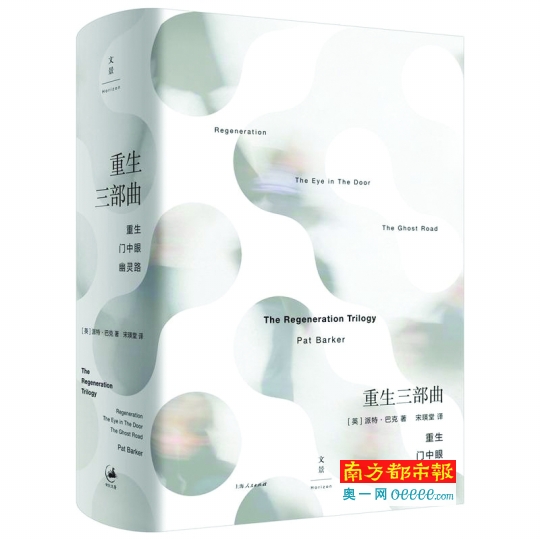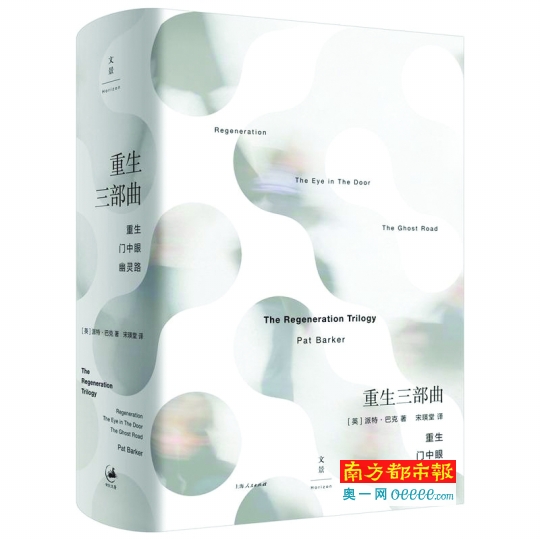
《重生三部曲》,(英)派特·巴克著,宋瑛堂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版,98 .00元。
□谷立立
读派特·巴克的《重生三部曲》,似乎难以想像到如此沉郁的战争史诗,竟然出自一位女作家之手。毕竟,在她成年后的时代,已经很少有女性书写残酷的战争,更别提要立下宏愿,要与《西线无战事》等经典作品相互比肩。似乎是要打破所有偏见,巴克勇敢地提起笔来。一部《重生三部曲》,将她从女性写作的狭小空间连根拔起,进入由男性一手掌控的战争写作领域,完成了一次华丽的变身。
《重生三部曲》有一个掷地有声的开篇:1917年7月,诗人西格弗里德·萨松写下著名的反战宣言,谴责战争的目的“邪恶无天理”。问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尉如何能扭转战局,叫醒深陷战争泥沼的英国。很快,他被迫离开前线,来到位于苏格兰爱丁堡的克雷格洛卡军医院,与众多弹震症(战争创伤综合症)患者一起,等待最后的裁决。仿佛打开了一道尘封多年的幽暗之门,毫无防备的我们还来不及调整心态,就被耳畔急煎煎的鼓声,催促着走入另一个颠倒错乱的世界:失忆的军官、恐血的医生、口吃的患者,齐聚一堂,在沉默中回忆各自的战争往事。
那么,当他们谈论战争的时候,他们在说什么?当然是痛苦。儿时的伙伴、亲密的兄弟无一例外地成了阵亡名单上的符号。这难道不是人生最大的伤痛?但“痛苦”已经不能概括巴克的主题。这位心怀大志的女作家丝毫不逊色于她的男性同行。当雷马克手拿《西线无战事》,满眼悲伤地望着他那一代青年(“时代燃烧着,我的生命却冰冷了”),巴克反倒愿意压抑内心的激愤,一笔一画地用力书写。虽然名为小说,《重生三部曲》却不是百分之百的虚构。巴克在虚构与非虚构两种体裁之间搭起桥梁,将英国诗人萨松、威尔弗雷德·欧文、历史小说家罗伯特·格雷夫斯、神经医学专家兼人类学家瑞弗斯,统统请了过来,与虚构人物下等军官比利·普莱尔一起,撑起了这部阴郁而厚重的战争史诗。
显然,巴克的阴郁来自她的文学导师安吉拉·卡特。曾经,卡特给了她最初的文学启迪,也教会了她如何写作黑暗故事。当然,这并不代表《重生三部曲》就是《派特·巴克的精怪故事集》。只是细读全书,我们仍然可以发现残留在字里行间的“精怪”气质。比如巴克一再提到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她疑惑,如果卡罗尔得知在半个世纪后,文明世界将会迎来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界之战,他还会不会写出如此绝美的奇幻故事?毕竟,战场没有梦幻,只有梦魇。这一次,小姑娘爱丽丝将会在梦的岔路上越走越远,彻底地迷失方向,直到把充斥着梦魇的“歇斯底里境”误认为“梦中仙境”。
当然,这样的“歇斯底里”并不限于战场。随着战事的升级,普通英国人长期遭压抑的“虐待狂冲动”被迅速撩起。整个国家一分为二:一边是劳工纷争、矛盾激化,另一边是参战与反战的对峙。这意味着,敌对无处不在,战争无处不在;既是身体,也是心理;不分老幼,无论男女。《门中眼》一部,病愈后回到国内任职的普莱尔偶遇儿时的邻居贝蒂·罗珀。老妇人贝蒂原本对战争一无所知,只是凭着善心营救逃兵,却被冠以“刺杀首相”的罪名被捕入狱。如此,外部的混乱与内心的迷茫,前线的炮火与后方的喧嚣,相互重叠,彼此交织,加速了普莱尔人格的分裂。
不过,《重生三部曲》既不是控诉,也不是自白。它更像是巴克与历史展开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对话。4年间,她不懈创作,把自己对人性、对世界的拷问写了出来。在她看来,当今社会的诸般弊端,皆源于历史。发生在100年前的一战,既是普通军士的至暗时刻,也是人类文明的至暗时刻。那么,什么是文明?是拿着文明棍、四处炫耀自家的先进,还是用新发明的坦克辗压自己的兄弟?如果站在人类文明进化的角度来看,20世纪初那些自诩“站到了文明尖端”的西方人,与南太平洋小岛上围着草裙跳舞的猎头部落,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因此,不管是萨松,还是欧文、普莱尔,都不过是战争的牺牲品,以各自的创伤完成了一次西方式的献祭。而他们的父亲(军队),就像美拉尼西亚的酋长,表面上一脸善意,厚待无家可归的孤儿,偏偏又要在十来年后孩子的成人礼上,拿起棒子狠狠砸碎他们的脑袋。
如果说,雷马克用纪实的笔法毫无偏差地还原了战争的“死”,那么,巴克在意的则是“生”。至少从一开始,她就旗帜鲜明地告诉我们,她写的是“重生”。可是,饱受身心双重蹂躏的普通军人如何能够重获新生?显然,“重生”才是最大的伪命题。巴克巧妙地借用神经医学的专用术语告诉我们,神经一旦被切断,自行恢复的可能微乎其微。这里,每一个被死亡包裹的战士,都是一根根被意外切断的神经元。战争好比绞肉机,绞碎了他们健全的身体与精神,更切断了他们与过去未来、与家庭社会的所有牵绊。战场几个月,人间已千年。哪怕费尽心思回到过去,也难逃噩梦的夜夜侵袭。此时,唯一的出路是再次踏上幽暗崎岖的“幽灵路”,重返前线这个“唯一干净的地方”,以残酷应对残酷,以鲜血反哺鲜血,然后在每一次终将来临的死亡中获得“重生”。
《幽灵路》一部,巴克展开了极具个人色彩的战争叙事。她以双线并进的方式,带我们回到“无战事”的西线。死亡就这样毫无预警地来临。前一秒,普莱尔还在日记里记录弟兄们的糗事,说着不痛不痒的冷笑话;后一秒,在运河边的一次突击中,意外的冷枪葬送了他和欧文年轻的生命。此时(1918年11月4日)距离正式停战,只有短短一周时间。故事讲到这里,所谓的荣誉、勇气、英雄,好比空洞的说辞,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仍有意义的只剩地名。蒙斯、卢斯、索姆河、阿拉斯、凡尔登、伊普尔。”这是他们抛洒热血的地方,在100年后的今天,仍然无声无息地存在着。好在有了巴克。她妙笔一挥,让所有尘封的历史在文字里复活,它们“安然地躺在语言里”,被今天的我们反复读起。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