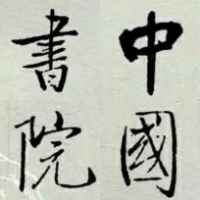王立新:衡山胡安国文定书堂的历史兴衰
一、衡山文定书堂的创立
衡山胡文定公书堂,又称“春秋楼”,始建于绍兴三年秋。
早在南宋靖康元年(1126),程门弟子侯仲良因避乱自三山赴湖北荆门。时胡安国一家正寓居荆门。胡安国见侯仲良学行、见识、人品超于常人,故令五峰胡宏及其兄茅堂胡宁从学于侯仲良。侯仲良议论时势,“纤维皆察”,建炎二年,侯仲良告诉胡安国,荆门不可久住,很快就会成为“盗区”,劝说胡安国抓紧迁移。胡安国听信侯仲良的劝告,举家于建炎三年冬迤逦来到湖南湘潭,定居碧泉,创“碧泉胡文定公书堂”。除了碧泉书院以外,胡安国在湖南还创立了另一书院,这就是被后世称为“春秋楼”的衡山胡文定公书堂。
绍兴元年(1131)春,孔彦舟与马友于衡州和潭州之间展开激战,“兵漫原野”。湘潭已无法安居,胡安国父子遂于四月间举家南迁至邵州(今湖南邵阳)。未及少息而他盗又至,于是继续南避进入山区,“与狪獠为邻”。[1]山居依然不得安宁,十二月,大盗曹成兵败之后,帅兵进入衡州,胡氏父子只得继续奔避,进入广西全州,一直逃到灌江和清湘一带。割茅草为屋,以避乱御寒。胡氏父子在“瘴雾昏昏,大风不少休。郁薪御寒,粢食仅给”的艰境下,挨过了一个难忘的冬天。绍兴二年(1132)春,朝廷有旨,召胡安国赴行在,胡寅、胡宁侍行,胡宏守舍。胡安国父子“行既远六”,大盗曹成率部卒到达全州,并于六月间进入灌江一带,胡宏及家人仓皇奔逃。一天夜里,盗匪忽至,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一家人于乱中逃散。直至年底,胡寅从江西丰城回,才在一所破庙中找到妻室张季兰和幼子胡大原。胡氏父子一家当时的境遇正如胡寅在诗中所描述的一样:“四海兵戈里,一家风雨中。逢人问消息,策杖去西东”。[2]
胡安国本于绍兴二年七月入对于临安行在,就任中书舍人兼侍讲。八月即因反对朱胜非的都督江淮军马除命被贬。胡安国离开朝廷之后,没有立即返回湖南,而是到江西丰城小住了半年。胡安国并不知道家中又遭此劫难,所以首先派胡寅回省家人。直到绍兴三年春,胡安国才回到湖南湘潭,七月全家才重新聚合于衡山,胡安国从此不想出山,准备在衡山和湘潭终老天年。此后,孔、李、马、曹等相继败亡窜叛,湖南一域稍安,胡氏父子这才获得了相对安定的生活。繄繄
胡安国在衡山紫云峰下“买山结庐,名曰书堂,为终焉记”。[3]这就是衡山紫云峰下的“文定书堂”,亦称“春秋楼”。胡安国就是在这里完成了《胡氏春秋传》的最后撰述的删改。“春秋楼”告成之日,五峰胡宏亲自撰写《上梁文》称:
我祖武夷山传世,漳水成家。自戎马之东侵,奉板舆而南迈。乃眷祝融之绝顶,实繄诸夏之具瞻。岩谷萦迥,奄有荆、衡之胜;江、湖衿带,旁连汉、沔之雄。既居天地之中,宜占山川之秀。回首十年之奔走,空怀千里之乡邦。燕中未适于庭闱,温情不安于枕席。背枕五峰,面开三径。就培松竹,将置琴书。良为今日之规,永作将来之式。工徒大会,筑削告成。所用修梁,聊申善颂:
抛梁东,爰有仁人住岳峰。万里春光来席上,四时和气在胸中。
抛梁西,诸峰秀色与天齐。人间日望兴云雨,雪月吾皆自品题。
抛梁南,靖深端北俯澄潭。池面跃鳞看似锦,竹间流水胜于蓝。
抛梁北,大家尚尔淹南国。春秋拨乱仲尼书,年来献扫妖氛则。
抛梁上,道与天通自奋扬。当仁不愧孟轲身,禅心事业遥相望。
抛梁下,明窗净几宜凭籍。道义相传本一经,儿孙会见扶宗社。
伏愿上梁以后,庭帏乐豫,寿考康宁;中外雍和,子孙蕃衍;流兴后世,受福无疆。
从绍兴三年(1133)底到绍兴八年夏初,胡安国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四年多的时间里,主要生活在衡山文定公书堂和碧泉书院两处,时而往返于其间。绍兴六月年底,《胡氏春秋传》告竣,胡安国自为之序,称:《春秋》是圣人“史外传心之要典”,上呈高宗说:“虽微辞奥义或未贯通,然尊君父、讨乱贼,避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庶儿,圣王经世之志,小有补云”。[4]高宗赞《胡氏春秋传》“深得圣人之旨”,诏赐银绢二百匹两。
衡山文定书堂在胡安国过世以后,胡宏、胡寅等亦曾在此讲学,直至宋末一直未废。历代胡氏子孙及乡人共祀之,尤其胡寅、胡宏过世以后,胡氏后裔与里人一道在书堂正中朔胡安国像,左右以致堂胡寅与五峰胡宏配享。
二、元以后衡山文定书堂的历史兴衰
明崇祯年间修复时,掘得宋元时旧祭器数件,[5]知宋元时即以岁时祭祀,后历元明而废。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六月乙亥,诏以宋胡安国、蔡忱、真得秀从祀孔庙,[6]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明廷又追封宋儒胡安国为建宁伯。[7]在此后相当长时间里,胡安国及其所著《春秋传》再度成为儒者之宗和圣经要典。朝廷倡导于上,地方官行动于下。彭勖在福建建宁府创办“尊贤堂”,以祭祀宋儒胡安国、蔡忱和真得秀。[8]明孝宗弘治乙卯岁(1495),监察御史郑维垣按衡山文定书堂原样,于原址处筹划重新修复,并嘱托当时同知衡州府邓淮具体经办。邓淮上奏朝廷,得准并且直接拨款。当时构造是中间设堂以祀胡安国,左右配享者是胡安国长子胡寅和季子胡宏。四周房屋、庖厨之类齐备,“又掘地得旧祭器若干,葺而完之”。每年春秋两季按古例祭祀。同时由乡里学者和胡安国后嗣子孙居住其间,以表明朝廷的崇儒重道。不久,兵部主事何孟春路过此地,前往拜祭。郑维垣托何孟春带书入京,请求当时任左庶子兼侍讲学士、太常少卿、史馆编修并直文渊阁参与机务李东阳为撰写记文,李东阳应邀作《文定公紫云书院记》。
李东阳于《记》中称:“公(指胡安国)之学,以尊王贱霸为本,安夏变夷为用。当金强宋屈之时,朝野靡然,附会和议者为识时论,雪耻者为主事。而公引经议政,正色直言,所以警君心而裨治道者至矣。身既不用,其所为《传》,卓然成一家之言。至我国朝,遂列诸学宫,用诸场屋,为不刊之典。使公用于一时,孰若传之后世之为远哉!若五峰,虽不见用,而出处明决,未尝屈己以干禄,深得乎家学之正矣。古者,乡先生没,必祭于社,而圣贤道在万世,则天下祀之。盖视其功德小大以为久远,有不可得而诬者。公今从祀孔子庙廷,天下之所亲视,儒臣之所分礼,天下学者必所尊祀也。……况公作述之善,有若五峰者,出而成之。征诸南轩之授受、考亭之议论,又若是著也。而可以无配乎?书院……前贤往迹,风教之所关,亦不容废,如兹院是也。衡之学者,读公之书,学公之学,故将亲羹墙于庙貌,思景行于高山。虽欲自尽于道,而亦有不容已者矣。……东阳世家长沙……闻文定公之风而有感焉,因为之记,以成贤御史及贤有司之志”。
衡山文定书堂在明代崇祯六年(1633)又加恢复重修,衡州守令何仕冢为作《记》称:“周东迁先师之《经》(指《春秋》)成,宋南渡先生之《传》(指《胡氏春秋传》)出。上下二千年间,揭大义以责鲁、宋之君臣,若同堂授受,锱两不差。逮我国朝,遂定其书为制科,左、公、谷皆属外篇。《春秋》乃不孤行,则先生之羹墙又遍天下。衡岳之有书院,盖先生之藏书处也”。[9]这次重修之时,胡安国及其子胡寅、胡宏的遗像已经将要毁掉了。乡学博士刘元淬、庞光辅建议胡仕冢想办法予以恢复,何仕冢深表赞同,并请清乐僧寻访胡氏后人,得胡来誉。何仕冢命其“董工集材”,并托付以书院之事。清乐僧提出要将长寿庵一同恢复,何仕冢表示同意。“不旬月而院工告成”。恢复“院田之昔废者”,并刻石记述了这次修复过程,附在石碑的背面。
清康熙时,胡安国后裔殿长、影桑又集族资重修,乾隆时,守令谢仲坑、高自位以官资再加重修,道光年间,胡安国后裔省山铲除亭中杂草,清理书院环境,归而后与族中人咸吉、楚池、砺之、恪甫诸人一道再度重新修葺,并增添房府等,使院制为之一新。曾国藩原于同治三年(1853)赴衡州训练湘军,当时曾赴衡山文定书院,拜谒胡安国父子,本拟在修复之后再度前往拜谒胡氏父子,但因同治四年奉命出山镇压太平天国,未果。同治七年(1857)乡人旷尧臣等晋谒曾国藩,请求为重修后的文定书院作记,曾国藩欣然应允,为作《重修文定公紫云书院记》。
曾国藩在《记》中称:“天下之书院,楚为盛;楚南之书院,衡为盛。以隶岳故也。岳志载衡书院十又八,惟胡文定公书院,独敕建为最著以传《春秋》故也”。曾国藩不同意把长寿庵一同修复,提出:“院毗长寿庵,修院不修庵”的主张。因为长寿庵时有扩充地域之心,并不时与胡氏后裔争讼。后胡氏后人自出资独修书院,曾国藩乃为题《记》,称颂胡安国对风化等的“丰功伟绩”,曾国藩并且赞扬胡氏后人贤能忠孝,以为“衡古院多虚,[惟]公(指胡文定公书院)院如鲁殿灵光,独巍然存也”,乃是胡氏后人的了不起的贡献。在他看来,“兹院春秋官记,非家祠”,“胡姓私修私祭,反小公”。他认为,胡安国“著《春秋传》,使人明君臣大义”,是大有功于纲常的宏勋伟绩。曾国藩甚至认为“干戈扰攘,忽忽十余年,而凯未奏。若明《春秋》,安得至此”。曾国藩甚至企图用胡安国的《春秋传》激励乡人,“诸君主读公之书,修公之院,是必深明《春秋》者。目击时艰,其激于义愤,当何如也?”曾国藩只言《春秋》,未及“春秋大义”,这是很有趣的。胡安国极尽对于“春秋大义”的强调,力主“用夏变夷”,而曾国藩则助满清,屠汉民,其惟取胡安国的“君臣之义”,而放弃夷夏之辨是非常明显的。这是他的人生态度和他的身份所决定的。而钱邦芑则在《文定公春秋楼记》中指出:“生人之道,无过五伦;明伦之学,无过五经。五经在宇内,上如日月之经天,下若江河之行地。世界之所以不毁,则斯道之纲维也。故古今大贤,凡注五经者,或德配天地,功侔帝工。其血食百世,非有所私也。道义之存于人心,自不能毁也。自吾夫子修明圣学,表章六经,而何以云志在《春秋》?则其精意之所存,盖可知矣。夫《春秋》一书,岂直二百四十年之事已哉!明千古之人伦,立君臣内外之大防,意甚深远。非浅学所能窥”。钱邦芑进而指出:“文定公作《传》,总会左、公、谷之旨,而折衷之。深切著明,其于人心世道,危微剥复之关,辨之精而防之密。是以前朝独取,列于学宫,为取士典程。而凡左、公、谷诸家皆列为外传。则文定公有功于圣学,有裨于世道之人心,岂他贤所可额媲?”钱邦芑盛赞胡安国说:“呜呼!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文定公在胡氏,为族姓之祖;在天下,为生民伦常之祖;在儒林,为经书之祖。过斯地者,能无饮水思源,……”[10]钱氏与曾氏之不同评价,一方面与各自的身份有关,另外也与双方对“春秋大义”的理解不同有密切关系。
衡山胡文定公书院后来在民国时,还有胡氏后人代为保护,直至大跃进时开始被毁,至文革期间更甚,今原址已成岳云中学校园,而胡氏父子及其“春秋楼”却早以被当地人所忘记。原有碑文塑像等均已不知去向,余尝苦苦寻觅而至今终无所获。其可哀之甚也欤!
注释:
[1]胡寅《斐然集》卷二十《悼亡别记》
[2]《斐然集》卷三《和文定题范氏壁》。
[3]《斐然集》卷二十五《先公行状》。
[4]胡安国《春秋胡传·序》。
[5](明)李东阳《文定公紫云书院记》,转引自《闽楚胡氏九修家乘》卷之三《庐记》。
[6]《明史·英宗前记》卷十,第一册第129页,中华书局,1974。
[7]《明史·礼四》卷五十,第五册,第1297页。
[8]《明史·彭勖传》卷第一六一,第十四册,第4383页。
[9]《闽楚胡氏九修家乘》卷之三《庐记》所引何仕冢文《重修胡文定公书院并长寿庵碑记》。
[10]《闽楚胡氏九修家乘》卷之三《庐记》。钱邦芑(1600—1673),字少开,江苏镇江丹徒人。曾任南明隆武时御史,永历元年因占据遵义之功升右佥都御史,并巡按四川。后招降张献忠大西军孙可望部。后清兵入州,悔恨出家,号为“大错和尚”。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哲学系
原载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第四辑,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