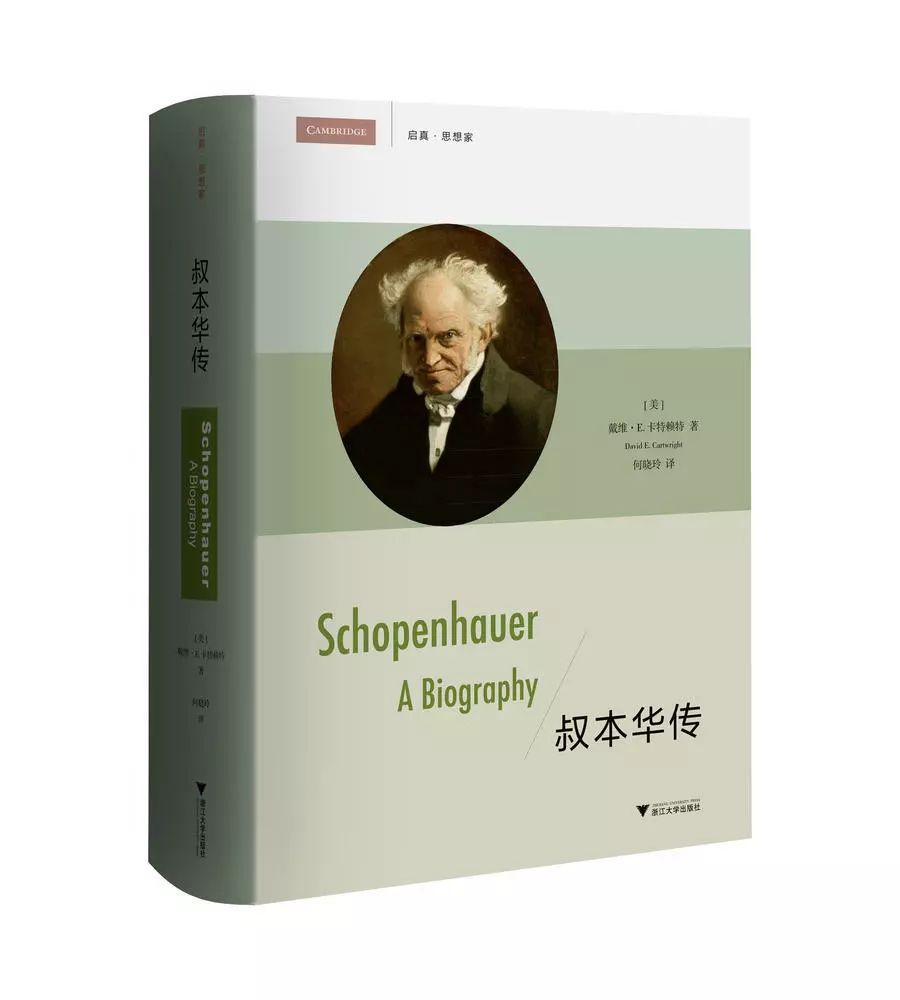选自《叔本华传》
【美】戴维·E.卡特赖特
译者 何晓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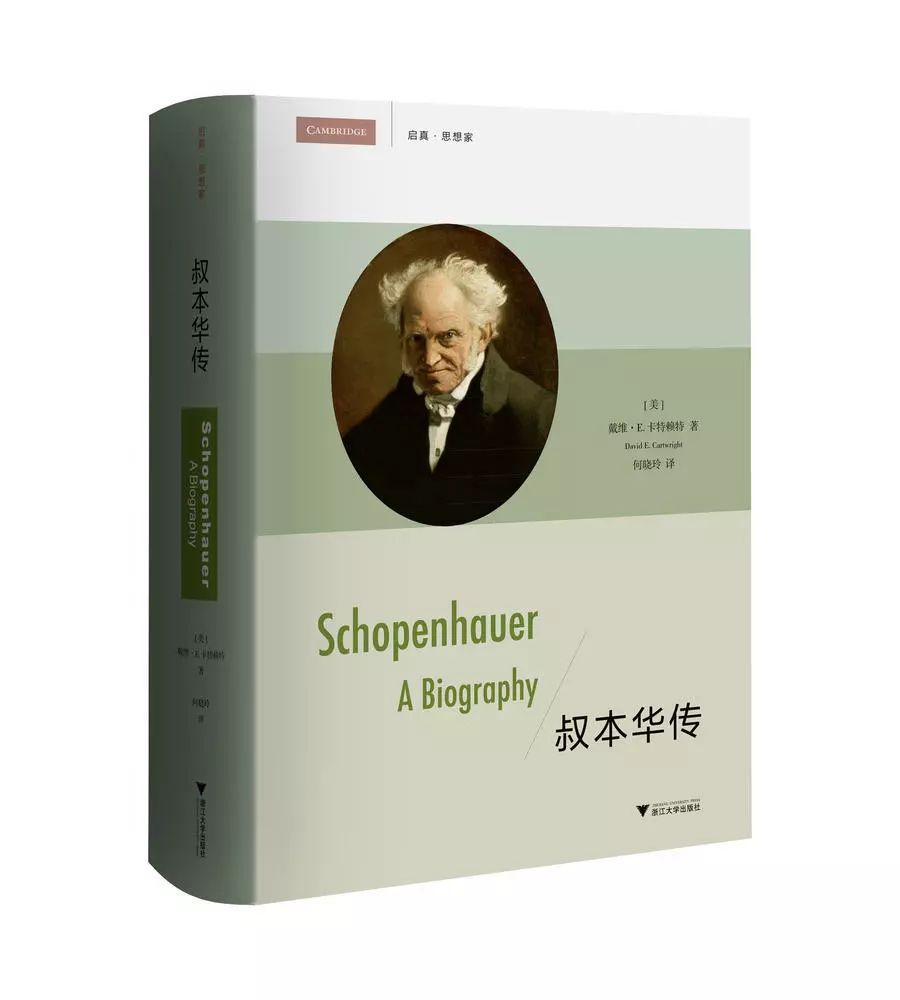
叔本华在晚年享有相对来说还算不错的健康身体,他认为这是持续运动与新鲜空气的共同结果。无论天气如何,他都每天坚持散步。
他向饱受病痛折磨的多斯提出忠告:
“每天都去散步,快走两个小时,那比任何一处温泉都对你更加有用,而且这还不用花钱。我如果未曾天天散步,就不会在七十二岁古稀之年仍然像现在所是的和依然如故的完全健康、精神矍铄、身体强健。”
他为自己不戴老花镜就能读书看报以及直至去世前都一直胃口奇佳而颇感自豪。
他坚持每天吹奏笛子,以确保自己获得适度的夜间休息。
当多斯告诉“师傅”他的生活繁忙得必须为读书而牺牲睡眠的时候,叔本华劝他不要这样做:
“睡眠是一切健康和精力的源泉,即便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也是如此。我每天的睡眠时间是七个小时,通常会达到八个小时,有时甚至九个小时。”
这位休息良好的漫步者依然活力十足地进行脑力劳动:读书看报、与他的门徒及仰慕者通信并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加进他手写书稿以及为将来出书所准备的材料当中。
就在他去世前三个星期,叔本华还给两位军校学生写了一封明白易懂的信件,认真地说明在他们担心否定意志必然会导致世界灭亡的忧虑当中包含某种“概念的模棱两可性。”
他准备出版自己主要著作第三版,而布洛克豪斯则迫不及待地出版了它(1859)。对这家莱比锡出版社而言,《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终于成为一桩“赚钱的买卖”。叔本华试图同布洛克豪斯一道筹备自己作品集的出版,但因其书的版权散布在六位出版商手中,这一计划便由于随之而来的繁琐法律程序而未能在哲学家生前得以完成。
直至1873年, 一套由弗劳恩席德特编辑的六卷本《作品集》(Collected Works)才由布洛克豪斯付梓出版。在叔本华去世前不久,他的《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二版于1860年出版,在第二版前言中,哲学家仍然在咒骂那些他认为因为没有授予那篇关于道德的论文以金质奖章而待他不公的人。
尽管年老的叔本华享有相对来说还算不错的健康身体,但这并不是说他就逃离了佛陀口中的“老年”恶魔。
19世纪50年代中期,他的双脚罹患风湿,他用白兰地酒和盐来治疗该病。他的听力持续衰退,这个问题自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困扰着他。1823年前,他的左耳已经完全失聪;而1856年将至之时,他正承受着丧失他那只好耳朵听力的痛苦。
他不再去剧院,只去看滑稽戏。他害怕自己最终只能去听歌剧,这种前景令他感到悲伤。
奇怪的是,这位对噪音特别敏感并在《附录与补遗》(点击蓝字阅读)第二卷“论闹声与噪音”(On Din and Noise)中对之颇有抱怨的哲学家,却并未把他对鞭子的噼拍、狗儿的狂叫、连续的锤打及猛烈敲击的毫无反应,视为对他不能去看戏所给予的补偿,这些声音本来已经是“一种我自己整个一生当中每日必受的折磨”。1860年,他从美景街十七号搬到了这条街的十六号,那是一套底层公寓,搬家的原因是他害怕自己可能会因为跑得不够快而无法逃离火灾。
1860年4月,他在从英吉利饭店回家途中,发觉自己行走的步伐难以轻快如常,并且因为气短和心悸而感到难受。这些症状持续了整个夏天。固执的哲学家除了缩短每日散步的距离之外,并未听从医生或友人劝告改变自己生活方式。
9月9日,他因“肺部发炎”而病到极点,他觉得自己就快命将不保。但在几天之后,他康复如初,并下床来款待访客。格温纳是叔本华友人中记录自己多次探望将死的哲学家情况的最后一位。9月19日,格温纳最后一次探望了自己这位英雄。尽管哲学家说他因心悸而感到难受,并且说话的声音也微弱之至,但他们俩还是一直谈到黄昏时分。
格温纳同叔本华谈到巴德尔对圣马丁著述的评论以及雅各布·伯麦的重要性。哲学家正在读伊萨克·狄斯雷利(Isaac D’Israeli)的《文学搜奇》(Curiosities of Literature, 1834),他开玩笑说道,自己都几乎可以收入作者关于致使书商倾家荡产的作家秘史的论述部分了。
他表现出对自己能够将一些重要补充材料加进《附录与补遗》之前就会辞世的忧虑,也表现出对以下事实颇感自豪:他加进《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的东西,与他早期著作一样鲜活灵动,甚至更为明晰。这位一直认为自己哲学为读者提供了形而上学安慰的哲学家,表达了这样一种希望:在一个痛失信仰的年代,他的非宗教学说会填补这一空白,成为内心的安宁与满足的源泉所在。
这位曾经如此有力、广泛且深刻地就死亡进行过写作的哲学家,从容地面对着自己的行将辞世。他语气轻柔但却言辞辛辣地告诉格温纳“想到他的身体很快就会有蛆虫来啃噬,他并不觉得生气。相反,一想到他的神魂会如何被那些‘哲学教授’的双手妄加滥用,他便会毛骨悚然。”
他告诉这位老朋友,他会带着理智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到达绝对的虚无对他而言只会是桩幸事,但不幸的是,死亡却并未提供这样的前景。”
究竟叔本华的这最后一句话是在开玩笑,还是格温纳的记录有误,抑或哲学家已经忘记了自己在主要著作第一版结尾部分曾经驳斥过存在某种“否定的无”(nihil negativum)的说法,实在不甚明了。
格温纳永远再也不会见到活生生的哲学家,9月20日,哲学家在起床后摔倒在地,头部受到猛烈撞击。不过,他在那天夜里倒还睡得不错,次日早晨起床之后也并无异常。他按照每天的惯例,在用冷水洗浴完毕之后吃了早餐。女仆打开叔本华房间的窗户,好让哲学家觉得对健康极为有益的新鲜空气涌进房中。
她在叔本华的医生到达前的几分钟离开了房间。新鲜空气并未对老人起到任何作用,人们发现他倒在长沙发的一角,已经与世长辞。
他看起来像是睡着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有过痛苦的挣扎。
叔本华去世的那天是1864年9月21日,这一天和他出生的那天一样都是星期五。
没有人对叔本华的遗体进行过尸体解剖。他头部戴有月桂叶花冠的尸体,在墓地的停尸房里停放得比一般情况要长(哲学家害怕自己在被人埋葬之时尚有生机)。除了那个月桂叶花冠之外,所有一切都是依照叔本华的指示办理。
在9月26日这样一个下着雨的星期三,举行了一个非公开的小型葬礼以将哲学家葬入墓穴,在墓穴上面所放的那块平整黑色大理石石板上只刻了“阿图尔·叔本华”这个名字。
贝克尔、克尔策、霍恩施泰因、格温纳及路德教牧师巴瑟博士,护送叔本华已在腐烂的尸体到达墓地(叔本华像他的唯心主义英雄乔治·贝克莱一样,知道尸体在停尸房停放五日里所发出的腐臭,会证明其人确已死亡)。
牧师举行了一个福音派的仪式。格温纳所致的颂词,既言简意赅,又情真意切。这位首部叔本华传记的作者,赞扬了哲学家对真理始终不懈的绝对忠诚,赞扬了他在追求那位腼腆的女主人过程当中的甘于寂寞,以及叔本华那种渴盼对自己所得到的遗产—这使他得以投身于自己使命的完成而不必为世间俗务所累—定不相负的热切愿望。
格温纳特别提到说,戴在叔本华双眉之上的月桂叶花冠,直至他垂垂老矣才姗姗来迟,却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他对自己命定的使命是何等坚信不疑。
格温纳最后用一句会令哲学家高兴的引言结束了自己的演说:
“真理是伟大的——无比的强大!”
这句话出自《以斯拉上》的引言,曾经被用作《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的扉页警句。该书第二版面世于其作者去世前的几个星期。这位崇尚意志、倡导同情的哲学家,在几年前就已经给出了他对自己一生的反思,进行这一反思的出发点如同格温纳颂词的出发点一样,并非基于他人所见的一生,而是基于本人所过的一生。
叔本华在他私人日记中是这样来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诉诸表达的:
“[我一直都希望死得轻松。]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孤独终生的人来说,他都更能比别人对这一孤独的况味作出准确的评鉴。我不会出去混迹于适合那些无才乏能、徒具人形的两足动物的胡言愚行,而是将怀着已经完成自身的使命并即将回归于那赋予我如此之高天资的来处而感到满心喜悦,以结束自己的人生旅程。”
叔本华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