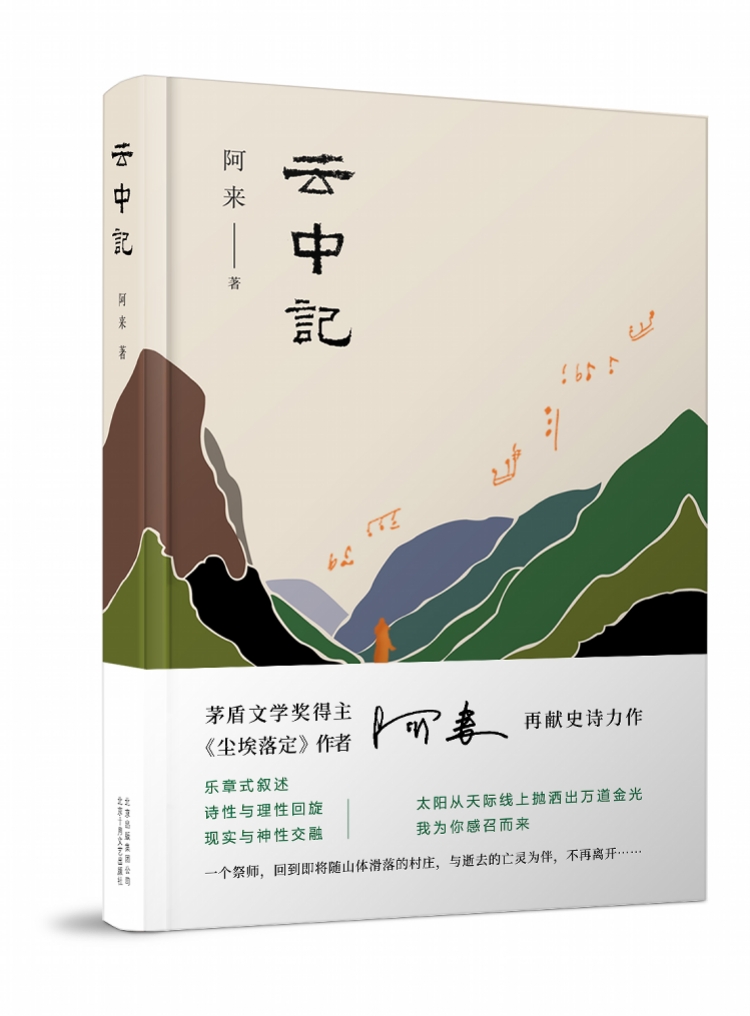有人问阿来一辈子什么经历最难忘?他说就两个。一个是年轻时代的爱情,一个是大地震。
“5·12”汶川地震过去多年,阿来在长久的静默之后,以他独有的空灵、低回的语调,写下了长篇小说《云中记》。云中村的祭师阿巴,在全村整体移民四年后,只身返回荒芜的村庄,去敬奉山神、去照顾鬼魂。当他披戴祭师的行头,在废墟上摇铃击鼓、念念有词,发生在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的那场灾难不断在记忆里闪回———大地颠簸摇晃,人们先是讶异,然后跌倒、奔逃、躲藏,哭声撕心裂肺。正如云中村的古老史诗所唱的:
“大地不用手,把所有尘土扬起,
大地不用手,把所有石头砸下。
大地没有嘴,用众生的嘴巴哭喊,
大地没有眼睛,不想看见,不想看见!”
阿巴是云中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大地震之前,村里搞文化旅游,恢复山神祭祀。阿巴是个半吊子祭师,虽然上过培训班,代表自己身份的专有名词一直念不全,时而说“我是非物质文化”,时而说“我是非物质遗产”。突如其来的灾难,让阿巴对死者有了怜悯,有了敬畏,他明白祭师的职责就是安抚死者的鬼魂。即便科学家预测,云中村将在一次山体滑坡中整体堕入岷江,阿巴也要独自上山。
“从开始,我就明确地知道,这个人将要消失,这个村庄也将要消失。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阿来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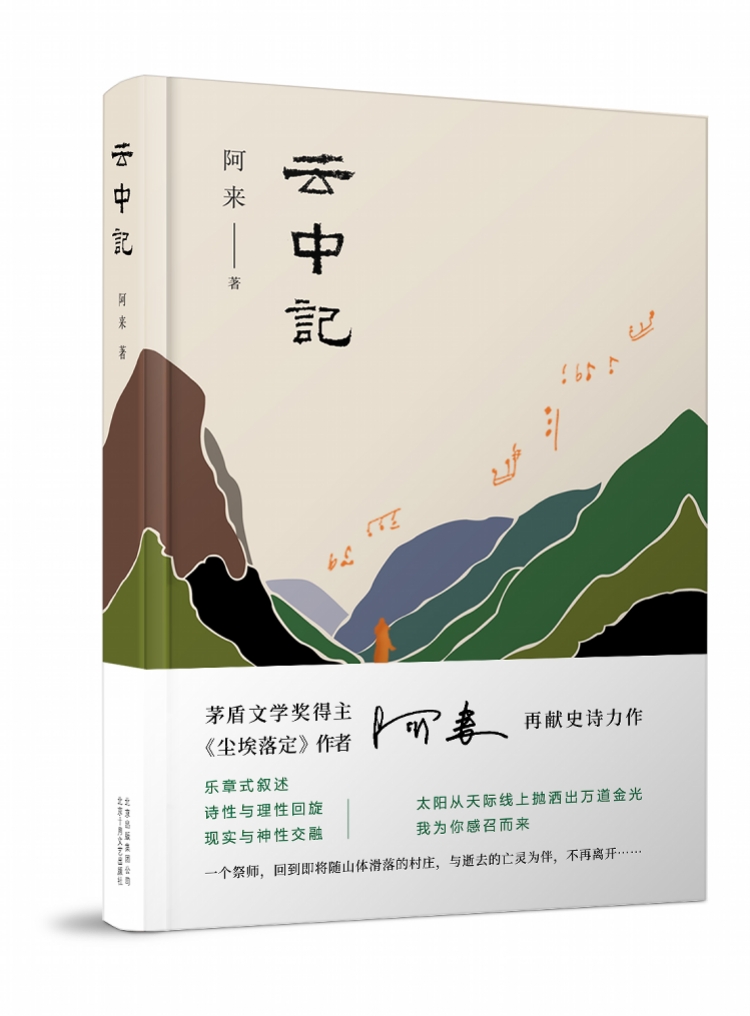
阿巴在成了废墟的云中村与世隔绝地生活了六个月。这六个月里,他喝泉水,吃糌粑,刨地种菜。他与两匹马作伴。他与柏树、杉树、桦树、樱桃树、长着羽状叶子的花楸树,与忍冬、绣线菊、鸢尾花、香得让人头晕的丁香花作伴。他的菜园无需照顾就漾起一片亮晶晶的新绿,吸引从雪山下来的雄鹿清晨用前蹄轻叩院门。
在《云中记》里,真正抚平创痛的,是自然,是自然中生生不息的生命。是人与自然的亲密相处、重归和谐。
野画眉天天在头顶上叫,阿巴就说,知道了,知道了。天气好,天气好。
读着读着,就会分不清,谁是祭师,谁是作者,谁是阿巴,谁是阿来。眼前总有那么一个人,一路行走,一路念诵,轻言细语、庄重仁慈。他离开活人的村庄,来到死人的村庄。他走过阳光照耀的土地,也走过阴影遮蔽的土地。他对自己说话,也对众生说话。他的心中藏着朴素但巨大的疑问。未知生,焉知死?未知死,又焉知生?
《云中记》本身就是一曲安魂曲,阿来没有沉陷在对肉身毁灭的无限哀悼中,也没有停留在触目惊心的再现和泪眼滂沱的抒情中。他借祭师身份获得一双灵视之眼,一层语言的灵光,一种神性的轻盈,以及与自然万物毗邻、与阿吾塔毗雪山毗邻的位置———从而为小说找到了不被新闻写作挤占的另一重可能。
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说:“关于想象性文学的伟大这一问题,我只认可三大标准:审美光芒、认知力量、智慧。”阿来推崇这三个标准。在北京举行的《云中记》新书发布会上,他说,审美的光芒来自小说形式本身、文字本身;通过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文学能产生宽恕、理解和沟通的力量。这两样加起来,就是智慧。“是关于社会、关于世界,更重要的是关于我们自己生命的新的智慧。”
阿来说,《云中记》要不是我写的,我想说“伟大”这个词。
阿来在北京举行的《云中记》新书发布会上
南都专访作家阿来
文学跟新闻不一样,需要沉淀
南都:2008年5·12地震发生后,您也亲自到灾区参与抢救,什么时候赶到的现场?具体做了哪些事情?
阿来:第三天。救援通道打开以后,首先保证救灾物资、抢险部队进去,然后才慢慢有志愿者进去。我们也是作为志愿者去的。
刚好我自己的车是一个越野吉普车。那时候所有人往灾区去,都是先跑到超市,把所有东西往车上搬,超市的人也来帮忙。到了现场其实做不了什么事情。尤其是后期的救援,必须专业的人才能做。而早期的抢救是地震后的头一两天。那时候救援人员还没有到达,是灾区的人们自救。等我们进去,好救的都已经被救了,不好救的必须靠专业的工具和技术。我们就是去送点东西,帮点小忙。
当时有很多人想书写地震。我就说,我们不要那么着急,文学好像不是这样。倒是经受灾难的人,你们能不能留下一些口述史?经受灾难的人,在灾难之后就是两种反应。一种是你说什么他也不开口,一声不吭。还有一种就有强烈的倾诉愿望。因为媒体都跟现场直播一样的,作家还能写什么?更何况很多文化人容易有些表演欲,去了不是去干什么,而是要向大家表示“我到了这儿”,很多人在废墟前一站,拍两张照就消失了。就当他已经去过了。
当时我们有一个国家重点工厂,叫东方汽轮机厂,生产我们国家的好多水电设备和风电设备,是一个大型国企。今天也是我们国家水电和风电设备最强的生产企业。因为大国企有这个意识,我就跟工厂讲,与其让别人写,工厂里的干部、工人都有点文化,为什么不自己干?先是遭受灾难,后来又重建。他们两年就恢复生产,甚至最早在地震后三个月,损毁不严重的车间已重新开工。他们自己的工人、干部写了两本书,一本书讲受灾、救灾的经过,一本书讲重建的过程,这两本书都是我写的序。我觉得将来可能会是很好的材料。这也算我们作为文化人起的作用。
南都:您怎么评价5·12地震以后作家们为此创作的文学作品?
阿来:应该说没有太成功的。大家在那种情境当中都有点急于表达。我觉得可能太快了。那个时候我曾经委婉地说,不要着急来写。他们觉得这个人不对,为什么你要反对我们写重大题材?加上我是四川省作协主席,大家说你怎么能讲这种话?我说,作为主席可能不应该讲这种话,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应该讲这种话。
那两三年地震题材的作品数量很多。我当时就说,文学是需要沉淀的,跟新闻不一样。有些事情在心里多放一放,久一点,然后才慢慢慢慢发现一些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东西。
坐在他们中间听就是了
南都:在《云中记》里,地震只是一个引子,地震过后有许多次生灾害发生,比如裂缝造成的山体滑坡最终造成云中村的消失。这是小说的一个非常好的切入角度。现实当中,次生灾害也是如此频繁发生吗?
阿来:对。因为地震发生了,已经造成很大破坏,留下很多隐患。比如山体滑坡把一个村子掩埋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最后一次,离大地震已经十年了。十年当中,有些人重新开始,终于重建了自己的生活,甚至家庭,很多人是第二次又失去亲人。第一次地震的时候,有的小孩长到七八岁、十几岁,死掉了。好不容易到了中年,重新组合家庭,用尽种种方法重新怀上,结果又来一次,房倒屋塌……你从这个角度看,那种残酷性才真正显示出来。
南都:次生灾害可否通过科学预测来防范,就像书里写到的那样?
阿来:科学预测可能有误判。另外中国人确实恋土恋乡。《云中记》里写到的移民是一个村子整体移民,这种情况还好。实际上,中国哪有一整个村子可以移民的地方呀?都要把村子解散,这个村儿插一户,那个村儿插两户。打散了,安顿到几百里外,周围全是陌生人。不光是背井离乡的问题,还要离开原来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在陌生的人群当中重新开始建立生活,对农民来说还是难的。所以他不愿意离开。
所以在《云中记》里,大地震本身成了一个背景。只有处理成这样。如果直接宏观地写,不好写。而且当时已经有那么多新闻报道。小说也有自己的空间,新闻报道、影视的出现,挤压了小说的一部分空间,它跟19世纪的小说就不一样了。但不是说小说就没有空间了,还是有空间。关键是写小说的人能不能把这个空间找到。
南都:写作《云中记》的时候,5·12汶川大地震已过了十年,您依靠什么去回忆大地震时经历的种种细节?
阿来:他们问我一辈子什么经历最难忘?我说就两个。一个是年轻时代的爱情,另一个就是大地震。
心里好像总有一个东西放不下。其实也没有想过我一定要写地震。但它总是一个事情,有时候像一种情绪,有时候像一个痛感很强的记忆。虽然死亡的都是别人,但是那么大面积的死亡我看到了。而且后来那种漫长的治愈过程,别人不关心了我们还在关心。包括次生灾害的出现,刚刚重建的生活又遭到再次的毁灭。我们都以为,救灾、把人挖出来,新房子盖好,一切就结束了,其实人性不是这样。
南都:您面对面地跟灾民聊过吗?
阿来:不要聊。我们也不是记者。你坐在他们中间听就是了,他们随时都在说。不光是灾民,也有干部,它是立体的。灾后,很多干部自己家里就有死伤,还要全身心地投入抗震救灾,还要承担相当重的责任。
文学有的时候就想到最基层的灾民,其实在重建过程中,有各种层面。我比较反对只是写普通人,因为它不是社会的全貌。干部、群众,只要是灾区的,都受到打击。很多人其实就是身边人。一问,你老婆呢,死了呀。最近见一个人,怎么老不提他的儿子,死了呀。女儿很漂亮,截了一条腿呀。只要一回到家,就生活在这些人中间。
这些人直到今天也是,只有两种反应,一种是滔滔不绝,他忍不住要向你倾诉,还有一种就是一言不发。
南都:这种重大的灾难题材确实很难处理,驾驭得不好,小说容易被题材吃掉。
阿来:我本事还是大嘛。哈哈。
作家阿来
写小说就是要找到一种语调
南都:您为什么选择一个祭师,一个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来做小说的主角?
阿来:灾难到底留下什么?如果只是创痛,就没有意义。我们应该把人的死亡带来的这种创痛,变成一种精神洗礼。因为中国文学有个短板,我们不会写灾难,包括战争,战争也是最大的灾难。我们打了那么多仗,但我们哪有好的战争文学?我们停留在死亡带来的悲痛当中就完了。我们先是悲痛欲绝,然后靠时间来遗忘。但是对死亡的终极意义、对生命的终极意义的思考,是我们欠缺的。我确实是带来了新的东西。
不光是悲伤,我不想要那么多悲伤。人都是要死的,我们开脱一点看,只不过这些人早死一点而已。更重要的是它对活着的人的意义。
刚好在那个地方有祭师,他在乡村里担负了沟通人和亡灵之间的媒介。当然我又不想把他塑造成一个没有时代感的人,他上过中学,是村里最早的发电员,在当发电员的时候,灾难已经预演过,他因为水电站滑坡而失忆,苏醒的时候已经来到了新的一个时代。这个时候因为旅游,因为政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他当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因为他们家族就是干祭师的。起初他三心二意的,但是经过地震灾难以后,好像把他的内心唤醒了。所以他要去履行祭师的职责。
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过。有个村子在地震以后搬迁了。有人跟我说,你知不知道那个村儿啊,他们的巫师回去了。巫师说,活人政府管,我们老家的鬼没人管,我就是管鬼的。小说里的这句话也是真的。时时有人会给你传递这些消息。我的小说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给我讲这个消息的人也搞摄影,拍了一张巫师的照片。确实穿着那一套巫师的衣服,在村子的废墟里头击鼓。我问他在做什么?那个朋友说,他假定有鬼,他就在一家一家地告诉,现在活着的人是什么情况。
南都:小说里为什么没有一句描写阿巴的外貌特征?
阿来:我不想写。我们过去写人都像画素描一样。我想让大家自己去构建一个关于阿巴的形象。而且这个小说就是写他的情感,写他的内心,写他的信念。他长什么样子不重要。
南都:阿巴独自祭山神那一章,写云中村的祖先阿吾塔毗的故事,很像是藏区先民的史诗。山神崇拜在藏区是确实存在的吗?这种古老的信仰今天是否还在延续?
阿来:山神崇拜在藏区很普遍。每到一个村落,我一听山神的故事就知道他们部族的历史。这些部族大部分都是从更远的地方,在公元七八百年的时候迁徙来的。这个山神往往就是部族的早期首领,或者是期间产生的英雄,是为部族做过很大贡献的。大家不愿意忘记他,就把他作为一个跟山合二为一的神祇。
在藏区每一座山的神是不一样的,它都是跟住在这一座山下的人、这些部族的历史是有关系的。
但过去的文化必然要消亡。所以阿巴也是吊儿郎当的,虽然当了非遗传承人,但那些文化已经淡了。地震过后,那么多死亡摆在面前,大家好像又愿意信仰山神了。因为一切都化解不了死亡的创痛。早期很多地方恢复民俗其实是为了发展旅游业,所以小说里,地震之前正在做村子里的旅游规划,要把山神节恢复出来。其实这个传统已经中断很多年了。这些地方非遗的保存,背后的推手往往是政府和商业。
南都:在《云中记》的新书发布会上,北大的陈晓明教授说,《云中记》最了不起的一点在于把灵知的部分和现实的部分结合得非常好。
阿来:这是很难的。一方面要写原始的东西,但他们过的又是当下的,充满现代性的生活,而且有很多现代性的焦虑。这个其实是靠语言的技术。
南都:写的过程会有撕裂感吗?
阿来:没有。我的世界就是浑然一体的。其实写小说就是找到一种语调。成功的小说就是成功地找到了一种语调。这个题材捂在心里这么多年没有写,就是因为我没有听见那个语调。这不是我一个人说的。是写《野草在歌唱》的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说的。她在得诺奖的演说词里说,我总是在听自己的内心,我一直在等待那个腔调的出现,而不是在寻找一个题材。题材到处都是。很多时候题材在内心,但是那个声音没有出现,那个调子没有出现,好像你没有办法下笔。
她用的词是“腔调”。对这些关键词我有点较真。后来我想是不是翻译的问题,我查到英文原文,故意把前后都截掉了,拿去找英文好的人,一问,就是腔调。
南都:您写的每本书腔调一样吗?
阿来:肯定不一样。因为每本书的内容不一样。每本书都需要一个特别的讲述方法。有些可能更写实一点,有些可能更空灵一点,有些可能更沉重一点,低回一点,有些可能更明亮一点。
南都:《云中记》读起来还挺空灵的。
阿来:这个书有两个考验。怎么把苦难不写得那么让人痛苦和绝望?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写,就一定是这个方向。第二个是我们现在写实的时候,太写实了。我们应该有一种在平凡生活当中,用诗歌的方式把现实照亮的能力。这个时候,空灵感就会产生。而空灵是重要的,它相当于哲学上说的形而上的力量。现在我们有很大的能力是写形而下,就是真实层面。但是光是写真实层面对文学是没有意义的。所以那天新书发布会上我说,假如是别人写的小说我就要说它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其实我也就把它说出来了。
小说中也有许多变奏
南都:《云中记》里对大地震不是直接描写,它全部来自回溯,来自阿巴的记忆。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结构。
阿来:就像那天发布会上江河谈古典音乐。古典乐里有一种“主题变奏”,一个乐句不断出现。比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它的主题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一句,在乐章当中这一句过一阵子又出现,有时候是小提琴拉的,有时候是大号吹奏的,表达的东西不一样,就这样一步一步升华,一步一步升华,最后整个乐队合奏,震耳欲聋,这就是音乐的主题变奏的方式。
小说里这个变奏就是过去的灾难场景。你一次写没有意思。但是在不同的情境里,当阿巴要去安抚鬼魂的时候,在他的回忆当中这个场景不断出现。因为是经过回忆,已经进行过一次隔离,那种强烈感好像就降低一点。
南都:这个结构跟古典乐很像,跟史诗的结构也很像,史诗里经常出现重复的段落和吟唱。
阿来:对,它必须强调一种东西。音乐里是吟唱式的,循环往复的,而循环往复的东西经常是重要主题的变奏,它以不同的调性出现。
南都:在小说扉页上您向莫扎特致敬,“写作这本书时,我心中总回想着《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安魂曲》如何出现在了您的写作过程当中?
阿来:我在灾区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因为没有地方住,我就睡在车里。白天其实还是很累,总不可能抄着手站在那儿。晚上睡不着,满天星光。第二天大家要开工,很多军人,只有十几二十来岁,都睡了。只有一台挖掘机还在轰轰地工作,干什么呢?在挖坑:为第二天埋葬受难者,做着准备。
白天的哭声也消失了,人也哭不动了。这时候我就想,我们中国人除了用哭以外,没有办法面对死亡。而西方人,尤其是基督教、天主教,他们会用语言,会用歌唱。我们也有哀歌,但那个难听极了。除了哀乐以外,音乐在那种现场几乎是个禁忌。我车里头就有一套碟子。本来想放《弥撒曲》。但难道不能用美一点的方式,表达对死亡、对生命的痛惜和悼念?过去我不太喜欢莫扎特,我觉得有点女性化倾向。我喜欢更有力量一些的。但那天看到《安魂曲》,就这三个字就可以。当时我就把音响打开,我一听,眼前的星光模糊了,我自己也泪流满面。但我觉得很美,哀伤的、悲悯的,但经过洗礼又有种净化。死了的人就死了,重要的是他的死亡留给我们什么。我第一次这么喜欢莫扎特。我想这个东西贝多芬也不会搞,柴可夫斯基也不会搞,只能是莫扎特。
而且《安魂曲》莫扎特没有写完,他自己也对他的死亡充满预感。这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作品。所以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写之前就先把音响打开,听《安魂曲》,尤其它那种高音的合唱。
作家阿来
真正能使人净化的就是美
南都:《云中记》里有一段非常好看的情节,就是阿巴独自一个人在荒芜的云中村里生活。陪伴他的有两匹马,有从雪山下来的一群鹿。一个人在荒野中生存,是世界文学里的一个母题。您自己有过这种重返自然的体验吗?
阿来:那是我写得最得意的。阿巴一个人怎么过日子?怎么写?我给了他两匹马。那个世界就是动物的世界、植物的世界。
我经常在山里行走,在山上露营。早上还没醒,手在睡袋外面,真的马就在舔你的手。鹿有点怕人,可能在三四米外看你。
南都: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段是,一只雄鹿走进阿巴的菜园里吃罂粟,头上新生着一对鹿角,晶莹剔透。
阿来:鹿茸是一年一生,在初夏的时候刚好是透明的状态,到秋天就变得硬了,掉到地上。我们中药店里就是把嫩的鹿茸切下来,为什么叫鹿茸,因为上面全是细毛,里头全是血。然后慢慢骨质化,老了就变成骨头,冬天自动掉在山上。
我上山有时候不为什么,看植物,看动物。书里写的这些都是靠积累。我是一个比较狂热的植物学爱好者。到现场,读植物志,两相对照,认得许许多多植物。这本来是植物学家的事儿。可小说需要描绘,想做到真实,就需要动植物的知识,更需要地理的知识,更需要那个信仰的文化的知识。这些都是日常的积累,都是因为熟悉那片土地。
我的小说里从来就有人和自然的关系。在今天的中国文学里,通常只有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人,有时候就往恶处走,往黑暗处走。而自然是有神性的。斯宾诺莎的哲学当中有一个重要概念是自然神性,我是在这个意义上喜欢他。自然既是我们生存的环境,另外有一个巨大的美学力量,森林、草原、沙漠,真正能使人净化的就是美。
南都:如果上一次水电站山体滑坡给阿巴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他为什么还决意再经历一次山体滑坡,和云中村一起消失?他为什么选择死而放弃生?
阿来:这是他对于职业的认知。原来吊儿郎当的,但后来经过地震的洗礼,他觉得他就是来祭神和安慰鬼的。新的移民村文化已经改变,已经不需要他这样的祭师。所以他宁愿跟旧世界一起消失。本来他已经走进新世界了,我们又把他摁回去。生命有很多消亡方式,这是一种绚烂的消亡方式。我们这些人都没有这种荣幸去寻找这样的死亡。
南都:《云中记》里涉及到很多当代的现象,比如选秀、直播等等,您把这些现象写进小说的意图是什么?
阿来:这些都是今天生活中大量出现的。有很多商业机构在做这些事情,甚至是普遍发生的。有时候我们写古老的文化遗存,想象它必须跟今天的现代性发生一种隔绝或者强烈的冲突。其实在任何一个文化的演进的过程中,这些都不像我们观念当中具有那么强烈的冲突。自然而然地它们就出现了。你还没想清楚它为什么出现,它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了。我不反对现代性,但我反对出于商业利益对灾难的消费。对于灾难,对于贫穷,对于弱小,对于疾病,我们的这种消费多了。文学能够做的,就是把它呈现出来。至少是读到这些文字的人,我相信一定会触发他的情感和反思。
南都:这部小说在您的整个创作当中算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
阿来:我不这样看。将来可能会很重要。因为我自己的每一部作品我都觉得很重要。除了年轻时不成熟,从《尘埃落定》到现在的每一部作品,第一我是倾注全部心力,第二我想每一本书都达到了我当时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你说重要不重要,更多可能还是将来批评家、读者来做这种解析。我很少这样定义我的作品。从学界来说这是批评家的事情,从市场来说是读者的事情。
每本书的命运肯定是不一样的。有些书其实我用的劲儿是一样的,甚至我觉得它好的程度也是一样的,但面向社会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同样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