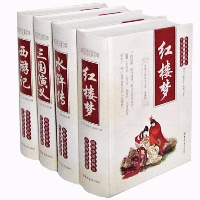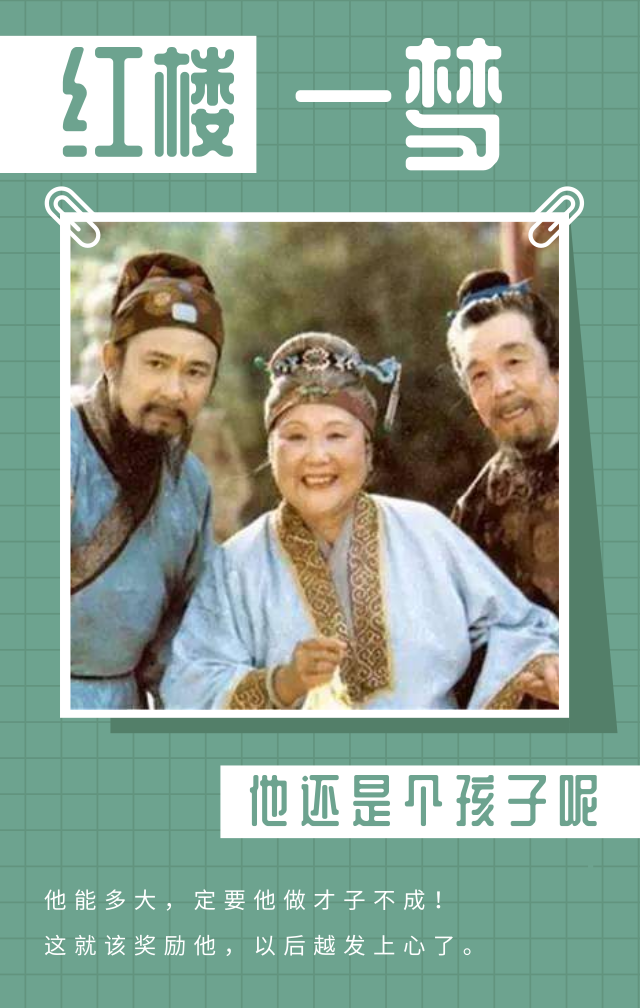最近在研读《易经》,发现有一个词在六十四卦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贞吉。
贞吉的意思指坚守正道能得到吉祥如意的结果。所谓坚守正道,简言之就是待人处世不违背良知。
不违背良知,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很难,不是说不害人就叫不违背良知。很多时候,主观上不想害人,客观上却造成了害人的后果,也可称做违背了良知。所以,人生在世,要长智慧,不能活成糊涂蛋。
红楼中的贾母,被奉为老祖宗,看起来好像很有智慧,实际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糊涂蛋。因为她居高位却听不到真话,看不到真相,活在假象里而不自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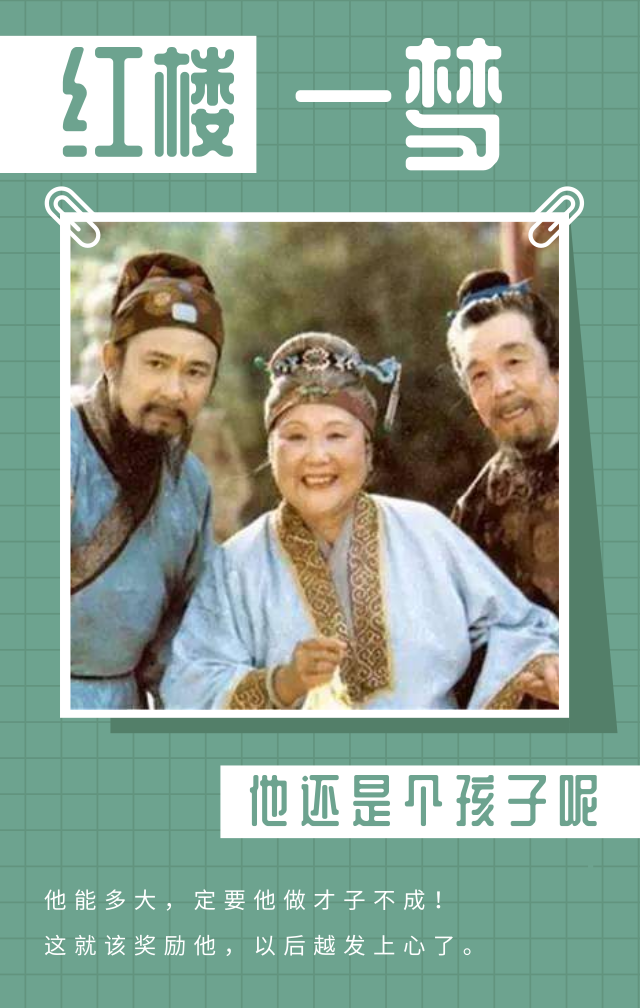
比如她对宝玉的爱,就是一种看不到真相的溺爱,从而从根子上毁了宝玉,让宝玉活成了一个“无国无家无望”的废物。
宝玉是有资质的,他不求上进就和贾母的溺爱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她给这个宝贝孙子搭建了一个安乐窝,让他享尽男人都想享的福,而且为他建造了一堵防护墙,只要宝玉不想做的,她都能替宝玉挡掉。
上有所好,下必从之,为了迎合贾母,有关宝玉的一切,下面的人就只拣她爱听的说了。
第七十五回,荣府的中秋夜宴,两府的人都参加了,作者曹先生写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贾母笑问道:"这两日你宝兄弟的箭如何了?"贾珍忙起身笑道:"大长进了,不但样式好,而且弓也长了一个力气。"贾母道:"这也够了,且别贪力,仔细努伤。"贾珍忙答应几个"是"。
贾母为何有此一问?
前文有交代:
贾珍近因居丧,每不得游顽旷荡,又不得观优闻乐作遣。无聊之极,便生了个破闷之法。日间以习射为由,请了各世家弟兄及诸富贵亲友来较射。
以习射为由,请了富贵亲友来较射,实际上却是开赌局,且请来的人都是“斗鸡走狗,问柳评花的一干游荡纨纨”,“一日一日赌胜于射了”。就连尤氏都看不下去,每天往荣府躲,避开这些乌烟瘴气的人。
荣府的主子们不清楚内幕,贾赦贾政还以为他们真的是在习射,“命贾环,贾琮、宝玉、贾兰等四人于饭后过来,跟着贾珍习射一回,方许回去”。
在这样的环境下,宝玉真能“大长进了”吗?
没关系,贾母爱听,说了她就会信,反正她从来不会去验证。
击鼓传花时,宝玉因贾政在席,不好讲笑话,主动要求以作诗代替。
宝玉的诗作得怎么样没有明写,但却写了贾政母子的对话。
贾政因欲贾母喜悦,便说:"难为他。只是不肯念书,到底词句不雅。"贾母道:"这就罢了。他能多大,定要他做才子不成!这就该奖励他,以后越发上心了。"贾政道:"正是。"因回头命个老嬷嬷出去吩咐书房内的小厮:"把我海南带来的扇子取两把给他。"
贾政不擅长说谎,但还是“因欲贾母喜悦”而说了个“难为他”,其实重点在后面的“不肯念书,到底词句不雅”。
贾政都需要婉转,不能直接说实话,何况其他人呢?
贾政都已经说了宝玉“不肯念书”,但贾母只挑“难为他”来听,并拿“他能多大”当理由维护宝玉,并要求贾政给赏。
“他能多大”,换成现代常用语就是“他还是个孩子”。这话是不是很熟悉?和袭人云雨都好几年了,贾母却一直当他是个孩子,并以此为理由,帮助他逃避生而为人该承担的责任。
人性都是趋利避害的,居高位者的习性如果被下属所掌握,就会被利用。
晴雯就利用过一次。
因赵姨娘的小丫头跑到怡红院送情报:“方才我们奶奶这般如此在老爷前说了。你仔细明儿老爷问你话”,宝玉急得连夜温书。
正好芳官说看到“一个人从墙上跳下来了”,晴雯马上要宝玉装病,说是受了惊吓。
为什么晴雯会想到这一招?因为贾母就吃这一套,对下面报上来的话,从来不辨真假。
试想,有这样一层又一层的保护,哪个孩子愿意用心读书上进?纨绔就是这样养成的,贾母成功地用她的爱,把宝玉养成了废物。
也许是受贾母的影响,宝玉和她一样糊涂,听不到真话,看不到真相,主要表现在对晴雯的认知上。
晴雯被撵,宝玉是真伤心,因为在怡红院,只有晴雯支持他不上进,愿意陪着她胡闹。
这是最好的玩伴。
但是,以晴雯的身份,她不应该成为宝玉的玩伴,正如她自己所说:“宝玉饮食起坐,上一层有老奶奶老妈妈们,下一层又有袭人麝月秋纹几个人”,她的主要职责是和袭人麝月秋纹一样照顾宝玉的饮食起居。但她非常清楚宝玉喜欢什么,于是投其所好。
这样的晴雯,在宝玉眼里当然是可爱的,无可指摘的。
但是,真实的晴雯是什么样的?宝玉看不到,更没有人会跟他说,他只能听到他想听到的。
于是,作者又给出了一个细节来表现。
司棋被撵出去,正好让宝玉遇上了,婆子们说起晴雯的哥嫂也进来领人了。
因笑道:"阿弥陀佛!今日天睁了眼,把这一个祸害妖精退送了,大家清净些。"宝玉一闻得王夫人进来清查,便料定晴雯也保不住了,早飞也似的赶了去,所以这后来趁愿之语竟未得听见。
作者曹先生经常在细节处写下骇人之语,如粗心略过,就容易曲解。
婆子们的称愿之语,为何不让宝玉听到?这里的作用有二:
其一,婆子们称愿,说明晴雯犯了众怒,对她有意见的不仅是王善保家的;
其二,刻意写宝玉没听到,说明他一直处在糊涂中,而且还会继续糊涂,从而为后面的怀疑袭人埋伏笔,也为用各种溢美之词写《芙蓉女儿诔》埋伏笔。
宝玉用他的糊涂,看似保护了晴雯,让晴雯在怡红院养尊处优过着小姐般的生活,实际上却是为晴雯的命运埋下祸根。
晴雯死后,宝玉不肯相信晴雯“一夜叫的是娘”,因为这不是他想听到的。所以伶俐的小丫头便编谎话骗他,说晴雯不但临死前对宝玉念念不忘,而且还是当芙蓉花神去了。
这里作者又用了一个细节:“一时诌不出来”,说明这都是小丫头的胡诌。
可是宝玉信了,因为这正是他想听的,小丫头也是投他所好,照他爱听的来编。
这便闹了个天大的笑话:宝玉着重其事地写《芙蓉女儿诔》来祭奠晴雯,其实与晴雯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便是贾母和宝玉的同款糊涂:真相不重要,自己舒服最重要!
贾母的糊涂毁了宝玉,同时也加速了贾府的衰亡;宝玉的糊涂毁了晴雯,也毁了他自己。
所以,红楼是一本忏悔录,直到衰亡之后,宝玉才悔悟,于是有了这一部写满血泪的经典巨著:“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纨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愧则有余,悔又无益”,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从《易经》的角度来看,这祖孙两人是典型的不贞,即不守正道,违背良知而不自知,导致了凶险的后果,害人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