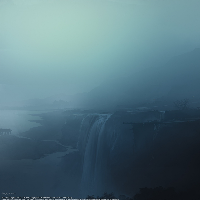盖琪

“荒诞喜剧电影”作为一个概念术语,其关键词就是“荒诞”。而此处的“荒诞”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命题。换言之,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虽然“荒诞”(absurd)作为一个词汇很早就存在,但是作为一种对人类极端生存境遇的提炼,它却是在20世纪初才真正获得具名的。而完成这种具名行为的,就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日益兴盛起来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存在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是西方社会危机的产物”。而这种危机就是愈演愈烈的现代性危机。简要地说,西方社会在踏入现代化进程之后,随着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不断扩张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其主流意识形态也在发生变化——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人的主体意识不断上升:人从对神的膜拜和附庸之下抬起头来,站直身体,越来越大地发挥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性自觉,越来越多地倾心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逻辑。
历史地看,在18到19世纪,这种高度信任人的主体性和世界的合目的性的观念显示出了不可磨灭的积极意义:它不仅推动了以科技创新为基础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而且促进了哲学法律、文学艺术等上层建筑领域的活跃变革。但是到了20世纪初,这套观念膨胀到极致,就逐渐走进了一条工具主义、科技主义、国家主义的死胡同,并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了大屠杀和核爆炸等“现代性之恶”的极端情境。
存在主义所指向的,正是经历了这些极端情境之后的人类。质言之,它指向的是经历了由现代性失控所导致的巨大灾难之后,深陷于前所未有的集体创伤中,因而无可避免地对文明的意义感到彻底灰心绝望的人类。存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其试图回答的,正是这样的人类如何重新去认识世界、认识自身的问题。
为此,存在主义哲学家(主要是法国的阿尔贝·加缪和让·保罗·萨特)“发明”了一个概念,对世界重新进行界定,也对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描述——这个概念就是“荒诞”。由此,在存在主义的叙事框架中,“荒诞”指的既是一切宏大叙事的虚幻,也是一切个人叙事的徒劳。存在主义认为,必须清晰地指出,世界毫无理性,人生亦毫无意义。惟其如此,人类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绝对的自由”,然后做出选择,并且承担责任。
存在主义的上述核心观念作用于同时代的文学艺术场域,最直接的成果之一就是荒诞派戏剧的诞生。“荒诞派戏剧就本质而言,可说是对存在主义哲学的戏剧图解。”20世纪50—60年代,欧洲戏剧界涌现了大量以诠释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荒诞”为目的的戏剧作品,代表作包括《秃头歌女》《等待戈多》《椅子》《犀牛》《一切人反对一切人》《女仆》《阳台》《啊,美好的日子》等。
值得强调的是,这些作品与此前和同时期产生的存在主义小说/戏剧相比,都是以存在主义哲学为精神内核的文本。但是其特殊性在于,它不再遵循传统小说和戏剧的模式、原则和方法,而是“将‘荒诞’的思想内涵以‘荒诞’的形式直接呈现在舞台上”,“以舞台上种种荒诞不经的语言、动作、道具陈设等,直喻世界的荒诞”。应该说,这种从主题到形式的“荒诞”具有非常大的创新意义,它直接影响了电影领域的创作实践,使得电影创作者们也开始尝试创作从主题到形式都具有“非理性”特质的电影作品,这直接推动了荒诞喜剧电影的诞生。
至此,我们就需要探讨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荒诞喜剧电影”中“喜剧性”的来源。换言之,为什么当“荒诞性”进入现代戏剧和电影场域之后,它大多以喜剧的面貌来呈现自身?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喜剧观念的巨大变革。历史地看,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悲剧和喜剧分别处于艺术光谱的两极,彼此对立、互不交融,但是到了文艺复兴之后,二者之间的界限就开始变得模糊起来,逐渐出现了可以被称之为“悲喜剧”或者“喜悲剧”的作品(例如莎士比亚和契诃夫的戏剧创作);而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悲剧和喜剧无论在艺术观念还是在艺术实践上都已经变成了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彼此不可分割,甚至可以随时翻转。
对于造成这种巨大的变化的语境原因,英国哲学家怀利·辛菲尔曾经在《我们的新喜剧观》一文中做出过分析,他指出:“我们已置身于二十世纪的‘尘埃和冲突’之中,并认识到落在人类头上的最可怕的灾难如何证明了人生归根结底的荒谬。人生的喜剧观与悲剧观已不再相互排斥。现代批评最重要的发现或许就是认识到了喜剧与悲剧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或者说喜剧能向我们揭示许多悲剧无法表现的关于我们所处环境的情景。十九世纪中叶,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这一点,索伦·克尔凯郭尔以一个现代人的身份写道,喜剧与悲剧在无穷的极点上相交——即在人类经验的两个极端上相交。”
由此可见,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过程中,西方社会对于喜剧性的理解逐渐发生了变化:荒诞性与喜剧性在现代人的视域里越来越显示出同质同构的趋势。对此,近年也有国内研究者做出了清晰的比较式阐述:“传统喜剧在理性原则的指导下,通常是通过对‘丑’的嘲笑与否定来彰显主体的胜利感、优越性和乐观态度的;而现代喜剧则丧失了主体的自信心和征服力,一变而为‘掩饰失望的假面具’、‘逃避绝望的良方’、求得超脱的智慧与勇气的一种途径。喜剧在现代被理解为另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与高度,有它自身的深刻性。”
至此,我们可以说,在“荒诞喜剧电影”这个概念中,“荒诞性”的根源是存在主义哲学,而“喜剧性”的根源则是现代喜剧观念。对于荒诞喜剧电影而言,“荒诞”不是粘贴到文本外壳上的时髦标签,而是深入文本肌理骨质中的主控思想。从哲学底色和文化逻辑的角度,我们可以把荒诞喜剧电影看作是人类自启蒙时代以来,怀着澎湃的自信与期望,踏上主体性实践的恢弘征程,然而最终却发现所有愿景注定是一条“死路”,所有努力注定是一场徒劳的时候,所发出的无奈的、绝望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