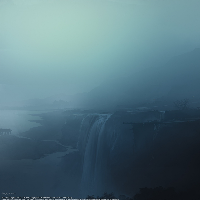盖琪

在类型电影的意义上,荒诞喜剧电影是作为喜剧电影的一个分支跻身于电影市场中的。换言之,对于电影文化而言,荒诞喜剧电影最为突出的特征或许是“荒诞”;但是对于电影产业而言,荒诞喜剧电影最为重要的属性其实是“喜剧”——而且是商业意义上而非哲学意义上的喜剧。由此,我们有必要弄清楚的是,从类型的角度来看,荒诞喜剧电影与其他亚类型的喜剧电影究竟有什么区别?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对“荒诞喜剧电影”这一概念的使用一直比较混乱——因为它与“疯癫喜剧”和“黑色喜剧”等其他亚类型喜剧电影的确面目相近。所以在媒体报道和学术讨论中,同一部电影被划到不同谱系之下的现象时有发生。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这几种亚类型在哲学底色上的同源性以及在修辞策略上的相似性。但就整体观照,它们还是展现出各有侧重的主题和形式偏好。
如前文所述,作为荒诞喜剧电影“前辈”的荒诞派戏剧本来就具有比较明显的喜剧倾向,而荒诞喜剧电影作为类型电影,具有的商业诉求比戏剧更为明确,所以其喜剧性当然也就比戏剧更为强烈。但是,如果从哲学文化的角度来看,荒诞喜剧电影还是非常完整地征引了源自荒诞派戏剧的叙事动机系统,从而形成了两个最为基本的特点:第一,它在哲学底色上是虚无的、绝望的(而不会保有理想和希望);第二,它在幽默目标上是指向深层的自嘲的(而非嘲笑或者讽刺其他对象)。可以说,正是从这两个基本特点出发,荒诞喜剧电影确立了它在喜剧电影家族的亚类型边界——在第一点上,它与疯癫喜剧区别开来;在第二点上,它与黑色喜剧区别开来。
先来看荒诞喜剧电影与疯癫喜剧电影的区别。疯癫喜剧电影一般体现出更为明显的嬉闹色彩,因而又常常被称为“闹剧”(farce)。而闹剧则源于古希腊时期在悲剧演出后加演的一种名为“山羊歌”的轻松戏剧,其目的在于逗引观众捧腹大笑。所以无论是在戏剧还是在电影中,闹剧通常都“把高度夸张或极其滑稽的各类人物形象故意安排在某些意外与荒唐的情节里,并且大量采用插科打诨的手法和扔蛋糕、落水等打闹动作以求得喜剧效果。”
就中国内地的类型喜剧电影来看,“开心麻花”团队主演的喜剧电影和韩寒导演的喜剧电影都是以疯癫喜剧为主的,前者如《夏洛特烦恼》《羞羞的铁拳》《西虹市首富》;后者如《乘风破浪》和《飞驰人生》。
我们看到,疯癫喜剧电影由于其人物的脸谱化和情节的漫画化,很多时候也会呈现出修辞学意义上的“荒诞”感。但是,疯癫喜剧电影在哲学底色上与荒诞喜剧电影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就深层价值观而言仍然指向传统喜剧观念所联结着的人类的乐观主义精神——虽然揭露、嘲弄乃至戏仿道貌岸然的人和事,但是却仍然相信并且期望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发生,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其实可以看作是讽刺喜剧在表现形式上更为极端化的产物;而后者就深层价值观而言则是悲观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既然不再相信人类自身的主体性和宇宙的合目的性,那么也就不再对人性和世界抱有期待,这种决绝的姿态与传统喜剧在精神内核上泾渭分明。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内地喜剧创作者和接收者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周星驰喜剧电影”其实大部分都属于疯癫喜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周星驰主演和导演的电影中,猥琐无能的主人公即使在前半部分受尽挖苦、出尽洋相,但是到了临近结局的部分却总还是会迎来属于小人物的“高光时刻”。这样的设计其实是在“作天作地”的解构之后,仍然给爱、善良、理想、勇气等人类的乐观品质留下了余地。比如《喜剧之王》《少林足球》《功夫》《新喜剧之王》等影片都是如此。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却有所不同;究其实质,这部电影能够算得上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荒诞喜剧。因为在《大话西游》两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至尊宝年少轻狂、骄矜自负,曾以为自己能够纵横捭阖、战天斗地,但到最后却失去了生命中最宝贵的情感,落得“好像一条狗”的悲剧性结局;而踏上取经道路的选择,与其说是英雄主义的自觉担当,不如说是看破红尘后的主动疏离——这不能不说是身处现代理性桎梏之中的人的深刻自嘲,所以也是其多年来能够被中国内地的新生代年轻人奉为“灵魂经典”的根本原因。而多年之后的《西游·降魔篇》虽然脱胎自《大话西游》的故事框架,但是却在结尾处,用主人公唐三藏“有过痛苦才知众生皆苦”的救赎情怀,赋予了文本中的努力和牺牲以更为宏大的意义,从而消解了文本的荒诞走向——这也是对日渐士绅化的市场口味做出了妥协。
再来看荒诞喜剧电影与黑色喜剧电影的区别。有点“麻烦”的是,无论在主题还是在形式上,荒诞喜剧电影与黑色喜剧电影都更为相似。追根溯源地看,二者分别是荒诞派戏剧和黑色幽默小说的创作观念/技法被引入类型电影场域的结果。而荒诞派戏剧和黑色幽默小说都属于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艺大潮之下的典型流派,本来就具有高度的语境互文性。正如有研究者所分析的,黑色幽默小说的诞生其实就受到了荒诞派戏剧的直接影响,因此黑色幽默小说也常常被冠以“荒诞派小说”的别名,或被指认为“小说领域的荒诞派”。
由此,荒诞喜剧电影与黑色喜剧电影在哲学底色、文化逻辑和美学风貌上确实都是十分接近的,但是如果细加区分,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黑色喜剧电影的文本核心在于黑色幽默,而黑色幽默的本质则在于“将愤怒和感伤情绪隐藏在极端冷漠的嘲弄文笔中”。美国著名的黑色幽默家冯尼格将黑色幽默形容为“绞刑架下的幽默”,因为它总是致力于制造一种“喜剧与恐惧的混合物”。因此,相比较来看,如果说荒诞喜剧电影通常更倾向于在形式上对现实世界进行大幅度夸张变形,通过彻底抛弃理性和逻辑,来建构混乱不堪、引人发笑的异质世界的话;那么黑色喜剧电影则通常更倾向于将现实世界中的愤怒、痛苦和不幸转化为笑料,“采取某种悖理的方式,把现实中的危险看作是‘取笑的机会’”,进而让观众感觉“事情已经糟到了你尽可以放声大笑的地步”。
进而言之,荒诞喜剧电影的喜剧性主要源自剧中人物自信、努力的姿态与虚无、徒劳的境遇之间的巨大落差,它的深层意旨是让我们从一群忙碌而愚蠢的人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忙碌和愚蠢——因此,荒诞喜剧电影既可以看作是一次深刻而清醒的自嘲,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在荒诞中苟活的策略;而黑色喜剧电影的喜剧性则主要源自人类所引以为傲的理性与剧中人物所遭遇的苦难的反理性之间的巨大悖反,它的深层意旨在于让我们从对灾难的哂笑中获得最后一点近似于反抗的快意——因此,黑色喜剧电影既可以看作是一次高傲而尖刻的詈骂,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保住最后尊严的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1992年由张建亚导演的《三毛从军记》应该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当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黑色喜剧电影;而近年来的《无名之辈》和《我不是药神》等也都可以更大程度上被归入黑色喜剧电影的谱系中。当然,由于荒诞喜剧电影与黑色喜剧电影在哲学观念上的同源性,上述的区分在很多情况下是相对的,在有些情况下也会有一些在二者之间不断跳跃折返的杂糅性文本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