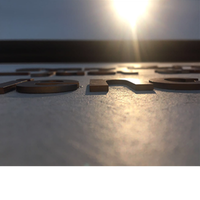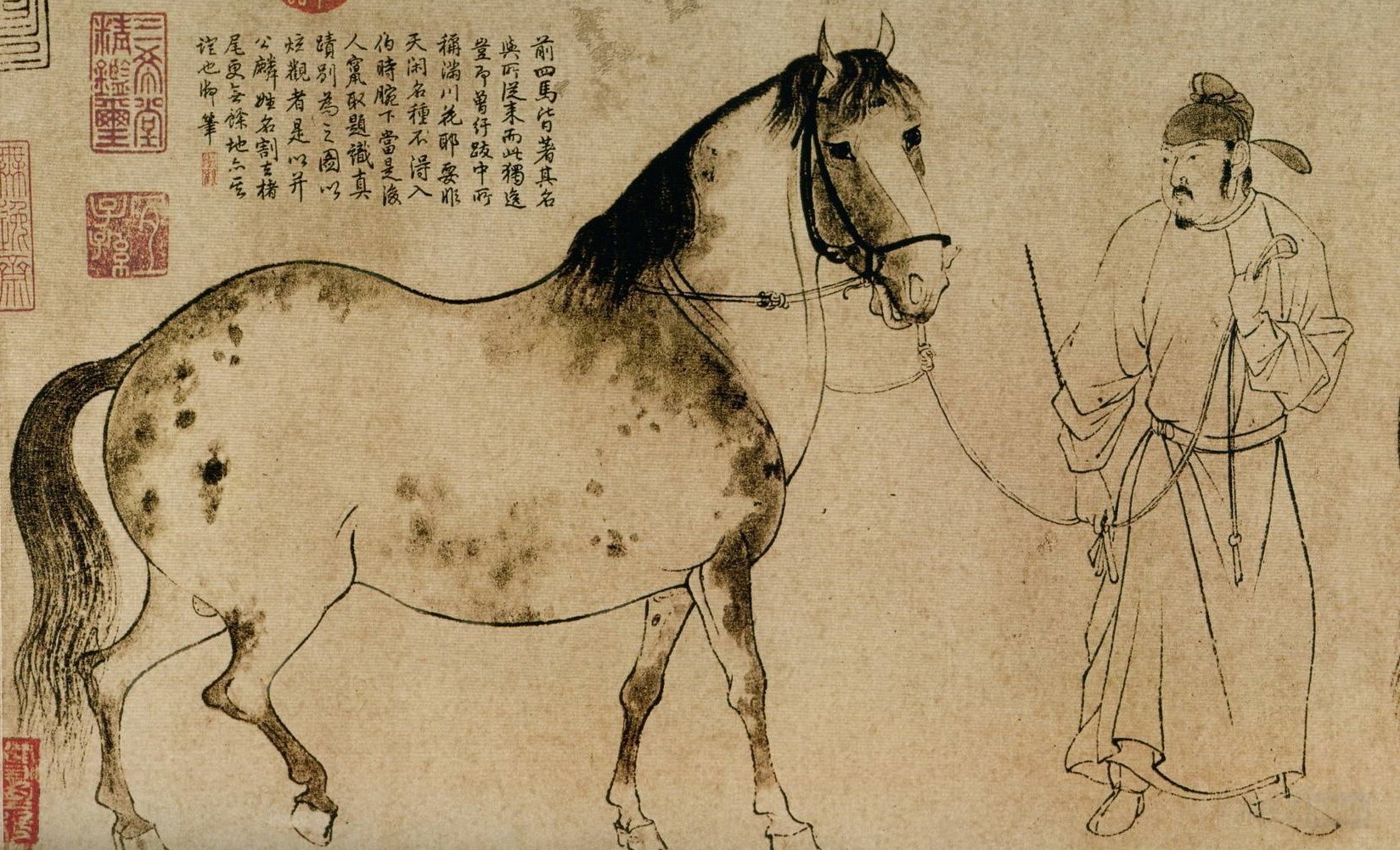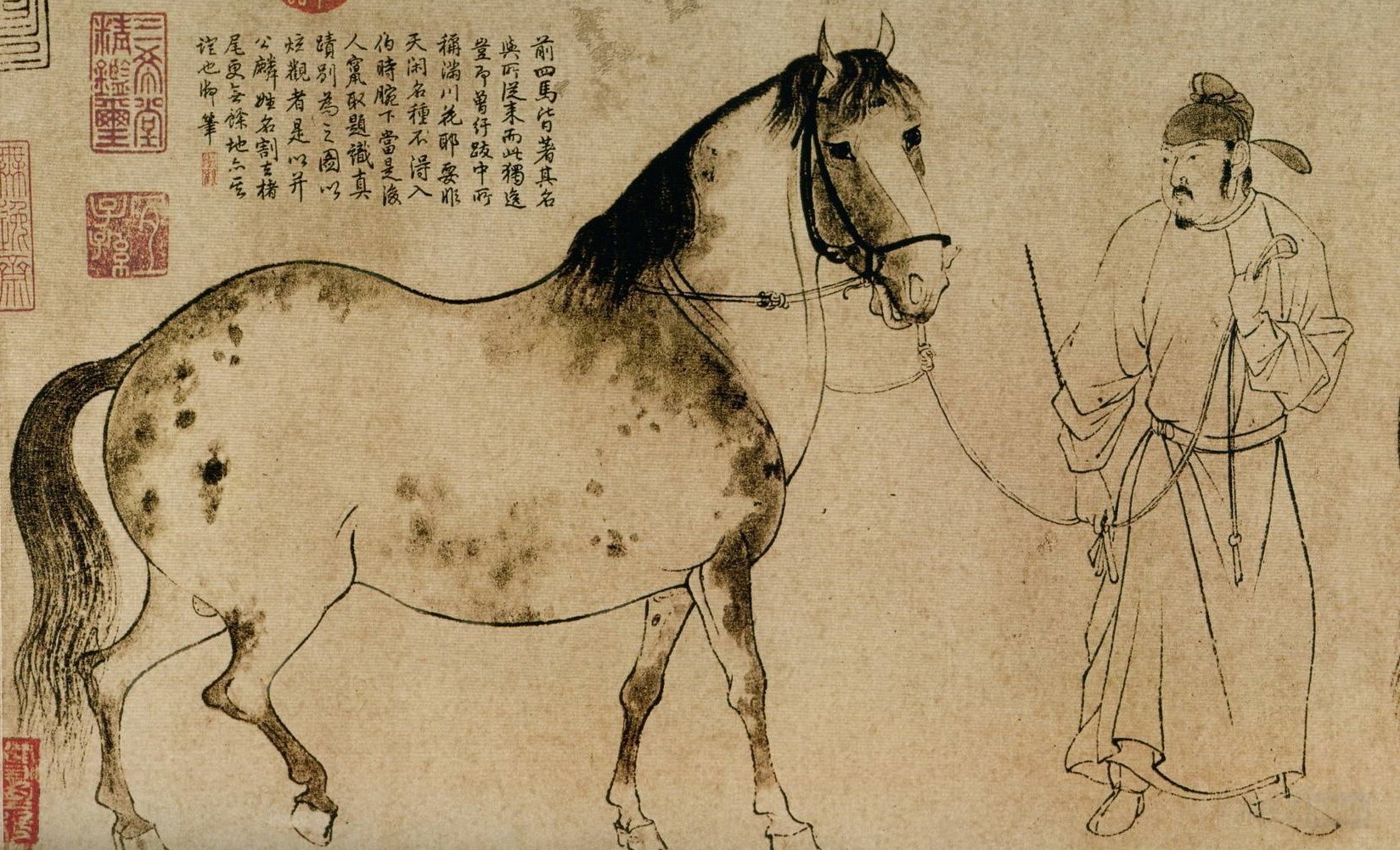
唐代宫廷斗争激烈,历任皇帝对太子防范很严,太子名为储君,实如囚徒,如履薄冰,动辄得咎。在这种情况下,东宫系统的职位,都有权职分离的倾向,实际工作往往和太子府上没什么关系。可是唐朝的东宫官制又特别完善,大多数东宫官成为地位崇高的优秩。三省事务烦剧,御史台刀光剑影,地方官员升迁坎坷,国子监和秘书省对文才要求高,相比之下,东宫就轻松多了。
杜甫中年向玄宗皇帝献文章,好不容易有个出身,吏部安排他做同州河西县尉,他推脱不去,后来托关系做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写过一首诗: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
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
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
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
单从职级上看,河西尉从九品上阶,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从八品下,确实有所区别,但这两个职位最大的差距不在品阶,而在社会地位,右卫率府属于东宫部门,清闲优越,很是“逍遥”,比起河西县尉地位低下、职事烦冗,实不可同日而语。
有的人看到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官阶低,“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认为很没价值,实际上杜甫以“献赋”得到这个职位,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东宫职权分离,杜甫根本不用去太子府上看大门,几乎是白拿薪资,所以杜甫很满意,甚至于“故山归兴尽”,再也不说归田园之类的气话了,这首诗体现的是杜甫获官后的喜悦之情,而非鄙薄之意。
东宫三太(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和东宫三少(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分别为从一品、从二品的大官,没有大功绩是做不到的,所以东宫官里,正三品的太子宾客和太子詹事,就是顶级待遇了,刘禹锡、白居易晚年都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刘禹锡被后人称为“刘宾客”,就是这么来的,他们在官场中所获得的待遇和声望,大概仅次于做过宰相的那一类人。
高适晚年进封散骑常侍,和太子宾客一样,都是正三品的职位,散骑常侍从南北朝以来就是有名的清秩,史书称“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可见当时人将高适视为达官显宦,在诗人中可称翘楚。
唐代人没有“革命工作不分大小,只是分工不同”的觉悟,只看重京官,都不愿意去地方做官,朝廷不得不出台激励措施,可是这也没什么用,不愿意去的还是不去,就算当县尉,也一定要当京畿附近的县尉。
杜甫不肯做河西县尉,高适早年授予封丘县尉,也做了没多久就辞职了,这是因为河西和封丘都不在京畿范围之内,假如是京畿地区的县尉,他们早就兴高采烈去上任了。
当然,京畿县尉不同于其他地方,一般人也出任不了,白居易考上进士之后,又中了皇帝亲自考试的制科,分到盩庢(周至)当县尉,盩庢为京兆属县,所以他很开心。他应制考的时候做模拟卷,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臣伏见国家公卿、将相之具,选于丞郎、给舍;丞郎、给舍之才,选于御史、遗补、郎官;御史、遗补、郎官之器,选于秘著,校正,畿赤簿、尉。虽未尽是,十常六七焉。”
这一段话,将唐代人心目中的好官一网打尽,这里简单解释一下:
公卿、将相不用说,指的是三品以上的大官,这是第一梯队;
丞指四品的尚书左、右丞,三省的侍郎(门下、中书侍郎后来提升到了三品),给舍指的是五品的给事中、中书舍人,这是第二梯队;
御史和遗、补,指的是御史、拾遗、补阙,郎官即郎中、员外郎,前文已经作了详细介绍,这是第三梯队;
秘著,分别指秘书省的秘书郎、著作佐郎,校、正指秘书省、东宫等系统内的校书郎和正字,都是九品的职位。畿赤簿、尉,指的是京畿地区的主薄、县尉,这是最低等级的梯队。
白居易大概没想到,他后来的进阶,基本就是按照这个路子来的,他中进士后,从校书郎开始,京畿县尉、左拾遗、郎中、中书舍人、秘书监、刑部侍郎、太子宾客,最后还升任了刑部尚书,九品到三品,一步不落,把他早年幻想的美好官阶全都做了一遍。
最后说一下翰林学士和翰林供奉,唐玄宗设置翰林供奉和翰林学士的时候,没把等级当回事,最开始两者甚至没有太大区别,他身边的供奉,包括李白、李泌在内,都没有官衔,仅仅是担任顾问性质的临时差事。
后来队伍规模越来越大,玄宗才考虑把翰林学士和供奉分开,前者成为皇帝专职秘书团队,后者以陪皇帝开心玩耍为主要任务。
按照“皇帝身边的人很重要”这一原则,翰林供奉虽然不入朝班,却拥有一些特殊的权力,最典型的就是唐顺宗时,王叔文、王伾以翰林供奉身份暴得大官,一度把持朝政,虽说情况特殊,但翰林供奉因为亲近皇帝而拥有权柄,则是不争的事实。
王叔文能够掌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掌控了翰林学士院,短短几十年间,翰林学士院就从一个临时人员群集的机构,变成足以取代外廷的中枢机关,体现的正是“离皇帝近的职位很重要”这一原则。
唐代著名诗人,绝大多数都具有官员的双重身份,在那个时代,原本就没有能脱离官场而独立生存的机会,他们终其一生,注定要在官场上奔波,喜怒哀乐与升迁贬黜捆绑为一体。明了诗人们的职位,并非要排个高低,只是为了更准确地了解他们的真实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