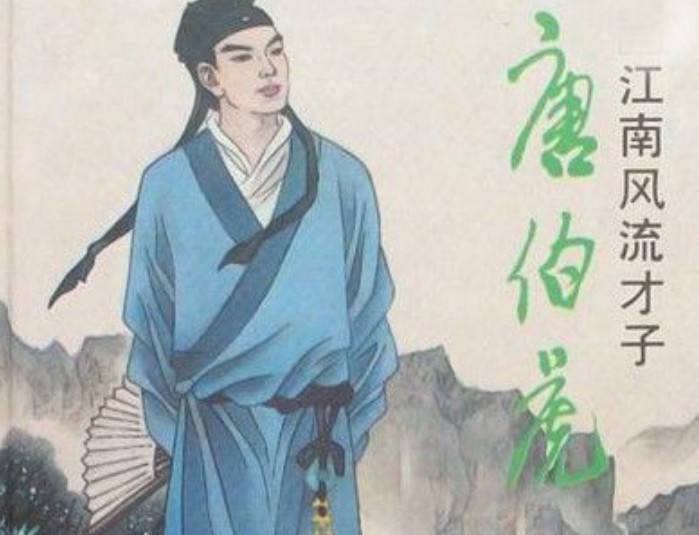徐经,明朝南直隶江阴人,其人在历史上名气平平,却在弘治年间因进京赶考,牵涉进了一桩震惊朝野的科举大案(另一涉案人是大名鼎鼎的江南才子唐伯虎)。
先说说徐经的家世,他们家在江阴是标准的世族,太祖父徐忞,因仗义疏才,救济难民,皇帝亲赐敕书,表彰为“义民“、荣耀一方。祖父徐颐,曾入京为官,出任中书舍人(在皇帝身边翻译、抄写文献等)。父亲徐元献,举人(成化十六年全省乡试第三名)。此后,徐经一脉更是出了个享誉全国、青史留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徐经是徐霞客的高祖,爷爷的爷爷)。
此案发生于明弘治12年(1499年),轰动京城,影响巨大。时至今日。民间素有徐经,唐伯虎二人科举考试舞弊的传闻,当年明月在其红遍全国的《明朝那些事儿》一书的结尾,亦提及:“据说是徐经作弊,结果拉上了唐伯虎,大家一起完蛋,进士没考上、连举人都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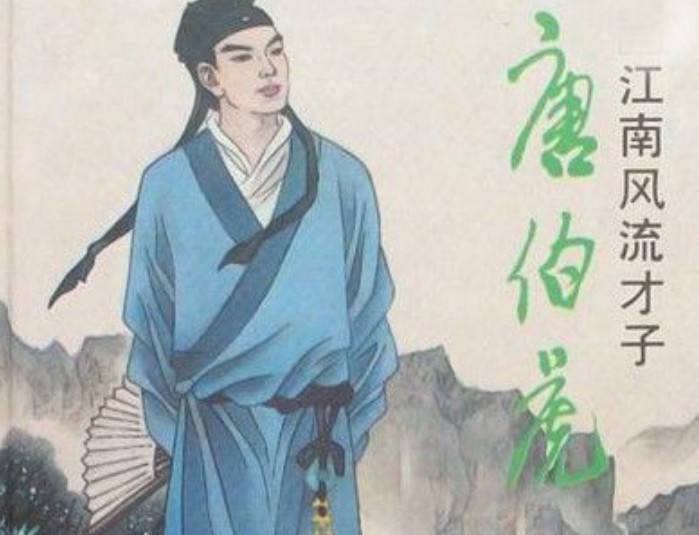
其实,坊间或当年明月,都是在以讹传讹,谣言传播久了,很多人就当真了。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今天,作为与徐经同县的江阴土著,本人要给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史实,洗刷徐经与唐伯虎的不白之冤。
当年,关于此事,明代官方编修的史书《明孝宗实录》、对此作了详实的记载:
卷一四七记录如下::(弘治十二年)二月,丙申,命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程敏政为会试考试官。(丁巳)户科给事中华昶奏:“国家求贤,以科目为重,公道所在,赖此一途。会试,臣闻士大夫公议于朝,私议于巷:翰林学士程敏政假手文场,甘心市井,士子初场未入而《论语》题已传诵于外,二场未入而表题又传诵于外,三场未入而策之第三、四问又传诵于外。江阴县举人徐经、苏州府举人唐寅等狂童孺子,天夺其魄,或先以此题骄于众,或先以此题问于人。此岂科目所宜?有盛世所宜?容臣待罪言职有此风闻,愿陛下特敕礼部场中朱卷,凡经程敏政看者,许主考大学士李东阳与五经同考官重加翻阅,公焉去取,俾天下士就试于京师者,咸知有司之公。”
译:这段话大意如下,1499年,朝廷命礼部尚书李东阳,侍郎程政敏为当年的会试主考官,户科官员(七品芝麻官,但权力较大,负责监督挑刺,相当于纪检组长)华昶对皇帝说,朝廷求取贤才,科举考试是重中之重,公平公正的最好方式,就是这个途径了,但这次会试,很多人议论纷纷,主考官程敏政泄题了,江阴县徐经,苏州府唐伯虎等几个老卵,不知死活,到处宣扬得瑟得到的试题,此等行为岂可容忍?请皇帝下旨,重新阅卷。
卷一四八:(三月)丙寅,下户科给事中华昶及举人徐经、唐寅于狱。会试事毕,大学士李东阳等奏:“日者给事中华昶劾学士程敏政私漏题目于徐经、唐寅。礼部移文臣等重加翻阅,去取其时,考校已定,按弥封号籍,二卷俱不在取中,正榜之数有同考官批语可验。臣复会同五经诸同考连日再阅,定取正榜三百卷,会外帘比号拆名。今事已竣,谨具以问章下礼部看详。尚书徐琼等以前后阅卷去取之间,及查二人朱卷,未审有弊与否。俱内帘之事,本部无从定夺,请仍移原考试官径自具奏,别百是非,以息横议。”得旨,华昶、徐经、唐寅锦衣卫执送镇抚司对问,明白以问,不许徇情。
译:三月,把举报人华昶,嫌疑人徐经唐伯虎一起关进了大牢(举报人也抓了,说明可能不实),礼部尚书李东阳对皇帝说,这个事,我们查过了,徐唐二人并不在录取名册中,是否有弊,没法判断。皇帝说,把三人送锦衣卫分别讯问。
卷一四九:四月(辛亥),下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程敏政于狱,革昶等,既系锦衣卫。镇抚司工科给事中林廷玉以尝为同考试官与知内帘事,历陈敏政出题阅卷取人可疑者六,且曰;“臣于敏政非无一日之雅,但朝廷公道所在,既知之,不敢不言。且谏官得风闻言事,昶言虽不当,不为自家计也。今所劾之官,晏然如故,而身先就狱,后若有事,谁复肯言之者?但兹事体大,势难两全,就使究竟,得实于风化可补,莫若将言官举人释而不问,敏政罢归田里。如此处之,似为包荒,但业已举行,又难中止。若曰朋比回护,颠倒是非,则圣明之世,理所必无也。”既而,给事中尚衡、监察御史王绶皆请释昶而逮敏政。徐经亦奏昶挟私诬指敏政,复屡奏自辩,且求放归。及置对镇抚司,以经、昶等狱辞多异,请取自宸断。上命三法司及锦衣卫廷鞫之。经即自言敏政尝受其金币。于是左都御史闵珪等请逮敏政,对问奏留中十余日,乃可之。
译:四月,皇帝下旨,逮捕礼部侍郎程敏政,把举报人华昶革职。锦衣卫给事中林廷玉(注:和举报人做同一种工作的)说,华昶虽然听得风闻风雨就上奏,但也不是为了个人利益,现在把他抓了,以后谁还敢说话呀(注:这段话,基本说明此案查无实据),徐经上奏,说华昶因个人恩怨诬陷程敏政,为自己辩护,要求还给自己清白,皇帝命令三法司锦衣卫当堂审讯,徐经说,程敏政拿了他的钱。
卷一五一:(六月乙丑)先是给事中华昶奏学士程敏政会试漏题,既午门前置对。敏政不服,且以昶所指二人皆不在中。列而复校,所黜可疑者十三卷,亦不尽。经阅乞,召同考试官及礼部掌号籍者面证。都御史闵珪等请会多官共治,得旨不必会官第,以公讯实以闻。复拷问徐经,辞亦自异,谓:“来京之时,慕敏政学问,以币求从学,间讲及三场题可出者;经因与唐寅拟作文字,致扬之外。会敏政主试,所出题有尝所言者,故人疑其买题,而昶遂指之,实未尝赂敏政。前俱拷治,故自诬服。”因拟敏政、经、寅各赎徒,昶等赎杖,且劾敏政临财苟得,不避嫌疑,有玷文衡,遍招物议,及昶言事不察,经、寅等汇缘求进之罪。上以招轻参重有碍,裁处命再议拟以闻。珪等以具狱上,于是命敏政致仕,昶调南京太仆寺主簿,经、寅赎罪。毕送礼部奏处,皆黜充役。
译:六月,程敏政不认罪,说徐唐二人根本不在录取名列,只能再次拷打审讯徐经,徐经说,来北京前,仰慕程敏政的才华,想套近乎才送上见面礼,求取他的赐文,前面被打的受不了,才招认了。。。
从卷一五一中可知此案的最终结论与处理结果是:
1.舞弊案查无实据,但鉴于主考官程政敏贪图钱财,不懂避嫌,污了考官的名声,招来非议(临财苟得,不避嫌疑,有玷文衡,遍招物议),故免去程敏政的官职。
2.告发人华昶没搞清楚状况,就匆忙举报(言事不察)、降职为南京太仆寺主簿(养老机构)。
3.徐经、唐伯虎两人投机取巧(汇缘求进,意指以钱财结交京城名流),贪恋名利,革去功名,废为庶人。
至此,真相大白,所谓舞弊之控,并未成立。
徐经玄孙徐霞客、满腹文才、不求取功名,却纵情于山水之间,不得不说,多少受高祖的影响。不过话说回来,没有这场风波,徐霞客大概也成不了古代最牛逼的旅行家、地理学家。
历史、就是这么地阴差阳错。他毕其一生写成的《徐霞客游记》,详细记录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被赞誉为十七世纪最伟大的地理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