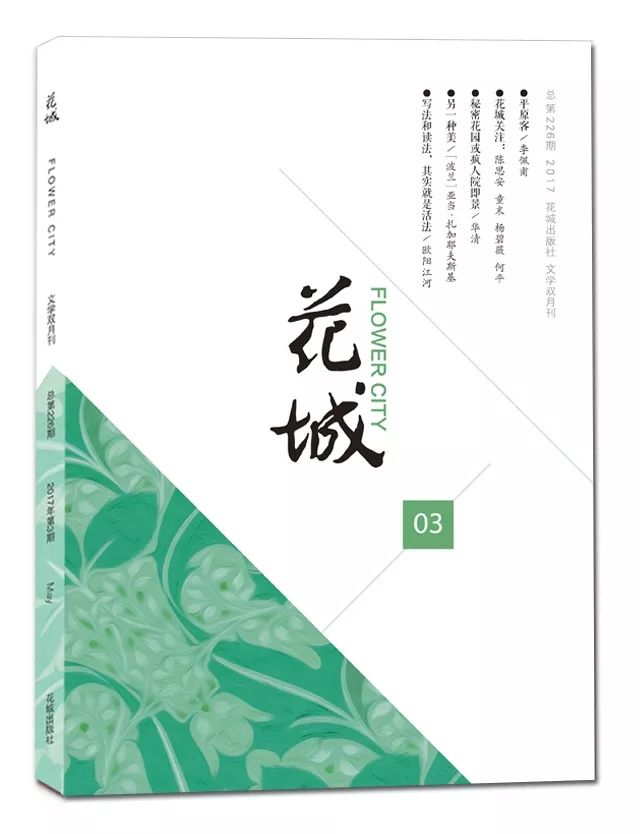李以亮《另一种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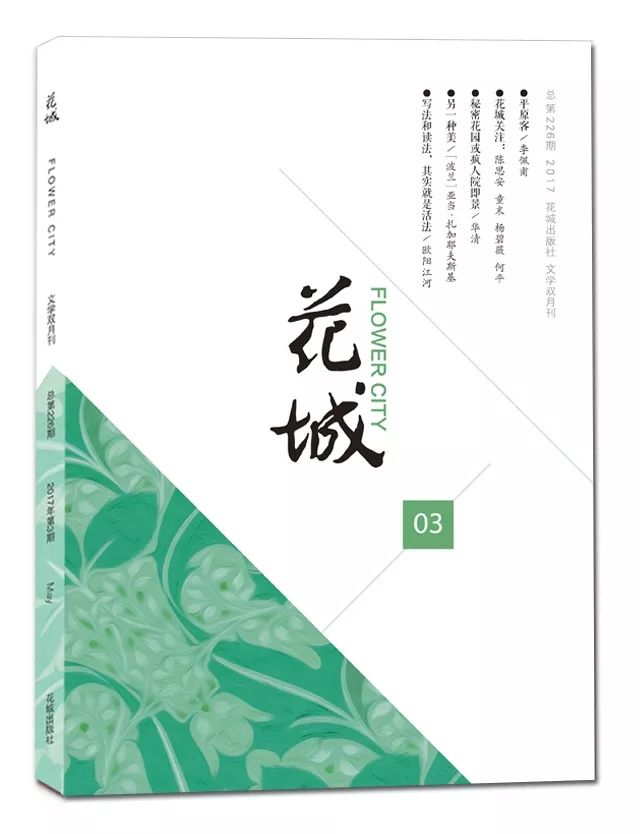
刊载于《花城》2017年第3期
美与救赎,与他人同在。“我们只能在另一种美里 / 找到慰藉,在别人的 / 音乐,别人的诗中。”
本文节选自“蓝色东欧”第五辑作品,波兰著名作家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的散文随笔集。作者回忆了思想执拗的亲戚,有点古怪的教授们,激情勃发的艺术家朋友,以及他神交已久的贡布罗维奇等诗人和哲学家。这些深陷在时代洪流中的人,或坚毅、或沉郁、或孤独、或平静,各有独特的精神气质。作者的描写尤为哀婉动人,读者也可从中得到作者本人作为一个年轻诗人的肖像——对诗歌和其他艺术之伟大性的崇拜者,对历史和公共领域的反思者。
利沃夫与格利维策,格利维策与克拉科夫,巴黎与休斯敦……《另一种美》以作者生活过的这些城市作为背景,抛开了具体的时间线,让心灵和感觉与历史和现实进行对话。
李以亮,诗人、译者。著有《逆行》,译有《希克梅特诗选》《无止境:扎加耶夫斯基诗选》《捍卫热情》《另一种美》《两座城市》。曾获宇龙诗歌奖、《诗探索》诗歌翻译奖、《西部》翻译奖等。
提名作品选读
我不能写下关于克拉科夫的历史,尽管它的人民和想法、树和墙、懦弱和勇气、自由和雨水都与我息息相关。还有思想,它们与我们的身体紧紧联系着,并在不知不觉之间改变我们。时代精神雕刻着我们的思想、嘲弄着我们的梦。我着迷于各种各样的墙。我们居住其中的空间并不是中立的,它塑形了我们的存在。风景和景观进入我们内心最深处,不仅在我们的视网膜上留下痕迹,也影响了我们人格最深的层面。那些天空灰蒙蒙的时刻,在一阵倾盆大雨过后,一无遮蔽地呈现于我们面前;一场安静的大雪过后,也是如此。通过我们的感觉和身体,思想也许会加强雪的力量。它们附着在房屋的墙上。然后,房子和身体、感觉和思想一起消失。但是,我不能写下关于克拉科夫的历史,我只能试着再现一些时刻、地方和事件,一些我喜欢和崇敬的人,一些我鄙视的人。
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我愿意有意识地、严肃地设定属于文学的历史记录功能。我不想学习现代历史学家树立的榜样,总的来说,他们是些没有情感温度的冷鱼,一生都消耗在被征服的档案里,然后写一些缺乏同情心、丑陋、木头似的、官僚语言的东西,其中,毫无诗歌的位置,语言单调如木虱、琐碎如日报。我想要重返早期的传统,也许就是希腊人的传统,回到那个历史学家-诗人的理想标准,如同一个亲历者,见识和经历过他所描写的一切,或者,懂得利用生动的口头历史的传统,利用家族或部落的传统,不怕承担义务和感情,而同时,他还懂得注重故事的真实性。事实上,我们正在见证一种文学的复兴,它正是服务于上述那样一个目的,但是,却几乎没有人注意这样一个问题:认真倾听古典文学的传统、作家们的日记、回忆录、诗人的自传,那种出于纯粹的个人立场的历史性的文学写作,而不是如现在这样,采取一个助教的立场、一个时髦方法论的奴隶的立场、一个国家雇佣人员的立场——随时准备谄媚权力,取悦巴黎出产的流行的认识论。举几个例子?随便说几个:埃德温·缪尔的自传、切斯瓦夫·米沃什、约瑟夫·布罗茨基以及其他诗人的写作,休伯特·巴特勒、尼古拉·乔洛蒙蒂的随笔,约瑟夫·恰普斯基、阿尔贝·加缪的笔记……兹比格涅夫·赫伯特、耶日·斯德姆坡夫斯基、患有肺结核的博莱斯瓦夫·米辛斯基所写的札记。这些人,一律都拒绝说谎,他们急切地想要发现真相,面对诗歌和恐怖(我们这个世界的两极)从不退缩,因为诗歌确乎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存在于某些事件、存在于那些罕见的时刻。同时,世界从来也不缺少恐怖。
那个认为可以自编祈祷词、而并不总是需要一本祈祷书的男孩,随着时间流逝也会懂得:教堂不是唯一可能发现神圣的地方。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对诗歌的攻击,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其程度还不算是最激烈的。贡布罗维奇的随笔(《反对诗歌》),他的指控,更像是遵循着家庭内部发生口角的路子:这位“散文里的诗人”,主要认为他的抒情兄弟在诗里压缩了太多东西、给他们的甜点增加了太多的糖分。
贡布罗维奇的观点,主要针对的是诗歌的内容,而非它的本质。是的,有些时期,诗歌似乎提供了过于丰富的可食之物(“太甜”)。那样的时刻,我们准备接受和理解诗之激情的时刻却很少出现。但是,在绘画和音乐方面,情况也是一样;只有电影在日常的基础上,通过释放我们平常的冷漠而一直吸引着我们。
英国清教徒史蒂文斯·葛森在他的小册子《罪恶的学校》里表现得要激烈、激愤和原始得多。葛森认为诗人败坏读者大众的道德,而且,事实上不比走钢丝的演员和流浪艺人更好(而且我们都知道,我们从这些人那里期待获得的是什么!)。葛森的攻击——发生在十六世纪——肯定已经被遗忘了,如果不是因为它促使另一位更有才华的作者起来反驳这种清教徒的指控。
这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当然就是菲利普·锡德尼爵士。直到过早离世之前,他同时写作诗歌和散文,而且他也是出类拔萃的诗歌捍卫者之一:他的《为诗一辩》是英国文学的经典。锡德尼为诗歌辩护、为富于灵感的诗歌辩护——灵感是来自上帝的礼物——诗歌出色的成就,使历史和哲学二者黯然失色。锡德尼的论文在其身后于一五九五年出版,捍卫了想象,并且强调了它乃是服务于善,而非恶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