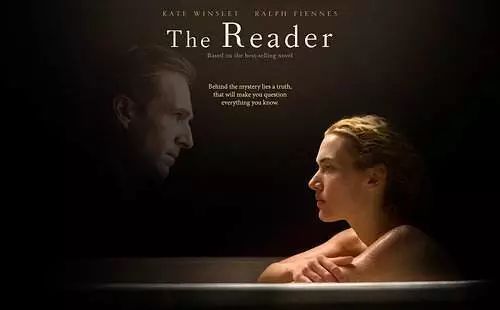○
民智推荐
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思考要达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而涉及恶的瞬间,那里什么也没有,带来思考的挫折,这就是“恶的平庸”。
随着信息获取更加便捷、透明,人们越发关注恶性社会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今年上半年一部以随机杀人为主题的台湾电视剧因为对加害者动机和境遇的现实刻画而获得超高收视率。
不得不承认,我们对“恶”背后的原因充满了好奇。但是在有些恶的背后,你甚至找不到任何思考的痕迹。
面对这样的恶,即便是最具智慧的政治哲学家或法学家可能也会表现出无力感。《朗读者》这部电影即是依托于二战后的余波,将这样“平庸的恶”呈现在人们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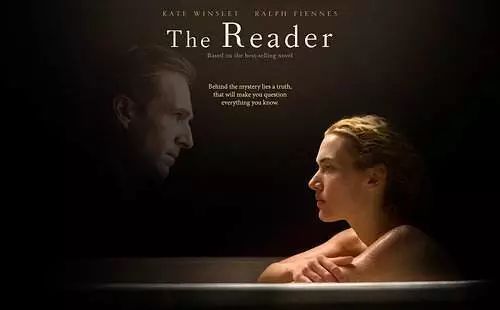
(《朗读者》(The reader)是一部2008年斯蒂芬·达尔德里导演的剧情片,由David Hare改编自1995年本哈德·施林克所创作的同名小说。该影片曾获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以及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多项提名。)
电影简介
在1958年的德国,一个15岁的少年迈克·伯格在街上病倒,被一个美丽的女子汉娜救起,当病愈之后他决定亲自去跟汉娜道谢,这样的相逢为他们两人牵起了一辈子难以割舍的情缘。
当迈克与汉娜两人再次见面之后,对于彼此的吸引毫不设防,汉娜喜欢迈克朗读各式各样的世界名著给她听,迈克对于汉娜的神秘与成熟的魅力难以自拔。但是有一天汉娜却突然不告而别,留下了迈克满腹的疑惑和心碎。
多年后,迈克成为法律系高材生,当他跟随着教授到纳粹战犯的法庭旁听时,却赫然发现被告竟然就是许久不见的汉娜,在抽丝剥茧的审判中逐渐将汉娜的过去呈现在迈克尔的眼前,也深深牵动着迈克的心,同时也撼动了两人的命运。
人物剖析:汉娜之恶有多平庸?
巧合的是,电影中的女主角与提出“恶的平庸性”的政治理论家都叫汉娜,而且恶之平庸也很好地展现在了在这位女主角的身上。
1
无思性
女主角汉娜虽然年近四十仍不识字,但她喜欢聆听迈克为她朗读各种文学作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并不愚蠢无知,甚至希望离文化世界更近一点。
同时,她也十分骄傲,宁愿被判刑更重,也不愿透露自己不识字的秘密。
然而她却是集中营雇佣的一名女看守,纳粹丑陋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她的任务就是拣选女囚犯,然后将她们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处理”。她从未思考过,更没有挑战过这一命令的合理性。即使在法庭上被质问,她也理直气壮地回应:“我只是在完成我的工作。”
在电影中与汉娜形成强烈反差的就是男主角迈克。他成长于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有强烈的向内的道德情感,且习惯于自我反思,是坚持忏悔的隐形基督教徒,迈克的这一形象更凸显了汉娜的“无思性”。
2
道德认知障碍
社会环境对人的认知的影响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
女主角汉娜是一个生活在二战时期的德国的普通人,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她不可能会怀疑元首希特勒。
也正是如此,作为一名合格的守门人,在发生大火时也不可能开门,因为那样囚犯可能会逃跑。不让囚犯逃跑就是汉娜奉为圭臬的规则,在她心中,这一规则的分量远远高于我们所推崇的人性和道德。
迈克永远不可能理解汉娜,因为他们的分歧源自二者价值观的差异,这一价值观是被不同的社会环境塑造起来的。
而且汉娜人性中的异化似乎也不能再通过情感教育和道德教化来矫正,因为即使在迈克为她朗读了诸如《奥德赛》、《一个带小狗的女人》这些充满人性的文学作品后,她仍未察觉自己“遵守规则”的行为实际上违背了人们的道德标准。
就是在这样的认知障碍下,她自以为合理地扼杀了集中营的几十条生命。
理论 vs. 现实:逃不开的现代性问题
国内学者经常将汉娜·阿伦特的思想“the banality of evil”译为“平庸的恶”,但实际上它的本意是“恶的平庸性”。
阿伦特并非说一个平庸的人就会产生恶,而是说明——有些“恶”的背后可能没有像复仇、堕落这样不平凡的动因,而是无思想的、自认为理所当然的。
从西方思想传统的角度,“恶的平庸性”是非常有开创性的概念,它与主流伦理学框架下的“恶”,以及基督宗教语境下的“罪”都是明显不同的。
理论源于现实,孕育出这一理论的现实背景正是电影中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阿道夫·艾希曼是第三帝国党卫军中校,负责把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兵站指挥官,对600万犹太人被屠杀负有重要责任。1961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在审判席上,他始终强调“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这句话引起了哲学家阿伦特的注意。
后来,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首次提出“the banality of evil”这一观点。她认为,平庸的恶是无意识的犯罪,无论犯下的罪行如何穷凶极恶,罪犯本身却并不凶残,也不恶毒。
“变得平庸的是不能够思考,不能思考正是艾希曼犯下的罪的名字。”就像电影中男主角的教授所说“社会赖法律以运行,而非依靠道德来维系”,这恰恰是绝大多数战犯所谓的“我仅奉命行事”的学术说辞。
“恶的平庸性”这一说法本身已经点名了使恶产生的原因所在,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杜绝它,这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也是当前社会需要警惕的问题。
催生“恶的平庸性”的元凶正是“不思考”,在后真相时代,键盘侠已经倾向于不经思考地无脑跟风,这难道不是“恶的平庸性”的缩影吗?
如何破解愈演愈烈的“恶的平庸性”呢?
我们或许还是要从阿伦特给出的解决方案中获得灵感:
1
思考基础上的判断
我们也许会自然地认为,由于“恶的平庸性”是因为不思考而产生的,那么只需要学会思考和质疑就能有效避免这类恶。
但阿伦特认为仅靠“思”是完全不够的,必须加上判断才更具有效性。
因为无论在什么年代,思考都是一个少数群体才会专门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做的事情,而“判断”比“思”更具有人们之间的“一般性”,并不专属于某一种特殊的群体或职业。
就像西塞罗所说:“在博学的和无知的人之间,在判断之中的差异是多么的小,虽然在制作中有最大的差异”。艾希曼的错误正在于对自己的行径不做判断。
2
人的行动才能建立和维系公共空间
承上所述,由于判断只有在阿伦特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中才会出现,无论是在场参与者的判断还是事后旁观者或,历史学家的判断都是如此,只有在这样的场域中,为判断所必需的“扩大化的心智”才可以运作。
而公共空间的建立和维系离不开人们的行动。阿伦特也强调行动,只有行动才能形成对周围世界的健全判断。因此,深思熟虑之后的行动才是消除“恶的平庸性”的途径。
但遗憾的是,阿伦特在《人的境况》的后半部分提到,在现代“世界沉沦”的条件下,“本真的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她并没有提出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就像在电影中主角最后的结局:女主角汉娜仍未真正因为道德情感而忏悔,男主角也无法真正理解她的内心世界。
那么“恶的平庸性”如何破解?这一涉及社会心理学、法律的内在道德等领域的命题仍留待我们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