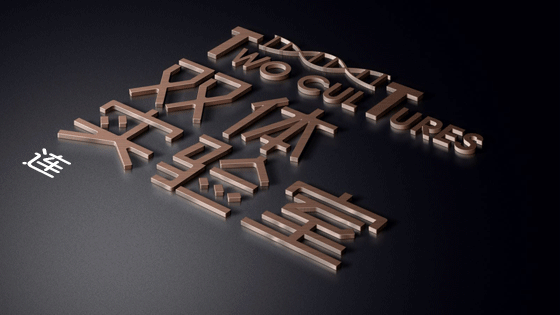作者:刘青峰
在《“大一统”与科技发展》一文中,我留下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伟大的发明在中国首先出现,但以后却又停滞了。其实,这与儒家的“伦理中心主义”有密切关系。例如,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直接影响科学理论内容。它使科学理论摆脱不了稚气。即便是已经踩着近代科学门槛的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仍然在宣讲什么“夫声气风力实传心光,受命如响,神不可测”。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人们很难把自然界当作科学的客观对象来研究。理气之争与善恶相随,天地日月之论与君臣等级相伴,世界是万物交感的世界,学问家的任务在于建立起包括自然现象在内的给出伦理说明的理论体系。
更为重要是,“伦理中心主义”造成了科学的政治化和理论的技术化倾向。限于篇幅,这篇短文将主要从“伦理中心主义”及其造成的科学政治化和技术化,来探讨古代中国科技走向停滞之谜。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祖冲之(429—500),他算得圆周率为:3.1415926<π<3.1415927,并以355/113为圆周“密率”,比德国的奥托取得这个值早了1100多年。他精于历法,创《大明历》引进虞喜发现的岁差现象,定出交点月日数为27.21223日,同现代我们测定的相比只差十万分之一日。他为了《大明历》的实施,曾和朝廷宠臣戴法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论战中,祖冲之往往据理力争,驳得戴法兴无言以对。这些是人们经常谈论的。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祖冲之也犯了一些错误。辩论中戴法兴有些看法是正确的。如戴法兴批评《大明历》把上元积年的算法搞得愈加复杂庞大了。上元积年本是一个虚设的数。在三国魏时杨伟立《景初历》(公元237年),和南朝何承天制《元嘉历》(公元443年)时,已经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来处理上元积年了。但祖冲之并没有用这些先进的经验,反而认为戴法兴的批评没有道理。另外,戴法兴在辩论中为了维护十九年七闰的说法,提出“日有缓急”,也就是说太阳的运动不是匀速的。祖冲之把这种看法斥之为:“未见其证”。这样,又过了一百多年到6世纪时,北齐天文学家张子信根据长期观察,发现太阳的运动在冬至点前后较快,在夏至前后较慢。后来隋代刘焯又发挥了这一思想。本来,在两个科学家争论时,各有对错并不是什么奇怪现象,但在中国古代科学辩论常常和政治斗争直接相关。如果科学辩论被看作政治斗争,那么一派的胜利就表示另一派观点全部被否决,甚至遗忘。从来没有一切都对的科学家,戴法兴压制祖冲之是不利于科学进步的;后来祖冲之胜利了,戴法兴提出的太阳视运动是不均匀的这一重要天文发现也被抛弃了。这样,科学理论又怎么进步呢?
中国古代,科学理论特别是天文、数学和政治密切结合,它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殊产物。天文历法和大一统王朝直接相关。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意识形态结构与政治结构一体化的国家,是由儒生组成国家机器的。科学理论一旦纳入儒家思想方法的框架之中,科学家一旦成为科学官僚,那么科学必然会官方化,与政治密不可分。
汉武帝时的大儒家董仲舒曾创立了“三统之说”。所谓三统,就是夏代为黑统,商代为白统,周为赤统,三统依次循环,每换一统就更换一个朝代。这本来是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国家学说,和历法关系不大。但是,到西汉末期世胄出身的大科学家刘歆却把三统说巧妙地引进历法,制定了《三统历》。我们姑且不论《三统历》在科学史上的地位,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天文历法和政治统治的关系。在《三统历》前的《太初历》中,过三个1539年之后,朔和冬至又回到同一个甲子日。于是,刘歆就把这1539年的周期称为“一统”,三个1539就是三统。他说:“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 这就为王莽篡位获得“天命”作了舆论准备,刘歆当上了王莽的国师。
正因为如此,像天文历法这样被国家上层官僚机构垄断的官方学科,必然与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最典型的例子是隋代关于历法的一场斗争。隋文帝杨坚称帝后,当年为他相面说他有帝王之运的道士张宾,便成为宠信。还有个叫刘晖的天文学家因为阿谀逢迎张宾也当上了太史令。张宾在南朝何承天的《元嘉历》的基础上,稍加修改搞了个《开皇历》。当时有两个天文学家刘孝孙和刘焯上书指出《开皇历》不够科学。主要是说这个历法不懂岁差,也不会算定朔。公元5世纪时,祖冲之就已把这一科学成果引入历法创《大明历》了。《开皇历》实则是个退步。但张宾和刘晖就给刘孝孙扣了顶“非毁天历,率意迂怪”的政治帽子,又骂刘焯“妄相扶证,惑乱时人”,接着又找了个碴子,把二刘赶出京城。
刘孝孙好不容易熬到张宾死了,再次上书,奏章落在那个还在任上的刘晖手中。刘晖扣压了奏章,又把刘孝孙骗至京城,把他搁在司天监中“累年不调,寓宿观台”。刘孝孙苦于自己的意见不能上达,一气之下用车子推了口棺材,抱着他的历书在皇宫门前大哭。这下惊动了隋文帝。于是皇帝命人评定历法的优劣。结果,刘孝孙取胜。刘孝孙多年的积愤爆发了,他没有考虑让自己的历法怎样实施,而是要求处死刘晖。因这个要求冒犯龙颜而未获准。不久,刘孝孙就死了。
刘孝孙在司天监时有个同事叫张胄玄,在皇上评定各种历法时他支持过刘孝孙。但科学不过是他向上爬的敲门砖。刘孝孙死后,他占其遗稿,又投靠隋文帝的亲信大臣,伪造天象吹捧杨坚,得到杨坚的赏识。他又同袁充勾结,一齐排挤隋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刘焯。因为刘焯揭露过张胄玄抄袭刘孝孙的历法。刘焯在公元600年撰成了中国天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皇极历》。这个历法的计算在数学史上也很重要,他给出了推算日、月、五星行度的内插公式,这是个二次函数的计算。深受隋文帝、炀帝宠信的张、袁二人一直压制刘焯。刘焯终于在公元608年抱恨而终。
在中国天文历法史上,每一次改革都要做出极大的努力,改革的阻力不仅仅是旧历法的保守,更多的是政治阻力。因为天文历法乃是和皇室权威联系在一起的。有时为了一点改革,天文学家不得不耍花招掩人耳目。南宋天文学家杨忠辅在制定历法时丢掉了“上元积年”这个包袱。他制定的《统天历》(公元1199年)把回归年长度定为365.2425,这和公元1582年以后通行至今的《格里高利历》完全一样,但是,杨忠辅害怕守旧派的攻击,他公布历法时仍虚立了一个上元积年。这种改革仍逃不脱守旧派的眼睛。历法公布4年后,守旧派抓住杨忠辅推测日食的时间比实际天象早了一个半时辰,而罢了他的官。本来,天文机构推测日食不够准确的事常有,但因此而罢官的则不多见。后来有个大理评事鲍瀚之则明确地骂《统天历》是“气朔五星,皆立虚加、虚减之数”,这种历法“乃民间小历,非朝廷颁正朔、授民时之书也”。
这样,在两千多年历史中,历法并不总是越改越准确的。进两步退一步,就很不错了。比如公元前104年制定的《太初历》是中国天文史上影响很大的历法,比以前的历法有很大进步,但在定回归年日和朔望月日上,它却比以前的《四分历》退步了。天文学一旦和官僚政治连在一起,它进步的速度就可想而知了!
纵观两千年历史,天文历算的政治化是愈演愈烈的,官方色彩越来越浓!相传,中国早在周代就发现了勾股定理:“故折矩以为句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据传是一个叫商高的贤大夫发现这条定理,盖天说也是他提出来的。从秦汉中国统一后,第一个和历法有关的人就是位至宰相、功以封侯的大官僚张苍。宋太宗在978年下令“召天下伎术有能明天文者试隶司天台,匿不以闻者,罪论死”。第二年,各州就送了一批天文术士进京。国家通过考试选了一些人进司天台,其余的人则黥配海岛。科学家不是官僚,就是罪犯,没有中间出路。这样,自然民间的天文仪器制造能手就很稀少了。到南宋,已找不到这样的人。当时曾想造浑仪,遍访找不到人。后来找到大科学家苏颂的儿子,又找来苏颂写的《新仪象法要》,但是他连看都看不懂。最后好不容易找来一架金人劫余的浑仪模型,才勉强照着拼凑了一架。
明以前,只禁止民间私习天文,而未禁止私习历法。明以后,控制更严了。明代有个叫沈德符的人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国初学天文有厉禁;司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这就造成了民间很少有人学习和继承这一学问。所以到孝宗时,因官僚机构中的管天文的官员们也不会推算历法,国家只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学者以备选”,结果是“卒无应者”。也不知是不敢应召还是真没有人懂了。
上面我们举的是数学和天文学的例子,其他学科如何呢?我们不要忘记,在数学和天文学中原始科学结构较容易产生和发展成长。在中国历史上,其他学科的政治化倾向虽没有天文学、数学严重,但儒家文化政治结构又给它们带来另一个特点,这就是:技术化倾向。
中国古代一方面是技术发达,另一方面儒家理论模式的经验和直观特点,使得中国古代科学理论中关于技术经验的总结很丰富。特别是在宋朝的技术高峰之后,经元至明,到了对中国古代技术进行全面总结的时期,《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就是在医药、农、工三大领域中最高水平的总结。据统计,主要是记录、总结技术经验的著述在历代理论成果积分中多占20%左右。
技术总结丰富本是好事,但科学理论结构具有过分技术化倾向时,就成问题了。
中国古代即使在纯理论研究中,技术化倾向也很明显。儒家除使对自然界的认识为伦理学说服务之外,其积极入世的现实主义精神又使它并不绝对排斥某些为现实生活服务的技术,这两点就造成了理论的技术化倾向,而不重视理论体系的自我完善。于是乎,天文学附属于历法,数学偏重于解题和运算技巧,生物学知识几乎完全存在于农学与医学之中。历法经常随着需要而修改,但天文学理论几乎是停滞的。盖天、宣夜、浑天三学说两千年来发展迟缓。数学的发展主要是运算技巧越来越高超。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数学没有理论,而是说这种理论与计算技术不可分割,没有形成严密的结构体系和简明的表达方法。同样,植物学分类基本上囿于实用的本草学范围。显然,中国古代科学理论的这种技术倾向,使科学理论难以得到相对独立发展的机会。
本文改写自《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