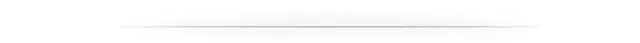民智国际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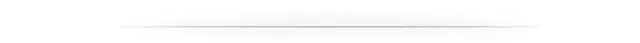
○
民智风报
战争观念是一种采取集体暴力手段的政治斗争观念,它的变迁需要放入浩瀚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去细细考察。
导语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尤其是军事力量的迅猛增长,“中国威胁论”的论调甚嚣尘上,国际格局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从美国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提出,到如今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部署,西太平洋地区的局势愈发紧张,中美关系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而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更为中美关系的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如今,美国保守派接连粉墨登场,对华态度日益强硬,中美之间难道必有一战吗?
“中国威胁论”
壹
什么是战争?
出于对现实形势的考量,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是战争。
有人认为,战争就是杀戮,就是毁灭,就是人类文明的倒退。
的确,这些都可以用来形容战争,但它们都只是战争的一种表现形式。
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对战争做出这样的界定:战争是迫使对方服从我方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需要实现某种政治目的,其本质仍然是政治斗争。
而战争观念,即是一种采取集体暴力手段的政治斗争观念,它的变迁,需要放入浩瀚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去细细考察。
贰
国家观与战争观
战争是政治共同体之间发生的集体暴力行为,而这种政治共同体,在人类历史上主要表现为国家。
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爆发的战争,绝不是个体间受激情支配的搏斗所能类比的,人类的战争形态与战争观念,是随国家观的变化而变化的。
西方战争观念的嬗变
从城邦国家到民族国家
城邦国家是西方最早的国家形态。
人从属于城邦,公共利益与公共生活是人生的价值追求,实现城邦的“善业”即是人之为人的最大意义。
爱国主义被镌刻在公民道德中,保卫国家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义务。
在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中,具有公民身份的人才能成为真正可靠的战士,因此城邦间的战争,就是不同城邦公民间的战争。
无论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亚历山大帝国,还是环抱地中海的罗马,它们的起源都是小小的城邦。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声势显赫的罗马都可以被视作以罗马为核心的城邦联盟及其殖民争霸过程中所夺取土地而组成的庞大政治共同体,公民兵是捍卫罗马的军事支柱。
直到帝国后期,兵制崩坏,蛮族雇佣兵才逐渐取代公民兵成为罗马军队的主体,而这时也离罗马灭亡不远了。
中世纪是宗教统治的时代,中世纪西方的政治结构呈现出世俗政权与宗教权力并立的二元权力格局。
军事形态由政治形态决定,同样受到世俗政权和宗教的双重影响。
一方面,封建领主间往往以继承权等理由发起争夺领地的战争,英法百年战争的爆发是为一例。
另一方面,在教会的巨大影响下,基督教世界能够暂时搁置争端,发起针对异教徒和异端的战争,十字军东征最为典型。
封建制度下争夺采邑的战争观念随着绝对君主制的逐渐确立转变为国王之间的争霸战争,但近代宗教改革引发的宗教战争却将战争形态推向愈发残酷的境地。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民族主义因民族国家的建立而生。
法国大革命将法兰西民族主义推向高潮,民族主义热情动员起来的法国军队士气高昂,连连击败君主制国家征募而来的干涉军。
当拿破仑发起征服欧洲的战争,民族主义思潮也随拿破仑的大军传播至全欧洲。
高涨的民族主义武装下的平民,天生就是对敌对国家怀有刻骨仇恨的战士,各个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被无限放大。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受民族主义浸染的欧洲各国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战争浩劫,以一代欧洲青年的生命为代价,证明了民族主义战争的毁灭性。
中国的天下观
”内与外“的战争
中国作为唯一延续至今的古文明,其社会历史具有高度的延续性和继承性。
受限于地理条件,古代东西方文明的沟通是相当有限的,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很小,因而中国形成了迥异于西方的独特文明形态。
战争观念作为文明的一种衍生物,自然带有文明自身的特点。
与罗马灭亡后便四分五裂的欧洲不同,自秦以来,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几乎每次内乱都能够迅速重归统一。
在古代史上,中国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建立了稳定而有序的“朝贡体系”。
中国就是文明的化身,而在中国统辖范围之外的,皆为“蛮夷”。
因此,中华文明便是“天下”,在天下观的基础上,将世界分为了中华文明的“内”与蛮夷的“外”。
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大多是“文明”与“野蛮”、内与外的战争。
将军白发征夫泪
中国的内外观念如此根深蒂固,从秦汉北击匈奴,到清代马嘎尔尼来华,中国一直视“外人“为蛮夷,以至于近代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中,”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仍然保有这种内与外的战争观念。
当然,“天下观”并不能与现代民族国家很好地融合,近代中国的转型同样需要民族主义的塑造。
因此,当中华民族真正的民族国家建立,民族主义强大的军事动员能力以及对爱国情怀的激发令中国军队的面貌焕然一新。
近代以来被世界嘲弄的”东亚病夫“在朝鲜战场硬生生抵御住联合国军摧枯拉朽的攻击,保卫了新生的共和国。
当今的国际形势依然是丛林法则支配下的无政府状态,我们需要一定的民族主义来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保卫国家不受到他国侵犯。
但民族主义是一种需要节制的情感,需要在理性的控制之下,而不能任由其生长泛滥。
叁
社会生产力与战争观
生产力的进步是战争潜力的倍增器。
我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技术进步直接推动者战争形态的改变,战争观念也随之变化。
汉代陈汤有言:“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
汉王朝对周边国家社会生产力和技术的领先优势使周边小国对汉忌惮不已,不敢妄启战端。
而古罗马凭借在抛石器、弩炮等先进的工程技术装备,实现了对周边蛮族的战术优势,加快了罗马扩张的步伐。
除此之外,发达的社会经济也为长城、罗马大道等军事工程的修筑提供了必要条件,进一步拉大了古代文明之间的战争潜力差距。
西班牙废弃的战争壁垒
当然,在生产力水平不够发达的古代社会,经济差距和技术代差尚可以凭人力拉近。
但是工业革命以来,机器化大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不但增强了战争的烈度,还扩大了战争的规模。
技术水平高、杀伤性能强的现代军事装备可以在标准化的工厂内以极短的时间批量生产。
社会经济和医疗卫生水平发展带来的人口增长为军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
近代之前,战争受限于社会经济条件,常常表现为较为克制的“有限战争”。
敌方的人口、物资可以在胜利后转化为我方的生产力量,因此战争的破化程度也是有限的。
但是,现代战争往往表现为你死我亡的“全面战争”,这既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又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
现代战争最后往往就成了工业潜力的比拼,二战中的苏德双方和太平洋战场上的美日双方将工业生产能力对战争的决定性作用表现得淋漓尽致。
肆
战争是必然的吗?
近代以来,屡次爆发的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惨不堪言之战祸”,为何战争依然会频繁爆发?
亨廷顿说,这是“文明的冲突”。
艾利森认为,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间无法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引发了战争。
这两种时下最为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人类历史上爆发的一次次战争。
就像马克·吐温所说的那样:历史本身永远不会重演,但却常常惊人的相似。
“修昔底德陷阱”
01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从而引发不可避免的战争。
在近期的畅销书《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中,作者艾利森列举出自15世纪后期以来,西方近现代历史上的16个修昔底德陷阱案例。
“修昔底德陷阱”的16个案例
纵观历史我们可知,从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到20世纪末冷战结束,修昔底德陷阱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间的竞争屡见不鲜。
然而我们从艾利森总结的16个案例中也可以看到,尽管多数竞争最终以战争为结果,但新兴国家与守成国家之间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
只要建立有效可控的协调机制,现代国家就可以用非战争手段处理竞争关系。
因此,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引发战争的必然因素。
文明的冲突
02
自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出版以来,引发世人的广泛关注,异质性文明之间爆发战争似乎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诚然,无论是古代的希波战争,还是中世纪浩浩荡荡的“十字军东征”,抑或是近代奥斯曼帝国同欧洲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仿佛都在印证“文明冲突论”的必然性。
但是,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所认识的“规律”是否只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观?
文明之间并非只有冲突,共存、共生、共荣才是文明之间更普遍的相处方式,否则当今世界怎会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文明形态?
在古代,古罗马不遗余力地学习、吸收古希腊文明成果,缔造了伟大的罗马帝国。
中世纪,伊斯兰文明继承、保留了古希腊、古罗马丰厚的文明遗产,并反馈给黑暗的基督教世界精神营养。
伊斯兰文明
伊斯兰文明
在东方,健陀罗地区见证了西亚、中亚和南亚之间源远流长的文明交流史,更不必说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制千年来始终保持着极大的稳定性。
“文明冲突论”是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世界观下必然的产物。
西方所谓的“普世主义”外衣下掩盖的是唯我独尊的排外特性,战争只是西方文明的选择,没有资格代表全球文明的发展大势。
因此,无论是“修昔底德陷阱”还是“文明的冲突”,它们只是一种政治解释范式,与战争的爆发并不构成必然联系。
我们仍然要从社会历史的发展路径,去考察战争观念的变化。
终
战争只是杀戮吗?
军人们在战场上厮杀是战争的必然。
然而,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达到战略目标就需要无止尽地杀戮吗?
克劳塞维茨认为,使敌人放弃抵抗是战争的目标,为此必须最大程度地使用暴力。
然而我国古代兵圣孙武却主张“上兵伐谋”。
中国人对力量的理解也不是简单的暴力,而是信奉“止戈为武”。不节制的暴力只能带来无序与混乱。
如今的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无数平民因战争流离失所,甚至失去生命。
历史的悲剧重复上演,人类频繁地发动战争,使用暴力,最终打开的只会是毁灭的潘多拉魔盒。
无论什么时代,战争都不应放纵杀戮,政治目的单靠暴力也绝不能实现。
因此,现代战争观念应当是避免战争,将战争束缚在可以管控的机制之内。
当然,避免战争绝非畏战,更不能松懈了军事建设。
一旦入侵者来临,保家卫国就是每个公民的义务,消灭来犯之敌就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图片编辑:郝宇婧
文字编辑:郝宇婧
图片来源:网 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