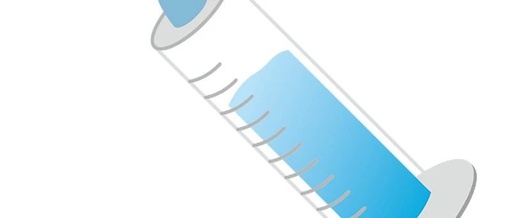摘要
儿童的给药剂量通常基于体重、体表面积制定。
然而,儿童本身处于生长发育的动态变化,影响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可能改变药物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临床实践中为达到患儿个体的药物治疗,除了疾病状态、药物本身药代动力学,还需结合生长发育特性、基因多态性和其他因素。
为达到最佳的儿童药物治疗,可借助的技术手段有药物治疗监测、药物基因组学等,并注意应选择适宜各年龄段儿童的制剂。
关键词
药物治疗;个体化治疗;精准用药;儿童;新生儿
正文 |
儿童从出生到成年会发生很大的生理变化,虽然大部分儿童遵循相同的生长模式,但其发育成熟的时间却各不相同。
药物在儿童体内的代谢动力学各方面都受到生长和发育的影响。药物吸收受各种机制影响而变化,特别是出生后几个月内,差异最为显著。
青春期也不是童年和成年之间的简单连接,而是一个生理显著变化的独特时期,很多在此期间服用的药物的疗效和毒性都会发生改变。
儿童的个体化药物治疗,除通常的生理、病理、遗传和环境因素(药物相互作用、药物食物相互作用等),更需考虑儿童的特殊性。
有许多病症是某些年龄段独有的,比如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或动脉导管开放,给药方案没有成人或大儿童的参考。
儿童群体的各项药代动力学、药效学数据不能从成人直接等比例缩放;某些成人可忽略或可承受的药物不良反应风险对儿童可能有重大危害。
儿童可以根据年龄进一步分为新生儿(又分为早产儿和足月儿)、婴儿、幼儿、学龄前儿童、学龄儿童和青少年。
儿童个体从低于1kg至几十kg的体重不等,各年龄段生理功能与药物代谢水平差异不容忽视。
相同年龄水平、体格的儿童个体发育程度不同,影响着某些药物的处置及反应;处于快速生长发育期的儿童,如新生儿,每日间的个体内差异亦很明显。
因此,为达到儿童的最优化个体化药物治疗,需要考虑儿童生长发育特性,结合药物治疗监测、药物基因组学等技术手段,并注意应选择适宜各年龄段儿童的制剂。
儿童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差异会影响药物的剂量和给药间隔时间的选择。大多数剂量计算公式以体重作为衡量儿童生长发育的指标。
1
发育药理学
当医务工作者对儿童开展药物治疗时,不能将儿童视作缩小版的成人,儿童有其自身独特的起始剂量与毒性范围,已成为共识。
最常见的儿童剂量方案基于年龄、体重或体表面积制定。
然而事实上,处于生长发育过程的不仅是儿童的体格,亦有全身含水比例、内源性物质分泌水平、受体敏感度等区别,反应到药物治疗,一方面是药代动力学的差异;另一方面是药效学的差异。
发育药理学便是着眼于儿童生长发育特性对于药物治疗影响的学科。
1.1 吸收
非静脉给药,需要考虑药物的吸收过程。
口服吸收:经口给药途径在儿童中受到如下因素影响:肠胃排空速度、胃酸分泌、肠道环境。
新生儿刚出生时胃内大约为中性,足月儿于生后24~48h内会有一过性的胃酸分泌增高,pH降至1~3,之后pH回至接近中性。
早产儿无一过性的胃酸分泌激增,生后1至2周,胃酸分泌增加,pH降至4~5并维持数月,但直到2至3岁才会达到成人水平[1]。
当胃内酸性较弱,不耐酸药物的口服吸收增加,例如青霉素、红霉素、苯巴比妥等弱酸性药物吸收则降低,如果从静脉给药改为口服应适当增加剂量[2]。
婴儿期的胃肠道动力较弱,药物达到最大浓度时间延长。
肠道菌群会影响某些药物的活化或降解,新生儿期出生时肠道相对无菌,足月儿在数日之内才有正常细菌定植,而对处在相对更无菌的重症监护病房的早产儿可能会延迟。
对于依赖胃肠道菌群的药物,其药效可能会发生显著改变[3]。
皮肤吸收:足月儿基本具有完整的皮肤屏障功能,而早产儿往往皮肤薄很多,角质化不完全。
新生儿时期体表面积与体重之比高出成人近2倍,表皮水化程度高,总体经皮吸收程度比年长儿童和成人高,局部用药的吸收增高可能造成全身反应,因此出生后2周内最好避免使用经皮给药[3-4]。
如局部应用某些制剂,必须密切监测和关注不良反应,曾有报道8~12月龄的婴儿局部涂抹利多卡因和糖皮质激素引起的全身性毒性反应[5]。
肌肉吸收:婴幼儿肌肉组织和皮下脂肪少,出生的2至3周内,肌肉血流量变化大,药物吸收不稳定,相较口服,肌内注射给药通常会导致新生儿血药浓度达峰时间延迟[6]。
1.2 分布
药物分布受器官相对大小、体内含水量、脂肪储备、血浆蛋白浓度、酸碱平衡、心输出量和组织灌注变化的影响,婴儿出生后第1年内变化的程度最大。
在生理条件相对确定的情况下,影响药物分布的因素主要包括膜通透性、药物水/脂溶性、血浆蛋白结合率、转运体等。
儿童时期,器官占全身体重比例、体内含水量、体脂含量、血浆蛋白浓度、酸碱平衡、心输出量、组织灌注等生理条件处于变化中,从而改变药物分布方式和渗透程度[3]。
早产新生儿体重约85%、足月新生儿体重70%~80%是体液,而1岁时体液仅占60%~65%,主要是细胞外液的液量变化,而细胞内液相对恒定。
水溶性较强的药物,如庆大霉素、利奈唑胺在新生儿的表观分布容积比婴儿和成人更大[6]。
药物在新生儿中的血浆蛋白结合率通常较成人低。
某些药物,如吲哚美辛、磺胺类等可与胆红素竞争结合白蛋白,使游离胆红素增高,可能导致胆红素脑病。
因此,高胆红素血症的新生儿禁用头孢曲松,且磺胺类药物禁用于2月龄以内的儿童。
虽然,氨苄西林在成人的血-脑屏障穿透能力较弱,但在新生儿期,血-脑屏障通透性增加,药物更易进入中枢神经系统,且大脑占婴儿体重的10%~12%(成人约2%),全身血流到达脑血管的比例更高,所以氨苄西林可应用于新生儿脑膜炎[6],但同时,对于婴儿群体药物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引发相关不良反应的风险也越高[3]。
1.3 代谢
药物的代谢通常需要在特定酶的催化下进行,影响药物代谢的因素主要有肝血流量、肝转运蛋白系统、肝药酶代谢活性等。
Ⅰ相代谢酶主要作用于初步水解、还原和氧化反应,包括细胞色素P-450酶(cytochromeP-450,CYP450)以及非细胞色素P-450Ⅰ相酶,如乙醛脱氢酶。
Ⅱ相药物代谢酶通常作用于结合反应,如尿苷二磷酸葡糖醛酸基转移酶(UDP-glucuronosyltransferase,UGT)、磺基转移酶(sulfotransferase,SULT)、N-乙酰基转移酶(N-acetyltransferase,NAT)、谷胱甘肽-S-转移酶(glutathione-S-transferase,GST)等。
每种代谢酶的活性有各自的成熟时间和变化趋势。
除CYP3A7活性从出生后逐渐降低、GST在整个婴儿期酶活性稳定等,大部分肝药酶在出生后数周至数月内增长幅度最大,出生1年后,活性增长放缓。
药物代谢功能高度依赖于患儿年龄。最近一些研究已经明确婴儿期、儿童期和青少年期药物半衰期具有显著差异。
胎儿期至新生儿期,很多重要的肝药酶远未达到成人活性,如咖啡因主要由CYP1A2、NAT2代谢,咖啡因在早产儿的消除半衰期从40~230h不等,并且随生长会逐渐降低,至出生后6个月才稳定为4~5h[7]。
新生儿UGT活性低,导致氯霉素不能被及时代谢为非活性结构,造成灰婴综合征[8],出生后6个月时,UGT2B7对吗啡的代谢速率为出生时的6倍左右[9]。
CYP3A4是肝脏和小肠中表达最丰富的CYP酶。
CYP3A4在出生时活性极低,在第1个月达到成人活性的30%~40%,在第6个月达成人水平;在1~4岁超过成人(120%),在青春期后降至成人水平[10]。
1.4 排泄
婴儿期药物消除能力较弱,导致许多常用药物消除速率减慢。
整个儿童时期肾小球滤过率增加。
儿童时期使用肌酐清除率作为估算肾小球滤过率(glomerularfiltrationrate,GFR)的计算方程与成人不同。
药物排泄途径主要有经肾脏(通过尿液)及经肝脏(通过胆汁随粪排出体外)。
介导流入胆小管的活性转运体包括乳腺癌相关蛋白、多药耐药相关蛋白2(MRP2)、多药耐药蛋白1(MDR1)和胆盐输出泵等[11]。
肾脏是许多药物排泄的主要途径。
在新生儿出生后头几个月里,肾血流量增大,肾小球滤过、肾小管分泌、重吸收能力逐步增强。
以GFR为例,早产儿为0.6~0.8ml•min-1•1.73m-2,足月儿出生时为2~4ml•min-1•1.73m-2,前2周,突增至20~40ml•min-1•1.73m-2,6个月达到80~110ml•min-1•1.73m-2,而1岁至成人,肾小管滤过率为100~120ml•min-1•1.73m-2。
主要经肾排泄的药物,如呋塞米、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在新生儿中清除率变低,给药剂量和间隔基于其出生胎龄和生后日龄制定。
青春期GFR可能会超过成人的平均值,导致此类药物快速清除[6]。
1.5 药效学
对药效学,虽然不像对儿童和成人的药代动力学差异了解得那么清楚,但年龄对药效也有显著影响。
儿童在治疗反应和不良反应方面都会有不同的表现。
传统意义的药物作用靶点有α-肾上腺素受体、β-肾上腺素受体、阿片受体、多巴胺受体、组胺受体等。
受体的构型、亲和力密度以及信号传导通路的成熟随生长发育而变化,使相同药物暴露量造成的临床反应有所差异。
例如,婴儿长期以来被怀疑对β-肾上腺素能激动剂较不敏感,可能与早产儿或重症新生儿心肌的肾上腺素能受体密度相对低或受体下调有关[12]。
某些药物在治疗儿童病症时,利用特殊靶点的作用,如新生儿在整个围产期大量产生前列腺素,对调节动脉导管张力自动调节起关键作用,布洛芬及对乙酰氨基酚用于诱导早产儿动脉导管闭合,即是利用其对前列腺素合成酶的抑制作用[1]。
儿童中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除了因药代动力学特点导致毒性物质体内浓度升高、蓄积之外,也受到药效学差异的影响,处在某些发育阶段的儿童器官对药物更为敏感。
2
药物治疗监测
2.1 用于儿童的药物治疗监测
如果某药物在体内有效浓度与毒性浓度接近,且剂量与血药浓度关系难以确定,则监测血药浓度,结合患儿的病情给出给药方案的调整建议,能更好地确保药物有效及预防不良反应。
儿童禁慎用的药物并非绝对不可使用,在权衡利弊后,如确有应用指征是可以在严密监护下使用的。
如氨基糖苷类,在确需使用的新生儿中应进行血药浓度监测,根据监测结果调整给药方案[13]。
某些慢性疾病需患儿数月或数年的长期用药,过去通常根据是否复发、是否发生毒性反应作为剂量“爬坡”和减量的依据。
而通过药物治疗监测有的放矢地调整剂量,将可更快达到合适浓度,减少不必要的浪费,防止延误病情及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
新生儿人群内部个体间差异、个体内差异尤其明显,因此新生儿人群的用药需要尽可能借助药物治疗监测达到最优化的治疗。
然而,在新生儿尤其早产儿中应当注意,抽取血液应经过仔细计算选取采样时间,如新生儿的稳态血药浓度可能比大儿童到达得更晚。
并且应当开发取样量低、可靠的分析方法,应当规避新生儿血液样品成分的差异(如蛋白质、胆红素)导致的不准确性[14-15]。
2.2 定量药理学应用于儿童药物治疗监测
定量药理学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包括群体药代动力学(PPK)、生理药代动力学(PBPK)等手段,可以定量分析考察各变异因素,如儿童的生长发育、药物相关的基因多态性、合并用药、生理状态等对剂量-暴露-效应关系的影响,并建模及仿真来预测血药浓度乃至治疗效果,除在儿童药物研发领域发挥突破性作用外,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儿童的临床药物治疗,结合药物治疗监测,使药物剂量的制定和调整更为精确、快速,个体化治疗的效率更高,可减轻患儿的痛苦及安全风险[16-18]。
3
药物基因组学角度
药物基因组学研究内容为寻找与药物反应个体差异相关的基因多态性,包括药物代谢酶基因、药物转运体基因、药物作用靶点基因等的多态性。
儿童群体中,生长发育特性与遗传多态性往往叠加,造成了不同个体间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差别。
因此,将药物基因组学整合入儿童药物的临床研究设计十分重要。随着其他组学的发展,药物代谢组学、药物蛋白组学有望与药物基因组学互为补充,发现更多重要的药物治疗相关靶点和通路,从而突破某些药物个体化治疗的瓶颈。
3.1 药代动力学相关基因多态性
某些药物代谢酶较早达到接近成人的水平,其基因多态性导致变异的影响比发育因素的影响更大,如CYP2D6、CYP2C19。
在涉及此类代谢酶的药物治疗过程中,获取患儿的基因型信息,将提升指导个体化用药的效率。
一项对6~1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用于治疗注意力缺陷(ADHD)的托莫西汀经剂量校正后的曲线下面积(areaundercurve,AUC)随不同CYP2D6基因型而相差达29.6倍[19],提示在ADHD患儿的治疗中,为达足够的托莫西汀暴露量,针对患儿个体进行药物基因组学和(或)药物治疗监测将很有益处。
我国已禁止可待因用于18岁以下的儿童。可待因通常有5%至10%经CYP2D6酶代谢转化为吗啡。
对于CYP2D6超快速代谢型患儿,常规剂量下可能引起呼吸停止和死亡[20]。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lymphoblasticleukemia,ALL)使用的化疗药物包括6-巯基嘌呤,其活性成分主要由硫代嘌呤S-甲基转移酶(thiopurineS-methyltransferase,TPMT)代谢。
如TPMT的代谢能力低下,易造成有效活性成分在体内蓄积,因此相较正常代谢者的6-巯基嘌呤起始剂量,中间代谢者的起始剂量应减少30%~70%,弱代谢者起始剂量应减少90%[21-22]。
药物转运体影响药物在体内透过不同生物膜的过程,从而影响吸收、分布、消除。
目前,对于转运体随发育的变化仍有较多待研究的问题,对于很多转运体来说,基因多态性的影响在转运体达到成熟水平时得以显现[23]。
对ALL患儿的研究揭示了转运体OATP1B1基因SLCO1B1的多种单核苷酸多态性变异,是使甲氨蝶呤清除率降低的因素,并与高剂量甲氨蝶呤毒性相关。
转运体MRP2基因ABCC2的多态性也与甲氨蝶呤的毒性相关[23]。
ABCC2、UGT1A9和UGT2B7基因的组合多态性与小儿肾移植受者的霉酚酸AUC有关[24]。综合考虑转运体与代谢酶的基因多态性,将是药物基因组学方法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3.2 药效学相关靶点基因多态性
精准个体化治疗的讨论通常聚焦于肿瘤基因组的变异,然而,大多数成人癌症不会发生在儿科人群中,而对那些儿童与成人共患的癌症,由于肿瘤生物学的差异和儿童的特殊性,儿童往往不能照搬成人的治疗方法[25]。
在其他领域的药物治疗中,有一些关于靶点的药物基因组学研究,例如在欧洲血统的儿童中,华法林所需要的剂量不但受CYP2C9*2和*3突变的影响,还受到药物作用靶点相关的VKORC1-1639G>A基因型的影响,尽管在日本患儿的研究中,CYP2C9突变携带者数量较少,VKORC1和CYP2C9无法得到充分评估[26]。
抗癫痫药的耐药除了与CYP系酶基因及转运体相关基因ABCB1、ABCC2的多态性有关,还与药物作用靶点,如SCN1A等钠通道相关基因有关[27]。
3.3 其他与不良反应相关的基因多态性
有些基因多态性不直接发生在药代学或药动学通路,但对于药物不良反应有重要影响,如服用卡马西平导致的严重皮肤不良反应Steven-Jonhson综合征/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SJS/TEN),与HLA-B*15∶02基因显著相关[28];
患有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glucose-6-phosphatedehydrogenase,G6PD)缺乏症的患儿,应禁用呋喃唑酮、亚甲蓝等药物,并慎用磺胺类、苯海拉明、异烟肼、维生素K等药物[29];
有多种基因位点可能与氨基糖苷类引起耳毒性的易感性相关,其中线粒体1555A>G突变的证据等级最高[30]。
4
制剂角度
4.1 儿童适宜的剂型
不同生长发育阶段的儿童由于其生理和认知能力发展水平不同,对不同制剂形式的耐受及依从性也不同。
儿童的单次给药剂量跨度也很大,因此为准确量取剂量,应提供适宜不同年龄层的制剂形式,在必要时提供不同的规格或浓度,以实现简单、准确和安全的给药[31]。
4.2 辅料的安全性问题
尽管辅料通常是“非活性”物质,儿童却可能对某些辅料非常敏感。
新生儿中乙醛脱氢酶的活性极低,影响其对药用辅料苯甲醇的代谢能力,苯甲醇暴露量过高可导致可致命的喘息综合征[32]。
因此,新生儿禁止使用含有苯甲醇及苯甲酸盐作为防腐剂的药品。反复肌肉注射含苯甲醇的注射剂,可引起臀肌挛缩症,因此禁止用于儿童肌肉注射途径[33]。
丙二醇在婴儿中可能诱导癫痫发作、呼吸抑制、高渗透等毒性[34-35]。
对遗传代谢病患儿,需注意避免使用含某些特定的辅料如乳糖制剂。
在危重患儿、婴儿的给药方案制定中,还必须仔细考虑活性成分的盐和辅料中的相关离子含量,以避免给予过量的电解质。
5
总结
“儿童不是缩小版的成人”,发育因素叠加于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共同造成了儿童对于药物反应的个体差异变化。
在定量药理学和先进药物分析方法的支持下,治疗药物监测是使儿童的个体化用药及临床合理用药更具备科学性的重要工具。
药物基因组学,连同其他新兴的组学发展,如药物代谢组学、药物蛋白组学,拓宽了儿童个体化用药研究的维度[36]。
总之,在儿童临床用药的实践中,除对患儿的生理状态、疾病进展充分了解,还应考虑儿童在药物治疗学的参数的变化,以及治疗药物监测和药物基因组学的应用,最终接近临床儿童个体化药物治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