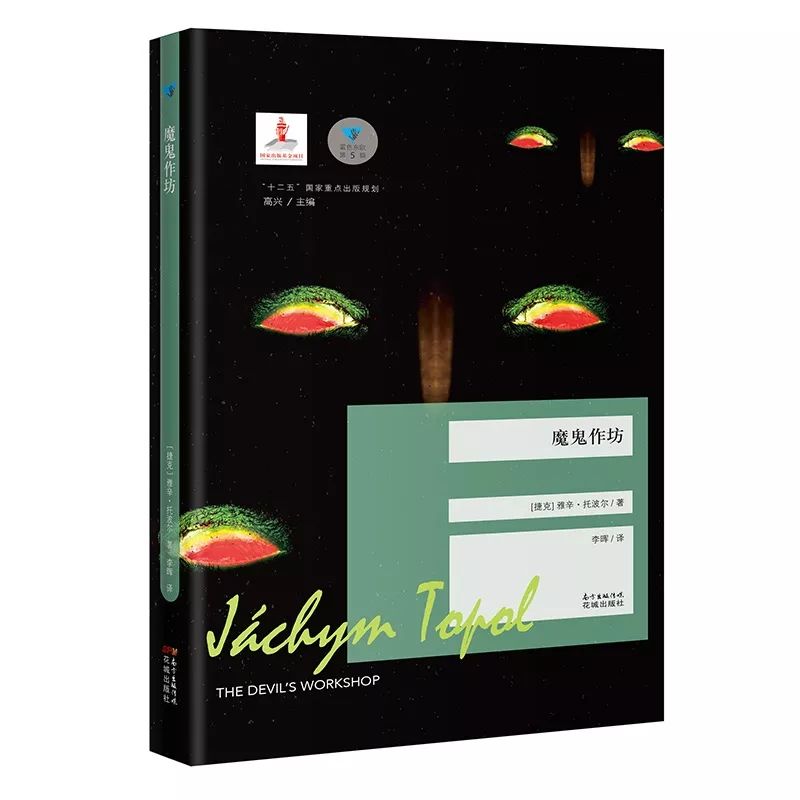苦难记忆与历史言说的深渊:《魔鬼作坊》简析
李 晖
责编 许泽红
平庸小说的宿命,是费力苦挨到故事结尾都难以避开套路陷阱;而优秀小说往往就像善于摆脱猎犬的野兔,刚开篇就能让敏感捕捉文字气息的读者紧张兴奋、心绪难平。捷克当代文学名家雅辛·托波尔出版于2009年的《魔鬼作坊》(捷克语原书名意为“穿越严寒地带”,此处依英译本标题翻译而成),显然属于后一种类型。
“我奔向布拉格机场。奔跑着……泰雷津的红砖城墙远远地抛在我身后,我故乡的城墙。”这部小说以主人公“我”从泰雷津到布拉格的暗夜逃亡为楔子,逐步铺展开梦游般光怪陆离的历险与追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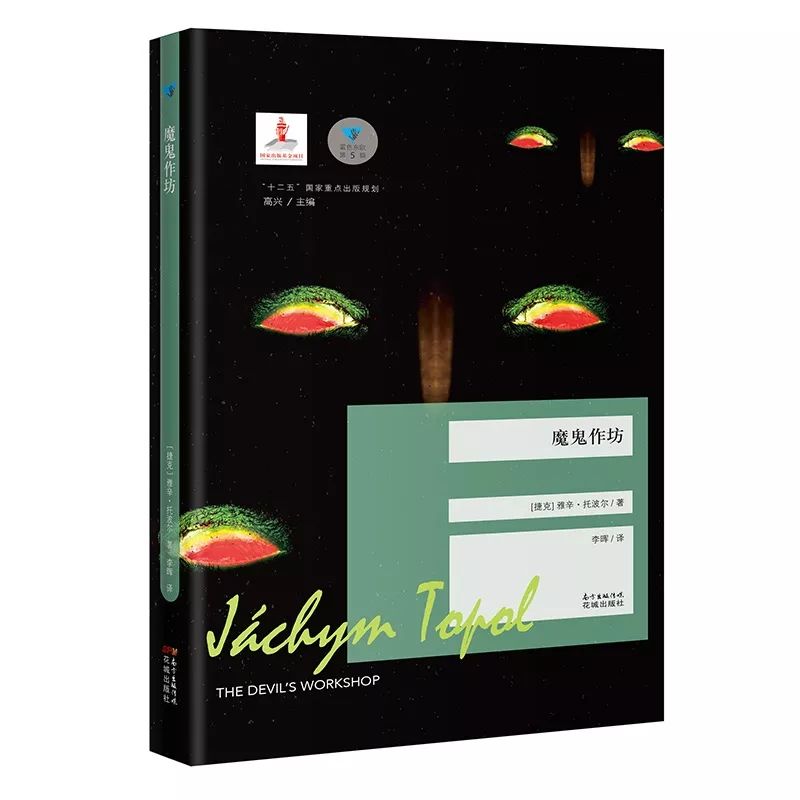
《魔鬼作坊》
[捷克] 雅辛·托波尔 著
李晖 译
花城出版社
历史的真实,虚 构的 真实
泰雷津这座捷克古镇的名字,曾经是跟达豪、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德朗西等名称联系在一起的恐怖地标。
它位于捷克北波希米亚地区的利托梅日采市郊,德语名泰雷津斯塔德,最初是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约瑟夫二世在一七八○年下令建造的军事要塞,并以其母玛丽亚·泰雷莎女皇命名。整个城镇规划复杂,功能齐备,代表了十八世纪末同类城镇建筑的最高水平。它从一八八八年起不再充当防御要塞,但依然作为驻军基地而存在,主要居民成分也由日耳曼人变成了捷克人。奥匈帝国崩溃后,泰雷津归于捷克斯洛伐克,一九三八年又随苏台德地区被德国吞并。一九四○年泰雷津沦为盖世太保的囚禁场所,一九四一年更设立了臭名昭著的犹太人隔离区。来自欧洲各地的十五万犹太人陆续抵达这里,有将近九万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关押,再分别乘坐列车驶向奥斯维辛和特雷布林卡等人类屠宰场。当时仅在犹太隔离区内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的人数就高达三万三千名。与之隔河相对的“小堡垒”监狱,则先后关押过三万多名囚犯,包括政治犯、地下抵抗组织成员和犹太人,被行刑处决以外的死亡数目则接近三千。捷克文学巨匠克里玛从十岁起和父母被拘禁在此,直到苏联红军前来解放这座城镇。

二战结束后,泰雷津重新成为驻军点,直到一九九六年完全结束军事用途。它至今完好保留着古代城防、犹太隔离区和城堡监狱等历史遗址,近年以来不仅是大屠杀历史研究和凭吊牺牲者的场所,还成了新的热门旅游景点。
乍看之下,《魔鬼作坊》很像一部伪造的当代新闻口述实录。它的故事时间应该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这几年。故事发生地主要是泰雷津、明斯克和哈滕村。哈滕村就是“魔鬼作坊”所在地。它位于明斯克以东五十公里处。一九四三年,全村共计一百四十九名男女老幼被以乌克兰裔通敌者为主的纳粹分子用残酷手段集体屠杀。虽然它与泰雷津同样都是当年魔鬼的施暴现场,但在小说里上述两地却构成了伦理价值与政治抉择的两极。
整部小说的叙述过程,都由故事内叙述者“我”来完成。“我”是一位敏感内敛、寡言少语、略微有些玩世不恭的青年。“我”的母亲是泰雷津监狱的幸存者,由于遭受过多苦难而精神失常,在“我”幼年时自缢身亡。“我”的父亲是当年跟随苏联红军解放泰雷津的捷克青年,在与“我”争吵时不幸从城头失足坠落而殒命。“我”因此身陷囹圄,后来获减刑出狱,又协助旧友雷波发起了泰雷津镇复兴运动并取得短暂成效。运动失败后,“我”被“魔鬼作坊”的积极参与者、潜伏到泰雷津刺探情报的阿历克斯和马露夏卡兄妹俩偷渡运送至白俄罗斯,从此卷入了巨大的阴谋漩涡,并目睹了一系列人间惨剧。
作者通过第一人称手法而创造出的“在场感”,将众多真实资料与虚构内容拼贴镶嵌到了一起。例如,泰雷津和哈滕村的过往历史和遗址面貌皆为真实,而所谓“泰雷津复兴运动”和哈滕村地下的秘密博物馆则纯属虚构;外国青年到泰雷津成立工作坊并寻找屠杀遗迹是事实,但所谓的西欧“囚铺探寻者”因为无法摆脱集体创伤记忆而接受雷波的教诲领导,并且联合当地反对迁移的居民与捷克当局发生暴力冲突,又全都是虚构;关于某国国内局势和政治矛盾的描述为实,而游行示威背后的巨大阴谋与利益勾结则是虚构;哈滕村惨案的细节复述,全部都依据真实档案资料,而以受害者直系亲属身份进行复述的几位主要人物,以及他们匪夷所思的行为,则纯属虚构;城市骚乱过程中有人跳上吧台朗诵反对独裁总统的诗歌,也是实有其文,但骚乱起因和时间地点却查无对证。
这种真实与虚构的拼贴镶嵌手法,很容易让人一时难辨真伪。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说:“诗比历史更具哲学性,且更为严肃:实际上,诗道出了更多的共相,而历史言说的只是殊相。”通过这种虚构与真实的并置,借助于光怪陆离的情节发展,作者或许想告诉我们:魔鬼之所以从瓶中获得释放,是因为它始终驻扎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心深处。“魔鬼作坊”能够被重新启用,是因为总有人想要以错误方式召唤起失真的集体记忆。
记忆与遗忘
按照古希腊作家赫西俄德在《神谱》里的说法,谟涅摩绪涅即记忆女神是司管历史的克利娥和其他八位缪斯的母亲。历史女神与记忆女神的直系亲缘,意味着历史和众多人文学科一样,无法脱离记忆而存在。
我们常说历史不会忘记,是因为我们还相信:即便存在着有意识、集体性的删除清理,也无法抹尽回忆言说的零碎声音。
但记忆与遗忘原本两面一体、不可分割。
所谓“历史不会忘记”,只是将无法自行言说的历史视为人格化主体的方便隐喻。真实发生的历史言说,从来只是众多个体声音在特定社会传播机制提供的有限时空内的汇聚交叠。个体心灵与头脑受到自身容量的限制,或出于惯性思维,会无意识地淡化或排斥那些异质、难以兼容的回忆内容,再选择自认为更有意义的记忆内容进行留存;或者为了趋利避害而屏蔽危及自我身份认同与社群凝聚的记忆。这是人性的本能。
乔治·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契》里说过:“如果我们的眼光和知觉对人生中一切寻常事物都分外敏感,这就如同能够听到野草的生长和松鼠的心跳,而我们会由于寂静另一极端存在的轰鸣巨响而丧命。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当中最为伶俐机智的人会用愚钝来填充自己,从而行走于世间。”
纵观历史,我们不难看到,许多曾经给无数个人和群体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沉寂在集体无意识之下、深层意义尚未充分发掘、有待于形成系统叙事的历史事件,因为创痛之深,很容易导致人们的本能回避,然后在若干年后趋于遗忘。
▲《魔鬼作坊》捷克语初版封面
《魔鬼作坊》里有一段情节,是阿历克斯痛斥世人仅仅听说波兰的卡廷森林惨案,却根本不在意哈滕村发生过更恶劣的罪行。他追随的精神领袖卡根,在明斯克地穴挖掘现场也向“囚铺探寻者”表达过类似想法:“现在我们将挖掘暴君们当年逼迫你们父母和祖父母跪伏的土地。你们和我一样清楚,这个政府不允许传播任何有关白俄罗斯人互相残杀的只言片语。但是我们将打破沉默!忘记过去的恐怖,就意味着向新的邪恶低头。”他们的担心并不是毫无理由,这种愤慨激昂并不纯粹是迫害妄想症:外部世界长期漠视历史真相,他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还承担着言说的使命,以免成为最不应该的遗忘者。
其实,反观卡廷森林事件在不同时期的解释说法,又何尝不曾遭受过同样的遮蔽篡改呢?在每一种历史言说形式的背后,存在着不同的叙事主体和不同叙事目标。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最后一章《记忆与遗忘》结尾处说:“民族传记从布罗代尔那无情层叠的墓葬群里提取出具有代表性的自杀、苦痛的殉道、刺杀、处决、战争与屠杀浩劫。不过,为了实现叙事的目标,这些酷烈的死亡必须作为‘我们自己的’死亡才能获得记忆/遗忘。”
小说里前纳粹军医路易斯擅长的印第安人缩头术和防腐技术,更是绝对权力试图让自己一手塑造的历史言说模式保持不朽的寓言。
……
在东欧文学评论家的眼里,托波尔堪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东欧“历变小说”的杰出代表。塞缪尔·托马斯在《1001本死前必读书》里则赞誉托波尔的首部小说《姐妹》是“现代捷克想象力的《独立宣言》”。
托波尔的叙述题材来源博杂,经常混杂着庄重与戏谑、神圣与亵渎、经验与幻觉。有人评价他的作品是博尔赫斯、乔伊斯和凯鲁亚克的混合体。他对语言形式的大胆尝试,尤其是句法、拼写、语法和对话的快速跳转切换,以及不同语域材料、文类和方言切口的运用,足以让传统读者瞠目结舌。这些尝试,充分反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长的这批作家对传统写实主义的排斥。
作家通过语言文字和叙事形式的调整,具体表现时代的变动不居感。这无异于提供了一面镜子,映照出价值碎片化的世界。至于这个碎片化世界背后的真正意义,则需要每一位读者自行体悟。
就像托波尔笔下的人物所说的:“我把旧词和新词混合在一起。有些意思我郑重看待,所以把它们更深地隐藏在话语里。”
雅辛·托波尔,当代捷克作家的杰出代表。年轻时就是一位积极的自印本诗人和词曲作家。小说代表作包括《城市、姐妹、白银》《用沥青漱口》和《魔鬼作坊》等,均已被翻译成英文。其中,《魔鬼作坊》曾获得捷克共和国最高文学奖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奖,并进入荷兰的“欧洲文学奖”短名单。
小说缘起托波尔受邀到泰雷津采访报道犹太隔离区和监狱等历史遗址。作者以此为背景,完成了这部书写纳粹罪行和受难者悲剧命运的惊世骇俗之作。通过第一人称手法,以主人公“我”的视角讲述泰雷津、哈腾村遗址保护者和囚铺探寻者的故事,绘制出一幅让人深感困扰的画像。它描摹了两个东欧国家如何面对旧日魂灵的困惑,并且发出疑问:我们应当在哪一时刻将往事彻底交还给历史?
译者 李晖,安徽宣城人。北京大学翻译研究博士,现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高级翻译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小说理论与翻译研究、现代主义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的外译传播、中西寓意叙事比较。译作有《美学·图画通识丛书》、《卢浮宫藏品精选》和《最佳欧洲小说II》(参译两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