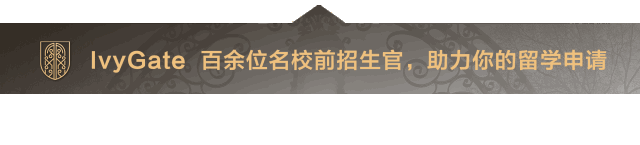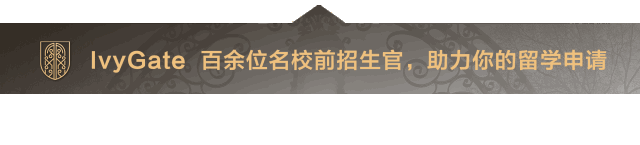 1.
1.
许俊
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IAS) 的咖啡馆里,在许俊(音译)毫无防备时,有人问他,与自己的数学恩师在学术上分道扬镳,是怎样一种体验?
许俊沉默良久,给出了答案:
“愧疚”。
许俊,1983 年出生,一名大器晚成的韩国数学家。 他本科学的不是数学,却硬申美国的数学博士,最终只勉强被一所学校录取。
但就是这样一位半路出家的数学研究者,却在读博生涯的早期就证明了一个困扰了数学界数十年的难题。
现在,许俊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数学讲师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落成起,就是学者开展纯学术研究的天堂,爱因斯坦、冯诺伊曼、哥德尔、杨振宁等我们津津乐道的科学家和数学家们,都曾在此取得划时代的学术成就。
虽然这家研究院的名字里有普林斯顿这四个字,但它并不隶属于普林斯顿大学,只是同样位于普林斯顿这座小城,并且有一些学术合作。
说句题外话,有家美国课后辅导学校叫 Princeton Review ,他们和普林斯顿大学毫无关系,只是名字里有普林斯顿这四个字而已。
一个温暖的早春清晨,拿着刚买好的早饭面包,许俊正在寻找麦克唐奈礼堂——他将要讲课的地方。 作为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员,他其实没有教学义务,但他还是在本科生院开了门叫《交换代数》的课。
“你为什么要分心去做教学呢? ”
“如果你讲一天课,你至少教书育人了,你至少为世界做了贡献。 但如果你做一天数学研究,你通常做不出任何贡献。 ”许俊如是说。
在这节交换代数课上,许俊带着学生们证明了希尔伯特的一条数学定理。
学生们的领会能力很强,毕竟,能被普林斯顿录取,又愿意一大早跑来上一门艰深的数学课,这些学生本来是一个自我筛选的群体。
这群学生中最有数学天赋的是宋卓群。
2.
总爱坐在第一排的宋卓群,在高中时曾连续五次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 (IMO) 中获得金牌——历史第一人。
宋卓群
宋卓群高中毕业于 Phillips Exeter Academy ,这是一所精英寄宿高中,位于波士顿郊外的埃克塞特镇。
冯祖鸣
Phillips Exeter Academy 盛产数学竞赛冠军,这成就多亏了两个人,一个是北大少年班毕业的冯祖鸣,他从 0 到 1 建立了美国奥数培训体系,燃起了美国教育者对数学竞赛的兴趣,就好像当年球王贝利让足球文化 (soccer) 在美国生根发芽。
罗博深
另一个是冯老师的学生,现任美国奥数总教练的罗博深,他接过师傅的奥数火炬,让美国国家队的光芒变得更耀眼——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战绩历史总榜挤进前三就是最好的证明。
冯老师是好老师,没有他,罗博深可能就要在数学探索之路上多走很多弯路,没有他的强烈推荐,扎克伯格不一定能进哈佛。
广中平祐 (Heisuke Hironaka)
我们故事的主人公许俊也有一位恩师,名叫广中平祐 (Heisuke Hironaka) 。广中平祐是日本家喻户晓的数学家,也是 1970 年菲尔兹奖得主。
如果说冯祖鸣对扎克伯格和罗博深的帮助是培优级,那广中平祐对许俊的帮助绝对是拯救级。
故事得从许俊的小学时光说起。
许俊小学时的数学成绩很差,但他很要强,于是他试图通过写诗来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
很多家长读者应该很熟悉这种自我奋斗的方向。 在上世纪 80, 90 年代的中国,许多青年男女都以写诗为荣。 能创作出优美动听的诗歌,在当时,是智慧和成就的象征。
不过,随着邓公南巡讲话的深入人心,经济发展成为国家的第一要务,许多年轻人的自我奋斗目标也变得更务实: 找个好工作,赚钱养家。
于是,许多人放弃了诗歌事业。
诗人许俊最终也停更了,因为没有出版社愿意接受他的作品,他终于接受了自己是平庸诗歌爱好者的现实。
于是,考进国立首尔大学的他,选择了天文物理专业,努力成为一名科学记者。 什么是科学记者呢? 以中国为例,科学记者就是为诸如《科学画报》等科普杂志供稿的记者。
在许俊大四时,广中平祐应邀到国立首尔大学授课一年。 他开了门全年的课叫代数几何。 拿了菲尔兹奖,写了多本畅销书的广中平祐在韩国也是学术名人。
努力成为科学记者的许俊,嗅到了高质量采访的机会。 于是,他带着为新闻事业献身的心态选了这门课,因为他并没有听懂这门课的必备数学基础。
这门课开课时共有 100 多个学生,其中有不少都是学术追星者。 很快,这门课的到课人数就跌至个位数,许多数学专业的学生也因为觉得课程太难,自己学不到东西,就退课了。
3.
不过,许俊坚持听课,因为他对课程内容本身的期待值很低, 偶尔能听懂广中教授讲的一个例子,他就觉得赚到了。
下课后,许俊常找广中教授吃午饭,慢慢地,教授也开始重视这位”好学“的韩国学生。
在吃饭时,许俊常问教授一些他个人生活的问题,毕竟,这些内容才是大众科普杂志读者最感兴趣的(和最可能读懂的)。
但广中教授说着说着总是会说回他自己的数学研究。 虽然几乎听不懂任何一句话,但许俊依旧敬业地扮演一个“数学爱好者”。
许俊演得太像了。
多年之后,广中教授回忆起这段时光,表示自己当时完全没看出许俊是数学小弱。
装懂,直到真懂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 许俊做到了。
广中教授对数学研究的热情感染了许俊。 他决定放弃科学记者的职业规划,留校读研,这回,他选择了数学专业,而他的硕士导师正是广中教授。
在硕士的两年中,广中教授帮许俊补了很多数学基础,他的讲法很有效,他首先给许俊讲很多的例子,帮许俊建立清晰正确的直觉,然后再讲这些例子背后共同的数学概念。
在这种“我的数学 1 对 1 辅导老师是菲尔兹奖得主”的顶级学习环境中,许俊的数学水平突飞猛进。
两人的友谊也因此越来越深厚,教授带许俊认识了自己的妻子,还多次邀请许俊去自己日本的家中参加家庭聚会。
有一天,教授很严肃地找到许俊,表示自己已经老了,希望许俊能沿着自己在奇点理论 (singularity theory) 的研究路线,自己往下探索。
等于说,广中教授希望许俊能成为自己学派的接班人,这是何等的欣赏和信任。
不过,可能广中教授还是被友谊干扰了判断。
虽然许俊的数学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毕竟他本科时的数学基础有限,所以,他在研究生时期的数学成绩也算不上顶尖。 这样来看,许俊离成为一个数学家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更别提成为广中平祐的合格接班人了。
但广中教授就是认为这个学生有别人看不到的数学天赋,他就是对许俊有迷之自信。 在 2009 年,在广中教授的强烈要求下,许俊开始申请美国大学的数学博士项目。
4.
最后,只有伊利诺伊香槟分校 (UIUC) 这一所大学看在广中的教授的面子上,决定赌一把,接受了许俊。
在许俊到了 UIUC 后,只在电影里发生的情节就发生了。 在他的博士一年级时,他就应用广中教授的奇点理论,证明了一个困扰了很多数学界很多年的难题: 里德猜想 (Read’s Conjecture) 。
里德猜想属于一个叫图论 (Graph Thoery) 的领域,这是一个许俊在读博前很陌生的领域,所以,他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者通常会用什么方法证明猜想,一无所知。
许俊以前的图论研究者根本没想过应用奇点理论,一种代数几何中的工具,因为图论和代数几何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但许俊没有这种思维定式,而且,他能熟练掌握的数学工具也不多,在他有限的几种能应用的高级数学工具中,奇点理论是最强大的,也是他最常用的。
当一个人手里只有一把锤子时,他看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东西都觉得像钉子 。 因此,许俊才不管什么什么图论学界共识这种陈规,他大胆地用奇点理论,解决了困扰了图论领域几十年的里德猜想。
如果你不知道许俊的这个数学成就有多惊人,我可以给你一个体育界的类比。 如果有个 18 岁才开始学习乒乓球的普通外国人,通过两年的练习,在奥运会上战胜了所有参赛的中国选手,拿到了金牌,你说这样的成就可不可怕?
许俊解决里德猜想的难题,论成就,超越了上面这位假想外国人的成就。
许俊并不孤独。
在学术界,这种外行战胜内行的例子虽然不多,但也绝对不少。
田中耕一
比如,在日本,有一位叫田中耕一的小公司职员,就用外行的方法攻克了一个化学领域的难题,并凭借这个研究成果,拿到了诺贝尔化学奖。
在田中耕一 28 岁时,他的老板派给了他一个任务: 公司为了制造仪器,需要在一个化学实验中测定某生物大分子的质量。
田中接到这个任务后吓傻了,因为他的化学只有高中程度。 如果搞砸了这次实验,自己可能会丢失去这份工作。
但胆小的他不知如何违抗老板的命令,于是他决定用自己有限的化学知识去完成这个任务。
当时化学界有一个常识: 如果用镭射光电离的方法测量分子量,最多只能测定分子量在 1,000 左右的化合物。
但是田中是个门外汉,他完全不知道有这个”常识“,因此,他依然用镭射冲击着大分子。 他手里只有这个工具了,他别无选择。
另外,在试验中他由于过于紧张,不小心把甘油滴进了钴试剂中。
就在这时,他作出了一个让内行震惊的决定: 他觉得这试剂还挺贵的,扔了太可惜,干脆再拿它继续实验吧。 于是他把试剂放进试验装置。
剩下的就是历史了: 他分离出了分子量超过 10,000 的化合物。 一个化学家们梦寐以求的学术成果。
田中耕一把实验过程和结果写成了一篇学术论文并发表。 最终,诺奖委员会发现了这篇神奇的论文,并决定把 2002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他,嘉奖他在质谱分析法研究中对人类的伟大贡献。
和田中耕一一样,许俊也是把自己对里德猜想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敏锐发现了这篇论文的价值,他们邀请许俊来办讲座,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
5.
在许俊讲座的那天,台下坐满了来自密大和多所其他大学的数学教授和研究者。 有趣的是,当年拒绝过许俊博士申请的大学,基本都到齐了。
始于一个奇点理论激发的灵感,许俊抓住了图论研究的重大机会,不断深度思考和推演,并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了严谨的论文。
其实许多人都有过灵感迸发的瞬间,但他们往往在瞬间的激动后,就重新回到了之前的生活状态,仿佛灵感从没来过。
在密歇根安娜堡,许俊的成果分享会震撼了在场的学者,密歇根大学当即决定邀请许俊转学,许俊当即同意了。
转学到密歇根读博期间,许俊在图论所属的组合数学 (Combinatorics) 领域取得了更大的突破。
最终,在 2015 年,他证明了比里德猜想更难的罗塔猜想 (Rota Conjecture) 。
这个成就不仅为他赢得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职位,也让他成为菲尔兹奖的热门候选人,一个他的恩师广中平祐曾拿到过的数学界最高荣誉。
现在看来,广中平祐慧眼独具,他对许俊无条件的信任和支持,让世界没有埋没一个顶尖的数学人才。
可是,许俊功成名就时,也是他与恩师分道扬镳的时刻。
6.
早在 2012 年,刚刚证明了里德猜想的许俊回到自己的母校国立首尔大学,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台下的听众中就有他的恩师广中平祐。
虽然广中教授很为自己徒弟的成就而自豪,但他也隐约感觉到,许俊可能已经失去了纯研究奇点理论(代数几何领域)的兴趣,只会把这个理论当成一个工具来用,不打算接自己研究的班。
分享会后,师徒寒暄中,广中平祐略带焦虑地问许俊,你打算放弃奇点理论的研究了吗?
“不,不,没有放弃,我还会继续研究。 ” 许俊对恩师说,但难掩言语中的勉强。
2015 年,许俊证明了罗塔猜想后,就彻底告别了奇点理论(属于代数几何领域)的研究,他把全部的研究精力都投入到了组合数学领域中。
2012 年首尔一别,师徒两人便天各一方,广中平祐再也没有见到过许俊。
今天,88 岁的广中教授已经退休,但依然在孤独地坚持自己的奇点理论研究。 2017 年,广中教授发表了一篇论文,称自己已经证明了困扰奇点理论领域的一个世纪难题。
许俊和其他数学家看完了论文后,既没认同,也没否认广中教授的结论。
广中教授的身体状况意味着他已不再适合长途旅行,但他还是期望能再次见到自己的爱徒。
“我只在网上读到他的新闻,但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了。 ” 广中教授表达了自己的思念。
但许俊已经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开辟了属于自己的新天地,他在物理上和精神上与恩师的距离,已经越来越大,大到无法弥合。
“我很内疚,但我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学术空间才能自由地思考。 ”许俊也道出了自己的难处。
又是普林斯顿美丽和静谧的一个早晨,许俊快步走进麦克唐奈礼堂,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春去秋来冬又至,学术界每年都在见证类似的离别。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 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 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
本文转自头条号:学霸山丘,侵删
资料来源:
1)What leads to success at math contests?
2)June Huh's Home Page
3)A Path Less Taken to the Peak of the Math World | Quanta Magazine
4)日本平庸小職員如葉大雄! 搞砸實驗獲諾貝爾獎 - 搜奇
5)专访美国奥数队主教练冯祖鸣 :中国学生数学优势止于中学_教师观察_教育杂志_千人智库
6)冯祖鸣: 给孩子“自由恋爱”的机会 - 科普天地 - 伊学数学
7)Alex Song ’15 Breaks IMO Record with Five Golds
获取留学资讯
加入留学社群
得到专业辅导
扫码添加藤门君 (ID: ivygate002)
开启你的留学成功之路
推荐阅读
编辑 | 藤门君
精彩回顾
|
学费汇总 |
本科录取 | | 申请策略
录取案例 | 语言培训 | 文书 | 干货 | 背景提升
|
-藤门国际-
| |
加入藤门
行业领先 | 菁英服务
Your Gateway to Elite Education.
搜索其他文章哟~
招生官、录取、案例、科研、项目
总裁说、规划、学校名称
ACT、家庭教育、心理。
点“阅读原文”立即和名师进行1v1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