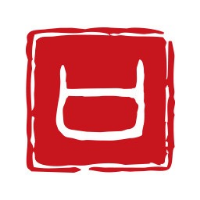西北人有一双好手,二细毛细韭叶宽,在兰州牛肉拉面店遇见“此生系列”的概率,要远远超过在簋街吃到一份称心如意的麻小。

这双手,吃起东西来也毫不逊色。
一盘二指宽的羊肉在简单的烹饪之后大放异彩,上了桌,赤条条、白净净,直接上手,筷子此时已经没了用武之地,手抓成为了本能般的存在。
造访手抓羊肉馆就是一次田野观察,豪放与不拘一格,这热气腾腾的一手资料,吃一遭全有了。
1
手抓,似乎总是带着某种文化暗语,在人工智能都能喂饭的今天,依旧有着自己的忠实拥趸。
和拆蟹还得搞个蟹八件不同,人们提起手抓,继而就会联想到力量、粗放、大开大合。手抓羊肉的力量值最满,干燥温暖的手掌混合油润腥膻的羊肉,对应的景观就不该是温柔水乡。
羊肉吃完手脚朝天,至于心平气和一点的,要数抓饭。
早饭时间开始,乌市的街边就是大锅抓饭的天下,但凡过了九点,头锅抓饭就已经没得吃。新疆人对抓饭的热爱,来源于生存环境之下重油重盐的饮食习惯,这种延续传递的偏好,甚至促成洋葱与胡萝卜成为这座城市最重要的经济作物。
胡里麻汤(稀里糊涂、乱七八糟,新疆话)是做不好抓饭的,他们总是这么说。红萝卜也好,黄萝卜也罢,抓饭的选料其实讲究得很,大米要晶莹饱满,羊肉要连筋带骨,皮牙子(洋葱)要辛香微甜。
“弯腰探手,四指拨过一口饭,在铁盘边上压实,回来用大拇指把饭团送入口中”,吃抓饭是个手艺活儿。也因此,吃抓饭的时候若没有一技之长傍身,结局多半狼狈。如果拖泥带水吃的到处都是,家里拿事儿的老妈子,白眼得翻上天。
手抓的量要充足,吃起来才足够愉悦,这是新疆抓饭。手抓的质要分明,吃起来才足够立体,这是德宏抓饭。
德宏低调地在云南边边伸展,梅里雪山、纳西古镇、人间仙境与这里无关,却偏偏因为“好吃”二字,让无数饕客心向往之。初来乍到,有门路的人会先被抓饭款待。抓饭在德宏已经不是一碗主食这样简单,它更像是一种筵席,绿叶衬托稻米,绿叶是碗,裸手是筷,因此也得名:绿叶宴。
所谓从田野到餐桌,当地随处可见的野味与山珍,伴随着烤、舂、揉、腌、炸、拌、煮,呈现在硕大的芭蕉或是东尖叶之上,茶树菇、五花肉、香茅草、炸猪皮将米饭层层围住。白的稻米饭,紫的糯米饭、黄的菠萝饭,在视觉上先声夺人,随之而来是混着香草与山菜层层叠叠的滋味。
正如元代李京在《诸夷风俗里》所载,“食无器皿,以芭蕉叶籍之”,在云南,饭拢上菜捻成团吃,颇有一番野趣。
2
不难想象,在人类创造出工具之前,手是获取食物与享用食物最重要的来源。
手与食物的联系,多与豪放和不拘一格挂钩,有时又会成为野蛮的象征。使用器具进食,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讲究饮食氛围的事情。
三千多年前,农耕文明尚未完全成熟之前,人们正在经历着以手抓饭的阶段。先秦时《礼记·曲礼》中曾载“羹之有菜者用挾,其无菜者不用挾”,这是有关筷子的最早文字记录。但在那时,筷子的用途只是用于从热羹汤里夹取菜叶,初不以之取饭,对其它的食材用之以筷,反而会弄得狼狈不堪。
东方渐渐形成的筷子饮食文化,与农耕文明高度发展相关,人作为集体中的一员被系于土地之上,箸筷成为宗族生活里“家具”的最小单元,维系起人与人之间的仁义礼智信。
在西方,从食无具到有具,也经历着类似的发展历程,刀叉用餐是文明的象征。只不过在13世纪之前的罗马,情形恰恰相反。上流贵族圈层中,用手吃饭成为潮流,食物被佣人分割成适宜入口的大小,再用手指送入口中,这种习惯的产生与宗教息息相关。
“这是天谴!”,中世纪时流传甚广的传说是,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妇人用餐叉进餐,不出几天就一命呜呼。手的使用,被视为对上帝所赐予的食物的感恩,这一点,从那时艺术作品里魔鬼多半手持岔叉也能得到佐证。
后来伴随着文艺复兴与理性运动,人们的关注点从神本回归到人自身,手、食物、神之间的联系被打破,再后来的殖民运动与工业革命,将欧洲的刀叉文化扩展到北美,与筷子二分天下。
而在刀叉文化圈与筷子文化圈之间,除了小范围的手抓习惯,仍有占世界人口约四成的手指文化圈存在,非洲、中东以及南亚成为其中最典型的区域。
如果抛开宗教信仰、迁徙习惯、民族性格,对于那些习惯以手抓饭的国家来说,在食物入口之前,先用手指触摸,可以提前掌握食物的温度与状态。就拿吃鱼这件事来说,鱼肉夹带的鱼骨,手指会比餐具更先感知到,这样一种习惯的存在,本就是趋利避害的本能。
3
人类有一个特性,就是想要探索、操控周遭自然物质世界,以顺应自己的需求和兴趣。这些需求和兴趣也包括我们的感官刺激,创造出能吸引我们脑子注意的感觉模式。
手与状态各异的食物接触,意喻着豪放、野趣、热情,哪怕简简单单用五指抓住一只肥腻流油的汉堡的瞬间,也会推波助澜,诱发出更深刻的感受。
将触觉与味道相连,已经超脱了其含义本身,成为人们一直舍不得放下的天赋人权。
文 | 林爱肉
图 | 部分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