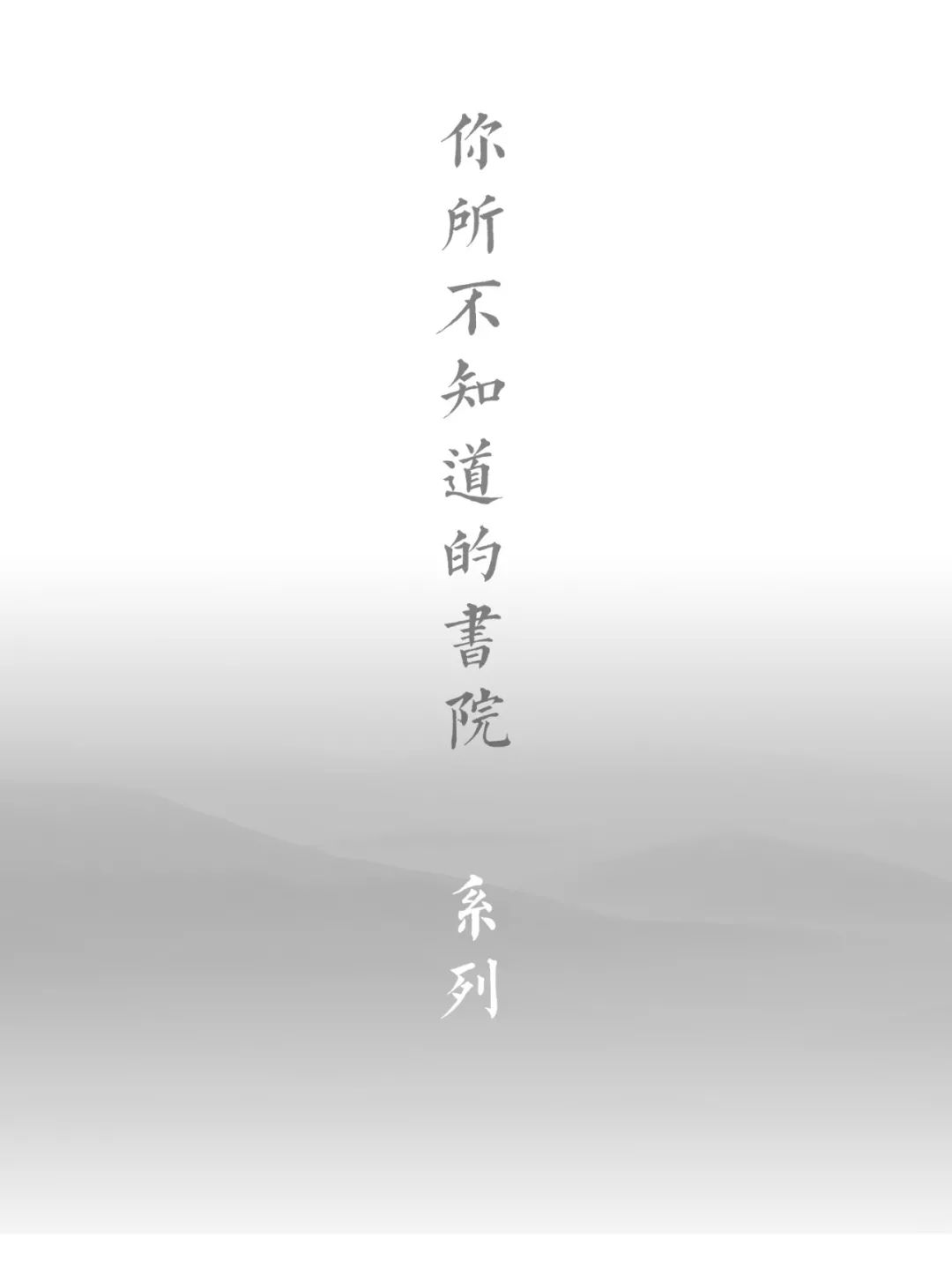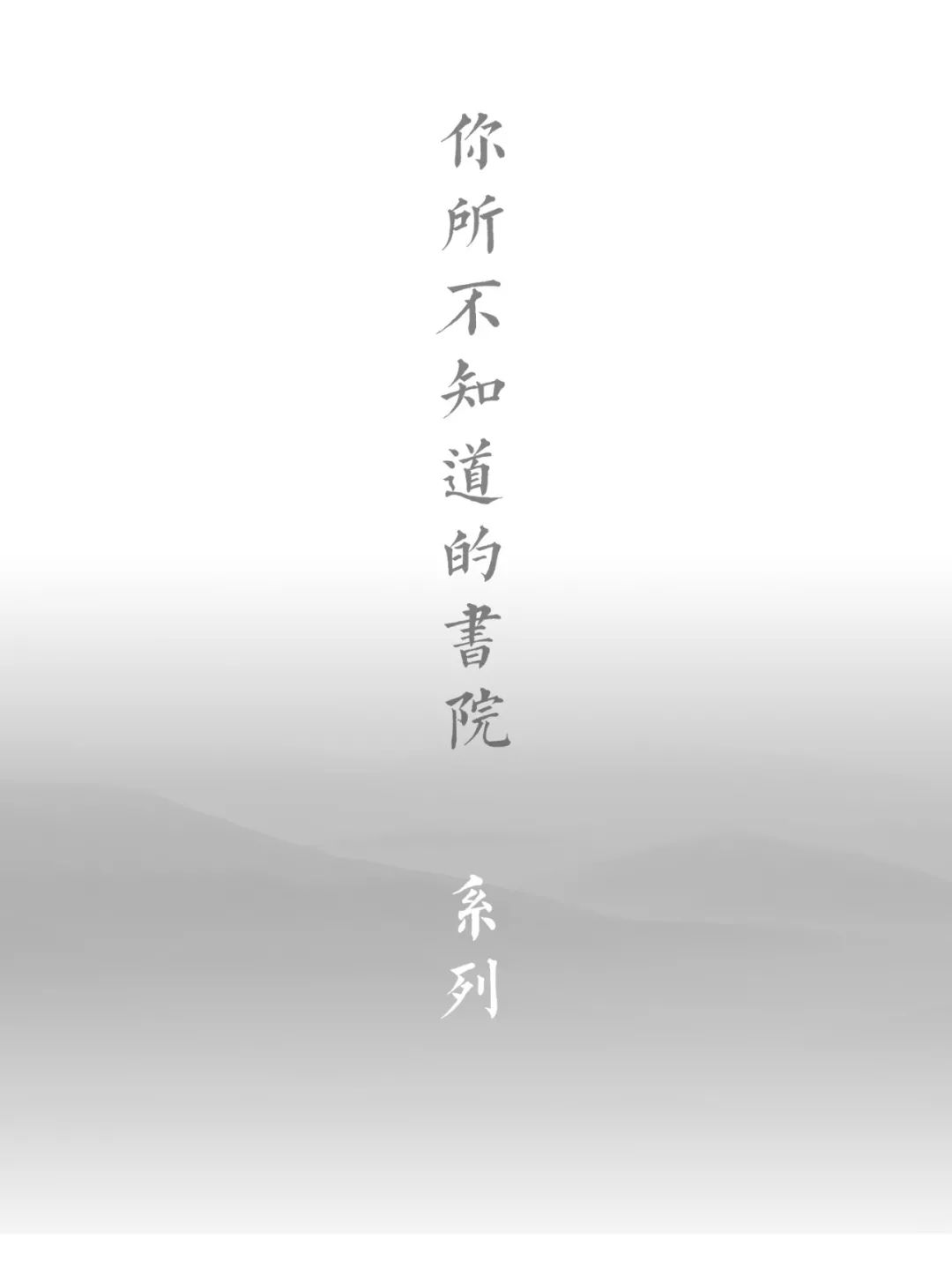
学田为书院“三大事业”(讲学、藏书、供祀)的经济基础,是书院经费的主要来源,它是书院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兹介绍学田来源、名目及其支出。
学田来源与名目
宋代
宋代李允则首辟水田“供春秋之释典”,属祭田性质,由此开创了岳麓的学田建设。以后,又陆续增加“膏火田”“岁修田”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书院后来还有“息金”“岁钱”等多种收入。
明代
明代岳麓学田的来源有三个,一是私人捐助,二是清复故田,三是地方政府拨入“公田”。其中“公田”比例最大,占总数的74.1%(租谷占总数的64%),私人捐助次之,占14.7%,清复故田最少,仅占11.2%。屡次增拨“公田”,反映了地方政府对于书院教育的重视。
明代岳麓书院学田统计表
(注:此表根据康熙《岳麓志》卷三《食田旧纪》绘制)
弘治重建时,开始捐置田亩,“以供祀事,以食学者”。 由粮刑官彭琢、李锡,参议吴世忠和监生李经、甘归受等相继捐置学田八十七亩,但实际收租仅三十八石,显然无济于事。因而到嘉靖年间,进行了清复书院学田的工作,以满足书院的实际需要。先是王秉良置田十八亩,后任孙存又置六十八亩,且从“屯田道屠”处请得“无粮田一百九十八亩”,同时,孙存决心清复书院久失的五十顷学田。但因世远人亡,不可卒问,清田成果不大,仅清出了陈友贤、陈友智隐占的九百一十亩水田,且因其中人事关系复杂,真正复归书院的只有陈氏卖给长沙卫前所军人谭玉的二百五十亩。而他们转卖给长沙卫指挥张清、杨溥、王政等的六百六十亩田却不能尽究,只能“俟后之君子考焉”,而不了了之!杨溥本人虽对书院建设还算关心,曾于弘治后期刊印《岳麓书院诗集》,正德元年(1506)为岳麓建了大成殿,但涉及到切身利害,却不能以“圣贤”律己了。
此外,孙存还先后两次“请入”公田。第一次“申呈屯田道屠”,将一百九十八亩屯田请入书院。第二次则是向“巡院黄衷、按院邓显奇、提学许宗鲁及布按守巡各处”,请准将按例没入官府的“绝民”刘光彻的田产一千四百余亩纳于书院名下。到嘉靖末年,“麓山弥望之区,悉为书生之恒产”,岳麓书院共有田产二千二百余亩,还有水塘四十一口,屋基三十一处,每年可收租谷八百余石,规模相当可观。
明代的学田名目分“食田”和“祭田”。上文表中所列只是书院学田中“以食学者”的部分,因此明修各本《岳麓书院志》皆称为“食田”。此外,还有“以供祀奉”的祭田,如邹志隆修道乡祠,置田四十亩,交僧人本空经营供祀用。但当时祭祀对象较多,如文庙、“六君子”、朱熹、张栻等,显然不可能从都有专款而去绝对划分了。
清代
明清之际,社会再次动乱,岳麓在明代艰苦积累的学田,又为豪势之家所占,到康熙年间,已是“皆不可卒问矣”。丁思孔重建书院时,“置田三百亩以资膏火”,一切又只得从头做起。
清代岳麓书院的学田建设,像明代一样,得到了社会人士的极大关注,虽然时有见利忘义之徒侵占,但随即查出清复,而且重义助学之士代有人在,因而清代岳麓学田基本恢复原有数目。较之明代,学田种类增加,整个书院经费来源中商品经济因素越来越大,又成了清代学田(包括经费)建设中的两个特点。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湖南全省最高学府的岳麓书院,它为通省士子肄业之所,其学田亦可由官府从其他府州调拨取用。
如洞庭湖区的磨盘洲,自元明以来即为岳州府学的官田,到乾隆初年,又因淤积,新增稀芦地1022亩、草地2700亩、泥地222亩,乾隆九年(1744),由岳州府、巴陵县两教官“联衔具详”,知府黄凝道“履勘”,“通详各宪”,再由岳常澧道严有禧“议覆”,至十年湖南巡抚杨锡绂批准:“每年以租课十分之三归(岳州)府(巴陵)县两学修庙,其余七分,半归岳阳书院,半解岳麓书院,均充膏火之赀。勒碑府署前,永为例。自道光以业,屡年水灾,芦稀课减,已详免解岳麓书院,惟充岳阳书院膏火之赀”。
由此可知,乾嘉时期七十余年时间,远在湘北洞庭湖本属岳州府学的近4000亩学田收入,有35%被湖南巡抚下令解送到岳麓书院充作诸生膏火费用。岳麓依巡抚之令,可取其他各府州官田课赋而作膏火,其作为湘省最高学府的地位,于焉可见一斑。
清代“学田”名目很多,有膏火田(又叫食田)、祭田、岁修田、朱张渡食田等。
岳麓生徒的膏火由“膏火银”和“月米”组成。膏火田即是“月米”来源之所在,到同治年间,书院膏火田有1595.5亩(另有租额47.49石的田亩除外),田亩比明代少五百来亩,但租额却大大超过明代。学田分散于各地,如宁乡县有2处,计258亩,长沙县有19处,计552亩。租谷也由各地官府代为“经理”收受,由善化县碾成米后连同每月的膏火银一起发放到院。书院有仓屋贮存粮食,“归门夫、堂夫启闭,并照料漏湿”。“膏火银”则类似现在的助学金,正课生每月一两,附课生减半,其经费来源主要是公款,经营方式则是将公款贷给商户,收取息金。
院长的食米供应,则另有“院长食米田”。《岳麓续志补编·杂记》载:“院长食米田,……其佃每年纳上熟白米二十二石。制斗。正月起至十二月止,随时供应。”经营方式不同于膏火田,而由书院直接掌握。
书院每年修理房舍、床榻、几案等所需经费,原为临时请于官府,没有专项,因此往往修理不及时,造成一些损失。道光十年(1830),书院将刘贺父子捐置的三十亩水田(租谷二十七石)定为“岁修田”,由书院直接收租,用于维修事项。
朱张渡是岳麓书院与对河城南书院及长沙城区联系的主要交通设施,从宋代起就成了书院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年张栻、朱熹讲学于岳麓、城南两院,即往来于此,因此改名“朱张渡”以为纪念。
清代特别重视渡口建设,除了确定“渡夫”、修建码头之外,还先后添置田产以为“岁修”“油艌”之费,称为“朱张渡食田”。雍正十一年(1733),刘克昌捐田八石,纳“早谷租”二十二石,“迟谷租”六十六石,又有租两石供渡船岁修费用。嘉庆间刘钜河捐田六石,纳租五十一石多,又将杨心瀚所捐田三丘(收租八石)从文昌祭田名下拔到渡口,作为“油艌费”。道光十一年(1831),杨振声捐银一百二十两,交“首事”生息,充作“岁修”费用。在此之前,蔡先广、先哲兄弟已捐置长沙城内铺屋二所,书院将其出租,收租金四十八点二四千文,作为经营渡口之用。
祭田是为解决书院祀事费用而设置的。明代见于记载的只有道乡祠祭田四十亩,到清代增加了文昌阁祭田六石,收租四十一石;三闾大夫祠祭田十石,收租一百石。到同治六年(1867),郑敦谨等又捐款四十千文,交三闾大夫祠住持收领生息,作为欧阳山长祠的祭祀费用。岳麓书院在清代设祀很多,地方政府每年从道库拨银若干以资香火,但仍“不敷备办”牲礼,“每值丁祭,系肄业诸生捐资助亨,丰俭无定,久远难期”。嘉庆元年(1796),岳麓书院学生欧阳厚垣等人捐银二百两,交商以每月一分五厘生息,每年获银三十六两,以供春秋之祀费。
上述田额的设置,反映出清代学田建设的盛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岳麓办学规模之扩大。同时,我们还看到,这种“田”已扩大至商品经济领域,既有银钱发商生息的金融收入,又有出租铺屋的房产收入,与明代的货币地租相比又进了一步。这些款项,对于书院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如嘉庆七年(1802),湖南盐法道达明阿与布政使通恩合捐白银四千两,以月利率一分二厘交长沙、善化两县“典商”经营,每年获息银六百八十两,于是岳麓就扩招附课生三十五名,城南则扩招附课生二十五名,童生附课生十名。
学田支出
岳麓书院的经费开支情况已无法全面统计,但从下面两个材料也能窥知大概。一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陈宏谋以钦赏及借司公帑银四千两、节年余息银二千五百两,分交汉镇(汉口)盐商和湘潭典商以二分和一分五厘的利率生息,年获息银一千四百一十两,作为岳麓、城南二书院的经费;又两书院每年共收“学租”五百二十一石四斗多,每谷一石碾米四斗四升,共有米二百三十一石二斗多。巡抚陈宏谋制订了经费开支《条规》,其中岳麓书院常年开支如下表所示:
岳麓书院乾隆二十八年经费开支表
(注:此表根据陈宏谋《培养堂偶存稿》卷四十八《申明书院条规以励实学示》制作)
二是乾隆五十年(1785)六月,岳麓书院又增正课生员十八名,附课生十五名。到嘉庆七年(1802)四月,再增加附课生三十五名,这样岳麓书院生徒名额发展到正课生六十八名,附课生总计一百三十八名。生额扩大的同时,经费也不断增加,其间人事亦稍有变化,因而经费开支情况也随之有些改变。本着陈宏谋所拟《条规》的原则,书院重定规章,同治年所修《岳麓书院续志》卷一中载有《书院旧规》及《给发膏火章程》。这个章程大概从嘉庆七年起开始实行,咸丰十一年(1861),院长丁善庆再次重申,到同治间仍然执行,影响书院七、八十年。其主要内容列表如下:
岳麓书院清代后期经费开支表
从以上两表中,我们既可看到清代岳麓书院的发展线索,又可发现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教学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薪金悬殊很大,“教职”远远高于“行政”人员。以院长和监院言,他们分别是书院的教学与行政首领,如果不考虑监院作为教官的政府俸禄,仅就书院范围而言,院长的束修金就相当于监院全部膳资的十倍多,以总额论,院长的年俸要比监院多十三至十四倍。一个充当斋长的正课生,每年实际收入与监院不相上下。其他学书、书办等办事人员及门役斋夫等后勤管理人员的年薪比住院生徒的膏资还要少一倍。
第二、书院组织简单。书院只有院长、监院各一人,加产生于生徒中的斋长,教学行政人员只四人,其他勤杂人员也只有八到十三人,管理范围却是包括岳麓书院在内的整个岳麓山。
第三、从经费分配来看,馆师、生徒薪俸膏火和祭祀费用,可以视作“教学费”,而监院、书办、斋夫等人的开支,可看成是“管理费”。两相比较,可以看到书院经费的90%以上是用于教学,而行政管理开支还不到10%。此种经费开支比例,值得今日教育当局参考。
附:清代岳麓书院奖助学金评定细则
膏火(助学金)
每年“除度岁给假一月外”,正课生“每名每月给银一两”作为膏火,“给食米三斗以为饭食”;附课生“每月课期二次,给纸笔银五钱,应一课者减半”,“不给食米”。后来附课的纸笔银也称膏火。
花红(奖学金)
考试成绩优秀者发给奖赏花红,“毋论正课、附课,凡考前列一体奖赏,一等不过五六名,二等倍之”。具体而言,官课奖赏由各衙门“各自捐给”:
◆ 巡抚的院课,一等首名奖银八钱,余名五钱,二等四钱。
◆ 两司、两道课,一等首名奖银五钱,余名三钱,二等二钱”。
◆ 山长每月十八日主持的馆课,“奖赏之数与司道同,由教官动支经费”,即在书院的常年经费内开销。
◆ 每逢乡试之年,所有正课生“每名给卷资银一钱二分”。
◆ 除此之外,道光十一年(1831)九月,巡抚吴荣光以公帑一千两发商,以每月一分生息,“统以每科八月前所得息银”作为“中式花红”,奖励岳麓、城南两书院乡试中举者,凡中式者按人均分,举人一份,副榜减半。
岳麓正课生每月至少有膏火银一两、食米三斗,而岳麓门夫、堂夫、斋夫等员工,每名每月总计只发工食银六钱、食米二斗。两相对照,岳麓诸生地位之高不言自明,如果考虑诸生考课奖赏、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食量大小、员工工食可以保证其基本生活,甚至要养家糊口等因素,则称岳麓正课生为当年“白领”阶层,亦不为过,此所谓尊重知识,落到实处,一点也不虚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