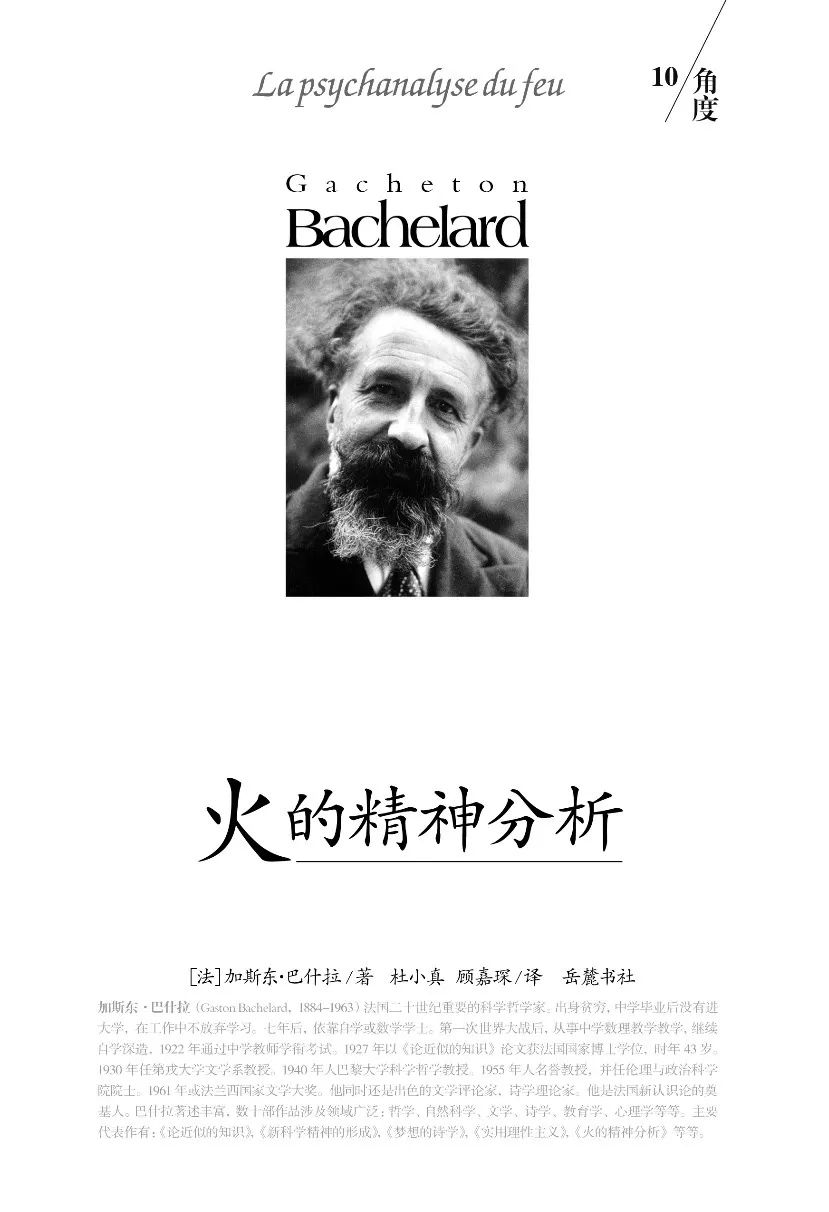作者 加斯东·巴什拉(法国)
翻译 杜小真 顾嘉琛
◆ ◆ ◆ ◆ ◆
也许人们在此能够把握住为了对客观知识进行精神分析我们所建议要遵循的那种方式的范例。这就是在经验和科学知识的基础本身找到无意识价值的行为。因此,我们应当指出这种相互的光芒,它不停地从客观的和社会的知识射向主观的和个人的知识,反之亦然。应当在科学试验中指出孩童试验的痕迹。这样,我们将有根据地谈论科学精神的某种无意识,谈论某些事实的相异性质。这样,我们将在对特殊现象的研究中看到在各种不同领域所形成的信念的会聚。
因此,人们也许并没有充分注意到火与其说是一种自然存在,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存在。要弄清这种观点的依据,无须发挥火在原始社会所起作用的论点,也无须强调保持火不灭的技术困难,而只要对文明精神的结构和教育进行研究就足以作出积极的心理分析。事实上,对于火的尊重是一种受教诲后的尊重,而不是天生的尊重。我们把手指从蜡烛的火焰上缩回来的那种反应在我们的认识中不起任何有意识的作用。我们甚至会感到惊讶,人们在心理学初级读物中如此重视这种反应,在这些书中,它被当作对某种反思的反应,对于最粗暴的感觉的认识的不间断的介入。实际上,社会的禁止是首要的。自然的经验不过是次要的。目的在于提供未预料到的物证,因此也是过于晦涩的以至不能建立起客观的认识。烧伤,也就是自然的抑制,在证实社会禁止的同时,在孩童心目中只是赋予父母的智慧以更大的价值。因此,在孩童有关火的认识的基础上,有一种自然的和社会的干扰,而社会在这种干扰中几乎总是首要。如果对针刺与火熨进行比较,人们也许会更好地理解这一点。这二者都会引起某些反应。为什么针尖不会像火那样成为受到尊重与惧怕的事物呢?这正是因为社会对针尖的禁止远不能同对火的禁止相比。
尊重火焰的真正基础是:倘若孩童把手伸向火,父亲就会用尺子打他的手指。火打人,而无需烫人。不管火是火焰还是灼热,不管是油灯的火还是炉灶的火,父母始终是同样警惕着的。因此,火从一开始起就是一种被普遍禁止的事物,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社会的禁止是我们对于火的最早的普遍认识。人对火的最初认识是不要碰它。随着孩子长大成人,禁止也精神化:打手心由训斥代替;训斥又由火灾危险的故事所代替,由天火的传说所代替。这样,自然现象很快地被纳入社会的、复杂的和模糊的认识中去,在这些认识中并无什么天真的成分。
于是,由于抑制首先是社会的禁止,个人对火的认识问题是一个巧妙的不服从的问题。当父亲不在身边时孩子想学他父亲的样,像个小普洛米修斯那样偷火柴。他奔向田野,在洼地同他的小伙伴一起建起了逃学的家园。城里的孩子很少见过这种在三块砖中燃着的火,也不曾尝过油炸黑刺李和烤在火上的滑腻的蜗牛。城里孩子不懂得这种普洛米修斯情结,而我经常感觉到这种情结。只有这情结能使我们懂得本身十分贫乏的火之父的传说为什么受到关注。此外,不可匆匆地把普洛米修斯情结和经典的精神分析的俄狄浦斯情结混为一谈。当然,在关于火的遐想中性的成分尤为强烈,我们下面还将对此进行阐述。然而,也许最好还是以不同的方式指明无意识信念的各种各样的细微差别,尽管随之会看到各种情结是那样相似。对我们提供的客观认识进行精神分析的好处之一,似乎就是对一个比原始的本能在其中展开的领域更浅近的领域进行审核。因为这个领域是中间的领域,它对清晰的思想、对科学的思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知道和创造是人们在自身加以标志的某些需要,而无需将它们同力的意志必然地联系起来。在人的身上有一种真正的知识性的意志。当人们将理解的需要绝对依附于实用原则时——这正如实用主义和柏格森主义所作的那样,人们便低估了理解的需要。因此,我们建议把所有一切促使我们同父辈懂得一样多、比我们师长懂得更多的倾向都归在普洛米修斯情结我下。然而,正是在支配对象的过程中,在完善我们的客观认识的过程中,我们才有希望使自己更明确地达到我们曾称羡的父辈与师长的知识水平。由更强烈的本能建立起的优势必然吸引着数量更多的人,但应当由心理学家进行分析的精神则会更少。如果纯知识性是例外,它仍然标志着人类特有的演进。普洛米修斯情结是精神生活的俄狄浦斯情结。
作者:加斯东巴什拉
(Gacheton Bachelard,1884-1963)
法国二十世纪重要的科学哲学家。出身贫穷,中学毕业后没有进大学,在工作中不放弃学习。七年后,依靠自学获数学学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事中学数理教学,继续自学深造,1922年通过中学教师学衔考试。1927年以《论近似的知识》论文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时年43岁。1930年任第戎大学文学系教授。1940年人巴黎大学科学哲学教授。1955年任名誉教授,并任伦理与政治科学院院士。1961年获法兰西国家文学大奖。他同时还是出色的文学评论家,诗学理论家。他是法国新认识论的奠基人。巴什拉著述丰富,数十部作品涉及领域广泛:哲学、自然科学、文学、诗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等。主要代表作有:《论近似的知识》,《新科学精神的形成》,《梦想的诗学》,《实用理性主义》,《火的精神分析》等等。
《火的精神分析》:(La psychanalyse du feu )
在这部诗学论著中,巴什拉明确用启发传统哲学和古典宇宙论的物质要素的符号标出想象的不同类型。在想象的王国中,可以规定一种四元素的规律,这个规律按照与火、空气、水和土的关系排列不同的物质想象。这论证的是建立在理性心理学基础上的想象理论。对火进行的精神分析是证明巴什拉的科学精神的具体应用。他通过对火的分析,希望把知识与对物质的想象统一起来。从理性精神分析的角度对普罗米修斯情结、恩培多克勒情结等进行分析,描述了火从原始形象到生死本能精神的发扬,再到火象征的光和热对人的灵魂的启迪和升华,直至最高的火的纯洁化的生命高度的过程。
译者:顾嘉琛,1941年生,江苏吴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曾发表过《系统法语语法》,主要译著有:《巴什拉传》,《重负与神恩》,《哥伦布传》,《看,听,读》,《文学与感觉》,《阳光与阴影》,《期待上帝》等。现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杜小真,1978年9月起任教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1993被破格提为教授,1999获博导资格。现兼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中国现代西方哲学会理事,国际哲学学院通讯教授(总部巴黎),法国巴黎七大葛兰言中心成员,加拿大魁北克哲学会《哲学》杂志学术委员会成员。巴黎高师法国当代哲学研究所成员。曾多次在法国、瑞士、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做访问学者、客座教授、访问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