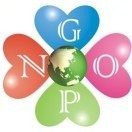每个周末,凤凰社区足球俱乐部的小球员们都在山坡上训练,家长们也聚集在这里,既是训练,也是一场社区聚会。(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图)
报告发现除了少数明星基金会,更多的社区基金会生存状况堪忧,“相当一部分社区基金会的实际发展情况可能不容乐观,甚至‘名存实亡’”。
活跃度很低的基金会主要问题是内在发展动力缺失。运作不积极的主要原因是:“当初倡导的人、后来带头做事的人、实际执行的人他们都不是一批人”,“因为运营的人可能是被动的,且后期没有足够的激励机制”。
2019年1月前,《中国社区基金会行业发展研究报告》(以下简称社区基金会报告)调研团队向141家社区基金会发出调研邀请,没想到50家社区基金会电话无法拨通,22家表示必须通过政府上级部门允许才可以参与调研。
报告撰写人郭嘉祺很无奈。她以志愿者的身份为公益机构提供咨询服务时,对社区基金会产生兴趣,当时计划通过调研摸清当下社区基金会实际运行的状况。
“社区基金会”是公益领域中基金会的一种类型,可以简单理解为立足于本社区,以“本地资源解决本地问题”的基金会。它可以成为社区资金的“蓄水池”,有了它,邻里突发大病、志愿者小分队购买物资、社区老年大学建设乃至小区里的广场舞大赛都可以从中得到资金支持。
近年,社区基金会广受关注。2014年起,深圳、上海、南京多地试点,发展社区基金会逐步上升为国家层面推动的政策,其数量快速增长。尤其是2017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其中写入了发展社区基金会的内容。
在政策制定者的眼中,它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能够补足社区发展的资金短板,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搅活社区”。
但郭嘉祺近两年接触社区基金会,却发现“空壳”现象,“有相当一部分社区基金会的实际发展情况可能不容乐观,甚至‘名存实亡’”。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唐有财也认为,尽管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对社区基金会热情很高,但行政驱动带来的动力不足、资源限制、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束缚着社区基金会的进一步发展。
为社区治理而生
凤凰社区位于深圳的“关外”地区,是高铁进入深圳的第一站。出了快捷高效的高铁站,开车十分钟,就到了凤凰社区门口,这里令人意外地节奏缓慢,浸润着邻里温情。
一座知青楼被改造成社区公共空间,内设老年协会、社工驻地、免费艾灸等丰富的活动场地,还设有社区厨房。
“Comeon!”身形壮硕的外教俯下身来,等待一名小男孩的答案。2019年9月的一个周末,凤凰社区的社工邀请他在活动室给孩子们上英语课。
这里不是什么知名景点,却因为“社区营造”“社区治理”被各地政府街道人员熟知,成为必到的打卡点。“我们这里很多人来,一个月好几拨。”小巷的一家越南肠粉店外,坐着闲聊的居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而打卡的起点就是2014年发起成立的凤凰社区基金会。
“社区基金会”概念是舶来品,诞生于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当时,随着工业化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新兴工业城市的许多贫民窟社区成为矛盾的集中点。为解决这些问题,社区基金会应运而生。
2009年,国内首家以“社区基金会”命名的千禾社区基金会落地广州。更早之前成立的桃源居社区基金会被视为中国第一家社区基金会,它由当地开发商捐资一亿元注册,主要支持社区里的公益项目。
2013年,上海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成立,社区基金会开始了以政府驱动为主的探索。在2014年深圳慈展会上,时任深圳市光明新区党工委书记张恒春曾向来自各地的公益人士详细介绍了深圳光明新区率先试点的五家试点社区基金会,其中就包括凤凰社区基金会。
五年后,凤凰社区基金会理事长曾木养回想起创办时的情形,笑称自己也是一知半解,当时“不知道具体怎么做”。
凤凰社区是典型的侨民社区,当地人口不到两万人,户籍人口约2000人,超过72%是越南归侨侨眷。曾木养是当地的第一代归侨,3岁回国,早在2009年就牵头筹办当地的社康中心,让附近居民享受就近医疗服务。社康中心闲置的楼层,也进一步被开发为图书馆、健身馆和少儿培训中心,皆为社区的公益服务。
无奈的是,图书馆和少儿培训中心因为没有注册,2011年因涉嫌非法办学而关停。“想要一个合法身份做公益”,曾木养当时认为社区基金会试点是一个机会。
按照当时的政策,曾木养需在一周内组建好理事会,并筹到100万注册资金。“现在有个能解决你每年捐款又过不了账的方法”,曾木养首先想到说服当地企业家曾文波。曾文波每年拿出十几万慰问老人,从没听说过社区基金会。之后,曾木养又拉来其他企业家担任理事,7人的理事会一周内凑成了,加上政府推荐的两名理事,基金会的框架也就搭好一大半。
政府大力推进
作为改革前沿城市,深圳2013年起推出系列措施推进社区基金会的目的很清楚,为社区自治补上资金短板。
当时,深圳已有社区党委、居委会、社区工作站及社区服务中心等机构,这些机构是由政府投入运作,居民议事会则由于缺乏资金,难以对社区自治起到实质性作用。
而公益领域的专家们对社区基金会的期待更高。“发挥着社区‘慈善枢纽’和‘公益引擎’的作用。”广州社会组织研究院博士胡小军认为,社区基金会可以助力回应社区多样化需求,同时“通过搭建捐赠平台、实施战略资助,培养社区人才”。
唐有财的观点也类似,“(社区基金会)有点类似心脏,提供各种社会治理的血液、资源。”2014年,时任深圳市民政局副局长余智晟曾表示,社区要去行政化,社区基金会其实是改革社区原有的管理方式:“政府要从社区往回退,把社区的空间还给社会。”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社区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来自企业捐赠、政府拨款。政府担心不能达到基金会注册资金的200万元门槛,又主动将注册资金降至100万元,由此催生了一批政府倡导型的社区基金会。
5家深圳首批试点社区基金会注册成立。“从章程、管理制度到项目检测、企业冠名,在当地党工委支持下,均给出了地方实践的指引手册。”郭嘉祺在报告中分析。
深圳系列推动措施,开了全国社区基金会制度化先河。当时有媒体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三五年内,深圳六百多个社区,个个都会有一个社区基金会了。”这将占据全国三千多家基金会的六分之一。
之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南京、杭州、成都、西安等城市借鉴推广深圳经验,先后启动社区基金会的培育孵化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政府引导或驱动成立的社区基金会占据主体地位。目前,全国登记注册的社区基金会有158家,大部分是由政府倡导发起的社区基金会,多数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上海、广东和江苏数量最多,上海有80家,广东有37家,其中深圳占了32家。
胡小军在研究中表示,主要由政府引导或驱动,是中国社区基金会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显著特征,也是短期内实现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社区基金会的“危”与“机”
理事一拍即合,企业捐赠资金,政府大力支持,凤凰社区基金会在短期内有序地运转了起来,直到次年的一场意外来临。
2015年底,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的红岰余泥渣土受纳场发生了特别重大滑坡事故,致多栋楼房倒塌、被埋,造成73人死亡、4人失踪。
滑坡事件后,红岰村整体迁离,连带着大部分企业也搬走了,企业一走,社区基金会的资源就没了,面临断粮之困。除此之外,凤凰社区的环境、文化等都遭到严重破坏,各种治理问题凸显。
“以为要做不下去了。”曾木养坦言当时压力很大。基金会秘书长凌六妹回忆起那段“艰难时光”,基金会开会的频率增加,大家在下班后赶来开会,主要讨论如何筹款、失业人员增加和社区居民心理如何安抚等问题,会议往往持续两三个小时。
“曾理事头发都愁白了。”凌六妹看到了曾木养的焦虑,没有专业的人士指导,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帮助困境中的社区居民。
在社区基金会报告中,这些问题很常见。报告认为,社区基金会主要面临着三大挑战:政策与环境带来生存的不确定性,整体社区慈善生态不成熟和居民公益参与度不足以及专业人士匮乏。
唐有财发现,社区基金会的人才要求高,需要基金会的专业管理能力,同时也要具备对社区的认识,“既要懂社区,又要懂基金会,这样的人少之又少”。
而社区基金会报告指出一个更为制度性的问题,基金会的管理费用要求不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目前的社区基金会的资金池小,人员工资少,而工作任务又很重。
资源、人员问题,在滑坡之后成为凤凰社区基金会活下去的巨大压力。
好在凤凰社区基金会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深圳市民政局及光明新区管委会于2016年共同启动凤凰社区管理治理计划。这项计划既包括当地社区重建,也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社区营造实验。
在政府的帮助下,凤凰社区首次引入了专业团队,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工作学院作为计划总体设计者,承担方案总体设计、社区营造人才培养、规划及吸纳社会组织参与、开展专业研究工作、宣传等等。
2019年9月底,南方周末记者在凤凰空间的一面白墙上,看到参与凤凰社区建设的“凤凰社区营造联盟”的成员图标: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工作学院、凤凰社区工作站、凤凰社区基金会、凤凰社区老年协会等共二十余家。
在外部力量的强势助力下,凤凰社区的内在力量逐步激活,凤凰社区成为“明星社区”,各地的街道工作人员、民政负责人纷纷组队前来参访。
但同期试点的光明新区五个社区基金会中,部分社区基金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外部支持,南方周末记者尝试联系采访时,对方表示社区在拆迁,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无法接待。
“盆景摆设型”基金会
“我们想知道,更多没有被关注到的一百多家社区基金会在做什么?”在调研中,郭嘉祺和团队发现除了少数明星基金会,更多的社区基金会生存状况堪忧。
唐有财则在解释上海社区基金会存在一种现状时,将其取名“盆景摆设型”。
2017年,唐有财受街道邀约,兼任上海凌云社区基金会秘书长。一番实践后,他发现,上海有一类社区基金会,主要是街道出资,应政策要求后成立,以党建或者行政化的方式来筹款,而不是像真正的社区基金会那样运作。因此,其可持续性成为挑战,活跃度很低,有些几乎不运转。
唐有财认为这类活跃度很低的社区基金会主要问题是内在发展动力缺失。“为什么运作不积极?”他分析,“因为当初倡导的人、后来带头做事的人、实际执行的人他们都不是一批人”,“因为运营的人可能是被动的,且后期没有足够的激励机制”。
能不能找到一个想做事的人来带头运营呢?“这点非常重要”,唐有财认为,但是总体来说,带头人的选拔还面临信任问题,公益事业本身背负了一定的道德要求,“好事不能做出问题来”。
于是基层政府将风险问题看得很重,社区基金会的带头人必须是政府高度信任的。但社会创新需要空间,需要放手,甚至允许犯错。唐有财认为,两者之间恰恰是存有矛盾。
唐有财向南方周末记者举例,他曾邀请一些社区基金会秘书长参与社区基金会论坛,结果秘书长需要向街道分管领导请假,领导不批准不放行。更为严重的是街道直接指定社区基金会每年的工作安排,“要花多少钱,怎么花”都由街道指定。“在这种模式之下,他(有能力的带头人)肯定就不愿意(管理社区基金会)”。
这一问题,胡小军等学者在《中国社区基金会2018年发展研究报告》中也曾指出:街道等通过直接出资或动员等方式发起的社区基金会,成立之初就面临对政府权力的依赖性较强、社会化程度较低、内在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加之基层政府的资源动员限制和能力限度,社区基金会可能出现“空壳现象”。
该报告同时认为,企业出资的社区基金会同样也可能面临内部运作失灵的情况。
培育社区活力是关键
2019年初,成都新民社会组织发展中心曾撰文描述社区基金会运营管理中的“四大”误区。
文章认为,社区基金会的功能可能在实际运作中被无意夸大了。在国家文件中,社区基金会的基础性功能是资金筹集,但实际上“它几乎成为社区治理的‘灵丹妙药’”,甚至可能导致社区基金会与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或其他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功能重合。
而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抛开政府主导式的发起,社区基金会的发展最终还需要培育社区自身的活力。
郭嘉祺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国内的社区慈善生态不成熟,大家不清楚“社区公益”是什么。调研中,郭嘉祺的母亲曾提出疑问,她能够理解电视上那些扶贫赈灾送“免费午餐”是公益,但社区里的亲子阅读也算公益吗?扫楼道算吗?资助广场舞队也是吗?
曾有基金会秘书长在调研访谈时说,社区有居民发起阅读活动非常热闹,社区基金会主动出资支持他持续做下去。对方拒绝了,害怕不“纯粹”。
调研中,郭嘉祺看到了社区基金会的温情与付出,尽管人员少,他们在社区里仍然做了很多事,清扫楼道、挖掘社区历史、开展亲子阅读等等,一年十多个项目。“这些是很暖心的”,但她也意识到社区需要更长时间的培育,“需要深耕”。
“基金会所做的事情是实实在在的接地气的事情,是社区居民能够感受到的项目。”胡小军认为运作良好的社区基金都有一定规律。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当天是周末。凤凰社区的“绿茵追风足球俱乐部”在山坡上训练,小球员们颠球、绕桩、实战比赛,玩得大汗淋漓。有家长跟着下场踢球,鼓起的肚腩挤着球衣,也玩得不亦乐乎,玩累了,他们就坐在边上为孩子们喝彩。
凤凰社区曾有踢足球的传统,1990年代没有场地,大家在种田之余就在水田中踢“野球”,后来中断了。2015年,凤凰小学培养出第一批小球员后,社区基金会开始支持他们外出参加比赛。
每逢周末,小球员们都会固定训练。这样的训练,不仅是踢球,也是他们久违的社区“聚会”。
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 刘怡仙 特约撰稿 吴采倩 刘炜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