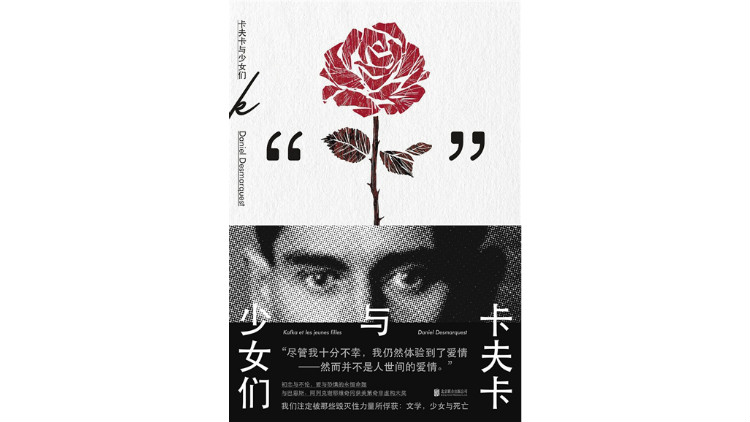撰文 | 远子
在马克斯·布罗德的笔下,卡夫卡是一个“非写不可”的文学圣徒。他的整个人生都建筑在文学事业之上,生活中再微不足道的时刻,也是他“创作冲动的标志和证明”。除此之外,布罗德还喜欢反复提醒读者留意卡夫卡眼中闪烁的热光:“宁可咬住生活,也不要咬自己的舌头。”“不要绝望,对你的不绝望也不要绝望。在一切似乎已经结束的时候,还会有新的力量,这正好意味着,你活着。”他说卡夫卡迈出了灰暗的绝望,走向明亮的绝望。
但在达尼埃尔·德马尔凯的传记《卡夫卡与少女们》里,卡夫卡却变得暧昧和复杂起来。在那本疑为伪作、但受到布罗德充分认可的《卡夫卡谈话录》里,卡夫卡几乎就没有谈过女性。但在这本书里,我们发现,卡夫卡终生都在绕着女人打转,简直就是一个靠吸少女的精气而存活的文学魔鬼。对于部分女性读者而言,这里的卡夫卡可能会让她们大失所望,甚至极其反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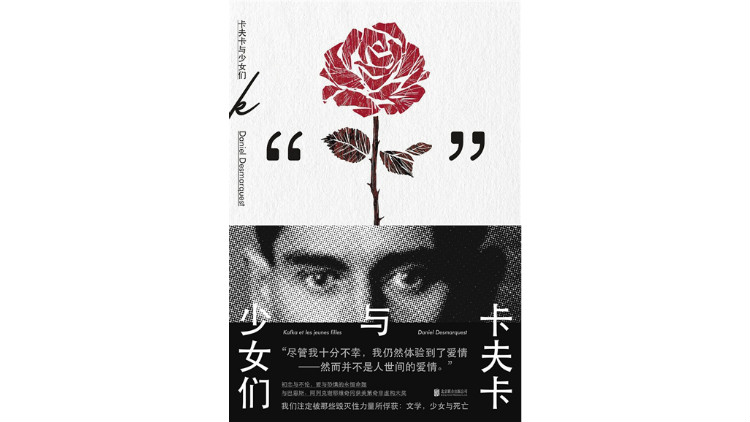
《卡夫卡与少女们》,(法)达尼埃尔·德马尔凯著,管筱明译,一頁folio|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9月版
不理解少女的风情
瞧,这个人。他处处留情,经常脚踩两只船,有时是三只。他用美妙的修辞来引诱少女,用才华来表达爱意。而在点燃对方的激情之后,他却又无法交出相等的火焰。所以他一再陷入“爱的险境”:“我爱一个姑娘,姑娘也爱我,可我不得不离开她。”他坚信“灵魂比肉体更能热烈而疯狂地相拥”(福楼拜语)。与肌肤相亲相比,他总是更愿意用书信交流。他用长篇大论来抚摸和折磨恋人,用她们哭泣的血“驱动”文学这架“机器”。作者德马尔凯甚至认为卡夫卡的大多数作品没有写完,是因为他从少女那里得到的光辉太过短暂,养料不足。
当然,书信里必须不时夹带照片,最好是童年时的照片。如果没有菲莉斯那张可爱的童年照,我们有理由怀疑卡夫卡甚至不会做出订婚的决定。永恒的少女是指引他升入文学殿堂的可怜的阶梯。一个想要登上峰顶的人必须忘掉身后的阶梯。
由此,我们想到一个本书作者并未明确提及的问题:这种依靠盘剥女性的情感来成就自我的“吸血”行为是否构成道德上的污点?
密伦娜,与卡夫卡相识于1920年。两人互相通信约一年半,数量可观,且极具文学性。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戳破一些泡沫。所有泡沫中飞得最高的那一朵无疑是爱情。在写给密伦娜的信里,卡夫卡直言不讳:“我爱的不是你,远不是你,而是我的生命,是通过你体现出来的我的生命。”这句并不动听的情话有着自私的真诚:如果我无法在你身上看见我自己,那么我还能爱你吗?生活是可悲的,但如果两个相爱的人都认同这一点,生活也许就没有那么凄凉。卡夫卡执迷于这种相认的瞬间,却忘了公认的爱情是拒绝不幸的。他并不理解少女的风情,而一个人是无法占有他所不理解的事物的。于是,他只能在爱情的大西洋上流亡,永远无法抵达幸福的“美国”。最后一个少女朵拉是一个例外,因为在卡夫卡的弥留之际,他已经没有力气在女人的眼睛里发现自己,他已经不再写作。
朵拉,卡夫卡最后的情人,和卡夫卡相识于1923年,两人相伴至卡夫卡1924年6月3日去世。
对女人的恐惧与迷醉
严格来讲,这世上有多少对恋人,就应有多少种爱情。但人们更愿去相信一种独立于所有解释之外的爱情,在这种情感之中,时间的刻度是“永远”,性只是点缀,所有要素都必须是欢快的。人们常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却忘了爱情也在扼杀婚姻。守墓人卡夫卡选择在夜里睁大双眼。他“给予性欲很高的地位”,肯定爱与性之间的模糊地带。对女人的恐惧与迷醉交替支配着卡夫卡。肉体是救生圈,更是旋涡。在《城堡》里,那对恋人“就像两只在地上拼命刨来刨去的狗”,这种近乎惊悚的画面在他的小说里随处可见。卡夫卡也许会认同波德莱尔的判断:“爱情唯一而崇高的快乐在于确信自己在作恶。”由于对性爱之中的无聊与邪恶过于敏感,卡夫卡比同代人更早地进入了现代。
卡夫卡的夜晚因而是一个现代人的夜晚。“如果你说你爱我,我会惊恐万状;如果你说你不爱我,我会立即去死。”“有些人声称,因为有了太阳,我们才没有悲伤。他却认为,因为我们悲伤,所以没有太阳。”……也许我们可以说,所有被这些格言触动的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卡夫卡之夜。
这种体验很容易遭到不解的蔑视,卡夫卡的父亲对自己的儿子便充满了这样的困惑:你没有上过前线,也没有经历过白手起家的艰辛,你甚至都没有饿过肚子,那么,你所说的痛苦到底是什么意思。坐在“靠背椅上统治世界”的父亲们未曾想过,这世上除了经济底层,还有精神底层。只不过和经济学的定义相反,在精神世界里,越丰富越饱满的人反而越是一穷二白。在逃离父母的尝试中,在抗拒工作的纠结中,在恐惧婚姻的寒颤中,卡夫卡感到自己一直活在“冥界的前厅”里,在“用一生来死亡”。
尤莉叶,1919年曾与卡夫卡有过短暂婚约。
在写给另一个少女闵策的信中,卡夫卡将生活之深渊说得更为透彻:“每个人身上都带着自己的魔鬼,它折磨他,毁掉他的夜晚。这也说不上是好是坏,因为这就是生活:没有魔鬼,也就不可能有生活。因此,你内心诅咒的东西,其实就是你的生活。”也就是说,要想顺利度过这样的卡夫卡之夜,必须承认并直面心底的魔鬼。
守住人的边界
我们无法斩妖除魔,却可以拥有一个驱魔仪式。对卡夫卡而言,这个仪式便是写作。不幸不会增加一个人的价值,但书写不幸可以,因为它能帮助人理解不幸。
卡夫卡相信一个应付不了生活的人,除了“用一只手挡开笼罩这命运的绝望”之外,还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这样的人“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谈话会马上并且永远失去其重要性,但如果将其记下来,“有时却会获得一种新的重要性”。他痛恨“与文学无关的一切”,为此他将写作的形式推演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了写作我需要独处一隅,不是像隐士,那还不够,而是像死人。”他必须像活死人一样住在地洞里写作,不这样做,他便无法“拂去寻死的念头”。
对卡夫卡而言,文学从来不是爱好,而是生命,是使命。他将文学发展成了宗教,写字桌是他的圣洗池,写字是他的祈祷,朗诵是他在唱赞美诗。于是,在卡夫卡与少女的情感纠葛之中,真正的问题也许只有一个:一个取悦于女人的人,是否还能取悦于神?卡夫卡摊开双手,表示自己无从作答,他只能继续“彷徨于无地”。“我写作不同于我讲话,我讲话不同于我思考,我思考又不同于我应当思考的方式。如此下去直到进入最深处的黑暗。”他是一个靠无能取胜的文学英雄,也许是唯一的一个。克尔凯郭尔的自白放在他身上似乎更为合适:“母腹中的十个月足以使我衰老。”
我们很难去验证用写作来抵抗死亡之侵袭的有效性,但至少可以肯定,卡夫卡借助写作从死中逃了出来。但凡有谁承受过卡夫卡内心煎熬的哪怕十分之一,恐怕早就无法维系生命。而他不仅活到了最后一刻,还一直坚持写作,一直在寻求爱并给出自己的爱。这本身就已是生命的奇迹,或者说文学的奇迹。
那么,道德问题呢?世人看起来没有污点,也从不犯错,也许只是因为他们从来不去思考任何值得思考的问题,也从不去做任何值得做的事情。他们从未真正从“他们”退回“他”之中,因而“他们”总是可以战胜“他”,不是“通过对他的反驳”,卡夫卡是不可反驳的,而是通过证明他们自己的力量优势。一个在过于饱满的精神世界里终日战栗的人,得到的总是空泛的议论。
卡夫卡与菲莉斯,1917年。菲莉斯和卡夫卡相识于1912年,两人两度订婚,又解除婚约。
卡夫卡想死,却又想要像少女一样活出真正的人味。在与少女的交往中,卡夫卡并不干净,但他渴望圣洁。这里的转折看似轻易,却像“地球运行轨道的半径那样长”。一个人与一群人的区别,便体现在这种转折之中。也许我们可以说,正是在对梅菲斯特之重力般引诱的克服中,卡夫卡守住了人的边界,并保持了仰望的姿态。他走出滂沱的室内,迎向倾盆大雨,他在雨中滑翔,但是且慢,“就这样,挺直身子,等待突然而至和无穷涌动的阳光吧”。
撰文:远子
编辑:张进、徐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