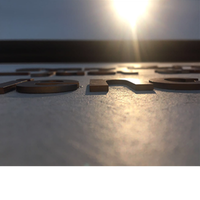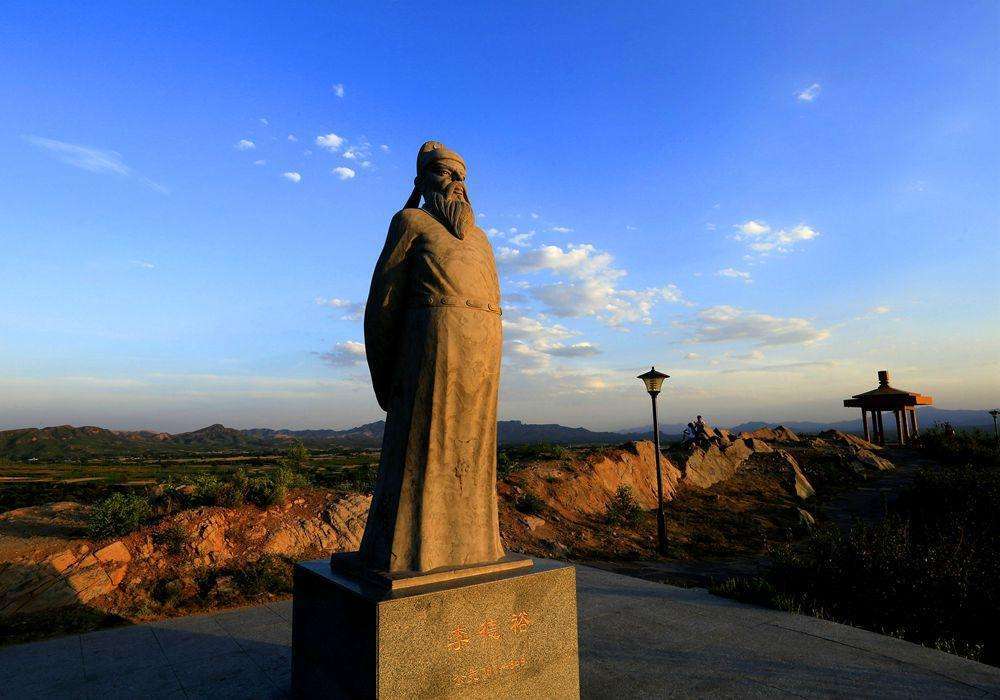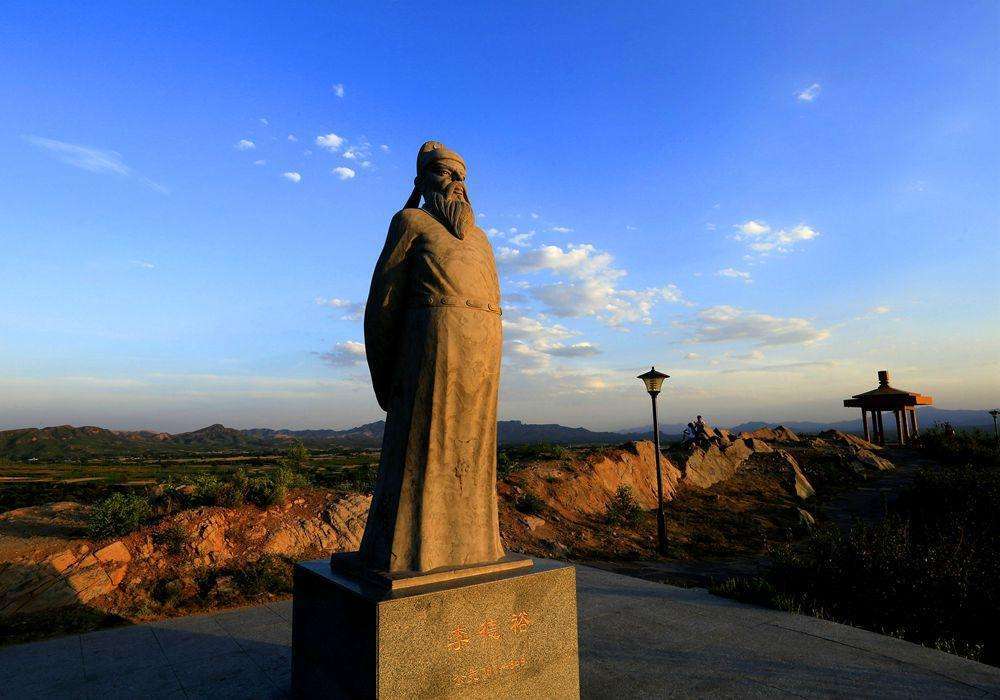
唐代诗人李贺的父亲名叫李晋肃,“晋”、“进”同音,李贺为避家讳,不能应进士举,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很不可理喻,所以经常被视作李贺遭人嫉妒陷害的明证。
避皇帝的讳大家都听说过,也都好理解,可唐代避家讳是怎么一回事,少有人提及,韩愈为李贺所写的《讳辩》(也有写作《讳辨》的)是第一手材料:
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辞。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
这里讲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韩愈写信劝李贺举进士,有人说李贺父名晋肃,不应该举进士,韩愈对此大为不满,以雄浑的笔力为李贺作了辩解。
他解释说:按唐代律令,二名不偏讳,比如孔子的母亲叫颜征在,那么孔子单独说“征”字或者“在”字,都不算犯讳,只要不连着说“征在”两个字就行了。同时嫌名不必避讳,比如同音字、近音字就不用避讳。晋、进只是同音,李贺举进士既不犯二名律,也不犯嫌名律。
接下来,韩愈大发议论,他反驳说,假如父亲名“仁”,难道儿子连人都不能做了吗?
他还引用孔子、曾参、汉武帝、吕后乃至唐朝皇室的例子,认为只有宦官宫妾才会如此极端地避讳,结论是,无论参照经典还是律令,李贺参加进士考试都不存在避讳的问题。
韩愈在后世地位很崇高,大家都按照他这篇文章来理解避讳,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可是根据唐代的实际情况,避家讳不仅仅是合不合法的问题,更是一条重要的社会规则,上文中有两句对话,向来被人们忽视:
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
皇甫湜明确提出,你这样做,和李贺都会得罪于世人,韩愈也明明白白回答说,“是”。说明韩愈本人也知道,他写这篇文章,是违背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的。
《旧唐书》作过一番这样的评价:
“李贺父名晋,而愈为贺作《讳辨》,令举进士……此文章之甚纰缪也。”
《旧唐书》编于后晋时期,去唐不远,社会风俗也相近,可见站在当时人的角度来看,韩愈的辩解纯属胡搅蛮缠。
韩愈生当德宗至穆宗时期,我们举几条同一时期的史料,看看当时的人如何避家讳。
其一是冯宿的案例,他和韩愈年龄相差一岁,又同在张建封幕府里工作过,很适合拿来比较。《旧唐书·冯宿传》记载,冯宿的父亲名叫冯子华,后来冯宿被委任为华州刺史,他以避父讳为名,请求换职位,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
其二是李涵,他父亲名叫李少康,李涵被任命为“太子少傅”时,有人说他应该避父讳,所以改任为光禄卿。
这两例都是避父讳的典型案例,朝廷为了让臣子尽孝,不惜为他们改任官职,证明在同字避讳的问题上,无论朝野,态度都是很一致的,
至于同音避讳,韩愈说得不错,确实没有律令规定,可并不意味着这项规则就不重要。
唐代赵璘《因话录》记载,与韩愈同榜进士,后来做过宰相的崔群,遇到过这么一件事情:
崔相国群为华州刺史。郑县陆镇以名与崔公近讳音同,请假。崔视事后,遍问官属,怪镇不在列,左右以回避对。公曰:“县尉旨授官也,不可以刺史私避,而使之罢不治事。”召之令出。镇因陈牒,请权改名瑱。公判准状,仍戒之曰:“公庭可以从权,簿书则当仍旧,台省中无陆瑱名也。”其知大体如此。
崔群出任华州刺史,僚属中有一位县尉叫陆镇,因为名字与崔群家讳同音,开会时只能请假。崔群与之商谈之后,陆镇申请改名为陆瑱,崔群同意了,还表示只要公务场合改一改就可以了,公文上不用改。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崔群父亲名“积”,崔群所写的一则墓志铭则记载其父名“稹”,两字写法近似(积的繁体为“積”),从这个案例来看,稹字显然是对的。
仅仅因为与长官父亲的名讳同音,陆镇就得把名字改掉,崔群格外开恩,允许他改口不改字,赵璘还赞誉崔群“知大体”,言下之意,崔群、陆镇、赵璘都觉得改名理所应当。这种在今人看来简直丧心病狂的做法,在当时却是为主流价值观推崇的。
还有一个例子来自日本僧人圆仁的证词,他曾赴中国学习多年,后来用汉文撰写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他于开成三年(公元838年)跟随遣唐使初抵扬州,拜见过镇守扬州的李相公,这位李相公就是罢相后担任淮南节度使的李德裕,他比韩愈小二十岁左右,勉强算同时代人。圆仁在书中记载了一个细节:
李相公随军游击将军沈弁来咨问,兼语相公讳四字:“府、吉、甫、云”四字也,翁讳“云”,父讳“吉甫”。
李德裕的随从告诉圆仁等人,相公家讳为“府、吉、甫、云”四个字,且提到李德裕祖父名“云”,父亲名“吉甫”。
圆仁这里犯了个小错误(不排除是传话的人说错了),李德裕祖父叫李栖筠,而不是“云”。李德裕讳“吉、甫”两字好理解,讳“府”和“云”字,则应该属于同音之讳(府、甫同音,云、筠同音)。
崔群、李德裕都曾经任宰相,他们的家讳,僚属和辖区内的百姓(甚至路过的外国人)都要遵守,可见家讳的作用范围之广、威力之大,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李贺倘若去应进士举,确实会寸步难行。
避家讳的做法后来一直延续到清末,《红楼梦》里有一处描述林黛玉避家讳的情形,写得很到位,林黛玉的母亲名叫贾敏,且已经过世,所以林黛玉读书时,“凡‘敏’字皆念作‘密’字,写字遇着‘敏’字亦减一二笔。”
作者将林黛玉设定为出身世家大族,且修养很高的女性,特意用这句话来体现黛玉的懂礼数,这种春秋笔法无疑是很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