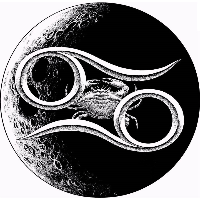选自《世界哲学简史》[美] 罗伯特·C·所罗门 著
梅岚 译/ 后浪丨江西人民出版社 / 2017
介绍哲学尤其是古希腊早期哲学,现在的标准说法是,哲学始于与神话——希腊流行文化中的民间宗教——的分离。 这种宗教包括奥林匹斯诸神(比如宙斯、赫拉、阿波罗和阿芙洛狄忒)以及许多希腊传说中的神话英雄和轶事。 请注意,我们通常只是把其他民族的信仰视为“神话”。 不过,希腊人有意识地区分了哲学与神话,并且把这种区分应用于自身。
在复杂的希腊社会,“信仰”分为很多等级,有对神话说明的完全接受,也有对其极为夸张、诗意甚至寓意的解释。 诗意的敏感性对于智慧来说是必要的,但智慧不能与世俗的真理相混同。 相信诸神的存在或多或少是切实的。 (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指控之一就是他“不信城邦的神”。 )然而,赫拉克勒斯、伊阿宋和阿尔戈英雄以及类似的历史寓言,在多数人看来不过是戏谑性的怀疑主义。 俄狄甫斯可能是真实的人物,《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中的人物(至少其中的凡人角色)也是真实的,这也没什么疑问。
希腊人为何编造奥林匹斯诸神与凡人之间尔虞我诈的神话? 据说,宙斯变成天鹅、牛和云甚至女性的丈夫,以各种方式追逐甚至奸污女性。 (这本身就是迷人的哲学难题,这个妇人因此而对她丈夫不忠吗? )神话人物变为树和花朵,有些还成为神罚的受害者——比如普罗米修斯(他由于为人类盗火而受罚,终日被一只鹰啄食肝脏)和西西弗斯(他被罚终生推石头上山,每到山顶,石头又因自己的重量滚落)。 有教养的希腊人似乎把这些神话当作道德(或不道德)故事,而不是神学教条。 这促使我们想知道没受过教育的人真正信仰什么。 第一批哲学家是在与迷信作斗争(这是启蒙哲学家的流行观点,他们自认为在重复这个过程),还是只不过在参与一项较为普通的事业? 或许,古希腊民众只是喜欢这些观念和形象所带来的娱乐,而那些认同他们的哲学家不过较为明确地表述了这种怀疑观点而已。
倘若我们要理解西方哲学的诞生,重要的是要谨慎对待哲学与神话之间被过于滥用的区分,这个区分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为了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和原创性而提出的。 人们认为复杂的希腊哲学源自流行(“俚俗”)的神话,并取而代之。 我们被告知,未经反思的神话与深思熟虑的哲学之间的差异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端,前者强调诸神,后者为“自然主义”的解释辩护。 神话持神人同形同性论,把人类特性向(我们认为)无生命的自然力量投射。 因此,古埃及人和地中海东岸的其他多数文化,通常根据人类行为来解释宇宙的起源和本性。 古希腊人则根据极为人性化的诸神的行动和情感来解释宇宙的起源和本性。 但是,从泰勒斯(公元前 625? —前 547? )和其他前苏格拉底的希腊哲学家开始,陈腐的故事仍旧盛行,不过解释变得更加科学、“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 这些早期的希腊思想家颂赞冷静的理性,强调物质原因,而不是幻想性的诗意解释或神灵在幕后的行为。
然而,这些过于简化和自吹自擂的观点经不起推敲。 因为,第一批希腊哲学家沉浸在神话之中,新颖的理性受到几何学的启发,但哲学中最伟大的突破——比如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做出的成就——完全拒斥对世界的唯物主义解释。 他们常常用谜语和寓言写作,更像神话诗人,而不像当代的科学教授。 哲学像科学那样提供切实的真理,这个观念一直受到怀疑。 现代哲学家(比如康德和黑格尔)也擅于使用隐喻和类比。 当然,科学本身是否也依赖于隐喻而不是直白的描述,这个主题远远超出了我们探讨的范围。
可以肯定,希腊哲学的起源也是西方科学的起源,但哲学不是科学(至少并不只是科学),而神话——赋予宇宙人格,使其具有理性的可解释性——也没有丧失它的魅力,这对于哲学家而言也是如此。 因此,诗意、神话的思考在哲学中仍然保留至今,这也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其他文化,尤其是并不像我们那样严肃对待科学的文化。 中国有比西方更为漫长的技术传统。 (比如,中国人发明火药、面条和眼镜比西方人早好几百年。 )但是,中国人对科学向来持实用主义的观念,尤其是儒家哲学,它更看重社会和谐而不是科学理论。 亚洲值得注意的技术史几乎与常常被理想化的“追求真理”没什么关系,与之相关的是健康的社会实用主义。 道教尽管也强调自然,但它实际上与科学毫无关系,佛教不仅认为科学是人类的大幻象,而且认为自然知识方面的进步观念也是人类的大幻象。
尤其在宗教哲学中,神话中的神灵与有血有肉的个体之间的区别非常大,远远超过神的模糊性所需要的。 希腊和印度的神灵很相似,都是形象模糊的人、超人或非人。 他们常常变来变去。 孔子和佛陀,与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相似,无疑是真实的人物。 (老子如果不是一个人,也会像荷马那样是几个真实的人物。 )耶稣是上帝的道成肉身,就此而言,作为人的耶稣与作为上帝的基督之间的明显矛盾,引发了贯穿整个基督教神学史的思想难题。
模糊性和类比是中国哲学的精髓,同时,儒家和佛教的“神灵”是个体的人,而不是基督这样的上帝化身,也不是为了教导我们真谛而化身为人的诸神。 因此,倘若谁认为这些神是与人同形同性的,就显然偏离了正题。 尽管古代中国有自己的神话,其中有龙这样五彩斑斓的生物,但是,哲学与神话的区分不能简单地应用于儒家和佛教。 佛陀的故事像耶稣的故事,象征意义远比历史意义重要。
在早期印度,这个故事复杂得多。 印度教充满了奇幻的生物和神灵,这至少和古希腊神话一样富有想象力。 在古典的印度神话中,诸神的“三位一体”至为根本。 它们分别是梵天(创造神)、毗湿奴(维护宇宙之神)和湿婆(破坏之神)。 但我们知道,它们是同一个神的不同面向,是一个实体而不是多个实体。 实际上,印度神庙一方面比希腊所见的神庙更大更复杂,另一方面又具有更为明确的统一性。 最令西方读者震惊的不是印度诸神各自的独特身份,而是它们具有多态性。
我们所熟悉的有六只或更多臂膀的湿婆,只是令人困惑的复杂问题的开端: 诸神通常会有各种样子,采用不同的容貌,履行极为不同的功能,因此有许多极为不同的名称。 比如,湿婆的配偶雪山女神,也是充满母性的安巴女神、破坏性的凯利女神和娑提女神,后者被认为是湿婆的力量之源。 印度神话在不同的城市和亚文化中也有不同的变化,印度的民间传说和文学由许多不同的故事构成,很像早期版本的古希腊神话,赫西俄德曾试图把它们加以统合(未能成功)。 这样的尝试在印度教中实际上不可想象,后来的神话专家证实了这一点。
古印度漫长的历史(正如相对短暂的古希腊历史)中有非常多的准历史英雄,他们也是哲学的典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薄伽梵歌》(神之歌)中的英雄阿周那,而《薄伽梵歌》是附在史诗《摩诃婆罗多》(巴拉塔王朝的伟大史诗)后面的宗教文本。 阿周那在战斗开始之前有所犹豫。 他不愿意攻打反对他的敌军,因为敌军中有自己的亲人。 然而,至高神克里什那(乔装为阿周那的车夫)告诉阿周那,尽管敌军中有自己的亲人,但战斗是他的义务,作为义务,他应该无私地执行,全心追随神明。
这种道德困境对我们而言似乎极为恐怖——这等于说,在某种处境下,我们有义务杀害自己的亲人。 但是,类似的恐怖也见于希伯来圣经、希腊神话和所有内战之中。 这些恐怖故事只是(就像哥斯拉电影)在拿我们逗乐吗? 还是说,这些深刻的道德传说让我们陷入了直抵人类道德和经验核心的深刻哲学困境? 甘地把阿周那的危机解释为我们每个人在心中进行的善恶斗争。 克里什那向阿周那显现其神性之际,我们的日常世界颠倒了。 神话事实上是哲学、思辨性思维的养料,但不一定以文字的形式呈现。
《薄伽梵歌》中的华丽故事伴随着深刻的思想评注,它们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富有哲学性,但对于平实的自然主义解释却毫无兴趣(与此相反,早期的西方人恰恰迷恋于此)。 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早期希腊哲学家并不常常关注自身,他们尽管拒斥粗俗、表面上难以置信的神人同形同性论,却仍坚持刻意的含混和古老神话所描述的那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图景。
与西方神话相比,印度神话最明显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它充满想象力的活泼戏谑,以及相对而言的无所拘束。 (宙斯可以变成公牛,但这只是暂时的策略,他仍是宙斯。 )比如以下这个广受喜爱的印度神话。 湿婆在儿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去打仗,多年后回来发现有个英俊的年轻人陪伴着自己的妻子,于是将这个年轻人视为情敌,砍下他的头颅,结果发现砍杀的是自己的儿子。 他在惊恐万分之际,发誓将接下来所见的生物头颅给予儿子使其复活,他最后看到了一头大象。
这些故事要从字面上来理解吗? 它们只是幻想的结果吗? 还是说,它们更可能在以娱乐形式呈现深刻洞见,在以较为有趣但未经消化的形式解释实在,而没有呈现为早期西方哲学的那种原始科学? 事实上,我们认为,印度神话的变化令人困惑且充满想象力,表达的也是相同的观念,它们支配着整个印度哲学的绝大部分历史。 甚至在最戏谑的印度传说中,我们都能看到生命的再生和延续这个恒久主题。 不过,“宇宙的统一性”是其中的关键主题,尽管它会呈现为诸多表现形式。 这唯一的绝对实在在哲学中以“婆罗门”之名出现。 但是,在早期神话中,诸神的多元化事实上是一神的不同表现形式,表达的是同一主题。 因此,从神话到哲学,与其说是逻辑的跳跃,不如说是描述语言的转变。
然而,这种不同不应使我们远离神话而倾向哲学。 两者各有优点。 神话涉及叙事(故事),尽管故事中的人物可能是虚幻的,但故事本身至为重要。 当我们设想自己是那些人物,这些故事就显得尤为重要。 哲学更关心系统性的理论,而不是故事。 但是,哲学如果遗漏历史叙事,完全脱离情境,往往会导致毫无背景的空概念被错误地解释为永恒真理。 神话的叙事可以容纳矛盾甚至荒谬,但因此更富魅力,更能抓住世界的混沌本性,而不会减少可信度和一致性。 (美国人沃尔特·惠特曼颂赞矛盾,不因矛盾而哀叹,也不试图“解决”矛盾,先贤中不止他一人这样做。 )与之相对,哲学只在身处极大危险时才容纳矛盾。 实际上,无论来自何种文化,多数哲学家都绞尽脑汁要避免矛盾,即便他们将矛盾和支离破碎视为生命和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尼采,以及禅宗传统的某些伟大哲人。
我们或许应注意尼采,他警告我们要小心现代哲学隐藏的神话: “原因”“实体”“自由意志”“道德”,当然还有“上帝”。 哲学有它自己的神话假设,这些假设不那么明显是因为它们是非人格的。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这些观念,但我们不应完全接受它们,而是要把这些概念归入神话王国。 人们可能坚持认为,神话有助于教养,哲学有助于理智,但是,最好的神话就像最好的哲学,既有助于教养又有助于理解。
同样,人们应该谨慎对待宗教与哲学的关系。 某些古希腊人小心地对两者加以区分,但是,在过去的两千年里,西方哲学绝大多数时候难以与犹太——基督教传统区分开来,即使那些终身致力于抨击这一传统的哲学家也无法做到。 只是在过去的两百年里,美国的许多哲学家和欧洲的一些哲学家才预设了这一分离,而在许多其他传统中,宗教与哲学的同一性仍然极为稳固。 在许多社会中,包括绝大多数部落文化,宗教规定着哲学。 在其他社会中,则哲学规定着宗教,最显著的是儒家和佛教,两者皆是无神论的宗教——没有神的宗教。 有人可能根据神话与哲学之间的模糊差别来区分宗教与哲学,或者通过批判性思想与纯粹“教条”之间的差别来区分宗教与哲学,但这常常意味着对宗教的误解。 无疑,哲学在宗教内外都起着重要作用,但如果因此而认为宗教、神学和宗教哲学(与更为世俗和批判的“宗教哲学”相对)在哲学的范围之外,则是个错误。
人们也应该谨慎对待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不要急于得出结论,认为,尽管我们试图区分哲学与宗教——如果哲学不是宗教,它就必定是科学,或者说,至少具有科学性。 生活中有很多值得深思之处——人的个人身份与社会身份、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我们的政治责任和政治关切、艺术品的美或精巧,甚至自然的奇观等等,它们都不必归入科学和宗教。 确实,现代人认为哲学应该具有科学性,但这种观念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主要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 实际上,这个观念在其提出之日就受到质疑,绝大多数其他文化也不怎么关注它——值得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文化还没有启蒙。 固然,科学特别要求客观性。 但是,科学和科学(诸)方法被用来定义客观性观念时(情形常常如此),这个假设值得用哲学来考察。 但是当科学和科学方法用来定义客观性的概念时,这种假设应该受到哲学的审查。 当然,科学所要求的非人格性和超然性不必推广到哲学中去,因此,(东西方)许多哲学家恰当地强调哲学是一门艺术、技艺、学问,是有别于科学或者至少比科学更具渗透性的实践。
甚至那些确实崇尚科学的哲学家,也承认科学有其局限。 因此,康德这位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牛顿物理学的狂热追随者,宣称有两种事物令他充满“敬畏”,即“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 他也承认艺术的美、宗教的虔诚、数学奇迹、邻人的陪伴和酒的醇香,以及科学的价值。 牛顿也绝没有把哲学局限于“自然”。 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他提出了一种神学来补充和容纳他的物理学。 弗里德里希·尼采也是(19 世纪)科学的狂热追随者,认为科学“真理”只描述了我们经验的小部分,因此认为“美学真理”更为重要,与哲学更相关。
然而,在哲学与科学的联系中,有某种值得崇敬和基本的东西,它不只是对客观性和理性的共同强调,不只是对真理的共同追求。 因此,许多年来,某些哲学家固执地认为,哲学问题不同于科学(当然,长时间以来,某些哲学家也认为哲学应该算作科学的一部分或科学的卫道士,清理科学的不严谨)。 根据这个观点,哲学问题无需任何经验证据,也不需要科学研究中的最新进展,或者说,根本无需任何经验和研究。 用哲学术语来说,这些问题能而且只能先天地加以解决。 换言之,哲学独立于所有经验或实验,要么诉诸逻辑和语言,要么诉诸直观。
结果就是哲学致命的贫乏,在哲学的某些领域,如今仍是如此。 那些不是“仅靠理性”,纯粹只需思考解决的问题,被贬斥为“纯粹经验”问题,或“心理学而非哲学”问题。 比如,沿着这些思路,某些英美哲学家近年来不厌其烦地争论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关系,而不费心去学习任何与大脑相关的东西,这本来与讨论的问题有某种真实的相关性。 某些哲学家则争论科学和自然的性质,却从不曾与物理学家交谈。 某些哲学家则仍详细地讨论人性,却从没想过去读几页弗洛伊德的书。 幸运的是,这种情形正在改变。
哲学与科学相连,这是我们要谨记的教训。 哲学既不是科学的母亲,也不是科学在概念上的护卫者。 但是,在科学家进行研究时清理混乱的术语和概念在探究诸多主题时,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 这在所谓的“某某哲学”领域更是如此(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艺术哲学或宗教哲学)。 没有谁能够明确区分经验知识和先验知识、内在知识与外在知识。 1932 年,爱因斯坦用了母亲类比,认为“哲学使科学得以诞生,人们不应嘲笑她的赤裸和贫乏,而应该希望哲学的堂吉诃德式理想会活在她孩子的生命之中,以免他们沉沦于庸俗。 ”
哲学与科学相连,恰如哲学与神话、宗教相连,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相同。 我们需要哲学、神话、宗教和科学之间的这些审慎区分,然后才能走进哲学的开端。 在西方,哲学诞生于宇宙论的兴起,或者,更为确切地说,诞生于宇宙生成论的兴起,它研究世界如何成为它现在的样子。
对科学“神话”的解构与西方哲学的危机
作者 | 陈兴安
阅读提示
◎因保罗·费耶阿本德观点趋于极端,维护和论证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反科学主义,提倡认识论无政府主义,所以被认为是当代科学哲学中的最大异端,得名“科学最坏的敌人”。
◎本书辑录了费氏一生讲课的精华,探讨了“科学是什么”和“知识是什么”等问题,紧紧围绕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世界观兴起这条主线来讲授哲学内容,强调科学家的伦理责任,批判科学成见。
《科学的专横》,[美]保罗·费耶阿本德著,[德] 埃里克·奥博海姆编著,郭元林译,韩永进校,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在我们的日常话语体系中,“科学”无疑是个高大上的概念,因为一提到它,人们总是会联想到“正确”“理性”“客观”“精确”“规律性”“完美”等。
通常的描述给人的印象是,科学是真善美的统一,是人类认识的理想型态和文明智慧的化身;科学是人类理性认识的结晶,是对外在客观规律的反映,是人们正确行为的指针。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则从专业的视角,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独到理解和看法。
保罗·费耶阿本德(1924—1994,以下简称费氏)是20世纪最知名的科学哲学家之一,是科学历史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纲要》《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以及《告别理性》等。
《科学的专横》根据费氏1992年在意大利特伦特大学向普通听众所作的系列讲座,经作者本人编辑整理而成,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他基本的学术观点。
由于是学术讲演,且听众多为非专业人士,所以该书异于一般的学术著作,在组织结构、表述形式和语言风格等方面就不显得那么严整、刻板和冗长,而是让人有某些轻松、直观和诙谐的感觉。
作者就像一位年长的智者,以讲故事的方式娓娓地谈论科学发现和发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仿佛在引导读者穿越时空,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下的圣哲进行交流,感悟和了解不同文明传统的思维和智慧的丰富多样性。
诚如本书的英文编者奥博海姆所言,科学对世界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科学是什么?它如何运动?它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
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是关乎我们每个人的事情。
作为一位科学哲学家和西方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费氏毕生致力于探讨这些问题,并且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可以说,《科学的专横》是费氏科学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浓缩。在发表这次演讲大约两年后,他便因病逝世。因此,也可以说这部作品反映了费氏对于科学的最后思考。
在本书中,他引用法国著名生物学家莫诺的话来评述西方现代文明:“冷酷而严格,没有提出说明,但禁绝其他精神食粮,这没有缓解而是加重了焦虑。它一下子声称横扫几十万年的传统,但这种传统与人性自身合为一体。它撕毁了古代人与自然间的泛灵论契约,但对这种珍贵的联系没有提供任何替代品,结果使得人类在孤独冻结的宇宙中焦虑地探寻。”(《科学的专横》第4页)
费氏在本书中指出,西方文明中的科学理论和科学知识,因为过分强调客观和价值中立的原则,导致人们在精神生活中驱逐了作为心灵依托的神,造成了西方文明的“断离”。
他举例说,把具有宗教信仰的科学家人为地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充当科学家,另一部分充当基督教徒。作为科学家的人拒斥信仰启示,远离意义;作为基督教徒的人信赖上帝,遵循圣训。
无法使科学家自身充满宗教精神。科学所要求和代表的冷酷、冷静和客观与宗教唤醒人们爱的目的之间,存在难以协调的矛盾。
作者在书中还批判了科学的“客观性”,感叹“在客观论证中所具有的客观性是多么少”。在他看来,所谓的“科学无涉价值”不过是一种武断的谬见。
“但绝对不是这样。只有当一个实验结果(或一个观察结果)明确不包含任何‘主观’因素时——只有当它能从产生研究结果的研究过程分离出来时,它才会成为科学事实。这意味着:在科学事实的构成中,价值起了重要作用。”(《科学的专横》第87页)
他认为科学的系统描述或许就是一种错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混沌无序的世界,将系统引入其中意味着引入假象。(《科学的专横》第46—47页)
他强调开放的世界观、多元方法论和多样性文化对于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科学不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唯一方式,也不见得全部正确,反对“科学之外无知识”的偏见,提倡各种思想的平等和互补。
此外,他从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立场原则出发,认为科学家的成就、贡献似乎与其崇高的社会地位不相匹配,提出和倡导科学家应当承担其应尽的社会责任。
指出科学研究中理论家与实验家的人为划分,而理论玄想受到不适当的推崇,工程教育中偏重理论原理而忽视实践知识等问题,以及强调科学家从事研究事业时应当具有信仰和耐心等。诸如此类的观点论述,都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科学的专横》中译本由天津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郭元林翻译,该书依据1996年最新英文版翻译而成,文笔流畅、简洁,准确、明晰,在表述风格上也保持了与原文的一致。
为方便读者查阅和进一步研究,译者精心编制了中英术语对照表,作为附录放在中译本正文后。另外,将英译本的书后注释,全部转换成页下注。凡此种种,也都可见译者的用心和细心。
笔者在通读该书中有一点体会,因受东西方文化以及各人专业背景差异的局限,国内普通读者可能会对其中一些术语或概念不甚了解,比如“诺斯替教”“超弦”等,如果在文中加上一些简要的译注,应该会有助于读者的理解。
但瑕不掩瑜,该书确是值得仔细研读的一本好书,无论是对理工科还是文科出身的人。
相信大家在看过此书后,一定会对近现代科学的发生、发展和深远影响,有更深入而全面的理解。
我国正处在社会文化转型的现代化过程中,如何面对西方现代化后的尴尬境地,如何避免西方科学的负面影响,如何更好地发扬中华优秀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中发展自己的文化等,都是我们必须面对和研究的课题。
了解和研究费耶阿本德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无论是专业的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读了这本书,都会启发我们作出自己的思考。
(作者系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