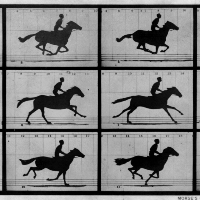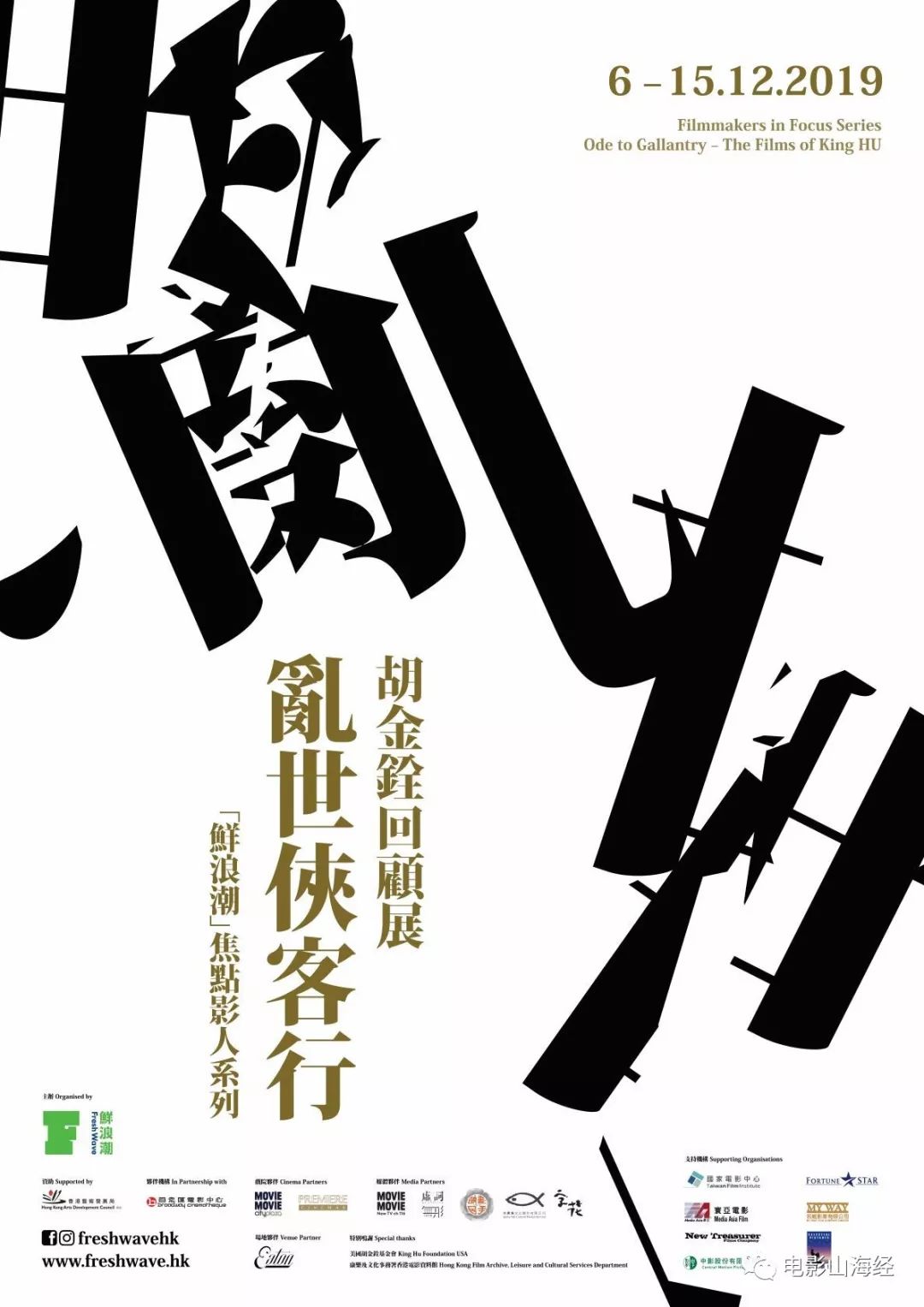2019年12月6日至15日,香港鲜浪潮在港举办“乱世侠客行”胡金铨回顾展,共放映胡导作品13部,除《忠烈图》和《画皮之阴阳法王》尚无修复版外,其余影片皆为2014年起开始陆续修复的修复版。胡导一生的作品也为数不多,这13部作品从第一部《玉堂春》到最后一部《画皮之阴阳法王》涵盖了胡金铨整个创作生涯,不啻为一次很好的回顾。香港的影展也做得颇为成熟,许多影片放映后都设有映后谈,请来各路嘉宾从自己研究的专业角度对胡氏电影做一一解读,此外还另设两场讲座和两场座谈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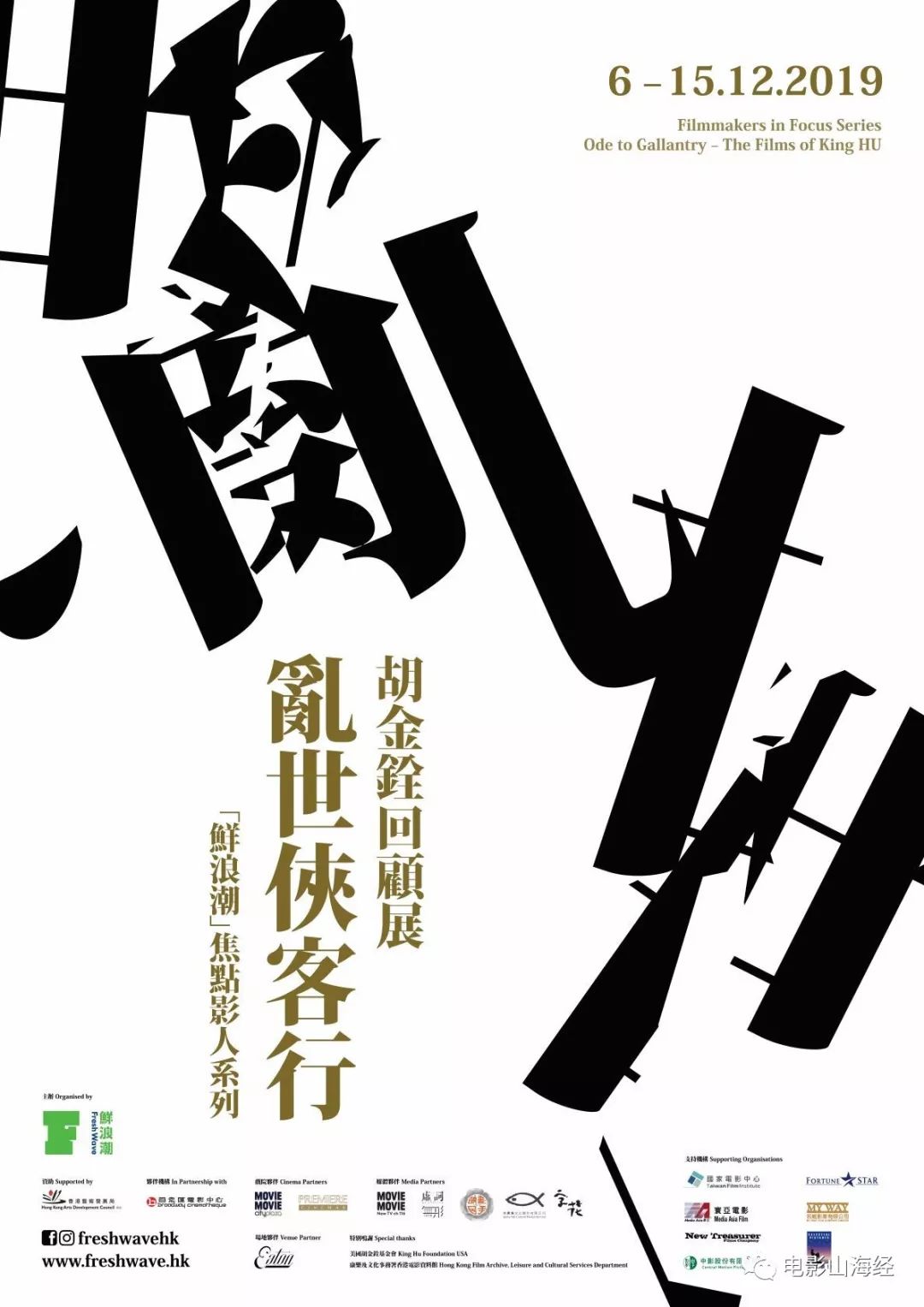
虽然胡导自己不认为自己拍的片子是武侠片,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古装动作片”,但笔者认为,武侠片和武打片还是有所区别,从广义角度看,它们确实都属于动作片范畴,只是武打片过于强调“打”,注重“打”的一招一式,而武侠片更突出对“侠”的阐释。
何谓“侠”,“侠”这个字最早出现在《韩非子·五蠹》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在他的眼里,侠客并不是什么好人。而到了《史记》,对游侠这类人也有了具体描述,司马迁还为他们专门列了传,赞扬他们言行一致,士为知己者死。司马迁还谈到,战国四君子(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也是具有侠义精神。笔者倒是觉得,换个角度看《史记·刺客列传》里的人物也具有侠客的某种特质,比如荆轲、聂政。但中国的侠客们又缺乏阶级性,不属于特定的人群,有的仅仅是路见不平一声吼,拔刀相助两昆仑。他们有的是官员,有的是富商,有的是农民,侠客这个行当似乎只是一种兼职。比照邻国日本,侠义精神更多体现在武士身上,而武士属于特定阶级,地位较低,黑泽明的经典大作《七武士》就有很充分的解读。日本武士的侠与中国的侠,既有共通,也有不同。而黑泽明对胡金铨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从1966年的《大醉侠》到1975年的《忠烈图》这9年间,是胡导的重要阶段。虽然《大醉侠》之后,胡金铨与邵氏公司分道扬镳,但他的风格体系从《大醉侠》之后一路继承下来,之后又做了不同的创新,探索。胡氏武侠风格一直贯穿始终,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独树一帜的武侠流派。
以《大醉侠》为武侠创作的开篇,胡导引领观众们进入了他一手构建的侠义世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客栈。胡导的客栈戏是他的标志,《大醉侠》、《龙门客栈》和《迎春阁之风波》人称“客栈三部曲”,再加上《喜怒哀乐》之《怒》一个小戏。胡导把客栈这一狭小空间能上演的戏码淋漓精致得呈现在观众的面前。如果说《大醉侠》只是胡导的小试牛刀,那么《龙门客栈》胡导就大显身手了,经典中的经典,典型的攻防之战,战斗不仅仅局限在客栈内,还延伸至客栈外围,既有肉搏战又有心理战。《迎春阁之风波》则赋予了客栈更多的功能,除了是战场,还是秘密接头的据点,后来又成了审讯法办的场所。而这些功能的增加都是为了突出人物,为剧情服务。
笔者一直觉得中国武侠片和美国西部片颇有诸多相似之处,侠客与警长,客栈与酒吧,刀光剑影与枪林弹雨。今后如有电影节策展时,如能把经典的武侠片和西部片放在一个单元,或者更大胆一点,单元名字就叫“客栈VS酒吧”、“剑与枪”,东西方电影的语汇在此对话,倒不失为一种思路。
《怒》是众多客栈戏中的佼佼者,取材于京剧折子戏《三岔口》,整个故事都发生在客栈内,场面调度运用自如,一楼二楼来回切换,客房与大堂,内屋与外院,焦赞和任惠堂,解差四人,店家夫妇三组人马,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堪称一绝的是店家用砍刀撬锁那场戏,京戏里面,这出戏是个意象,但在电影里就要据实表现出撬锁的这一过程,胡导运用了特写镜头,而整个过程又是京戏中的一招一式,把京剧的程式化语言在现实场景画面中完美呈现。
谈到京剧元素,就不得不说胡金铨电影里的中国味道,除了在打斗设计中融合了京剧武打的招式,在配乐方面也引入了京剧的锣鼓点子,起到渲染剧情,感染观众的作用。胡导的空镜头又突显了中国水墨画画风,飞鸟、夕阳、山川、竹林,这一点在胡导1979年的两部作品《山中传奇》和《空山灵雨》里发挥得尤为极致。这两部作品也是胡金铨对武侠电影的一种新探索。
《山中传奇》和《侠女》可互为一组,对比观看。这两部都是胡导的长篇巨制,超过三个小时,都取材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主演都是徐枫,石隽,但两者又有不同,《侠女》中石隽扮演的男主角顾省斋是一个文弱书生,不会武功,徐枫饰演的杨慧贞恰是忠臣之后,武艺超群,两人的角色实为互补,形成反差。“侠”字体现在了女主角的身上。而在《山中传奇》中,“侠”的味道似乎很难觅见,谁是“侠”?何谓“侠”?徐枫饰演的是厉鬼,谈不上“侠”;石隽饰演的何云青也没有丝毫侠义精神,影片反而对他这种懦弱儒生进行了嘲讽;倒是张艾嘉饰演的庄依云倒还颇有几分侠气。可见“侠”在这部片子里已不只是简单停留在先前的仗义相助的层面,而是将“侠”化于对儒释道三界的解读。尤其是胡金铨的佛学思想在其后的《空山灵雨》中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空山灵雨》的片名笔者就很喜欢,山,空空如也,雨,灵动多变。故事也从单打独斗上升到佛法的思辨,运用禅宗典故,充满禅意。
1983年的《天下第一》和《大轮回》(第一世)是胡金铨对武侠电影又一种新的尝试。《天下第一》充满了黑色幽默,神医,神技,神偷各种技艺粉墨登场,颇似《史记·滑稽列传》中各种人物。《大轮回》(第一世)里所有人物都命归西天,这也是在以往的武侠影片里不曾有过的。纵观整个胡氏电影风格,将故事融入于历史大背景,大场面,这得益于他对中国历史的潜心研读,但有时候还是会感到有点缺憾,就是对人性的探讨和揭露似乎还略显乏力,这可能也是因为动作片的先天不足引起的。
谈论胡金铨的电影,徐枫,石隽、田丰、郑佩佩、白鹰总是被反复提及,其实除了他们,还有一个人物也值得一说,那就是韩英杰。韩英杰不仅在多部影片中出场,还是《大醉侠》、《龙门客栈》等片的武术指导,在《迎春阁之风波》里,韩英杰的弹唱更是一绝。
胡金铨导演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如今回看他的这些作品,仍会引发我们一些思考,“侠”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影响有多大?当今社会是否仍需要侠义精神?而在2019年的岁末,在香港,举办胡金铨导演回顾展,各种机缘巧合,颇具玩味。
2020上海艺术电影联盟:
至爱影院 | 大河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