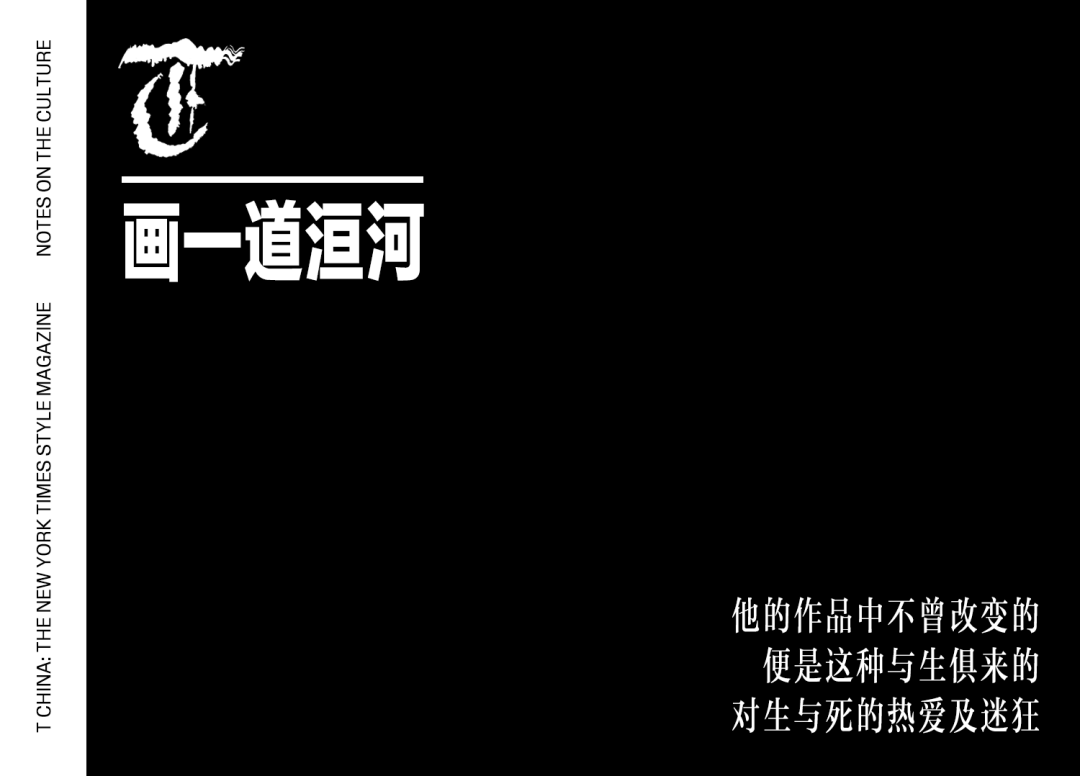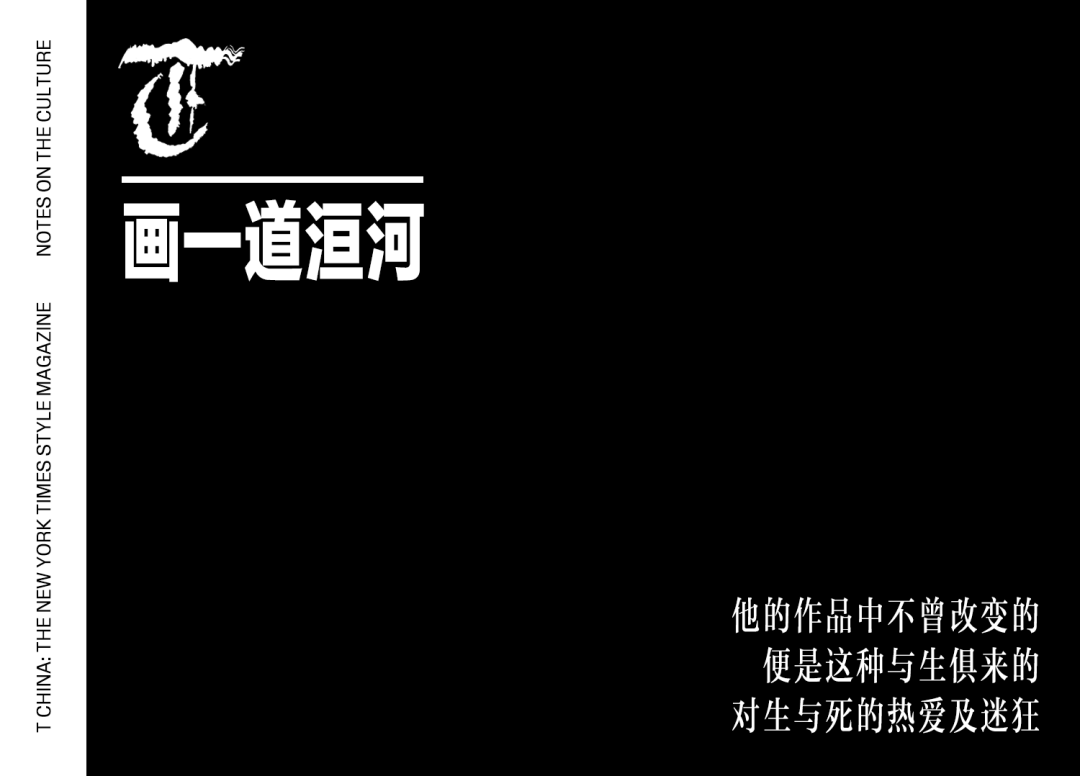
「我的祖先是商纣王,我是河南安阳人,殷墟文化。洹水就是安阳河,甲骨文就在这条河里发现的,殷墟就在这儿。我祖先是商纣王,我就有商纣王的基因在里面。他的基因是三个,打仗、女人、喝酒。我是创作、家庭、喝大酒,一天基本上我的这个生活就是三部曲,早上运动,九点我去工作室工作到晚八点,回家以后,等着,朋友去喝酒,基本是这样。」
一袭白衣的张洹放松地坐着,在被问到创作与灵感来源时,非常平和地说出这些话。
上海工作室;张洹站在《生命之水》前
看上去一点不像以暴虐著称的商纣王的后代。
商纣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公元前 1075 年至前 1046 在位,他的历史评价和罗马帝国的尼禄相似,《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民间则传说纣王受了狐妖妲己的蛊惑,嗜杀成性、荒淫无度。
或许艺术家标志性的白衣算是殷商文化的一个体现。《吕氏春秋·应同》中记载:「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殷商是金德,金属白,那个时代属于帝王的颜色便是白色。这种说法由两千多年前的阴阳学家邹衍提出,金木水火土五种能量为五行,它们相生相克,每个奉天承运的王朝都代表了五行中一种能量,这就是「五德」。每种能量经历自身的兴盛与衰败之后,被下一种能量所克制和替代,便是天道轮回,「五德始终」。
尚火的周灭了尚金的商,纣王携妲己鹿台自焚。灭了商的周文王,精通《易经》并著《周易》。纣王的后代张洹,同样读《易经》。他对家族与血脉有着更大格局的理解。这种理解基于他迄今所经历的一切。
张洹是春节出生的,这个节日给他一种强烈的宿命感。他说:「年,新年,过年,过年是什么概念?过年就是过鬼,年就是鬼,在过年的时候要把这些鬼,这些不吉祥的事物都赶跑掉。我们活着的亲人要团圆,我们还要去坟地把祖先请回家里跟我们团圆,所有在外边漂流的亲人,兄弟姐妹们回家一起团圆,这是过年。」
《生命之水》
2019 年春节期间,他提前与家人过完年,然后去了敦煌。初二到,在敦煌待了两周,每天 8 小时访窟。这是张洹与祖先的交流方式。在他看来,1650 年前开始建造敦煌洞窟的先民们「才是真正的祖先。我们对自己祖先的概念理解太窄了。」
如果说作品是艺术家对于时间与空间的具体表述,他从这些祖先那里继承的时空观便是《易经》式的:一面是周而复始,一面是穷极而变。「时间是易经,易经是变经,易经只讲一个字,讲什么?变,只有变字才是永远不变的规律,这就是易经。」但他又承认这种永恒变化中不变的存在,「《易经》讲了变,也讲变里面的不变的东西,早上日出,晚上落下,这是一个不变的恒定的东西,春天种完庄稼,秋天就有收获,种瓜不得豆,这是恒定的自然规律。」
对变与不变的领悟,融合于张洹的身体、工作、学习,潜移默化,自然贯穿于他的作品。他创作力旺盛,作品在相同的 DNA 下,却有着风格迥异的表现形态。1990 年代,张洹用逼近身体极限的方式创作了《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为鱼塘增高水位》《12㎡》等作品,在中国行为艺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98 年移居纽约后,他于 2002 年推出了《我的纽约》,用鲜红的生肉把自己塑造成筋肉极端发达的样子。这件作品给人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 2010 年 Lady Gaga 穿着肉片装走向第 27 届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领奖台时,不少人提及《我的纽约》并与之比较。当然两件作品即便创作元素相同,脉络与表达依然大相径庭。事实上,张洹并不在意自己的创作被公众如何理解,「别人平时各忙各的,为什么艺术家非要让他们来理解自己呢。他们没时间关注这一块或者关注的时机还没到,机缘还没到的时候,他误解就误解,误解就是理解。没所谓,不能强求啊,所有的事情强求不得的。」
张洹同样不在意作品风格延续性不强这件事。2005 年,他突然决定回国,工作室被安置在上海。他买下了前国有的液压容器厂,据一位记者描述,这个空间「特别地庞大,有上百个工人」。邀请张洹创作《生命之水》的轩尼诗传媒负责人说,第一次在他工作室里见面时,「他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高大恢弘,包括他本人,当时我坐在那里觉得自己很小很小。」
《生命之水》
就在上海,张洹实现了艺术表达上的一次跃迁。他的作品不再是用肉体对抗生活的行为艺术,而改为精神上的内省与洞察、接受与欢喜。
改变的契机始于静安寺,一个普通的日子。张洹讲叙了他与香灰画的因果:「10 年前从纽约回来,我在静安寺拜佛的时候,发现了香灰,这是一个非物质材料,这是精神材料,是精神的聚合,灵魂祝福的聚合,我把香灰请到工作室开始研究,把它转换成为艺术。香灰艺术为艺术史添了一个门类。」
在香灰虚无平静,空无一物的灰色阶段后,张洹创作了色彩极为斑斓缤纷的「罂粟花田」系列,成千上万明度极高的色彩层层堆积在巨幅亚麻布面上,一团团色彩组成的图案有形无相,你说它们是什么都可以:罂粟花蕾、死亡面具、骷髅头、欢喜佛、星空、宇宙……高度密集而明亮的色彩聚合在一起,看上去神秘旋动,有梵文的吟唱、活着的狂喜、梦幻泡影的虚空。一幅画,对他而言便是一次呼吸,一个宇宙。
我的罂粟地 No.1 (250 × 400cm)2014 年,亚麻布面油画
6 米长近 3 米高的油画巨制《生命之水》亦如是。这幅应轩尼诗邀请创作的作品由三块画布构成,一个个绚丽多彩的球体聚合在画面上,黑底色,随后是大篇幅的红色,像黑夜中的灯笼,又像静水深流中的河灯,然后是前景,红色变成肥皂泡的样子,反射出七彩光芒,中间又流动着同样绚烂的金与绿、橘与蓝、白与紫。这是张洹脑海中生命之水的样子,单一细胞的样子。他说:「作品核心是把一个单一的元素放到一个宇宙世界里,所以它的尺寸会放大,它必须把人融在其中,把你我融入其中,随后我们便理解了这个细胞,它不仅仅是一个细胞,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画面,或者单独的生命,它本身就是一个宇宙,就是一个世界。就是每个人的小宇宙。」
《生命之水》
提及这些绚烂的、因为笔触与形式的体积与厚度,在一起看似冲突却又奇妙和谐的色彩,他谈到了艺术的呼吸:「红跟绿不是冲突的,它们压根就是姐妹篇。就是红花绿叶必须在一起才好看。然后是红红火火,火到一定程度,需要把火气压一压,后面就要用重颜色黑色来稳住。所以这个作品的颜色里面,红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都在变化,这是我一直遵循的。一件艺术作品要呼吸,什么叫呼吸?人一呼一吸就是生命,没呼,没吸,人就走了,那么画面艺术怎么呼吸?每一个点都不同。所以我要求每一个部分的颜色不同,笔触不同,情感不同,构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宇宙和谐世界。」
为了能在今年 8 月之前完成这件作品并达到自己的期望,他和 5 个助理每天画 8 小时,最后三个月,每天每人工作 10 到 12 个小时。他不否认使用助理,且半开玩笑说:「我一算就说我死的时候还没有画完。我自己画真得五年,那个细节你懒不得,它不是抽象画,不是一泼、不是一甩,它是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局部都得用心,没有这个时间去精心地去塑造它,用这种感情去塑造它,你出不来这个效果。」
这个过程有一个插曲,最初张洹制定的方案是薄画,但画了一个月发现不行,达不到他要的感觉。于是重新开始画,「薄画法画得快,但效果不行,于是重新开始用厚画法,我需要把笔触塑造出来、需要回到绘画本身,需要用每个笔触呈现里边的碰撞与能量感。我要传达出人生与精神。人的能量转换为我们的生命细胞,转换为我们的生命之水,转换为我每一次落笔,所有这些微生物,这些宇宙量子,这种相遇,这种相碰,时而散,时而聚,无数次的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就跟我们的中国年挂上钩。」
在 10 月底,这幅巨制最终被悬挂在干邑区(Cognac)轩尼诗酒庄的一间空置蒸馏车间中。走过闪着柔和黄铜光泽的夏朗德铜制壶式蒸馏器以及散发着陈年橡木香的橡木桶,来宾可以看到《生命之水》被端庄地挂在车间最深处的墙壁上。你可以走到近前细细欣赏,从一层层的笔触中感受这幅作品的喜悦喧嚣,美满庄严。作品的创作者站在旁边,依然白衣,脸上有一种精疲力竭与心满意足在一起的光芒。
被安放在轩尼诗酒厂内的《生命之水》
这是轩尼诗为这幅巨作举办的盛大晚宴,品牌在即将到来的 2020 年新春特别版干邑中,同样使用了《生命之水》作为包装设计。为了鼠年春节,十二生肖新轮回开始的特别一刻,轩尼诗还特意制作了一个多媒体宣传片,并带张洹去黄山拍摄了一支短视频。
这十足的仪式感,非常「轩尼诗」。张洹对轩尼诗酿酒中的仪式感印象深刻,他甚至认为这种仪式感是帮助人们脱离世俗生活的一个过程,「他们能把一个品牌做到第 8 代传人。在一个小房间里,每天固定一个时间,11 点,一个团队,10 个品酒调酒大师在研究几千家送过来、甄选好的生命之水,然后从这么多里面去选择上佳的,适合调制在一起的。一个人要想成为品鉴团队中的一员,首先要先通过 10 年的学习,没有这 10 年学习,就不能发表意见。这个过程已经进行了上百年。这个仪式感给我的震撼非常大,每日相同的神圣庄严的仪式拥有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足以引导相关人员脱离世俗生活。」
轩尼诗晚宴
那些放置于品酒室中的原浆(即生命之水),同样给张洹精神上的生命力,「在他那个房间里那么多原浆、一样的瓶子在那放着,那种感觉那种已经不是酒了,不是原浆的感觉。你想想,每一个瓶子里装载着多少当地人民的这种情感,对土地的情感,对自然的爱都在这个瓶子里装着,这能量之大 —— 所以它叫生命之水,就像我收集的寺庙里面的香灰,这是灵魂之灰,爱之灰,它们是一个层面的意思,一个层面的材质。」
滑动查看更多张洹与轩尼诗合作系列的 2020 中国新年特别系列
张洹名字中的洹,是洹河,他老家安阳的一条河,古称洹水。对张洹而言,洹河、生命之水、春节有一种符号般的意义,象征着彼此奇妙的连接,这种连接不过是无数次缘分的又一次体现。而这次合作的缘,又为张洹种下一个未来创作的果。他讲起在黄山拍摄《生命之水》视频时的顿悟:「我发现了香灰与宇宙能量的关系。我拿了一个实心的玻璃球,坐在院子里,突然觉得手很烫。我一下顿悟到这是太阳的能量。玻璃球就像放大镜,我把一根香放在地上,那个香一下就燃了。燃烧的香所生成的香灰不正是充满着祈愿与祝福能量的材料吗?我觉得这是我今年最重要的一个发现,我计划在明年圣彼得堡的个展中,做一个相关的公关艺术项目,用巨大的玻璃球,10 吨 8 吨重的玻璃球,以香为底座,每天以玻璃球聚集的阳光会点燃它们,最后太阳的能量将形成一幅巨大的立体的创作。」
张洹与他的新作《生命之水》
所以,当问到这位灵感生生不息的艺术家,非常经典的,关于死亡,关于死前最后一餐会吃什么,和谁一起吃的问题时,他说:「我会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吃一碗家常的西红柿鸡蛋面。」他不在意死亡,如同不在意自己艺术手法的连续性。又斟酌了一下,他补充:「其实关于死亡,我之前会经常梦到死亡。」对于这位艺术家而言,他作品中唯一延续的,充沛表达的,便是这种与生俱来的,充满生命力的,对生与死的热爱及迷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