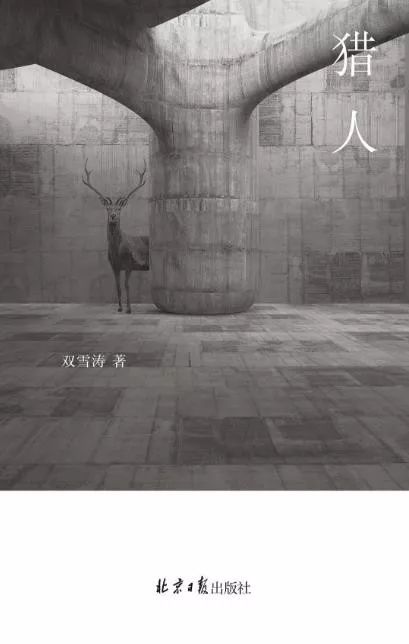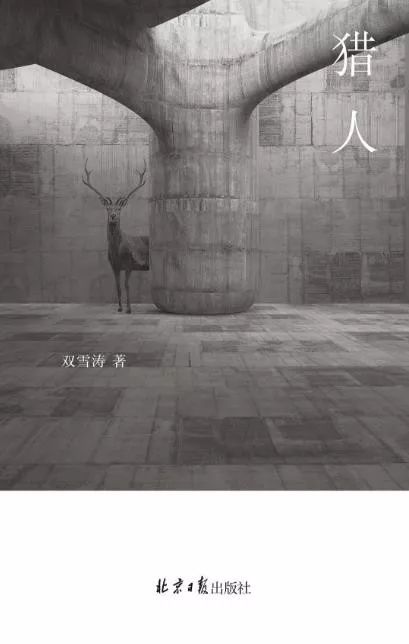
《杨广义》被收进了双雪涛的新小说集《猎人》
双雪涛小说中的消失,从《杨广义》说起
作者:周郎顾曲
改革开放后,文学日益呈现出一股潮流,那就是虚构叙事中产化。在步入中产的作者大批接受创意写作训练,对写作的理解愈发学院化后,他们创作的作品变得克制、洁净、规整,遵循基本的掌控人心的套路的同时,刻意展现出一种高级感,这种高级感就像毕肖普的诗歌或者爱丽丝·门罗的短篇,他们总体来说代表了中产对世界的理解。这类写作本来是为了对抗意识形态对文学的侵扰、商业写作套路对纯文学的腐蚀,为了回应那些刻意的文学、套路的文学或者诉诸于虚情假意的宏大主题的文学,但现在,它成了另一种套路,同一层审美辩识自我的方式。这是一种写作班文学。
天下苦写作班文学久矣,读者渴望看到新的叙事。在这个背景下,东北作家群脱颖而出,双雪涛、班宇、郑执、贾行家等,他们风格各异,但都试图摆脱迎合中产想象的文学。共和国之子东北,作为地缘上的“关外之地”,埋藏着一代人的苦涩记忆,成为一片得天独厚的异质性经验土壤,恰好为作家的视野拓宽提供可能。
双雪涛是其中很好的观察对象,他的艳粉街故事深入人心。《杨广义》是艳粉街世界里的又一部小说。这部小说有几个值得琢磨的地方。首先是它的叙述者“我”——1983年出生的人,和双雪涛同年,但不等同于作者。从叙述者的年龄开始,虚构和非虚构的界限就开始模糊。
其次是它的叙事时间,有几处转换,不仔细琢磨会干扰判断。为了便于读者理解,笔者用顺序的方式整理故事如下:
1982年,杨广义在沈阳铁西区某工厂里做工;
1982年夏天,杨广义出了一趟差,下到村子里给农民修理拖拉机,回来之后拥有一把短刀,大概一扎长,两边开刃,柄是木头的,有动物花纹。杨广义对掌柜说,自己学了一套刀。第二天一早,他失踪了;
1982年夏天,杨广义离开十天之后,厂子后身艳粉街街口的一颗老杨树被人劈开。又过了五天,厂门口扔了五只死鸟,都是麻雀,也是被人当中劈开。很快,派出所和厂里保卫科联合开了会,认定杨广义公然触摸治安底线,要抓他;
1983年初,“我”的父亲陈皮寻找杨广义,无果;
1983年夏天,沈阳出了一个纵火犯,连烧六把火,警方怀疑是杨广义,把“我”的父亲叫去问话,父亲最后签字,在材料上写:不认识杨广义,若他是纵火犯,跟他势不两立,若是有缘相见,不惜一切代价将他抓捕。五天后,工厂附近发现一具死尸,人被切成两半。警方确认死者为纵火犯,民间怀疑杀人者为杨广义;
1983年冬天,叙述者“我”出生;
1984到1995年,杨广义处于失踪状态;
1996年冬天年底,杨广义被人偷袭;
也是在那年冬天,“我”的叙述和母亲的叙述出现了差异。“我”断定杨广义被扎的那阵,母亲和父亲去看爷爷,没带上“我”。母亲却说,这是没有的事。同一天夜里,“我”自称见到了杨广义。
从顺序时间可以看出,1982、83年是小说里的重要年份,这并非闲笔,而是双雪涛唤起目标读者的记忆的细节。
1982、83年正是全国严打的时候,为了整治“十年内乱”滋生的打砸抢分子、强奸犯、抢劫犯、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公安部开展了严打行动,东北是其中的重点。当年2月,东北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大案“东北二王特大杀人案”,当事人王宗坊和王宗玮被警方通缉,但他们五次逃脱警察的追捕,到9月18日才被警方击毙,这七个月里,“二王”凭借枪支和手榴弹打死打伤公安执法人员和无辜百姓18人(打死9人伤9人)。正是因为严打,沈阳警方才格外注意杨广义这样的“闲杂人员”,尤其是在“共和国的长孙”铁西区,这里住满了工人,也潜伏着暴力,是警察防范的重中之重。双雪涛将故事地点设置在铁西区艳粉街,将文本顺序开始时间放在1982年,令人物的逻辑变得合理,也勾起了东北读者的记忆。
东北,下岗,严打等,是小说背景的关键词。在双雪涛的故事里,下岗潮深刻影响着人物。《杨广义》中,“我”、陈皮、赵静、她妈、她爸等,都是厂里的人。杨广义原本也是厂里的工人,后来才成了刀客。当他被民间神话成为民除害的当代侠客,有人找到“我”父亲说:“陈师父,我下岗了,厂长把厂子搞黄了,此人还有个情妇,我们的钱都让这烂货花了,你跟杨师父说一声,把他杀了吧。”
《杨广义》的语言有个性。双雪涛将方言、口语熔炼其中(东北腔,也有山东味),串联起东北的地理坐标、公共记忆,使得文本具有东北的日常感、历史感。这些沉重的故事,被“我”用日常化的口语复述,反而有了戏谑的意味。双雪涛没有把小说写成纪实报道,也无意居高临下地怜悯下岗的工人,而是试图在民间性和传奇性之中做个联结——语言和生活都是民间的,但聚焦的对象却有传奇的意味,杨广义和小说内部世界的格格不入,成为有趣的地方,而揭晓围绕在杨广义身上的谜团,成为小说的魅力之一。
但《杨广义》和类型悬疑小说不同的是:它并没有按照一般悬疑小说的套路,满足读者步步解密的欲望,小说不设置所谓的高潮,也没有在结尾完成叙事的闭合,相反,当读者读到结尾后,很多事仍是一头雾水的,杨广义这个人物也依然在迷雾中。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现实主义叙事,双雪涛在时空转换中,加入了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的元素,在小说后半段将现实与梦境混合,通过不同人物的对话,暗示叙述的不可靠。到最后,读者并不能确定杨广义是个真实的人物,还是“我”的幻想,杨广义与“我”和父亲的联系,也成为一个广阔的联想空间。双雪涛对此不多做解释,他的叙事就像是飘落在艳粉街的大雪。
“消失”的处理,出现在双雪涛多部小说。
比如《平原上的摩西》的结尾,“我”站在湖边,对她说:“我不能把湖水分开,但是我能把这里变成平原,让你走过去。”随后,“我把手伸进怀里,绕过我的手枪,掏出我的烟。那是我们的平原。上面的她,十一二岁,笑着,没穿袜子,看着半空。烟盒在水上飘着,上面那层塑料膜在阳光底下泛着光芒,北方午后的微风吹着她,向着岸边走去。”
又例如《武术家》的结尾,“话音刚落,女人化作一缕飞烟,被人群的热浪一鼓,到了戏台上盘旋了一圈,然后踪迹不见。”
在《杨广义》的结尾,“消失”不被明说,但可以察觉。杨广义说:“如果你什么时候想找我,就拿一个苹果,放在北陵公园东门的石狮子爪子底下。”我却在结尾说:“这么多年我吃了不少苹果,实话说,苹果是我最爱吃的水果,我一个也没有浪费过。”
我没能和杨广义再见,他就这么消失在历史的废墟中。那个杨广义,已经不是具体的人,它指向某种失落。许多读者在读到这些“消失”时,会下意识地联想到东北的往事,将“消失”与下岗潮中那些失去话语权的群体联系。这么联想有其道理,但笔者认为双雪涛近年来的创作,其实在有意摆脱过于“实”的处理,而是回归到《翅鬼》、《天吾手记》的创作姿态中,他仍然会把东北作为背景,但在叙述上又试图摆脱一些对他的刻板印象。
《飞行家》、《刺杀小说家》、《武术家》和《杨广义》等,他们有的是俗世奇人般的作品,有的延续《平原上的摩西》的腔调,不能被一个总的叙述概括。
《武术家》发表后,复旦大学的望道现当代文学班就曾对双雪涛的小说进行讨论。陆羽琴在评论时说:“双雪涛只是想把很多外在的东西都‘洗’到很淡,从而有意识地回避某种戏剧化的冲突和爆发点。”这和《平原上的摩西》时期的写法已然不同,在《杨广义》里,冲突也不是特别明显的,杨广义的遭遇,和那个时期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他的突然消失、他的行侠仗义,都具有神秘色彩。或许,这是双雪涛对抗日趋猎奇、煽情的东北故事的一种表现,当局外人看东北日益陷入苦难、凋零的印象,双雪涛在力求走出《平原上的摩西》的阴影。
但仍可以看出:从《平原上的摩西》到《冬泳》,从《仙症》到这一篇《杨广义》,底层暴力已经是东北作家关注的重点,他们试图书写与时代剧变紧密结合的人物,让小说的意义不局限于自身。他们的小说里有一团化不开的迷雾,那是“一种温饱基本得到保证之后的贫困,一种很容易被社会、尤其是被富人和中产阶级有意忽略的贫困”(李陀语)。
作者: 班宇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出品方: 理想国
这个现象不只发生于文学圈,它的表象是作家对中产阶级叙事的不满,背后是一代写作者呼吁叙事革新、眼光放开的诉求。在一个新旧变革的关口,作者们深刻感受到了各个阶层的矛盾,意识到规范的中产阶级叙事对他者的忽略。
文学界的《冬泳》、《逍遥游》、《仙症》、《杨广义》和《巨猿》等,电影界的《血观音》、《风雨云》、《暴雪将至》、《白日焰火》、《大象席地而坐》,那些勇敢的创作者,都选择了直面现实,践行着新的叙事语言尝试。他们不再回避撕裂,也不再粉饰伤痕,而是把明明白白的东西摊给读者(观众)看,在最彻底的拒绝中,回应这一代人的创伤。
《杨广义》不是一部情节跌单起伏的小说,第一次读完,甚至有些戛然而止的感觉,但过后回想,仍有一些细节浮现在我脑海里,如同《白日焰火》中桂纶镁饰演的女人望见的烟花。《杨广义》里,我最反复读的是其中一段看起来和主线无关的文字:
“我爸不说话,刷完碗穿上衣服,跟我妈走了。 我从车间二楼的窗户看着他们俩把自行车推进雪里,逆风,俩人摇摇晃晃,终于骑上去,好像倒退一样往前走,终于骑出了大门,进了一片白雪花里,看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