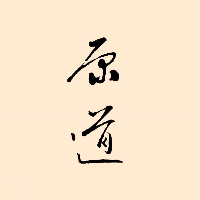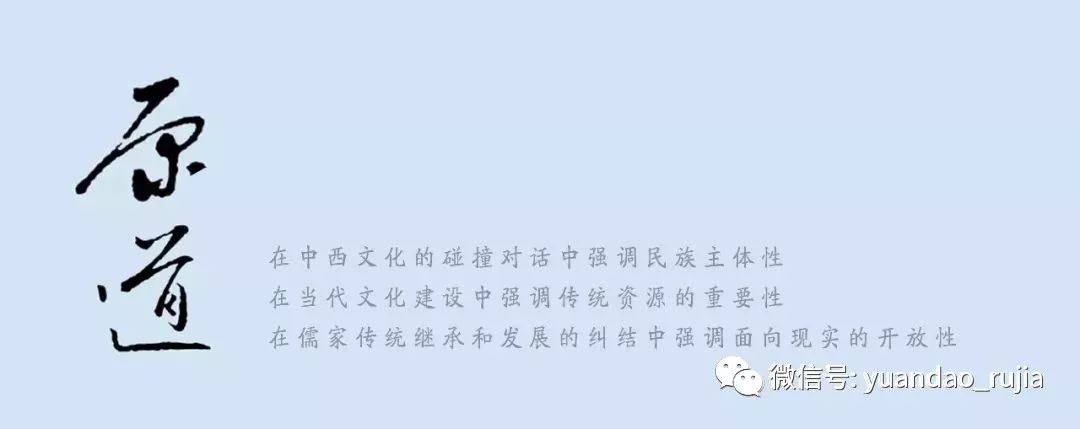
荀子说秦与秦之儒化:《荀子》相关章节疏解
姚中秋
内容提要:荀子入秦游说其君相,为其以生大事,更为儒家学术和行道史上之大事,亦为周秦之际政治演变史上之大事。荀子以为,秦将扫灭东方各国,可见其兵制乃至政制倶有可取之处;秦若一统天下,则重建王道有望,故“见几而作”,不计个人毁誉,毅然入秦,说秦王、秦相以仁义礼乐之道。
本文解读《荀子》所记荀子与秦王、应侯之对话,以探究荀子驯化秦制之思考,可见荀子对秦制之基本态度是,认可秦扫灭群雄、一统天下之功,而呼吁其引入儒学,以自我更化。
荀子第一个完整地表达了秦汉之际儒家重建良好秩序之中道方案,有别于有些儒者之僵化或曰激进方案,得以参与郡县一统之制的设计构建,故确曾推动秦制之儒化,并为汉代之全面复古更化示范先行。
荀子之入秦说秦君相即效法孔子之道,可见其殷殷救世之仁心,更可见《中庸》所谓“君子而时中”之大智。
关键词:荀子;秦制;儒家化;法家;时中;
一、引 言
荀子生当战国末期,在其壮年时,秦已呈吞并东方之势;当其去世时,秦王政已即位九年;[1]又七年后,秦灭韩,随后扫灭东方各国。面对强秦,东方各国官民莫不忧惧;荀子以行道天下为己任,其对秦态度异于常人,于秦昭襄王晚年、应侯范睢执政时入秦,[2]游说秦国更化改制,其对话记录于《荀子》书中。
本文解读《荀子》所记荀子与秦王、应侯之对话,以探究荀子驯化秦制之思考,可见荀子对秦制之基本态度是,认可秦扫灭群雄、一统天下之功,而呼吁其引入儒学,以自我更化。
荀子第一个完整地表达了秦汉之际儒家重建良好秩序之中道方案,有别于有些儒者之僵化或曰激进方案,故确曾推动秦制之儒化,并为汉代之全面复古更化示范先行。
二
、秦人对儒家之传统态度
荀子入秦,得见秦昭襄王,《荀子·儒效篇》记录两人对话,自秦昭王之语开始。秦昭王问孙卿子曰:“儒无益于人之国。”[3]荀子名满天下,秦昭王当然知道荀子是儒者;荀子入秦,他当然也知道其来意。
(秦 昭 襄 王)
但秦昭襄王毫不客气,对荀子劈头断喝,谓儒家无益于秦国。可见秦人之质朴,亦透露出荀子即将面对的秦国精英群体之共同观念,此观念完全不同于东方各国,而形成则可溯源于两组人物:秦穆公与由余,秦孝公与商君。
西周初中期,秦僻居西陲,与戎狄杂居。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秦人保王室有功,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故《诗经》之《秦风》始于《车辚》,这是秦人历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秦人得礼乐而逐渐华夏化。
西周末年,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于郦山下,秦襄公将兵救周,作战甚力。平王东迁前,乃封襄公为伯,“襄公于是始国,襄公始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4]秦更进一步华夏化。
此后,秦人一直向东方发展,秦文公且“收周余民有之”,[5]则不能不浸染于周人之礼乐。
然而,秦穆公东进,遇强晋而受阻失败,乃对礼乐化、华夏化之国家发展道路产生怀疑,故请教于由余,《史记·秦本纪》记“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由余是中国裔而戎狄化者,对华夏、戎狄文明均有较深了解。
穆公问: “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 由余乃曰: “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
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 [6]
基于其戎狄立场,由余以为礼华夏乐无用,不能致治,乃建议秦用戎狄治理之道,去诗书礼乐法度,唤起淳朴的情感,使君臣民团结如一人。
秦穆公完全接受由余之论,于是退而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7]穆公竟称由余为“圣人”,看见其价值观已严重扭曲,转向之意身为决绝。
穆公乃设计迫使由余降秦而重用之,当时也取得了“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8]的效果。如此,其政治、文化不能不戎狄化,并立刻表现在丧礼中。[9]
(秦 穆 公)
以生人陪葬,早为周之礼法所禁止,穆公大用人殉,可见其戎狄化转向是相当彻底的。后来事实证明,这一转向是短视的:周室虽已衰微,东方各国仍行华夏礼乐;穆公用戎狄之法,等于自去正统,丧失了与东方各国交往之文化正当性,更不要说统治东方各国。
这一转向对秦本身也是双刃剑:一方面,引入戎狄的组织方式和制度,秦之军力似乎确有增强,故穆公得以称霸西戎,此后秦在与晋的争夺中也颇能取胜。另一方面,秦内部则频繁发生政治动荡。
荀子对此有深入讨论,比如“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10]
礼乐可以定分止争,一旦去礼乐,则人心不定,故在孝公之前几代公侯之权力转移均不能正常进行,严重削弱秦之国力。
由此有秦孝公初即位时的沉痛检讨,在赞美了穆公之功业后,即指出此后“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11]
秦孝公决心改变秦在政治上的混乱局面,原本在魏国之卫鞅乃入秦。魏是战国初年最早展开制度变革的国家,年轻的卫鞅是有心的观察者,决意将这些新制度用于治秦。
他获得秦孝公的信任,展开变法。关于卫鞅变法之主要内容,在驱民于农战;而归于万民之“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12]此处“作壹”,即由余所谓“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
唯由余只有戎狄部落政治的经验,对秦这样的大国未必有效,卫鞅则借助最早出现于魏国之新制度,以强化王权为中心,更好地实现了这一目标。其所谓“作壹”者,谓国人绝对服从王者,效力于国,则以王为中心,千万国人如同一人矣,可谓国王任意驱使。
为做到这一点,卫鞅主张,当驱全民于农、战,建立军国主义体制,由此可使君国“富强”。商业、学术有悖于此,自应予以取消:“《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
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13]商君生活之战国中期,社会形态已大不同于由余生活之春秋中期,其时自由商业已较为繁荣,私学亦颇为发达,商君本人即私学受益人。
而他以集中王权、构造强国家为宗旨,认定商业和学术有害于驱民农战,有碍于王权集中,故主张禁止学术,废弃礼乐,这是在由余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故秦人本身就与戎狄杂居,其观念习俗颇有戎狄之风,经穆公、由余之逆转华夏化过工程,到秦孝公、商君全面走上军国主义之路,秦终于形成其独特的观念、制度传统:驱民农战,追求富强,拒绝文治,不容学术。[14]
(卫 鞅 论 战)
宜乎秦昭王见荀子而径谓儒无益于国也,这其实还是比较客气的,依商君之见,也即依秦国精英之普遍观念,以儒为代表的学术活动是有害于君、国之富强的。
此即荀子入秦所面对者,荀子说秦之难度是在东方各国所不能想象的。然而,荀子竟然入秦,并且成功地说服了秦王,此何以故?
三、荀子入秦之时机
对于秦之戎狄化及其精英厌恶学术之态度和禁止私学之法度,东方精英当然十分清楚,荀子周游各国,见多识广,自然了解,然则荀子何以冒险入秦?何以于此时入秦?
由余、卫鞅明确反对华夏之诗书礼乐,秦穆公、秦孝公接纳两者,都在国家发展遭遇严重挫折之后,故秦穆公-由余、秦孝公-商君都清楚此系非常态下的选择,偏离华夏之常道,意在剑走偏锋,以求国家“富强”。
凭借驱民农战的国家精神,秦之国力确实逐渐增强,最终在残酷的国家间竞争中渐占优势。当荀子入秦时,秦一统天下之大势已然明朗,则天下之学界和政界都不能不认真思考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新时代。
首先是秦国君相,在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之余,不能不认真思考未来如何有效地治理东方。他们清楚,秦与东方各国大不相同,首先在精神上,进而在制度上。具体而言,他们清楚,东方尽管在战场上接连失败,但在文化上是鄙视秦人的。
(荀 子)
在秦与东方分隔、对立之时,秦人可以对这种态度蛮不在乎,重要的是打败他们;一旦统治权扩展及于东方,甚至一统天下,则这将成大问题。
东方的面积和人口远远大于秦,若不能令东方人心悦诚服,则无以树立统治天下之政治权威。故在接近胜利之时,秦不能不寻思重构其统治之正当性。
秦秦孝公、商君以来,秦人以富强为最高价值,迷信武力,这渗透在秦人心灵中,让秦拥有强大的武力。东方人在这方面不及秦,作为军事上的失败者,当然不可能接受秦人以暴力证成之正当性。
东方的长处在道统,在历史的连续性,在传承有序的六经,在围绕六经而衍生之学术体系,在其学术所传承、且仍残留于日常之礼乐法度。
东方以此自豪,而这恰恰是秦人所一度偏离、抛弃的。现在,面临统治东方之前景,秦国君相不能不再度转向,方向正好跟秦穆公、秦孝公相反。
其次,从儒家角度看,秦即将一统天下,打开了重建王道之可能。王道之基础在于王一统天下,此为判断天下有道、无道之根本标准,孔子曰: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15]
列国争战,生灵涂炭,此最为无道,必须予以结束,孟子亦主张天下“定于一”,尽管其界定一之之道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16],但首先肯定了“定于一”这个政治大原则。
而看起来,秦即将结束这种无道局面,只是,秦是以无道而残酷的方式做到的。儒者当然对此方式根本不能认可,但至少其结果将是结束屠杀。孟子生活的时代,各国混战,局势混沌;若孟子生在荀子之时,讲如何看待秦?
将如何看待秦一统天下之大势?实际上,大约自荀子以来,儒者对于秦之一统天下是予以肯定的,贾谊曾道出秦汉之际儒者之普遍心声:“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四海养,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何也?
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
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17]
对儒者来说,在秦即将一统天下之时,其任务无非有二:第一,协助秦尽快扫灭东方各国,终结战争,一统天下,尽最大努力将此过程对生民之伤害控制在最低限度;
第二,在秦一统天下之后的创制立法过程中发挥作用,尽最大努力使其礼乐法度合乎先王之道,以行仁义之政于天下。而这就要求儒者介入秦的统一过程和立宪过程。
身在其外,或可间接影响现实政治,但在历史转折之关键时刻,儒者自不能不介入其中。否则,错失时机,道不能行于天下,生民持续遭受伤害,儒者之过也。荀子之入秦说秦君相,盖以此乎?
综上,在秦即将一统天下之际,秦国君相与儒者荀子相向而行,从而有了一番历史性对话。
《儒效篇》在记秦昭王、荀子对话前,也即本篇之开头,有一段议论,可见荀子之心曲: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
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而能揜迹于文武。
周公归周,反籍于成王,而天下不辍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当也,不可以假摄为也。能则天下归之,不能则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离周也。
成王冠,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明不灭主之义也。周公无天下矣,乡有天下,今无天下,非擅也;成王乡无天下,今有天下,非夺也;变执次序节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
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主枝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18]这段话毋宁是荀子之夫子自道:周公是大儒,君臣易位乃非常之事,然由此“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
荀子隐然自比于周公,其入秦说秦君相同样是非常之事,然如此方可以辅导秦王,教诲开导秦王使谕于道。
值得注意的是,《荀子》一书中“大儒”一词仅见于记载其见秦王事之《儒效篇》。
荀子首先区分出俗人、俗儒、雅儒,由此往上则为大儒。
荀子如此形容大儒: “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疑㤰;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 [19]
荀子入秦,儒林恐难以理解。[20]强调大儒能在鸟兽之中辨别仁义之行,这是不是暗示秦之扫灭各国,其残暴虽为人所深恶,但其一统天下制功亦可予以肯定?
大儒又能应当猝然出现之前所未有、前所未闻的事态,这是不是暗示秦人一统天下之大势突然明朗,常人不知所措,而大儒则无所犹疑、迟滞,迅速行动,尤其是“㤰”也即怍,在此甚有深意:荀子说秦王,乃非常之举,然无所愧怍,盖其中有大仁大义在。
其行为看似出奇,实则合乎大道。荀子以为,大儒乃立一代之大法者,必定身处所未尝闻见之情势中,不能不见几微之时,乾纲独断,大胆作为,执经而行权,然后可以创制立法。
荀子以大儒自任,荀子又谓:“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无百里之地,则无所见其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调一天下,制强暴,则非大儒也。”[21]
荀子入秦说秦王正是为了“见其功”,参与到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参与到治天下之礼乐法度的创制过程中,以“制强暴”。
荀子知道秦之“强暴”,凭此强暴,秦将一统天下;若不“制强暴”,则天下虽一统而不宁;儒者此时不出,其乃天下苍生何?此盖荀子之心曲也。
四、荀子说秦王之义理
秦昭王首先表达秦之传统观念,断定“儒无益于人之国”。秦昭王之用词值得注意:对东方学者而言,儒或其所传之六经是自身文明传统,自然而然地传承,且有深厚情感;
秦僻处西陲,对其并无情感,虽曾接受之,终究视如身外,故对其采取功利态度,秦穆公、秦孝公以其“无益”而去之,秦昭王之问同样展示了明显的功利态度。
荀子乃起而力辩之: “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执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贪。
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呜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执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
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必蚤正以待之也。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罔不分,有亲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 [22]
秦昭王之问是功利的,荀子也从功利角度予以回应,故本篇题名《儒效》,论述国家儒化或儒者治国之效用。不过,荀子相当谨慎,在这一段仅说明“儒之为人下”也即儒者为臣之效用。荀子特别强调,儒者即便不获任用,也“必为顺下”。
可见荀子心思甚为缜密:商君当初之所以禁止学术,主要就是担心学者法先王,而不顺君王,甚或以先王之法扰乱人心,妨碍国家之“作壹”——后来李斯、秦始皇焚书,同样基于这一理由。
当然,荀子最终还是全面地论述了儒者之效用:在朝为官,则可以秉公为政,在野为民,则可以敦美风俗。后世的士大夫也确乎如此。
然秦昭王毕竟是一国之王,更为关心儒学对君王治国平天下之大用,乃发问如下: “王曰:然则其为人上何如?
孙卿曰: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君子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欢。是何也?
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夫其为人下也如彼,其为人上也如此,何谓其无益于人之国也!
昭王曰:善!”[23]荀子所言乃儒者之正论,其所谓“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与孟子之谓“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如出一辙。而对秦昭王而言,最有吸引力之处在于能使四海之内若一家,天下之人莫不顺服。
秦已有吞并天下之势,秦昭王当然希望在武力夺取天下之后,天下顺服。两人初衷或有不同,但确有交叠处。故由荀子之论说,秦昭王看到了归儒之功效:秦王归于儒,有助于其在一统天下后获得天下人的顺服;以儒者为臣,也可以更有效地治理天下。 故秦昭王对荀子之说颇为满意,曰“善”。
荀子未记秦王此后有何作为,然而,鉴于秦自穆公晚年以来形成的排斥礼乐文治之深厚传统,秦昭王愿见儒者荀子,且肯定荀子曰“善”,已属秦人思想观念之一大历史性突破。
此事此言表明,秦昭王已不再简单地排斥东方学术、尤其是儒学,而很有可能在认真思考如何吸纳儒学,以使其日益增长的统治权获得东方之认可。
在这段对话之后,《儒效篇》记荀子大段论述,首先论儒家士君子之独特能力;其次抨击当时各家游士;其次论为学则可以由贱而贵,由愚而智,由贫而富;其次论君子不争而能让;
其次区分民德、劲士、笃厚君子与圣人,儿童叹美圣人为“道之管”;最后论诗、书、礼、乐、《春秋》之功用。
推测起来,这些议论很有可能是荀子在秦对其官员所发。接下来,《儒效篇》又记荀子与一位客人的对话,推测起来,此客人或为荀子在秦所遇之客: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
应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负扆而立,诸侯趋走堂下。
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孰谓周公俭哉!
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氾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
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声乐,于是《武》、《象》起而《韶》、《护》废矣。
四海之内,莫不变心易虑以化顺之。故外阖不闭,跨天下而无蕲。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戒矣哉!” [24]
这段对话与《儒效篇》开篇之论周公遥相呼应,其下则申论上文所引“大儒”之义。客人所论周公之德当属“雅儒”之德,荀子则谓周公乃大儒,于非常时刻行非常之事,超乎普通道德,故其救周时不恭,定天下时不俭,灭纣时不戒,唯如此,终得安定天下。
《儒效篇》以“大儒”二字开篇,最后收结于畅论大儒之所能,荀子之心曲袒露无疑矣。荀子以为,秦完全可以扫灭各国,代周而起,兼制天下。这看起来超越常态下的道德观,但不如此,则王道无望。
同样,荀子之说秦王也是大儒之举,唯有如此,方能致王于道,以秦所获得之权威重建王道,行仁义之政于天下。以常态社会中一般道德观念衡量此举,甚无谓也。依荀子,当乱世,惟大儒可行道于天下。
[1] 参见孔繁:《荀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2] 钱穆考订曰:“荀卿在齐襄王十八年后曾赴秦也。至昭王五十二年应侯罢相,荀卿赴秦当在此十二年间。”又谓:“荀卿大抵荀卿留秦决不久,其去秦东归,当在长平一役之前”。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529、532页;
[3] 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7页。
[4] 司马迁:《史记》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9页。
[5] 穆公十二年,晋饥荒求援,大臣有反对者有支持者,穆公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于是输粟于晋(《左传·僖公十三年》),可见深明大义。
[6] 司马迁:《史记》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2-193页。
[7] 司马迁:《史记》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3页。
[8] 司马迁:《史记》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4页。
[9] 司马迁:《史记》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4页。
[10] 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4-165页。
[11] 司马迁:《史记》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2页。
[12]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页。
[13]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页。
[14] 太史公于《六国年表》序曰:“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 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及文公逾陇,攘夷狄,尊陈宝,营岐雍之间,而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是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见司马迁:《史记》第2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5页。太史公盖以秦之兴起为礼崩乐坏之主要驱动力量,终代周而兴;而其最后一句话颇与荀子谓秦之获胜“非幸也,数也”相近。
[1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1页。
[16]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6页。
[17] 《四库全书》本《新书》卷一《过秦下》。
[18] 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4-117页。
[19] 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0-141页。
[20] 叔孙通之遭遇或可参照:刘邦命叔孙通作礼仪,“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司马迁:《史记》第8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22-2723页)叔孙通所说“鄙儒”就是荀子所说“俗儒”。
[21] 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7页。
[22] 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7-120页
[23] 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0-121页。
[24] 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4-137页。